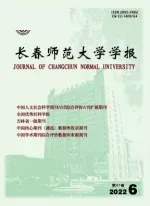朱得之《列子通义》的心学思想
2012-08-15刘佩德
刘佩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朱得之《列子通义》的心学思想
刘佩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朱得之继承王阳明心学的观点,认为心是一切造作的根源,只有控制住自我的心,才能得道。儒家、道家、佛家,三者名异而实同,因为无论哪一家都是来阐明“道”的,而“道”是没有差别的。这也是朱得之所秉承于王阳明心学的最大特点。
朱得之;《列子通义》;心学
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自号参元子,直隶靖江人,为王阳明晚年客居靖江时的入室弟子。关于朱得之的生平,主要见于他所修的《靖江县志》中。书中记录了朱氏家族的兴衰,并保存了许多正史中所不见的珍贵资料。根据《靖江县志》中的记载,朱得之也算是仕宦之家,因祖父遭陷害而家道衰落,父亲也因为此事而死,并客葬他乡。后,朱得之凭借王阳明的声望,将其父亲的尸骨迁葬回乡。这段坎坷的经历使他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因此,在被王阳明收为弟子之后,甚是好学。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载:“南中之名王氏学者,阳明在时,王心齐、黄五岳、朱得之、戚南玄、周道通、冯江南,其著也。”[2]由此看来,朱得之也算是王阳明的得意弟子之一。
心学是儒家思想到宋代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学术体系,虽然仍然标榜儒学、尊崇儒家,但其已经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混合体。儒家重实用之学,很少谈及关于宇宙人生的问题。随着释道思想的不断发展,崇奉儒家的先驱们开始思索如何才能使儒家思想更加完善。而释道思想中关于宇宙人生的探讨,恰恰可以弥补其本身的不足。因此,在宋代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融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体的理学便悄然而生了。周敦颐开理学之先河,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得周真传,朱熹在这三位圣哲的基础上,对理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宋代是理学发展的高峰期,朱熹与陆九渊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两座高峰,尤其是经过朱陆辩论之后,理学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元代是理学的整合期,宋末元初的一段时期,朱陆两家的思想开始慢慢合流。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阳明心学即是这种思想合流的产物。
王阳明是明代理学家,他的思想历来被认为是远绍陆九渊,由此确定了其学说以“心”为主的思想特征。具体来讲,他吸收思孟学派的“心性天命学说”,以及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学说,同时也吸收朱熹思想的可取之处而创立了心学。陆九渊,字子美,抚州金溪人,因讲学于贵溪象山,人称象山先生。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观点,他说:
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俱是理,心即理也[4]。
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4]。
陆九渊认为,人都有心,而人心生来都是善的,世间的一切道理都存于这颗心当中。所以,心即是理。后世学者重学习,无外乎穷理,既然心中包含了所要学的理,那么只要尽心就可以了。现在的人正是因为不注重“存心、养心、求放心”的功夫,刻意约束心,所以使得心有所蒙蔽,不能达到明理的境界。如果人人都能够时刻警惕自我,时时反省自我,明白心的重要性,那么理也就不讲自明了。不难看出,这种思想带有非常浓重的禅宗色彩。王阳明在这种心学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心的重要:“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5]“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5]在王阳明看来,人心是根本,只要能够降伏人心,就能与天理即道相应。这一点是直承于陆九渊的。
朱熹与陆九渊的根本分歧在于怎样入手达到心的解脱。朱熹主张由外而内,通过外在的学习,亦即阅读大量古人的著述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以期达到净化心灵、提升自我的目的。而陆九渊则认为若要明理,首先要使心达到解脱,只有根本问题解决了,才能明了圣贤著述的内在含义。否则便是舍本求末,永远也不能达到解脱。王阳明虽然承袭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但他也吸收朱熹“格物致知”的观点,也承认外在学习对于心性修养的重要性。他在《答吕子约》中说:“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源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5]在强调体悟本心的同时,王阳明也承认文字的作用。这种思想倾向是经元代朱陆合流之后,朱陆思想在明代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朱陆二人的观点虽然有分歧,但同属于理学的唯心范畴,只是对于如何达到心的解脱的着眼点不同而已[3]。客观来讲,他们二者有走向两端的嫌疑。王阳明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吸收二者的长处,融合发挥,成为明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得之即是王阳明这种思想的忠实追随者。据《明儒学案》载:
朱得之……从学于王阳明,所著有《参玄三语》。其学颇近于老氏。盖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者也。其语尤西川云:“格物之见,虽多自得,未免尚未见闻所梏。虽说闻见于童习,尚滞闻见于闻学之后,此笃信先师之故也。不若尽涤旧闻,空洞其中,听其有触而觉,如此得者尤为真实。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途径堂堂,万世昭然。”即此可以观其自得矣[2]。
朱得之也认为朱熹的格物之说未能达到体悟的境界。学者虽然承袭着先师的学问,但却不能从先师的讲学中走出来,也即是说不能使自我达到真正解脱,所持有的学问仍然是先师所讲的。虽然师传很重要,但为学是为了能够开悟自我的心胸,若不能有自我的创见,那这种学问也是空有其表。因此他举子夏与曾子为例,子夏笃信圣人之言而无创见,而曾子则在学圣人言之余反求己身,从而成为亚圣,为后世所尊仰。由此可知,朱得之对于王阳明心说是深信不疑的。他在《列子通义自序》中说:
其立言初意,然不然,不论也。学者诚有得于言意之表而法其为己知几之功,则世之先后,与其言之所泛出,自不屑多辩。而逐块之技,庶几其脱然也。虽然,得于辞而后可以通其意。斯籍也,其文则纪事者也,而因事以明道也。道不容言也,惟解缚而道自存……故凡起心、起意、起知者,皆人也,非天也。学也者,学于无朕无言之地,而有名有形者皆缚也。
读书人最初思想正确与否且不论,重要的是通过言辞来体会内在的含义。文字是用来纪事的,学者求明道,则需从这些文字当中来求得。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为这些文字所束缚。在朱得之看来,所有有形体的东西,都是一种束缚。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得于辞而后可以通其意”这一人间通理,大有庄子言意之辨、孟子不得不言的意味在内。在他看来,一切的文学言辞,都是为了明道而服务的。而道是不能言说的,只能在解脱束缚之后才能见到道。而一切的知识言辞,都是承载道的工具,得道之后,这些人间的智巧就可以抛弃了,因为人已经达到了解脱,超出了世间的束缚。虽然他极力申明不要为有形的文字所束缚,但行文之中还是透露出肯定文字作用的意思。从这里也可看出,虽然王阳明在阐述其心学思想的时候极力掩饰其对朱熹思想的借鉴,但到朱得之这里,这种倾向反而表现得更加明显。为了表明人心本来就是善的,朱得之在《说符》篇中说:
善者,吾性之本体。惟知识起而功利迷,假善以眩人,便利归诸己,此虽善而不善矣。子居曰:必慎为善。率其性无所为而为,一毫便利之私不萌焉。斯则慎为善之旨也。
人心本来的善由于后天的习染,而导致了迷于世情的后果,本性中善的因子被世俗的人欲所迷惑。由于有了人欲,虽然是行善,但也不能称为善了,因为起心动念之处已经不纯粹了。因此,他又借用道家的观点,认为只有达到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那种境界,完全率性而为,心中不存一点私欲,才是真正的善,也才能与天理即道相契合。他在《刻列子后序》中说:“余原此书之著,必在梦奠两楹之后,删书之泽渐湮,天德王道不明于天下也。故寄情游戏,以发五经之微意。”朱得之认为《列子》一书是由于孔子没后,诗书教化的功用渐渐堙没,作者有感于天德王道不明于天下,遂著书立说,以启发后人。因此,《列子》的本义也是发明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虽然作者是在孔子的外衣下来探讨《列子》,但由此透露出儒道合流的倾向。但对于儒家的理论,他也不是一味遵从,注重有益于人心教化的方面,也即是有益于心性的修养方面。在“列子适卫食于道”章解释后稷诞生传说时,他说:
姜嫄从高辛之后郊媒以求子。……及以初生不难,疑而弃之,上帝益显灵异,岂谓履巨迹、无人道而生子乎?且周公尊祖配天,但当颂其德之格天,岂应以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为言、自坐淫慝无忌惮者乎?……此书信传言而不考,史迁信此说而不疑,遂致后学因仍舛谬,陷圣母圣子于怪异,深可惜哉!
后稷之事见于《诗经》,后人因其为孔子所删定而深信不疑,奉为经典。朱得之则大胆否定,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怎么可能“无人道而生子”呢?后世应当颂扬后稷的德行,不应当出此不羁之语。在朱得之看来,圣人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们有超乎常人的神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德行高尚,遵从了天道,亦即万物变化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朱得之是把儒道纳入一个统一的概念即“天道”之下的。而天道又是为人服务的,正因为有了人的存在,天道才显现出它的作用。天与人是互为作用的:
公私也,心一而境殊。天,人也。知天者,人亦天,天亦人也。……盖天地者,万物之总称。万物者,天地之别名。虽各私其身,其本根原不相离。物物皆出于天地,天地不离乎万物。苟各認之,以为自有,非惑而何?此所谓天地委形,非我有也。……生即天地之一气,身即天地之一物。事无公私,情无爱吝,自然而已。
儒家的本旨是经世致用,孔子从来没有专门探讨过关于宇宙天理的问题。理学思想则专取释道关于宇宙天理的观点。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心即理”的前提下,把人与天相沟通。他在《谨斋说》中论述到:“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事于学。”[5]把心与天联系起来,认为人性即是天理,明了了人性也就明了了天理,也即是明了了道。朱得之在这里进一步阐发了这种观点。公私是人心的差别,天是人,人也是天,天地是万物的总称,万物是天地的别名,二者之间名虽不同,而质实一。万物与天地是互相为用的,天地间的事物,没有公私的分别,只要遵从自然就可以了。老子主张自然无为,庄子进一步主张天地无差的齐物观点。朱得之将这些观点糅合到儒家的理论中,从而补充了儒家思想在宇宙天理方面的不足。在《周穆王》篇“老成子学幻”章注释中,他说:
生死幻化,一而非二。神化之机,非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穆王之遇化人,老成子之学幻,殆中庸君子所不语者与?
生死与幻化是一而非二的。无论周穆王所遇的化人,还是老成子所学的幻术,都是与生死一样的东西。只有“达天德”之人才能明了其中的至理。现在恪守儒家中庸理论的所谓君子,只知道在这些文字中转圈,而不努力使自我的心达到解脱,殊不知天理就在本心当中,心得解脱,天理自然显现。而心的解脱除了借文字知识的启发,还有就是自我的心性修养,也即是通过自身意志的磨练而产生定力,以期获得一时的顿悟而豁然开朗。王阳明曾专门提到修定的功夫,他说:“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固且教之静坐、息思虑。”“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5]修定本来是佛家的理念。佛家认为,人的智慧是由定而生发的,定修习到一定的程度,智慧便由心而生起。也即是说,心是一切造作的根本,人心被世间的欲望所束缚而不能反观本心。修习禅定,能够使人的身心达到统一,从而激发心中的智慧,明了大道的根本,最终成佛。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定,即是由此而借鉴。这样,两者在心的修习上便有了共同之处。
修定,其实就是怎样束缚自我的身心,也即是修心的问题。佛教认为,人间一切的造作都是由心而起,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坛经》说:“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金刚经》也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当作如是观。”朱得之也赞同这种观点,在《周穆王》篇“梦有徵”章注释中,他引大慧宗杲禅师写给向伯恭一封论述梦与非梦的书信来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至人无梦,非有无之无,谓梦与非梦,一而已。佛梦金鼓,高宗梦得说,孔子梦奠两楹,不可作梦与非梦解。四关时间,犹如梦中事,惟梦乃全妄想也。而众生颠倒,以日用目前境界为实,殊不知全体是梦,而于其中复生虚妄分别,以想心系念,神识纷飞为实。殊不知正是梦中说梦,颠倒中又颠倒[6]。
大慧杲是南宋禅师,其所弘扬的是自达摩以来所传的禅宗法门。以修心为主,以十六个字为其宗旨:“教外别传,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种独特的方式,适合中国文人的独特心理。因此,禅宗在宋代大盛,并逐渐融入到中国古代的文化血液之中。当时的多数文人都与禅师有交往,并亲身体验坐禅与参禅的快乐。在佛家看来,所谓的梦与无梦,其实是一回事情。只是因为众生没有能够冲破妄想牢笼的束缚,起心动念之处都是在围绕着现实当中虚幻的东西,而且深陷其中,反而将真正的大道认为是虚幻不实的、无用的东西。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人心没有达到开悟。这正与朱得之对心的重视相符。
朱得之的心学观念是直承于王阳明的,而王阳明的心学理念是在前代理学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宋代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儒、释、道三教思想逐渐融合,体现在学术上就是理学的产生。理学思想的产生,起初就借鉴了佛教关于心性方面的观点,尤其是宋代大兴的禅宗;道家思想作为本土的一种学说,自古就是以后各家学说的思想基础;而儒家的理论,也充分强调了人在修为方面的重要性,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因此,朱陆去世之后,经过元代合流,到王阳明时所产生的心学思想,实际上是综合吸收了各家思想的一种混合体。因此,从本质上讲,朱得之所遵循的心学观念,可以说是三教融合的历史产物。而这种混杂的思想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讲似乎更符合《列子》书的思想特征。
[1]朱得之撰.列子通义[M].刻本.靖江:朱氏浩然斋,1565(明嘉靖四十四年).
[2]黄宗羲.明儒学案[M].沈芝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578,585.
[3]侯外庐.宋明理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749-767.
[4]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9,64.
[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5,2,129,263,16.
[6]宗杲.大慧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120-121.
The Thought of Study of Heart inLieh Tzu Tong-Yiby Zhu Dezhi
LIUPei-de
(Department of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Zhu Dezhi accepted the viewof Study of Heart by Wang Yangming.He thinks the heart is the source of all the things.If you want to attain the Tao which contain all things,you must control your heart.Although Confucianism,Taoism,and Buddhism have different names,they have the same substance,because they all illustrate the Tao,which has nodifference.This is the important feature ofStudyofHeart byZhu Dezhi.
Zhu Dezhi;Lieh Tzu Tong-Yi;StudyofHeart
B248.99
A
1008-178X(2012) 02-0018-04
2011-10-03
刘佩德(1980-),男,河北邢台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从事先秦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