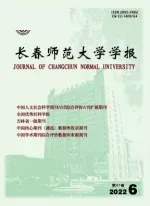被困的灵魂
——《八月之光》中乔安娜·伯顿的双重性分析
2012-08-15左贵凤
左贵凤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被困的灵魂
——《八月之光》中乔安娜·伯顿的双重性分析
左贵凤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411201)
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和家庭使命的重负,使乔安娜的本能欲望遭受严重的压抑。在欲望决堤后,她虽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却无时无刻不在精神上忍受着煎熬。正是种族优越性和家庭使命造成的精神上的禁锢,使乔安娜的举止具有双重性并酿成了她的最后悲剧。
压抑;沉沦;禁锢;双重性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和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他一生创作颇丰,作品广受读者的关注,影响十分深远,尤其是约克纳帕塔法系列,被认为跻身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列。
《八月之光》是福克纳的代表作之一,也是10部最受欢迎的南方文学作品之一。乔安娜·伯顿并非作品的女主人公,而仅仅是男主人公克里斯莫斯的白种情人。她虽然一生都致力于帮助提升黑人,骨子里却充满了对黑人的歧视和偏见。种族优越感和父辈的废奴主张使得她苦行僧般地坚守着家族的使命,忘记了年龄,忘却了性别。因为克里斯莫斯被怀疑具有黑人血统,在与其交往的过程当中,她反复无常,飘忽不定,几次三番试图压抑自己的本能欲望。然而生命的本能与生俱来,不容压抑[1],因而她备受折磨,饱尝炼狱般的痛苦。她从欲的压抑走向性的沉沦,却始终无法摆脱长久以来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所受的禁锢,这种禁锢不仅是她悲剧的起因,也注定了她悲剧的结局。
一、自我:欲的压抑
乔安娜·伯顿是一个中年白种女人,在黑人聚居的区域,在那所孤零零的白色大房子里,她孤独地生活了近20年,毫无正常女人所具有的恐惧和需求。她的穿着打扮十分中性化,面容沉着严峻,几乎就像个男人一般,并从遗传和环境中形成了男性思索的习惯,拥有着男人果敢、坚决、理智的处事风格。多年的独居生活使她忘记了自己的性别,她也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女人。即使是在克里斯莫斯成为她的情人之后,面对他时“她既没有女性的犹豫徘徊,也没有女性终于委身于人的扭捏羞态”[2]210。甚至在他们成为床头伴侣长达一年之后,克里斯莫斯也几乎对她毫无所知,因为他们几乎从不交谈,有时候在游廊里碰见,也只是几乎像陌生人那样简短地说上两句,要么言不由衷,要么不知所云。最终,她虽然向克里斯莫斯敞开了自己的心门,叙述了自己的家族历史,但是她的声音里既没有女性特有的温柔气质,也没有悲伤和追思回想的意味。
乔安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极端的废奴主义者,并将废奴作为家庭使命传承给了乔安娜,这使得她虽身为女儿,却不得不像一个男人般,一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与使命。在长达40年的日子里,她从事着帮助黑人的神圣任务。每天,她会花一段时间安详地坐在桌边,静静地为年轻人和老年人写信,同黑人妇女谈话或听她们讲述,写信给南方10多所黑人大、中学校的年轻女学生,甚至这些学校的校友,奉献出她个人的切实可行的劝诫;隔一些时候她会每次离开家三四天,亲自去访问那些学校,同师生们谈话。
几十年如一日,乔安娜就这样生活和工作着,独自生活在那所孤零零的大房子里,没有朋友,甚至没有邻居,而她似乎既不需要男人陪伴,也不需要在困难的时候有个坚强的臂弯可以依靠,她仿佛成了一个有着男人体肤的女人。然而,“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结构部分,主要是由性的冲动构成,只受自然规律即生理规律的支配,遵循‘快乐原则’行事”[3]77。因此作为一个生物体,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中年女人,她跟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一样具有生命的本能,渴望爱也需要性,唯一的区别是她的本能被牢牢地压抑了。
这种压抑,不仅出现在她40多年的单身生涯中,甚至在她跟克里斯莫斯关系的第一阶段,也是如此。因此,当克里斯莫斯进入她的房间,试图通过蛮力拥有她的时候,要么“她一直抵抗到最后”[2]210,要么“他手下的身子却仿佛是一个死去的女人,只是还未僵硬而已”[2]212。如果克里斯莫斯不去大房子里找她,她绝对不会主动去找克里斯莫斯,哪怕她找不到任何别的男伴。
显然,多年的独居和性压抑,使乔安娜遗失了做女人的某种特质。甚至当她跟克里斯莫斯的关系进入到第二阶段时,尽管她的身体在黑夜之中完全让位于性欲,但是在白天,她依然是那个“孤独地生活了二十年的中年女人,面容沉静冷峻,差不多像个男人,毫无女性所具有的恐惧”[2]232。整天,她或在做一些家务,或坐在一张破旧不堪、表面凹凸不平的桌边不停地书写,或同黑人妇女谈话,或静静地为年轻人和老年人写信……她的日子与往常没有任何区别,甚至也不会分神去想到克里斯莫斯。
如果说欲望是一匹野马,乔安娜无疑是一个出色的骑手[1],她压抑着它,抗拒着它,掌控着它。
二、本我:性的沉沦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本我是任性的、本能的、冲动的,只遵循快乐原则行事。因此,性欲的火焰一旦被点燃,便无法用理智去扑灭。在与克里斯莫斯关系的最开始,虽然乔安娜有所抵抗,“但那不是女人的抵抗,女人的抵抗要是真心实意,任何男人也无法攻克,因为女人在肉体搏斗时绝不遵守任何规则。可是她进行的是公平合理的抵抗,遵循了在某种紧要情况下缴获投降的惯例,无论抵抗是不是能够到头”[2]210。另一方面,虽然她对克里斯莫斯初期的入侵表现得漠然而冷淡,但当克里斯莫斯为她的冷漠和无所谓的态度所激怒,粗暴地脱去她的衣服,想让她明白自己仅仅是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毫不抵抗,甚至仿佛在帮他忙,到了最需要帮忙的时候,她的四肢稍稍地改变着姿势”[2]211-2。毫无疑问,在力比多的驱使下,尽管她的头脑是严峻的,似乎属于另一具躯体,她的身体却无法拒绝肉体的欢愉。
当她将家族的历史和使命向克里斯莫斯和盘托出之后,似乎那些长久以来压抑着她本能欲望的外在禁锢也暂时消失了,她完全变成了一个放荡的女人。在夜晚黑暗的掩护下,她尽情地展示着性渴望与性幻想。她喋喋不休地坚持要把白天发生的点点滴滴都告诉克里斯莫斯,并要求他也细述一天的情形,像一对情人通常做的那样;她会出乎意料地凭空臆造一些假想敌,然后大发醋意;她将一些书信和纸条隐藏起来,坚持要克里斯莫斯去寻找,否则就对他又哭又闹;她给克里斯莫斯递纸条让他去她房里找她,自己却躲进衣橱或空房,渴望地等待着他,两只眼睛像猫眼般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她还常常约克里斯莫斯在附近的某个灌木丛中幽会,赤身裸体或把身上的衣服撕成碎片,缓慢地扭动着身体,做出各种挑逗性的姿势和动作,完全沉浸在追求男性的狂热里[2]。所有的这些,都是她的性空虚和对爱的一种报复和弥补。她似乎想在此时抓住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去满足她狂乱的受阻的性欲,她“如饥似渴的迫切心情掩盖着备受折磨备受挫折的岁月无可挽回的真实绝望,她似乎想在每夜加以弥补,相信每个夜晚都是人世间最后的一夜,不惜使自己永远沉沦于祖先所在的地狱,不惜生活在罪恶之中甚至污秽之中”[2]231-2。她完全迷失在这种混乱里。在这种混乱里,她对性爱的歪曲反应,是“她长年被压抑的性欲的惊人爆发,也是她在深受家族使命困扰后的短暂释放”[4]59。
从第一阶段的冷若冰霜到第二阶段的疯狂放纵,从白天的严峻、理智到黑夜的放荡、纵欲,她的举止如此对立与矛盾,以至于在克里斯莫斯的眼里,她就像是一个身躯里的两个可怜人,像两个灰暗的影子挣扎在灰暗残月之下的黑水深潭的表面,陷入一种或另一种痛苦的深渊。对于她的二重性表现,Andre Bleikasten作出了十分生动的论述:“有两个乔安娜:一个是夜晚的、疯狂的黑暗之女,是狂乱的性欲驱使之下的牺牲品;另一个是白天的乔安娜,刻板、冷漠、克制,是精神错乱的‘夜晚姊妹’的幽灵般的衬托(拙译)”[5]288。
三、超我:灵的禁锢
从第一阶段的欲的压抑到第二阶段的性的沉沦,乔安娜的举止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当他们的关系进入到第三阶段后,乔安娜的态度又发生了一个极端的变化,她开始寻求原谅和进行自我救赎。她先是想跟克里斯莫斯生一个孩子来减轻自己的罪孽,但当她发现自己并非怀孕而只是绝经之后,她便开始强迫克里斯莫斯承认自己的黑人身份并加入她的帮助拯救黑人的家族事业。
乔安娜的举止是如此的反复无常和极端,但如果联系到根深蒂固的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和她自小便受到的严厉的家庭教育,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旧南方社会,信奉白人优越论以及贵族世家高人一等的思想,认为黑人低贱而肮脏,属于另一个次等种族。在种植园家庭里,等级森严,规矩极多,白人主人与黑奴之间界限分明。南北战争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废除,黑人虽然在政治上开始取得跟白人平等的地位,但白人依然在经济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白人至上的理念依然根深蒂固,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黑人不仅不能享受和白人一样的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还只能生活在隔离区,甚至在很多公共场所也是隔离而不平等。很多白人虽然支持废除奴隶制度,愿意去帮助黑人,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依然是建立在白人至上的理念之上的[6]。
乔安娜的祖父就是一个残暴的废奴主义者,在与人争辩蓄奴问题时,他打死了对方,为逃避追杀,举家迁往圣路易斯。在这里,伯顿花了很多时间谈论政治,时常能听到他“直起粗声粗气的嗓门大骂蓄奴制和奴隶主”[2]217。因为他随身携带手枪,他的意见大家至少是没有异议地接受,他的声誉也逐渐建立起来。此外,他还花了很多的力气去培养子女们对蓄奴制的态度,周六的晚上,他时常喝醉了威士忌回家,然后重手重脚地推醒孩子们,对他们说,“我要你学会憎恨两桩事,那就是地狱和奴隶主”[2]218;星期天的时候,他通常还强迫孩子们穿戴整齐,聆听他用谁也听不懂的西班牙语朗诵《圣经》。
毫无温情的家庭教育,使他的儿子纳撒尼尔不堪重负,在14岁时离家出走,16年后却又携带一个西班牙裔的妻子与一个肤色黝黑的儿子归来。面对这个黑皮肤的孙子,伯顿不停地诅咒:“伯顿家又出了一个黑杂种……那些低贱的黑鬼,他们之所以低贱是由于承受不了上帝愤怒的重量,他们浑身油黑因为人性固有的罪名沾染了他们的血和肉”[2]222。
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乔安娜的悲剧似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早在乔安娜出生之前,她的祖父和同父异母的兄长,就已经被顽固的前白人奴隶主所杀害,为避免他们的尸骨被挖出后遭到屠戮,她的父亲把这些坟墓都掩藏起来。当她还是一个不到4岁的孩子时,她被带到祖父和兄长的坟前,聆听父亲口里的“白人的诅咒”。在那个庄严的地方,父亲的话语让乔安娜天真的灵魂承担下家庭的责任:“你必须抗争,站起来,而要站起来,你必须把黑影一同支撑起来。可是你永远不可能把它撑到你自己的高度”[2]191。年幼的乔安娜当时并不能完全明了这些话的意思,却本能地感觉到“她的生命在那一天里获得重生,重生在罪恶里,重生在上帝加在种族头上的诅咒里,这个罪恶和诅咒将追随着她的一生”[4]56。
父亲在乔安娜的内心早早地种下了对种族制度的仇恨。因此,作为一个在严峻的宗教家庭里长大的白人,在乔安娜看来,黑人“他们不是人而是物”[2]227。虽然她的一生都在帮助黑人,但是她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却是深入骨髓的。因为她的家庭背景,她的反对隔离的主张并不能说明她相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平等。对她来说,黑人就是上帝给的一个诅咒,她认为她有责任去提高他们的层次,但是平等是永远不能达到的。因此,“在她眼里,克里斯莫斯永远只是个黑鬼”[7]46。甚至在那些灌木丛中,在她跟克里斯莫斯最放纵形骸的时候,她的嘴里还在嘘叫着“黑人!黑人!黑人!”
在与克里斯莫斯的交往过程之中,她屈服于放纵的性欲;与此同时,她又意识到这是违背了某一个社会规约的。因此,她陷入到一种情感的冲突之中。一方面,克里斯莫斯的身体满足了她对性欲的需求;另一方面,他的种族身份却成为了她不得不背负的压力。可以说,从始至终,她与克里斯莫斯的性爱经历就经受着一种精神上的两难抉择,一端是性爱欲望,另一端是种族优越感和家庭使命,她的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左冲右突,进退维谷。
最终,乔安娜所感受到的罪恶感使她选择拒绝这种性伙伴关系,并试图通过想方设法的弥补来重新皈依祖先的严厉教条。一开始,她想通过跟克里斯莫斯生一个孩子来避免她的赎罪,减轻她与一个黑鬼有性关系的罪孽,使她的激情能变得无罪。但当她发现自己并非怀孕而只是绝经的时候,这一结果加深了她对堕落的认识,也促使她进行刻不容缓的改变。因此,当克里斯莫斯伸出手去摸她的时候,“她以男人般的沉着坚定掀开他的手”[2]241。她要求克里斯莫斯去跟一位黑人律师学习打理她的家族事业——去为帮助提升黑人而工作,并强迫他进行祈祷。克里斯莫斯如果这样做了,就相当于确定自己的黑人身份,而她也获得了唯一能挽回她的放浪行为和获取她的内心慰藉的方式。当克里斯莫斯拒绝她的要求时,她准备用枪打死他,却不料被克里斯莫斯抢先一步用剃刀割断了她的脖子。
四、结语
乔安娜·伯顿是一个具有浓厚悲剧色彩的女人。她渴望做一个得到爱、享受爱的女人,但是她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种族观念使她的这一愿望成为泡影。她深受家族使命的困扰,在自我的性别身份中来回挣扎。她拼命地压抑着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却又在欲望决堤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然而,根深蒂固的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和自幼便沿袭的家庭使命又使她每时每刻都在精神上备受煎熬。绝望之余,她企图迫使克里斯莫斯承认自己的黑人身份从而减轻她的罪孽,而这一举动却给她招来杀身之祸。乔安娜的双重性是由家族使命的重负和性欲的压抑而造成的,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她真正的自我与她的身体相分离,她成了一个被困的灵魂。
[1]Freud,Sigmund.The Egoand the Id[M].NewYork:Norton,1962.
[2]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M].蓝仁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
[3]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4]袁莉.福克纳小说《八月之光》研究——从存在主义视角解读[D].东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07.
[5]Bleikasten,Andre.The Ink ofMelancholy[M].Bloomington and Indiannapolis:Indiana UP,1980.
[6]Howes,KellyKing.HarlemRenaissance[M].U·X·L,an imprint ofthe Gale Group,2001.
[7]吴永红.光明的使者与被困的灵魂——《八月之光》中莉娜·格罗夫和乔·克里斯默斯的对比分析[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07.
[8]张莹.黑暗中的光明[D].济南:山东大学,2007.
[9]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0]姜燕.威廉·福克纳小说中的女性与父权[D].济南:山东大学,2004.
[11]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An Imprisoned Soul—Analysis on the DualityofJoanna Burden inLight in August
ZUOGui-feng
(School ofForeign Studies,Hunan Universityof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White people’s racial superiority and Joanna’s family mission severely repress her instinctual desire.Although she loses herself once the instinctual desire has been aroused,she burdens herself with the spiritual torment.It is the spiritual imprisonment caused by racial superiority and her family mission that lead to her duality and the final tragedy.
repression;degradation;imprisonment;duality
I712.074
A
1008-178X(2012) 02-00105-04
2011-10-30
左贵凤(1980-),女,湖南衡阳人,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