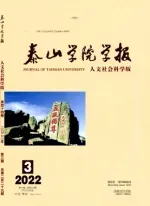鲁迅早期书信中革命话语的内涵演变
2012-08-15赵强
赵 强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革命”一词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正如李欧梵所说:“从晚清到现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和文学都笼罩在这个革命的‘话语霸权’之下”。[1](P2)可见,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不可能忽略对革命话语的使用,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话语。而且关于革命话语并不是相当然地就是一个含义,其具体内涵也是历史变化的,而使用他的主体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取舍与偏重。因此,考察现代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对于革命话语的使用及其内涵演变就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须要厘清的。当然,鲁迅在其小说和杂文等多种文本中对此都有所涉及,前人对此也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但是作为最为私密性文本的书信,鲁迅在对友人和亲人的交流中是如何对革命话语进行认识和使用的,却没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从鲁迅早期(1905-1927)书信中对革命话语的涉及,结合革命话语演变研究,分析鲁迅早期对革命话语的态度及内涵界定。
“‘革命’一词本来是个本土词汇,但它在本世纪初的复活,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日语的翻译,也即受了某种西化的洗礼,遂构成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说的‘革命之谜’——在本世纪最初二十年里激进主义的形成。”[2](P2)陈建华对革命话语的词源演变及内涵演变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中国古语里“革命”一词是早就存在的,只不过最初在《易经》里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包括了对旧皇族的杀戮。但是这里面临的问题是革命合法性从何而来?是武装背叛还是正义革命,其关键在于是否顺应天道民心。因此革命的正义性、合法性多少年来聚讼纷争没有统一的标准,最后就成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强权逻辑,而世界范围内英法革命的爆发,又提供了暴力革命之外的新的元素。正如陈建华所指出的:“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霍布斯鲍姆提出的英法‘双轮革命’说即基于此”[3](P7),那么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和平渐进的改革元素是如何进入中国的革命话语的,这就必须要借助日本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传播媒介,以及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革命的。最早把日本含义的革命话语引入中国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经过数年的对于革命话语的实践和思考,最终对于这一与现代中国命运密切相关的词语作了一个相对科学的界定。他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解决了革命话语中不同要素的体现。“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武力向于中央政府是也。”[4]可见梁氏对于革命话语所包含的诸多要素都进行了必要的涵盖。其中的最广义所说的有形与无形,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了制度层面也包括了思想和文化层面,且没有运用暴力的要素完成这种变革,这与鲁迅一直致力于的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不谋而合。而第二种含义则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变革,其手段则和平与暴力皆可。其狭义则是专指暴力革命,正如毛泽东对革命的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P17)
但对于中国的革命历史进程而言,却并不是简单的择其一而否定其它的。仔细考察应该是三种涵义都有。正如费正清所说的:“在西方世界,革命一般发生在诞生它们的文化中。一般说来,革命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候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我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这些疑问就使我想到,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用‘转变’这个字来概括,更精确一些?然而,我能看出,‘转变’这个词,除了用在宗教方面之外,不像‘革命’——我用这个词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那么激动人心。”[6](P49-50)因此很多叙述中使用革命一词更多地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话语更具有煽动性和表述的激动性。但具体到不同的个体在使用革命话语的过程中却具有相当复杂的特质。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中诞生的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于革命问题自然会有他自己的思考,而这种对革命话语的独特理解和使用通过对其早期书信中所涉及此类问题的分析,应该能够了解鲁迅思想深处对革命话语的真正态度及认识程度。
《鲁迅全集》所收鲁迅早期书信(1905-1927)共有269 封。其中给友人以及同乡官员的大约200封,给许广平60封(因为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作者本人于1934年将其中大多数作了增删修改,编入《两地书》出版。但是《两地书》所收书信与原信差异较大,因为考虑到公开出版所以功用不同内容也差别较大,为准确了解鲁迅当时的真实思想,本文所引用书信均为未经删改的原信。)在这些书信中明确提及革命的次数并不多,但其变相提及革命和变革问题之处也不少,这些言论体现了鲁迅早期的革命观。
当辛亥革命刚刚发生时,鲁迅以其知识分子的特有立场提出了自己的革命观。1911年11月写给辛亥革命后绍兴县议会议长张琴孙的信中明确提出了教育在共和大业中的重要作用。“比者华土光复,共和之治可致,地方自治,为之首涂。……侧惟共和之事,重在自治,而治之良否,则以公民程度为差。故国民教育,实其本柢。上论学术,未可求全于凡众。今之所急,惟在能造成人民,为国柱石,即小学及通俗之教育是也。顾教育一端,甚关国民前途。故区区之事,亦未可缓。”[7](P350)鲁迅在信中指出国民教育实在是地方民众能否自治的关键,而地方自治则又关系共和之事是否可成。因此教育一端就成为甚关国民前途的大事。由此可见,鲁迅对于国家改革大业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远离暴力而关注国民素质改变的,这也是梁启超对革命所作定义中的最广义的解释。直到1920年5月4日写给他的学生宋崇义的信中还谈到“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重臣,亦非强国也。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8](P383)鲁迅在这封信中对于学生运动影响到学界其实是颇有看法的。他认为:“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9](P383)他在此信中明确指出学生的运动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既不能过誉,也不能过毁,但是如果没有学问做底蕴,爱国之类,都是空谈。由此也可见鲁迅对当时的五四学生运动的态度,这也反映出他一直坚持的教育才是改变国家民族的主要举措的观念。但是1925年3月18日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再谈到教育以及中国的情况及将来时,则表示出他的悲观和怀疑。他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里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其中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10](P466)对于现在的中国却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将来也是虚幻的,而教育也不过如此而已。这表现出鲁迅的悲观、迷茫,因为现在的中国像一只黑色的染缸,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了,可见鲁迅实在是开不出改革的药方了。至于他最初所坚持的教育救国论,自然也受到了质疑和否定。
鲁迅在对教育的推崇产生质疑后,又明确地把改造国民性与中国的改革联系起来(鲁迅所使用的国民性改造话语其内涵就是今天的改革,之所以有人用革命,只不过是叙述更加引人注目而已。)1925年3月31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正面谈到革命和改革问题:“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最后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不但此也,现在虽想将政象稍稍改善,尚且非常之难。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11](P470)鲁迅在对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过程进行了总结之后,认识到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专制共和那种制度的改变只是换个招牌而已。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类改革的艰难,不但无从下手,而且困难重重,对于当时活跃的两种主义鲁迅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外新内旧。间接地表明了鲁迅对当时的政治主义的疏离和批判,对改革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重视。在后面的一封信中鲁迅对这个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并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在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指出:“大同的世界,怕一时未必到来,即使到来,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大同的门外,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近几年似乎他们也觉悟了,开起军官学校来,惜已太晚。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的。”[12](P476)这段话首先指出了中国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像中国现在似的民族,即使到了将来的大同世界,也是会被排斥在大门以外的。其次,鲁迅认为孙中山的失败在于对武力控制的乏力,并认为军官学校的开办已为时已晚,这反映了鲁迅思想中的矛盾,也说明鲁迅在对革命内涵的理解中,暴力革命和武力掌控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当然尽管他自己没有主张武力的革命,但他对孙中山革命徒劳的评价和分析,也表现了这点。但很快又回到了国民性堕落的分析上来,并且认为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且伴随着卑怯和贪婪。而且是比较顽固的劣根。在同一信中鲁迅还谈到了自己的反抗方式:“关起门来长吁短叹,自然是太气闷了,现在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但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需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照例要遇到的。我现在还在寻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再多几个,就来试试,但那效果,仍然还在不可知之数,恐怕也不过聊以自慰而已。”[13](P476)自己想办法起来进行攻击的依然是“思想习惯”,这表明了鲁迅一贯的思想革命和国民性改造的立场和态度。但是在另一封给许广平的信中又反映出鲁迅思想上对革命内涵的复杂态度,比如在1925年7月29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对革命党的革命时的不够暴力进行了批评。“我常想:治中国应该有两种方法,对新的用新法,对旧的用旧法。例如‘遗老’有罪,即该用清朝的法律:打屁股。因为这是他所佩服的。民国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等到第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的新党不文明,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再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现在已他妈的骂背着祖宗的木主自傲的人,夫岂太过也欤哉!”[14](P513)在这段话里鲁迅明确指出民国革命时不应该如此宽容和文明,应该学习旧党的手段——杀,并且认为如果当时更坚决的使用暴力,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了。而在早些时候的另一封信中,也表现出鲁迅的这种纠结。在1925年4月14日的信中谈到宣传对于革命的作用时指出:“我有时以为‘宣传’是无效的,但细想起来,也不尽然。革命之前,第一个牺牲者我记得是史坚如,现在人们都不大知道了,在广东一定是记得的人较多罢,此后接连的有好几人,而爆发却在湖北,还是宣传的功劳。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15](P480)宣传其实是非暴力的革命要素,但是鲁迅既觉得好像是无效的,可是又觉得有点作用,并且举例肯定了宣传的功劳。可后面的话中很快就提到宣传只能稍作辅佐而已,最根本的还在充足实力,此处的实力虽没有明确是军事政治实力,但肯定不是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实力。由此也可以看出鲁迅对此的犹疑和矛盾。果不其然,鲁迅在另一封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对自己的反抗和牺牲进行了质疑。在1925年5月18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谈到:“我现在愈加相信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是著著得胜。然而,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虽然还要坚持试一试,但是对于说话和弄笔墨这种反抗方式,也即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方式发生了怀疑和否定。“我那时曾在《晨报副刊》上做过一则杂感,意思是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16](P491)借用杂感中的言论再次表明自己牺牲的无意义。这不仅是对自己反抗方式的质疑,而且是对自己反抗价值和意义的怀疑。这恐怕是更可怕的一种认识和想法。从坚定不移地认识到改造国民性并积极投身到国民性改革的事业中,到后期对这种改革的意义和方式发生怀疑和否定,反映了鲁迅思想随时代发展的复杂变化,及对社会变革和革命的复杂性认识。
政治革命的局外人意识越来越强烈而明确。在1925年6月13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对上海的学生运动表现了他一贯的理性冷漠。他说:“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可是今年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不过这些表示,真所谓‘就是这么一会事’。试想:北京全体学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钉,女师大大多数学生而不能去一杨荫榆,何况英国和日本。但在学生方面,也只能这么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飞来的公理。”[17](P496)对于学生运动效果的质疑一如既往。而且还有淡淡的嘲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政治事件——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事件,鲁迅表示了适度的关注。在1926年10月15日致许广平的信中对北伐军的胜利消息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但自然不知道可确的。一,武昌已攻下;二,九江已取得;三,陈仪(孙之师长)等通电主张和平;四,樊钟秀已取得开封,吴逃保定。但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18](P575)虽然其胜利的真实性并不确定,但这表明了鲁迅对此的关注和肯定的态度。并且在1926年10月2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明确批评了那种只做学问不问政治立场的学者。“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吗?”[19](P581)尽管鲁迅激烈地批评这种没有政治立场的学问,但对于自己他并没有特别强调应该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依然是他者的批评立场,并没有把自己放在这个大的历史漩涡中。在此后给许广平的几封信中,鲁迅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到底应该选择创作还是选择教书的个人未来,而对于北伐战争只是偶尔从报上看点不知真假的消息,也很少提及。并且因为广州当局对顾颉刚的邀请,而对当局的看人和用人眼光颇不以为然。而他自己的最大野心就是到广州后给研究系也就是顾颉刚之流进行打击,这是他的首要目标,其次才是同创造社联络,向旧社会进攻。第一个目标实为个人恩怨,而向旧社会进攻才是鲁迅从事思想革命的正业。可见鲁迅关注的重心所在,显然并非当时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当然,我们不是要求鲁迅没有私心,毕竟顾颉刚之流对他的打击和伤害让他耿耿于怀。但这至少表明了他对当时北伐的关注和态度。在1926年11月26日给许广平的书信中对厦大的国民党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今天本地报纸上的消息很好,泉州已得,浙陈仪又独立,商震反戈攻张家口,国民一军将至潼关,此地报纸大概是国民党色彩,消息或倾于宣传,但我想,至少泉州攻下总是确的。本校学生民党不过三十左右,其中不少是新加入者,昨夜开会,我觉得他们都不经训练,不深沉,甚至于连暗暗取得学生会以供我用的事情都不知道,真是奈何奈何。开一回会,徒令当局者注意,那夜反民党的职员却在门外窃听。”[20](P633)先是对北伐的进程表示了一定的关注,继而批评本校民党的幼稚,不经训练,不深沉,表达了他的无奈,依然是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在提到厦大风潮时,也对许广平表明与己无关的态度和对此的不以为然。1927年1月5日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们少一刺激,或者不再举动,现在是不行了。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能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21](P12)在1月8日给韦素园的信中则认为这种学生的改良运动,未必能改良也未必能改坏。保持了鲁迅对于学生运动的一贯的态度。“与我不相干”这恐怕正是鲁迅所要表达的真实想法。
在1927年“四一二”之后,鲁迅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李霁野的,在信中简单描述了广州的情况,依然是旁观者的立场。1927年4月20日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说:“这里现在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22](P30)对于辞职的理由,也没有说是因为要营救被捕学生未果而为,他的解释是:“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23](P30)所以鲁迅对于广州的清党事件参与极少,此后5月15日给章廷谦的信中所说“广东也没有什么事,先前戒严,常听到捕人等事。现在似乎解严了。我不大出门,所以不知其详。”[24](P33)“不知其详”也表明了鲁迅的局外人身份。而此后对顾颉刚之流对他辞职流言的解释,更加说明了鲁迅对这次政治事件的态度。1927年5月30日给章廷谦的信中说:“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25](P35)对所谓的“亲共”传闻,一概斥之为流言,并且表明他的离开与政治没有关系。鲁迅在撇清自己与政治的关系之后,又多次谈到自己的打算,在给章廷谦的信中,他曾经说自己现在相信“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显得比较消极。到上海后,则抱怨除了应酬之外,无法看点书,或译作文章,并明确表示远离政界、学界。1927年9月19日给翟永坤信中表明了这种态度:“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卖卖罢。”[26](P67)在自己的好友章廷谦无端受连累,传言与共产党有关而被捕的事件时。鲁迅重申了自己的无奈和得过且过的态度。1927年12月9日给章廷谦信中说:“池鱼故事,已略有所闻。其实在天下做人,本来大抵就如此。此刻此地,大家正相互斥为城门,真令我辈为鱼者,莫名其妙,只能用绍兴先哲老话:‘得过且过’而已。”[27](P96)而在 1927 年 12 月 19 日给邵文熔信中明确表示了这种局外人态度:“时事纷纭,局外人莫名其妙(恐局中人亦莫名其妙),所以近两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昨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已应之矣。”[28](P98)至此鲁迅对于政治革命的疏离从思想到行为都比较明确而自觉地得以完成。
总之,从鲁迅早期的书信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鲁迅对革命话语的不同理解和自己的参与态度。早期是积极主张教育改革,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到后来对此产生质疑和否定。但同时又积极投入国民性改革和批判中,这其中出现了很多矛盾的因素,对于暴力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鲁迅有时是处于矛盾和犹疑之中的,再加上个人的很多恩怨,鲁迅对自己所从事的国民性改革也发生了怀疑,虽没有彻底否定,但却表现出勉力为之的悲壮和底气不足。而后中国政局颇多变动,鲁迅值此多事之秋,更多地表现出他对政治革命的远离态度,表明了他政治革命的局外人立场,颇多避之为恐不及之感。因此,从鲁迅的书信中我们能认识到鲁迅对于革命话语的复杂认识和自己立场的变化。对于全面了解鲁迅的革命思想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1]李欧梵.革命的现代性·序[A].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3]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A].新民丛报[N].第46-48合号,1904年2月.
[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A].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
[6]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鲁迅.鲁迅全集[C](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1][22][23][24][25][26][27][28]鲁迅.鲁迅全集[C](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