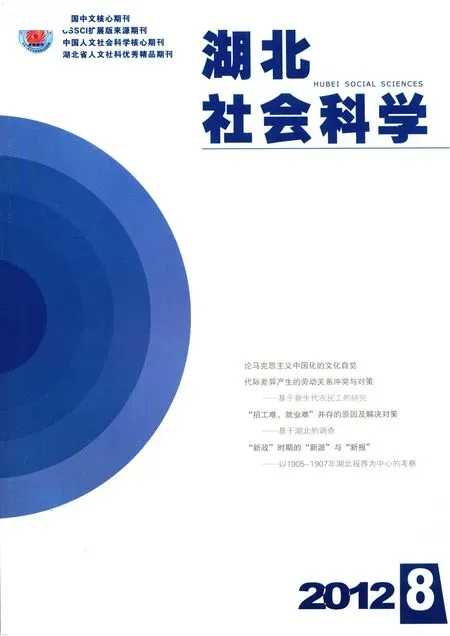钟嵘的永明诗歌风格论
2012-04-12蔡平
蔡 平
钟嵘的永明诗歌风格论
蔡 平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广东 湛江 524009)
永明诗风形成之后,钟嵘是第一位对其展开直接评论的文学理论家。他对永明诗歌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永明体主要诗人谢朓、沈约、王融、范云的品评里。“清”是永明诗歌的总体风貌;“怨”是永明诗歌的情感内容取向;“密”是永明诗歌的形式追求。
钟嵘;永明体;诗风
严格意义上的“永明体”,应该是沈约、谢朓、王融、范云等主要永明诗人尽在时期,以诗歌声律探索为重要内容,涉及诗歌艺术形式及风格等诸多方面的探索体式。永明诗人大都是萧子良“竟陵八友”中人,八人中,沈、谢、王是永明体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范云在当时的影响也不小,只是留下的作品相对三人为少。萧衍虽为八友之一,而且诗作也多,但只因他帝王的特殊身份,又不屑于沈约等人的“四声论”,往往不把他看作永明诗人。至于萧琛,在“八友”的年辈是最小的,永明年间他为六岁至十六岁,①永明年间(483—493),沈约(43—53 岁)、范云(33—43 岁)、任昉(24—34 岁)、萧衍(20—30 岁)、谢朓(20—30 岁)、王融(17—27 岁)、陆倕(14—24 岁)、萧琛(6—16 岁)。《梁书》本传谓其“少而朗悟,有纵横才辩”(《梁书·萧琛传》),今存诗作《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仅录其四首:《和元帝诗》、《别萧谘议前夜以醉乖例今昼由酲敬应教诗》、《饯谢文学》、《咏鞞应诏》,其诗风的倾向性并不明显。陆倕于“八友”中年龄也是较小的,永明时期为十四岁到二十四岁,他并不长于诗,而长于笔,《梁书》本传说他“少勤学,善属文,与乐安任昉友善”(《梁书·陆倕传》),其诗今存八首:《释奠应令诗》(五章)②逯钦立谓此诗“九章,一、二、三各章脱,四章残。”、《和昭明太子钟山解讲诗》、《以诗代书别后寄赠诗》、《赠任昉诗》,也非永明体探索的直接参与者。任昉虽有二十三首诗,却不是他的擅长,钟嵘说他“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诗品》卷中)这样一来,“八友”中也只剩下沈约、谢朓、王融和范云四人,他们的诗歌才是永明诗风的代表。
一
《诗品》所品诗人,在“竟陵八友”中只有沈约、谢朓、范云、任昉、王融五人,除了任昉外,钟嵘将沈约、谢朓、范云置于中品,将王融置于下品。评四人为:
沈约:
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也。(《诗品》卷中)
谢朓:
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不在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后进士子所嗟慕。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诗品》卷中)
范云: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迴雪。……故当浅于江淹,而秀于任昉。(《诗品》卷中)
王融:
元长、士章,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为足以贬卧龙。(《诗品》卷下)
钟嵘将丘迟与范云合品,将王融与刘绘合品,盖当风格近似而为。“八友”之外,刘绘(26—36岁)和柳恽(19—29 岁)也是永明体诗创作的积极参与者。柳恽,钟嵘未做品评,①《诗品序》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故仅以上述品中诗人看钟嵘眼中的永明诗人五言诗创作风格。
钟嵘认为沈约之诗“清怨”、“工丽”、“词密”、“意浅”,“宪章鲍明远”。那么鲍照又如何呢?《诗品》卷中曰:
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鲍照诗风又“源出于二张”,这“二张”为西晋诗人张协和张华,又以谢混、颜延之作比,四家各擅其长,鲍照则“总四家而擅美”,其风格“諔诡②“諔诡”,奇异之意。《庄子·德充符》:“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靡嫚”、“巧似”、“危仄”、“险俗”。沈约宪章的是鲍照的“靡嫚”和“巧似”而舍弃“諔诡”、“危仄”和“险俗”,即得其“擅美”的一面。“二张”、谢混、颜延之又如何呢?《诗品》卷上评张协云:
其源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词采蔥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张协文体“靡丽”、“华净”、“巧似”,“词采华茂,音韵铿锵浏亮”,[1](p153)鲍照得其“靡丽”、“巧似”。沈约对声协、调利的追求当间接得之于张协。《诗品》卷中又评张华曰:
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託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谢康乐云:“张公虽复千篇,犹一体耳。”今至之中品,疑弱,处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间耳。
张茂先诗风与张协同出王粲,文体“华艳”、“巧似”,多儿女情长,少气骨,格弱。这些特点也为鲍照所继承,永明诗人的气弱与儿女情长、绮丽工巧,当亦间接得之于张华。《诗品》卷中评颜延之曰:
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颜延之的诗风是“尚巧似”、“绮密”、“古奥”、“典雅”、“乖秀逸”、“错彩镂金”,《诗品序》又云:“颜延、谢庄,尤为繁密”。鲍照舍弃颜延之之典雅、滞奥而独取其“巧似”、“绮密”,重在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而不似其诗风。所谓“骨节强于谢混”,意指不似谢混之“才力苦弱”。《诗品》卷中合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五人而评之云:
其源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
张华文体以“华艳”、“巧似”、多儿女情长、少气骨、格弱为特点,谢混尽取茂先所长,而总成“弱”、“清浅”、“流媚”。鲍照避“弱”而就浅俗靡丽。
鲍照综采四家,形成自己的诗风,“尚巧似”至沈约变而为“工丽”。于“尚巧似”,曹旭释颜延之“故尚巧似”云:“此与评张协‘巧构形似之言’,评谢灵运‘尚巧似’,评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意同。”(《诗品集注》卷中)沈约“清怨”杂合鲍照的“靡嫚”、张协的“靡丽”、张华的儿女情长。“词密”含词采华茂、妍冶之意,亦当含颜延之的“体裁绮密”,这是鲍照、张华、张协、王粲、曹植一系诗人所共有的。“清浅”,乃变鲍照的“险俗”和谢混等的“清浅”和“媚趣”而来。钟嵘于中品评沈约语中并未提到“四声论”的诗歌声韵问题,其于《诗品序》中已对此加以批评,而评张协谓“词采蔥蒨,音韵铿锵”。在钟嵘看来,沈约的“音韵”当不同于张协的“音韵”,即张协是自然之声韵,而沈约为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的音韵。
钟嵘认为,谢朓的特点是:“细密”、“秀句”、“才弱”,从诗篇的整体布局着眼,“工于发端”,“篇末多踬”。其“细密”当同于沈约的“词密”,当然“细密”不光是“词密”,它的意义内涵更广,也可指作品总的风格、风貌。小谢的“才弱”正合于谢混的“才力苦弱”,因而钟嵘评其为“其源出于谢混”。谢朓的“秀句”在永明诗人中独树一帜,这一点是受谢灵运影响的。范云诗是“清便宛转”、“浅易”、“清秀”,“流风迴雪”意当同与谢朓的“圆美流转”。钟嵘并没有指出其诗源出何人。论王融则极简易,仅是“词美英净”,《诗品序》责其“词不贵奇,竞须新事”,亦未说明其承续、渊源。加上另外一位“八友”之外的刘绘,与王融合品,共为“词美英净”。
显然,钟嵘不是站在“永明体”以诗歌声律之探讨为主线的视角品评沈约、谢朓等永明诗人,但对五人诗风的纵向溯源与横向比较,却给出了他们在永明诗坛一个比较客观的定位。他的这些品评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他的出发点是鉴于对当时齐梁文坛风气 “庸音杂体,人各为容”、“师鲍照、学谢朓”、“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诗品序》)现象的不满,而“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诗品序》),分品论人,从而规范诗坛,确立文学风格的正宗。将钟嵘对永明诗人诗歌风格的客观定位综合起来,便可以形成他的永明诗风认识论。即沈约的“清怨”、“工丽”、“词密”、“意浅”、“宪章鲍明远”;谢朓的“细密”、“秀句”、“才弱”、“源出谢混”;王融和刘绘的“词美英净”;范云的“清便宛转”、“浅易”、“清秀”、“流风迴雪”。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体裁、章法、遣词造句的精巧细密和通体的流美;“才弱”而“意浅”;清便流丽、怨思宛转。 《诗品序》独以“精密”、“细微”为创首之王融,扬波之谢朓、沈约诗风之准的,谓其“文拘忌,伤真美”,指责的同时亦透出三人在“精密”、“细微”上风格的一致性。不同之处在于:沈约以“清怨”见长;谢朓以清词丽句独擅;王融、刘绘词体的清丽与洗炼;范云兼而有之却无个性。
二
南齐文坛的大家不多,所可称者,只为永明体诗人沈约、谢朓、王融几人。因而,他们每个人的诗风也都是永明诗风的一部分,共同构成永明体诗歌的总体风貌。这种风貌就是“清”、“丽”、“秀”、“密”、“浅”、“易”、“怨”、“弱”等美学范畴的集成。虽然这些质素不是在每个诗人身上都有突出的彰显,但每个人在突出几者的同时,其它方面便顺带而出,因为这些审美质素本身是互通而勾连的,是纯美文学质的规定性,类似以后宋人词派中“婉约”一系。
《诗品》论诗,出现最多的几个词是“清”、“密”、“怨”,尽管钟嵘并未将这几个诗论范畴用于每一个永明诗人,论沈约“清怨”、“词密”,论谢朓“细密”,论范云“清便”,但这些概念却都是对每个人品语中最为核心的词语,那么,钟嵘用于品评永明诗人的“清”、“密”和“怨”究竟其内涵何在呢?这需要对《诗品》中其它以“清”、“密”、“怨”的品诗之语加以分辨,并与对永明诗人的“清”、“密”、“怨”比较。
考《诗品》中,“清”字出现19次(排除引诗中出现的“清”字),分别为:
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诗品序》)
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诗品序》)
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诗品序》)
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诗品》卷上品“古诗”)
《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诗品》卷上品“班婕妤”)
然託谕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诗品》卷中品“嵇康”)
善为悽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卷中品“刘琨”)
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诗品》卷中品“陶潜”)
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诗品》卷中品“谢混”等)
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诗品》卷中品“鲍照”)
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逥雪。(《诗品》卷中品“范云”)
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诗品》卷中品“沈约”)
永嘉以来,清虚在俗。(《诗品》卷下品“孙绰”等)
安道诗虽嫰弱,有清工之句。①陈延杰:《诗品注》作“清上之句”,《历代诗话》本《诗品》同。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作“清工之句”;曹旭《诗品集注》作“清工之句”,此处从许文雨和曹旭之。(《诗品》卷下品“戴逵”)
希逸诗气候清雅,不逮于范、袁。(《诗品》卷下品“谢庄”)
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诗品》下品“汤惠休”等)
令晖歌诗,往往嶄绝清巧。(《诗品》下品“鲍令晖”)
祏诗猗猗清润,弟祀,明靡可怀。(《诗品》卷下品“江祏”)
子阳奇句清拔,谢朓常嗟颂之。(《诗品》卷下品“虞羲”)
以上十九次用到“清”字,除“庾白二胡,亦有清句”之“清”字外,其他十八处分别构成“清刚”、“清浊”、“清音”、“清捷”、“清远”、“清拔”、“清靡”、“清浅”、“清雅”、“清便”、“清怨”、“清虚”、“清工”、“清巧”、“清润”十五个复合词,这些复合词从语义和语法上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清”后接一形容词,构成并列式的复合词,这一类占大多数;一类是“清”后跟一名词,构成偏正式复合词,如“清音”、“清怨”,这一类仅此二词。下面分别考察各词目语义。
清拔,曹旭《诗品集注》:“清拔:清新峭拔。”形容文字清秀脱俗。《梁书·吴均传》:“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据《诗品集注》,两处“清拔”,义同。清音,《诗品集注》:“清音独远:谓清越之音传之久远,令人旷世同情。《文选·晋左太冲·招隐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清虚,《诗品集注》:“清虚:清议虚谈。指当时崇尚老、庄的风气。《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若夫严子者,绝圣弃智,修生保真,清虚澹泊,归之自然,独师友造化,而不为世俗所役者也。’”清雅,《诗品集注》:“(评鲍照)颇伤清雅之调:颇有点损伤清新典雅的格调。”“(评谢庄)清雅:清新优雅,此为褒赞之辞。”《三国志·魏志·徐宣传·桓范荐表》:“窃见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 ”清远,《诗品集注》:“清远:清峻深远。 ”《晋书·王导传》:“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清浊,“清浊”一词在《诗品序》中先后出现两次,其意义不同。《诗品集注》:“辨彰清浊:品评、辨析五言诗人流别。”“清浊通流:即平仄协畅之意。清,指平音;浊,指仄音。”清刚,清新刚健。“清刚之气”,曹旭释为“清新刚健的气质。”清捷,明快清婉。“辞旨清捷”,曹旭释为“辞藻诗旨明快清婉。”清靡,华美清丽。“风华清靡”,曹旭释为“风韵华美清丽。”清浅,清明浅易。清便,曹旭释为“清新便捷。”清怨,清愁哀怨。“长于清怨”,曹旭释为“长于清愁哀怨之发抒。”清工,曹旭释为“清新工巧。”清巧,曹旭释为“清新工巧。”陈延杰《诗品注》:“令晖诗:‘谁为道辛苦,寄情双飞燕。容华一朝改,唯余心不变。’是其清绝者。”清润,清靡明润。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仲伟评祏、祀兄弟诗,清靡明润。 亦可谓‘鲁、卫之政’矣。 惜其诗并佚耳。 ”[2](p142)
以上凡十五个含“清”复合词,按品评风格可以分为三类:其一,主意(雅),重清刚雅健、风清骨峻。分别为“清拔”(评刘琨、虞羲)、“清雅”(评鲍照、谢庄)、“清刚”(《序》)。 其二,主情(俗),重华美工巧、情缠意绵。分别为“清捷”(评班姬)、“清靡”(评陶渊明)、“清便”(评范云)、“清怨”(评沈约)、“清工”(评戴逵)、“清巧”(评鲍令晖)、“清润”(评江祏)、“清浅”(评谢混)、“清音”(评“古诗”)。 其三,主玄思,重清思玄远、超尘绝俗。 分别为“清远”(评嵇康)、“清虚”(评孙绰)。 而“清浊”两义分别为:分辨五言诗人流别和声律的谐畅,非谓诗歌的总体风格。主情一类多用,而且分别细致,足见五言诗自其产生便受到人们的喜爱,在逞词寄情上的优势。而且钟嵘将永明诗人沈约和范云置于主情这一类别中,在他看来,沈约和范云的诗风无清刚之气,而多清靡之音,是趋俗的、以情为指归的美文学一途。“清”的范畴可以归为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的“情文”[3](p537)之属。 无论是“雅情”抑或“绮情”,皆属“摇荡性情”而“形诸舞咏”(《诗品序》)的。
“密”字出现共7次(排除引诗中出现的“密”字),分别为: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诗品序》)
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诗品序》)
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诗品》卷中品“颜延之”)
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诗品》卷中品“谢朓”)
故当词密于范,意浅于江矣。(《诗品》卷中品“沈约”)
孝武诗,雕文织彩,过为精密,为二藩希慕,见称轻巧矣。(《诗品》卷下品“刘骏”)
兰英绮密,甚有名篇。(《诗品》卷下品“韩兰英”)
“密”也是钟嵘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它在《诗品》中的构词法为,在“密”之前缀以形容词或名词,除“词密”为名词前缀外,余下皆为形容词前缀。分别构成“繁密”、“精密”、“绮密”、“细密”、“词密”五个复合词,就其语法结构而言,前四者为并列式,后一为主谓式。
繁密,《诗品集注》云:“颜延之、谢庄喜用典故的繁密诗风,改变了当时的风气。《宋书·谢灵运传论》:‘延年体裁明密。’《南史·谢灵运传》:‘(灵运)纵横俊发,过于延之,深密则不如也。’”精密,《诗品序》中“务为精密”,《诗品集注》未作解释。卷下评宋孝武帝解释为:“精密:精致密丽。杨祖聿《校注》:‘精密,贬词也。仲伟,诗观,以自然中正为高。’”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孝武诗如‘屯烟扰风穴,积水溺云根’、‘长杨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其雕织精密,殊见轻巧。”绮密,《诗品》中“绮密”一词出现两次。《诗品集注》评颜延之注:“体裁绮密:此指延之诗风绮丽,缀词繁密。”评韩兰英注:“兰英绮密,甚有名篇:谓韩兰英诗绮丽细密,有不少著名的篇章。”细密,《诗品集注》:“细密:指谢朓新体诗多讲平仄对仗、声律繁密之特点。与品语‘细密’意同。”词密,《诗品集注》:“词密于范,意浅于江:谓沈约诗作词采比范云细密,文意比江淹肤浅,不易之论也。”
《诗品》中“密”的复合词虽然不及“清”的复合词多,但它们归结起来仍然表达了特定的美学内涵。它相当于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形文”和“声文”的问题,即诗歌语言形式的创造。“繁密”指颜延之的典实之密;“精密”指刘宋孝武帝刘骏的“雕文织彩”,指绮词丽句之密;“绮密”指颜延之、韩兰英五言诗整篇所显现出的绮艳与密丽;“细密”指谢朓诗歌声偶上的绵密;“词密”有是指沈约诗歌在遣词造句、运用声律上的精雕细刻。这里从篇章的典故和排偶的运用,到用词的色彩和声韵之美,都显示了诗歌语言形式着意求工、求丽。当然“密”也还指“情密”,五言诗之新变,就是情之密与词之密的有机结合,密词辅密情,密情融密词。这种“密”无论从诗人的人品,还是诗品,都变得柔弱了,纤纤如春风弱柳了。诗从人生高歌、天地宇宙走向楼阁亭榭,从阔大山水微缩为一器一具、一草一木、绮衫罗袜、香帐软席,生活越来越越闺房化了,人也越来越女性化了,对女性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女性的地位因为这种世俗观念的变化、生命个体向原生态的回归化而显示它的重要性。这种绮罗香帐的文学是诗人离开高堂明镜后给自己本质的还原,诗人的角色环境意识加强了,多重角色、多重性格、多面体的人生,在永明之后的社会比比皆是。梁简文帝萧纲就公然提出“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4](p354)足见时人对立身、处事人生、文章的理解。永明诗人及其所开创的永明体使整个南朝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以文学的形式彰显开来,它除了具有重要的文学审美价值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认识价值。尽管钟嵘品语不无批评之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文坛的实际状况。
“怨”字出现9次(排除引诗中出现的“怨”字,如“《诗》可以群,可以怨”),分别为: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託诗以怨。(《诗品序》)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句,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诗品》卷上品“古诗”)
其源出于《楚辞》,文多悽怆,怨者之流。(《诗品》卷上,品“李陵”)
《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诗品》卷上品“班婕妤”)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文被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诗品》卷上品“曹植”)
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品》卷上品“左思”)
夫妻事既可伤,文亦悽怨。(《诗品》卷中品“秦嘉、许淑”)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诗品》卷中品“郭泰机”)
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诗品》卷中品沈约)
託诗以怨,谓借助诗歌以抒发胸中愁怨。虽多哀怨,言“古诗”多抒发哀思悽怨之情。以上两者《诗品集注》未作疏释。怨者之流,评李陵“怨者之流”,《诗品集注》云:“怨者之流:可作二解:泛指李陵诗为悽怨悲怆之属;又‘怨者’指屈原。”怨深文绮,评班婕妤“怨深文绮”,《诗品集注》云:“怨深文绮:谓哀怨深切而文词绮丽。”情兼雅怨,评曹植“情兼雅怨”,《诗品集注》云:“情兼雅怨:谓兼《国风》、《小雅》之长也。陈延杰注:‘按,陈思有忧生之嗟,故乐府赠送,杂诗诸什,皆具《小雅》怨诽之致。’”文典以怨,评左思“文典以怨”,《诗品集注》云:“文典,文词典则。怨:怨刺。此指左思《咏史》以史实典事抒胸臆,刺怨情,颇得风人讽谕之旨。”文亦悽怨,评秦嘉、徐淑“文亦悽怨”,《诗品集注》云:“文亦悽怨:指秦嘉、徐淑赠答诗如同室晤言,共倾衷肠,哀怨悽绝。”孤怨宜恨,评郭泰机“孤怨宜恨”,《诗品集注》云:“孤怨宜恨:谓‘寒女’诗写孤寂怨恨,颇能抒其愤懑之情。”而长于怨,评沈约“而长于怨”,《诗品集注》云:“而长于怨:谓沈约不善于应制、奉诏之类的经纶之作,而长于清愁哀怨之发抒。”
“怨”与“清”一样,也有雅、俗之分,也分雅怨和绮怨两种,曹植、左思所有的是“雅怨”,而沈约、班姬等所有的则是绮怨和个人的不平之怨。在下列的所有“怨”中,最为特立而有别于众“怨”的便是沈约之“怨”。沈约之“怨”是唯一的南朝人之“怨”,南朝人之“怨”不再有“楚臣去境”之怨,“汉妾辞宫”之怨,“魂逐飞蓬,负戈外戍”(《诗品序》)之怨,沉沦下僚、郁不得志之怨,他们有的只是闲愁之怨、绮情之怨、亲疏之怨。鲍照之“怨”虽开南朝绮怨之先,但他的“怨”中更多的还是庶族寒门的不平之怨,真正的“绮怨”还是永明文人作为高门士族在南朝政治格局出现变化时的失落之怨,他们将这种“怨”从刘宋时谢灵运等的“怨而反”变成“怨而转”,转向一种男女间的闺怨。这是一种情思缠绵的怨情,而大谢狂放不羁的是一种豪情,尽管小谢亦得山水之灵于笔端,然而却已是大大不同于大谢笔下之山水了。永明文人中要算得有点豪情的恐怕也只有一个王融了,欲图大业而终不得,落得个丢掉身家性命,豪情转化为怨情,临死前怨子良曰:“公误我。”(《南齐书·王融传》)怨而无功转化为冤情,这是一个绮怨的时代环境,王融不能审时度势,孤掌难鸣,终致“折风落迅羽,流恨满青松”(沈约《伤王融》)的结局。 “怨”使“声文”、“形文”、“情文”的外形华丽、闲情逸致多了一份宛转与迭宕,这种“怨”是属于南齐永明文人所独有的。至萧梁嬗代,萧衍一手遮天于梁王朝的始终,真味的怨情变而为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乃至于走向绮辞、绮情、绮怨的终极,宫体诗便成了脱离永明环境的永明体的变体了,永明体作为一种仅属于永明时代的诗歌美学范畴被宫体诗歌的新范畴所取代,这大概也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吧。
钟嵘的《诗品》成于梁代前期,它的著述自然受永明文学的影响最大,他的以品论人、以品论诗客观地揭示了永明体的诗歌风格,这种风格便可以高度简化为三个字,即“清”、“密”、“怨”。 其中,“清”是永明诗歌的总体风貌,“怨”是永明诗歌的情感内容取向,“密”是永明诗歌的形式追求。钟嵘对“清”与“怨”多所肯定,而对永明诗歌创作在典实、辞藻与声律上的“务为精密”(《诗品序》)则是持否定态度的。
[1]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I207.2
A
1003-8477(2012)08-0123-05
蔡平(1964—),男,文学博士,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