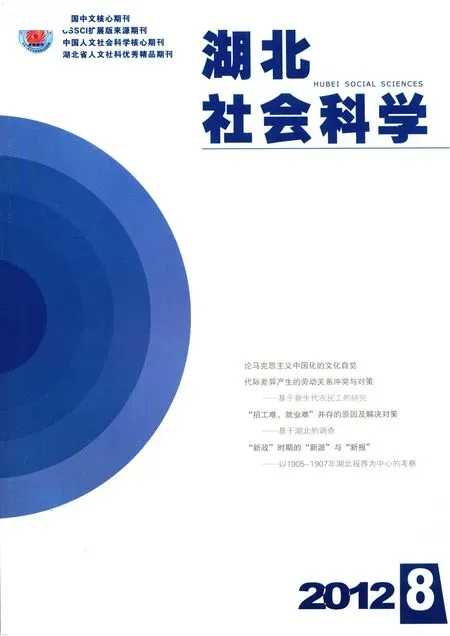“新政”时期的“新派”与“新报”
——以1905-1907年湖北报界为中心的考察
2012-04-12梁方
梁 方
(湖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2)
“新政”时期的“新派”与“新报”
——以1905-1907年湖北报界为中心的考察
梁 方
(湖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2)
20世纪初期,湖北时为全国“新政”重镇,“新政”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流动和结构调整:传统“士绅”的边缘化、新知识分子的崛起、商人和军人的“异军突起”。日益活跃的新社会阶层与正在成长的新式报刊一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分崩离析。
新政;新社会阶层;新式报刊;学生运动;社会流动;结构调整
晚清“新政”是为了保住清王朝,但是事态的发展与“当道”诸公的意图恰恰相反,“1901年以后清廷搞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那些在后来将有助于推翻清王朝的社会集团和组织。这些集团和组织包括新近纷纷成立的商会阶级、一个新的军人集团和一个新的知识阶层。”[1](p545)到了1905年——中国的转折点,逐渐活跃的“新派”与正在成长的“新报”一起,加速了“四民社会”离心离德的分裂局面。即便如此,至少在1908年之前,清廷仍表现出一种顽强的适应韧性,不时出现复苏的迹象,并调动足够的力量控制新思潮和社会舆论,以防止它们对原有的秩序构成任何严重的威胁。1905-1907年,“当道”和“新派”同时面临着两种前景:或许前途光明,但确实危机四伏。
之所以以1905-1907年的湖北主要是武汉报业为考察对象,是因为武汉时为全国新政重镇,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及新式报刊的繁盛,从一个侧面记载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各种新生社会集团的政治诉求和力量的博弈与消长,以及由此形成的1905-1906年革命热潮。1907年,由于“当道”的“文治武功”,这个热潮迅速走向低谷,然暗流涌动。尤其是新军学界中的“笔杆子”们,潜行地下,以其微小却有力的声音,迅速唤起了1908年湖北革命的再次复苏,最终迎来了1911年的“文字收功日”。历史合逻辑地发生发展,这一切在1905-1907年湖北(武汉)报业的吉光片羽中,已“一叶落知天下秋”。
一、“绅商”的尝试与诉求
20世纪初年,在“新政”改革的推动下,绅、商互渗合流的趋势空前增强。“1905年左右商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标志着绅商已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2](p428)这个跨居“绅”与“商”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新兴群体逐步脱离传统轨道,其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出现了带有近代趋向的微变。不可否认,日益获得新内涵和活力的绅商们将某些近代因素融入到传统权势阶层的内部,使长期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某种分化和裂变。为了自身发展并希图对社会施展政治和思想影响,他们将视野投向了新式报刊,借此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这种影响力还未能单枪匹马地左右社会,他们仍不得不依附于使其脱颖而出的传统权势阶层——实力派官员。
(一)从《汉口日报》到中文《楚报》:“由商而绅”者的直白。“张之洞是第一个从他的长江中游的基地武昌把新口号应用到工业项目的主要人物”,这个“新口号”可以归纳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官商合办”。[1](p494)“新政”时期,他在湖北先后创办的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不仅如此,张之洞还主动倡导和积极筹办“商务局”,鼓励和支持商人们的“自组织行为”。故湖北“敢为天下先”,较早设立商务局,官商共同管理。1902年,商务局设立商务公所,5年后,汉口商务总会正式成立。
第一届汉口商务总会(1907年)协理刘歆生、议董宋炜臣,都是富有革新精神和善于冒险的商人,不仅致力于经济现代化而大获成功,誉满华洋;而且,或企慕绅士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或谋求官府的权势保护,竞相解囊捐纳“候补道”,跻身于“制抚臬藩道”之列,成为“由商而绅”的绅商。由于刘、宋涉足更多近代经济活动,且与外国商人保持紧密联系,致使他们的社会态度和投资倾向显得与众不同,更乐意尝试新的领域,比如报业。
1902年秋,宋炜臣投资的《汉口日报》开馆见报,此乃以“汉口”命名的第一张民办报纸。“创刊之始,抨击时政甚烈”,内容严正,文风意趣,广受称许,销路颇畅。该报笔政吴趼人——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家——“性强毅”,“负盛气”,“不苟合于流俗”,多次撰文讥刺针贬武昌知府梁鼎芬之“德政”,招致嫉恨。1903年4月,拒俄拒法的爱国浪潮波及湖北,梁鼎芬极力阻挠,吴趼人振笔直言,《汉口日报》载文诋斥,终不为当道者所容,旋改为官办。[3](p73)1905年4、5月间,英文《楚报》开辟中文版,由刘歆生出面主办,委冯特民主持报务,冯曾任《申报》访员,后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重要成员,“日知会案”后潜至新疆,主办《伊犁白话报》,孜孜宣传革命大义。时人欧阳瑞骅曰:冯氏“办《楚报》,署民鲜民,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忌”,为世人击掌,为官方侧目。是年,“总督张之洞,小英(美)人密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特民觅得全文,竟夜抄出,悉载报端,撰文掊击”,触怒张之洞,遂被“严办”查封。旋主笔张汉杰被判处10年监禁,成为武汉报界惨遭摧折的第一人。[3](p94-95)绅商投资现代报业的积极行为,必然因触怒“当道”而稍纵即逝,但他们的一现昙花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新兴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了传统社会的裂变和转型。可惜这种力量实在太有限了。
(二)《汉报》:“由绅而商”者的多重角色。晚清“新政”对工商业的重新评价已经使近代商人在思想上受到尊重,地位日渐攀升,从而大大加速了“由绅而商”、“官渐趋商”的社会流动。经营商业的绅士或官员在“重商思潮”的鼓动下,成为新绅商阶层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部分。其中,那些参与商业的官员们最初无非是实行一般的监督,后来开始以民间身份独立出资或靠朋友筹集资本投入商业活动以谋利,“这使“官”字有了新的意义:它现在指的是官员个人,不再有“政府”或者“官员集团”的意思了”,[1](p523)如此一来,他们集投资者、经理和官方资助人的多重角色于一身。
1906年2月4日,《汉报》创刊,“川人朱彦达(江苏候补知县)邀约甘肃吴赓梅共筹资金2200元(共集22股,每股100元)。馆设汉口花楼正街苗家码头巷内。朱彦达自任总理(因系在册命官,经张之洞正式委任)……该报接受政府津贴,经张之洞批准,由湖北签捐局每月支助100元,成为湖北民办报纸获得官方资助的第一家报馆。”[3](p98-99)因为是官员顶办,该报获得官方“支助”,并得到政府保护,但它从一开始就是官员以“民间身份”筹资主办,采取股份制经营,且始终坚持民办方针,因而避免了被官方操纵的厄运,担负起“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因此在言论上游走于官商之间。
一方面,《汉报》敢于针砭时弊,为世人请愿。该报曾刊发《论振兴工艺宜审其性质以定宗旨》,辨“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之异,[4]反对官办企业与民争利,积极倡导企业民办。又刊发 《改革内官官制感言》,批评清政府预备立宪之有名无实,“欺饰天下耳目”,[5]敦促政府加快实行政治改革。为争取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所刊《论舆论之势力》,略谓:官报“其作用专以备宣布文件、供人调查之用,故但有命令而无要求,有诫输而无督责”,民报的职责在于“对于国民而为向导,对于政府而为监督者”。[6]另一方面,他们的言论必然打上“官”的痕迹。虽同为“绅商”,朱彦达们比刘歆生、宋炜臣们在政治上表现得更活跃,具有更强的政治革新意识和民主自治精神。即便如此,他们仍小心翼翼于自己的报章言论,将政治主张限定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如对革命团体的兴起,《汉报》载文《团体辨》,斥责政团为“朋党”,饰说济私,破坏“官权法律”。[7]又如在“日知会案”中,武昌警察局抄出革命书籍《孔孟心肝》,《汉报》著文《纪革命党之逆书》,措辞激烈,称该书为“大抵离经叛道,以摇惑人心为宗旨”。[8]
可见,崛起之势将绅商们推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虽对腐朽王朝颇有微词,并力主鼎新,但讳言革命,这注定了他们要在正在来临的革命中扮演二流的角色,施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二、“四民之首”的没落与挣扎
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乃四民之首。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强制传统“士”阶层大分化,导致社会阶层关系重组的最重要的体制变动,给与其息息相关的“八股士”和由此维系的“四民社会”都打上了难以逆转的句号。此乃近代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科举制不仅仅是一种官僚选拔机制,也是一种政教相连、耕读仕进并举的社会建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起着“通上下”的重要功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循环的流动之中。如今此路不通,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不得不转向,其社会后果是深远的。与此同时,热衷于改革和废除科举制的“新政”官员们,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之奏折,从1901年到1905年间,几乎是几月一变,前折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建议已接踵而来。他们基本上只考虑到“科举”的教育功用,并试图通过兴办新式学堂来加以弥补,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时不我待的急迫情绪,终使他们不能耐心等到学堂制的成熟即立废科举制。旧的已“破”,而“新”的未立,新学堂无论从制度上和数量上均不足以代替和新启仕进之途,而期望上进的士人却并未消减,于是边缘化的“士”,在下沉中分化,或消极于玩世,或冷眼于观世,或积极于变化,构成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造因已隐伏在那里了。
(一)文人小报:“旧式绅士”的穷途之叹。“四民之首”的“士”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取“功名”,“功名”是获取社会优势地位和权势资源的凭藉和依据。整个“士”集团分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下层“如众多的生员(秀才,包括监生、增生、贡生等),只是小绅士,实际上已经介乎绅与民之间,他们没有上流绅士那么多财富和权力,又比一般的‘耕氓市井’之类多了一点功名”,[9](p416)在整个绅士集团中所占比例远远大于上层。而恰恰是这个相当庞大的下层绅士才真切感受到科举立废所引发的强烈冲击和社会震荡,《光绪朝东华录》载:“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不免穷途之叹”。[10](p5488)即使那些年龄尚可入新学堂的生员,又苦于学堂因师资、教材、经费、校舍等问题而规模有限,只得望之兴叹。这群既无法通过科举取士获得功名,又无法进入新学堂接受再教育的“旧式士类”,“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并重新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
据《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统计:自咸丰 10年(1860)至光绪 31年(1905)的 46年间,湖北新增士绅约为4万8千余人,其中进士257人,举人1,369人,生监47,310人。[11](p466)乐于吸收新知以改善政治和社会地位,谋求更佳出路的绅士们纷纷云集省城的新学堂,而无法被接纳。关于接受再教育的人数,初步估计在清末的20年间,湖北大概有2万余人,约占全部士绅人数的43%,均以15~30岁之间的年轻举贡生员为主。[11](p471)至于未接受“再教育”的“旧士绅”,因限于资料,无法详加讨论,但不难推测,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功名较低的“小绅士”,且年纪偏大。这批仕途中绝,又不被新的社会结构所吸纳的传统“士大夫”,很快就成为武昌城里“自由浮动”的“边缘群体”。其中许多人深受早年旧式教育经历的影响,沿着惯有的“诗书墨卷”和“游于艺”的志趣径直走向报业,在经营新事业的过程中逐步向职业报人转变。
1904年3月14日,《武汉小报》创刊,以刊发新闻小说、游戏文章为主要内容,是湖北最早发行的小报。1905年11月,据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的报告《有关汉口的报纸情况》,称:“目前发行的只有《汉口风月报》和《新小报》的小版面汉文报纸。这两种报纸与上海的《繁华报》为同一种类,仅仅是评论艺妓、演员的报纸而已”。[3](p96)1906年《现世报》创刊,此乃湖北第一家以专载妓女花事和诗词小品为主要内容的消闲小报。1907年2月20日,《花报》创刊,每日新闻三版,其中“花丛韵事”占两版,篇幅之大为“向来各报所仅见”,出版广告宣称:“同人创为《花报》,以纪其事,虽无补于当世之务,要亦滑稽微言,以小喻大之意也。”[3](p125)小报可谓一时风行。很可惜,武汉早期的小报资本少、规模小、寿命短,鲜有保存下来的,由于报纸实体的缺失,后人对它们的认识也变得模糊不清。就现有资料分析,武汉近代小报初创时大致“与上海的《繁华报》为同一种类”。大概来讲,最初的小报文辞气息浓厚,除登载少许对时事政治的点评“首论”,版面充塞着妓院消息、名妓的容貌、才艺、起居之类,对于文人之间互矜风雅的诗词、唱和格外重视,尤其是他们念情风花雪月,寄意清歌长舞的诗咏辞章,此乃传统文人士大夫自命不凡的雅文化游戏。
这些“旋起旋仆,为时不多”的小报,远不如创办或经营它们的“小报文人”那样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其一吴人凤竹荪,是专管附张诗词的。其二朱钝根,是担任论文撰述的。其三包抽斧、宦论之,是编辑新闻,或撰著短评的。其四王华轩,是经营印刷事业的。其五孙亚二、刘云集,吴耳似之流,是主办小报的。至于小说的撰述,大都是馆外的投稿,一个是李涵秋,一个是我的老友天门胡石庵。”[12](p21)他们多为官宦世家或秀才出身,是一批被阻断了仕进之阶的旧式文人,虽处于社会边缘,仍保留着传统文人士子的“笔墨”和“才情”。然随着“士”身份的丧失,他们也不得不趋俗附利,“为稻粱谋”,而孜孜不倦于卖文生涯。在大变革时代,“游戏”、“消遣”的小报或许为疏离政治、谋生其间的旧式文人提供了一个呤风弄月的舞台,一个展示才华品位的场所。
很显然,这些小报主要是迎合、取悦文人墨客及有闲有钱阶层的风雅消遣。然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空间,小报也逐渐向广大市民阶层倾斜,不仅栏目开始多样化,如《现世报》“设要电、游戏文章、齐东语、小说、词海、世说、楚词、花史、笑林、图画等栏目,兼刊告白”,[3](p110)而且内容朝着类似于“嫁人出象,调班打热捶,收歇开张,争客吃醋,班主虐待,滑头行骗,姘龟奴,姘戏子”[3](p125)的社会新闻方向延伸,以适合普通市民“酒后茶余,资为谈助”的文化趣味。“小报受众面的扩大,标志着小报由有钱有闲阶层的消闲文化向市民大众生活和消费文化转轨。”[13](p157)非官方化的经营方式,以及相对独立于官方政治权威之外的生存环境,随着向市民阶层的渗透,小报正为市民文化公共空间的建构准备着条件。
(二)《汉口中西报》:“超然”党政的“和平公正”。 在“功名”之外谋生存之道的传统士绅除了创办以上所介绍的消遣小报外,还认真创办了严肃的综合性日报,体现“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的积极用世态度,首屈一指者当属王华轩和他的《汉口中西报》。王华轩,湖北黄冈人,清末秀才,早年一度涉足政界,后改投报业,自设“中西印书馆”于汉口,先后独资创办有 《武汉小报》、《汉口中西报》、《汉口中西晚报》等多种,1938年武汉沦陷始辍业。王氏以“经济独立”而超然于党争之外,主办报业长达35年之久,成为武汉大有成就的职业报人。
1906年5月下旬,湖北历时最久的商办报纸《汉口中西报》创刊。该报历经30余年,发行超过万号,于汉上报界独占鳌头,位居全国第六,仅次于《申报》、《新闻报》、《大公报》、《时报》、《时事新报》。王华轩独资经营,自任经理,凤竹荪、王痴吾、曾莘庐、贡少芹、朱钝根、胡瞿园等先后参与编撰。馆员多为留日学生,但不聘用革命党人。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商务学务”为主旨。取名“中西”,意在“注重世界知识,把国际要闻列在重要篇幅,以唤起国人注意”。设上谕、论说、译电、时评、演谈、本省公件、紧要新闻、内国纪闻、外国纪闻、本省纪闻、短篇小说等栏目,以一半以上篇幅用于刊登广告、货物行情、钱帮行情,以此获利。该报在言论上“以公理正义为依归,持和平公正之态度,不为利诱,不为威屈”;在经济上自诩为“纯粹商办性质”,独资经营,从不接受官府、政团的津贴,“全持营业之挹注,以保持经济独立,严拒任何方面和任何私人之收买与津贴,以期避免恶势力之支配与软化”;在政治上“不偏不倚”,“超然于党政之外”,“绝对不卷入政潮之漩涡中”。[3](p102)辛亥武昌起义后,该报既不以黄帝或民国为纪元,也不用宣统年号,而以农历辛亥年某月某日应对,并避免使用“革命”和“起义”字样,竭力回避公开表态。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读书人内心政治情结的率直表露,科举制将他们的文化使命落实到政治使命之中,为他们实现政治抱负、社会理想开辟了制度化前景。这无疑鼓舞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无论政治上“进”、“退”与否,忧国忧民,痴心不改。然而,或“只谈风月”的小报文人或“绝对不卷入政潮之漩涡中”王华轩之辈,报人疏离政治的群体表现,正是科举制废除后,传统士绅逐渐从政治社会的权力中心退居边缘的深刻反映。
三、近代新知识分子的呐喊与奋争
“自居于士类者”的另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19世纪末开始的各种新式学堂所培养出来的近代新知识分子,包括为数不少的留学生以及从传统经生、儒士脱颖而出的知识分子。不同于那种“舍帖括八股书画之外更无其他学问”的“八股士”,他们接受过新思潮、新学理的洗礼,有着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在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下,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与执着逐步让位于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到1905年,一种新的回应正在中国发展着,“幸亏有了清廷的新政,学生运动才得以发展,才有新的机会使得受教育的人们能在创功立业的同时去推动革命”。[1](p556)
(一)从《湖北学生界》到《文华学界》:“湖北人谋湖北事”的学生界。19—20世纪之交,中国“留日学生潮”逐渐形成,以1903年为始,留日学生急剧增加,而科举制度的最终废除,使得1906年成为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综合多种资料表明,张之洞“新政”的湖北,留日学生总数在5000名左右,高居各省榜首。正是这么一群“热衷于让同胞分享他们新的知识,鼓舞同胞们的爱国思想”[14](p67)的留日学生,“当吾华似醒未醒、初醒之际,新故旧欤?彷徨莫定之时,有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有日本留学生之詈骂,有日本留学生之电争,以致国人为之大醒……在此醒悟时代,日本留学界,大大影响中国”。[15]
1903年1月29日,“湖北人谋湖北事”的湖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份以省名命名的刊物《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明确提出:推翻君主王朝,建立民主国家之主张。[16](p65)在《湖北学生界》的感染和号召下,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群起效仿,继而创办了《江苏》、《浙江潮》等,“皆明目张胆,痛谈革命”。[17](p195)与此同时,为了扩大对国内的舆论宣传,湖北留日学生发起创办昌明公司于上海,旋设分部于宜昌,“专售东京学界译著出物”,[3](p77)公开派售《湖北学生界》。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这些迈向革命的刊物,充满了反满的危险,使清廷越来越惶恐不安,“《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乃其最著者。清廷未如之何,乃严禁学生购阅……然禁者自禁,而此等报章依然秘密输入”,[17](p196-197)极迅速地流布于湖北学堂和军营之中。由此,湖北革命风气初开,故时人评价:“两湖革命思潮,多发源于二杂志矣(《湖北学生界》和《游学译编》)。”[18](p275)
与此同时,湖北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书院改制”,到1903年后大办新式学堂,造就了一个大约15万人左右的新式学生群体。“在省城,学生们在教室内接触到新的、经常是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校外则接触到日益活波、直言不讳的报刊。”[19](p51)据1904年日本人编制的《武汉报纸销数调查表》所统计,当时在武汉公开或秘密行销报刊约20余种,大致是《申报》、《中外日报》、《新民丛报》、《汉声》(前身即《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20]通过生机勃发的报刊的影响——尤其是在日本出版而秘密输入国内的《湖北学生界》,省城武昌不但成为教育事业的中心,也正在成为讨论政治和抨击政府的中心。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学生界率先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并积极担任起批判现状的主角。正如居正所云:“湖北自张之洞提倡学堂后,而新潮输入,革命已伏萌芽……同时,留学生创刊《湖北学生界》以鼓吹之,革命思想因之勃发”。 [21](p115~116)
1905年,中国国内的学生运动真正自觉地发动起来了。在1905至1906年的学生运动中,“最初由日知会领导的一个类似的学生运动,似乎在湖北也兴起了。一个伪托依附于武昌圣公会教堂的基督教徒社团,发展成为一个激进分子团体的阵线,这个社团包括了已经夭折的科学补习所的许多前成员。从一九○六年年初开始,日知会每星期举行关于各种激进问题的讨论会:有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些是非常传统的种族反满主义的”。[19](p64)1906年3月,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在武昌成立。“日知会”原为美国基督教圣公会附属之书报阅览室,革命党人刘静庵假其名号以相掩护,并借该阅览室所陈列之中外报章宣传革命思想。后教会刊物《文华学界》在武昌创刊,圣公会附设于文华书院主办,余日章主编,刘静庵等编撰。日知会更借助该报刊直接发表反清言论。
1906年夏间,学生运动决定性地转入了一个新的局面:与秘密会党和暴力革命公开联合。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爆发之后,在日本的革命报纸很快就和起义者连同一气。若干革命党人被同盟会派遣归国,肩负前途凶险的使命,在国内其它各地发动相应的起义”。[19](p74)1907年1月,镇压学生运动的风暴旋踵而至,“日知会”9位领袖被捕入狱,遂酿造震惊朝野中外的“日知会案”。
与国内学生运动在1905-1906年被严重摧残的困境相反,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运动却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潮。孙中山日本登陆时正值1905年7月学潮高涨,8月同盟会成立,11月机关刊物《民报》在两湖留日学生所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基础之上创刊。自此以后,革命运动在新的阶段如火如荼地加紧了。
(二)从“鸠译书舍”到《通俗白话报》:新知识分子的“新军”突起。1906年以后,国内大规模的镇压严重摧残了学生运动,“使它不复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名独立演员。直至辛亥年,它都不曾以一种可观的力量显露头角”。[19](p77)革命的领导权最终落到了新军的手中。“投笔从戎”,武汉发生的事情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新军是在那里开始1911年起义的。全国只有张之洞在湖北办了一所这样的学校——陆学特别小学,“这所学校的‘学兵’,从军队列内部选拔,生活隶属于正规的军队建制单位,可是白天上学”,[19](p179)以达到张总督募集有文化的士兵的宗旨和期望。与此同时,省城的中、高等文官学堂系统,没有能力吸收全省所有的受过部分教育的读书人,所以在1905至1906年,正当科举制度废止、新制学堂尚未建立之前,有一群为数可观的秀才在湖北参加了军队,“一个前士兵回忆,一九○五年和他一起在黄陂应募入伍的九十六人中,有三十六人是廪生或秀才。另外一个人表列了四十个参加军队的秀才名单,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革命党人。”[19](p178)张之洞花大力建立的湖北新军,集中驻扎于武汉三镇,在城市里,传统反满情绪的高涨,复兴民族诉求的急迫,反复批评清廷的报纸,不断激进革命的学生,深刻地感染着这支“数量最多、教育水平最高、训练最精”的军队。
早在1904年,湖北学生界就认为,军队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有意识地投身新军,为革命秘密工作。萍浏醴起义后,清廷对学生运动的灾难性的血腥镇压,加速了革命学生在军队内部展开动员的趋势。在此方面,日知会做了一次大胆而卓有成效的尝试,“据说有一个日知会,在组织普通士兵方面特别成功,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1](p587)这个团体与其他各处学生组织的不同,主要在于它不只是学生和教员参加,同时也努力网罗军人。他们在新军中的渗透活动日益频繁,主要包括利用革命报章、白话文书刊来煽动士兵。
日知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梁耀汉,清末武秀才,1903年留学日本,2年后回国返汉,为酝酿革命而服役新军前锋营。1906年,梁耀汉与黄州秀才吴贡三改写宋人石介所著《孔夫子心肝》为《孔孟心肝》,借附孔孟经义,论证种族大义,鼓吹民主共和,为刊印革命书刊,遂创办“鸠译书舍”。《梁耀汉年谱》中如是记载:“同年春,梁耀汉出资与吴贡三、殷子衡等在黄州成立‘鸠译书舍’,专事印刷发行《孔孟心肝》,刊印万余册,由黄楚玉、张佩绅、吴安吉等用竹箱先后挑运到武昌,散发军学各界,广事宣传。后来又有李在良在英山也翻印万余部,运往两广散发。时西路南路高小学生周海珊、黄桐生、熊礼方等常拿官票购买三五十部分赠同学。足见革命之潮由君等鼓吹而高涨矣。”[22](p505)是年,其兄梁钟汉从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退伍,亦赴日留学,每每返汉,秘密带回留学生在日本发行的革命小册子《猛回头》、《警世钟》等,均由黄洲“鸠译书舍”翻印,散发于军学界,策动革命进展。[23](p7)不久,梁耀汉偕刘静庵主持日知会事务,黄州“鸠译书舍”遂成为日知会唯一的印刷机构,“凡运动革命之出版品,皆使黄州殷子衡、吴之铨广为印送。学界则易于散播,兵士则传播颇难。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24](p130)梁耀汉、梁钟汉、吴贡三、殷子衡,同在“日知会案”被捕9人之列。毋庸置疑,湖北学生和他们的激进思想正是通过书报等传播媒介在有文化的新军中渗透、动员。
1907年“日知会案”,学生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湖北新军里的革命活动也似乎停止了,时人李长龄甚至有言:在日知会后,“武汉军学界绝口不谈革命,寂焉无响者殆年有余”。[25](p165)实际上,原日知会的领袖们或入狱或在逃,影响力却并未稍减,继续发挥着潜在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据梁钟汉的狱中回忆:“陈少武在汉口,办一《通俗白话报》,要我长期作白话文,送他登载,我于作文一道,不敢答应,即推举李亚东负责……陈少武等之‘白话报’馆与‘大江报’馆,皆带革命性质。”[23](p15-17)李亚东,“日知会案”9位被捕领导者之一,湖北将弁学堂毕业,被捕时任湖北新军第29标一营左队队官。入狱后,经梁钟汉推荐,通过陈少武密办《通俗白话报》,以“上逸”笔名撰稿,大力鼓吹革命。而“日知会案”之幸免被捕的梁耀汉旋奔走河南,游说赋闲的袁世凯,“遂出筐中《孔孟心肝》置案上,袁阅之狂走,大睁双目,炯炯如电光”。[22](p524)借助“无声之金鼓,诛奸之妙器”,[26]他们的不懈努力使得革命暗潮得以在新军中保存、延续。1908年7月,原日知会成员任重远、覃秉钧、黄申芗等在狱中征得梁钟汉同意,组织“湖北军队同盟会”,它的成立使消沉一年的革命活动又迅速活跃、扩大。不久,军队同盟会演变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再而演变为文学社。由此,革命之火,薪薪相传。
1905年科举废,从而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流动和结构调整。传统“士绅”的边缘化、新知识分子的崛起、商人和军人的“异军突起”,他们虽各行其事,但所创办的报纸“以新学界为主要读者,官商次之”,在提高人们对国家大事的认识中,在对政府政策和人物进行批评中,加速了“四民社会”的解体。对于统治集团而言,正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前景。
四、新式官报:“当道”的卫道与正学
同时,虽然“新政”的所作所为是瑕瑜互见,但总的来说,它表现的活力大大出乎任何人在1900年的预料,而且清王朝毫无衰退的迹象,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150年或200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1](p583)这确实是令反满革命的激进者们担心的前景。
“新政”以来,民办报纸公开报道政府的决策活动以及各级官吏的公私言行,俨然成为民众表达意愿、监督政府的重要工具,形成了对王朝官府的社会制约力。这一新的社会约束力的形成,迫使清政府承认报馆的合法性,并力图用法律加以控制,防患于未然。从1906年7月 《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0月 《报章应守规则》,到1907年9月 《报馆暂行条规》,都对报刊的注册、批准、审查、处分作了严格规定,不给所谓“悖逆”报刊以出版的机会。张之洞的《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一语中的:“闻华人有拟在汉续开报馆者,当此讹言繁兴之时,恐不免摭拾上海及外洋各报传讹惑众。将来开办报馆之人,必致自蹈法网,与其拿办于事后,不若预防于事先。如在华界开设者,禁止购阅递送,房屋查封入官;如在洋界开设,冒充洋牌,亦断不准递送,违者一并拿办。”[27](p309-310)故迄至1907年,当这位70岁的老总督离开湖北时,他所把持的武汉也未公开发行一份完整意义上的革命派报纸。在制订报律限制进步报纸出版的同时,1906年始,为了实行“预备立宪”以及抵制革命派报刊的舆论宣传,朝廷关于自办新型官报的倡议再次喧嚣一时,官报创办活动顿时熙熙攘攘。1905年4月5日,《湖北官报》正式发刊。基于对近代报刊尤其是舆论功能的深刻理解,张之洞亲自制订了该报的有关宗旨、条例。《湖北官报》公开宣称“正心术,止流说”、“正人心,息邪波”,明文规定“凡邪波悖乱之说,猥鄙偏谬之谈,一概不录”,[28]从而大大强化了官报“卫道”与“正学”的舆论导向功能。而体例上,除沿袭邸报,大量登载上谕、衙署文牍之外,它还独树一帜地开辟了 “国粹”、“纠谬”等思想控制方面的内容,遂为各省官报所师法,成为官报对抗进步舆论的主要蓝本,故后人称《湖北官报》“流毒全国”。
然1905年后的中国,政情繁杂,舆论歧出,清政府想通过创办一纸官报来纳归众口、转移风气,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官报自身的种种“积习”注定了它在舆论竞争中无法令创办者们满意。在此情况下,地方官员不得不设法变通,采取“官商合办”的方式,扩大官办报纸的范围,通过收购民间报馆商股,以操纵民办报纸“立言”,间接达到“代表舆论”目的。
“官商合办之报”,武汉以《公论新报》为典型。自1906年10月创办始,该报“自尽半官报之义务”,诋诽革命,不遗余力。1907年初,清廷围剿萍浏醴起义,该报急起配合,连日刊载社评,大肆攻击革命党为“贼匪”、为“乱民”,为“孙汶遗孽”,[29]力主清廷立置重典,断绝根株。[30]同年7月,革命党人徐锡麟击刺安徽巡抚恩铭,它又刊文詈骂徐氏为 “乱臣贼子”。[31]继而,又毁谤革命的湖北学生为“济恶饰奸”之徒。[32]如此种种,代官报立言,无官报之名,有官报之实。
在经过了1905-1906年的革命怒潮,安然无恙的清王朝轻而易举地夺回了舆论的主动权。到了1907年,湖北报刊的声音可能由于革命学生的被迫退出,变得多少有些沉默。但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必将合乎逻辑地发展,革命者的“笔杆子”与“枪杆子”合力叩响新纪元的大门,只是等待着武汉“牵一而发动全身”的那一刻。届时,新派们又将发出各自的声音,这在1905-1907年的武汉各色新报中,已见端倪。
[1][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周积明,等.中国社会史论:下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革命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4]汉报.1907-01-03.
[5]汉报.1907-01-12.
[6]汉报.1907-01-04~06.
[7]汉报,1907-01-16~18.
[8]汉报.1907-02-06.
[9]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10][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1]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M].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12]秋虫.武汉新闻史[M].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13]洪煌.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4][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5]朱庭祺.留美学生界[N].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第1册.
[16]宋应离.中国期刊发展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1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8]刘揆一.黄兴传记[A].辛亥革命(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9][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0]警钟日报.1904-11-30.
[21]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22]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C].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
[23]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A].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24]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卷[M].上海:上海书店,1982.
[25]李长龄.上日知会同志稽勋局书[A].武昌首义: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专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6]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M].大成印刷公司,1912.
[27]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六册·公牍·咨札[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28]饬开办湖北官报札[N].湖北官报第一册,1905-04-05.
[29]论剿办萍匪乱事[N].公论新报,1907-01-02.
[30]论治匪之方针[N].公论新报,1907-01-07.
[31]论徐锡麟[N].公论新报,1907-08-05.
[32]愤言[N].公论新报,1907-09-22.
K252
A
1003-8477(2012)08-0105-06
梁方(1976—),女,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2010级历史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高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