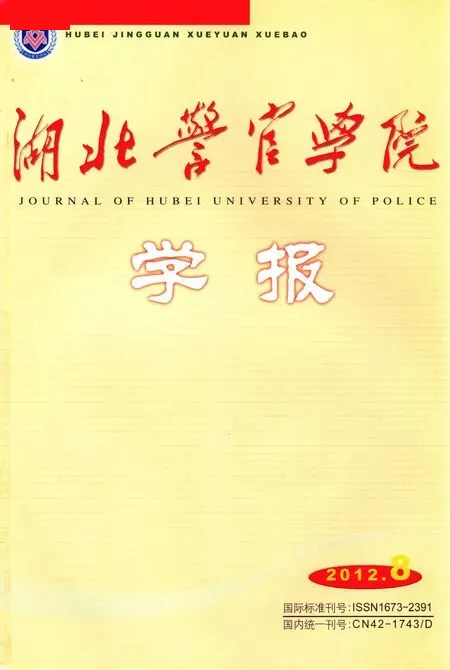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
2012-04-12甘尚钊
甘尚钊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
甘尚钊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401120)
关于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的学说主要有“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说与“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说,两种学说的明确性与划一性难以适应行政诉讼类型多样化的现实需要。确定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当根据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程序的实质特征加以确定。不同诉讼类型的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可能不同,相同诉讼类型又可能因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按诉讼类型的不同进行研究发现,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既可能是“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也可能是“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还有的在法律中有明确规定。
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诉讼类型;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
引言
行政判决既判力,亦称为行政判决的实质确定力,具体是指“判决发生形式确定力后,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于确定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且于其他诉讼中所为攻击或防御方法,不得为与确定判决内容相反之主张,而后诉法院于审理案件时,亦须以前诉既判事项为其判决之基础,不得为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之裁判。”[1]在内容上,它主要包括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客观范围与时间范围这三个方面。所谓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就是确定的终局判决及于哪些“人”;①笔者认为此处的“人”除包括作为行政诉讼当事人双方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与行政主体外,还包括居中裁判的人民法院。客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对哪些事项有拘束力;时间范围则是指确定的终局判决对哪一时间点上的事项产生效力。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行政判决既判力的主观范围与客观范围认识比较成熟、深刻,但对时间范围的认识则显得较为浅显。本文拟将讨论的“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亦即行政诉讼判决实质确定力中的时间范围,②各国各地区学者用词习惯有别。日本学者习惯用“时间范围”或“时间界限”;在我国台湾地区,有的学者喜欢用“时间范围”,有的则用“基准时”或“基准时点”;在我国大陆地区,学者以使用“时间范围”居多,偶有使用“基准时”或“基准时间”者。笔者认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点而不是一个时间段,使用“基准时点”的表述更加准确与贴切,因此文中统一使用“基准时点”一词。在德、日与我国台湾地区研究较早且成果颇丰,但始终没有形成定论。在我国大陆法学界,基准时点的专门研究长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由于基准时点的确定直接影响到行政判决的效力,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基准时点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的一般理论
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是指行政判决在哪一时间点上所确定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诉讼标的对后诉产生拘束力影响的问题。由于作为诉讼标的主要内容的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有可能随时发生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情况,因此,法院的审查与随后以审查为基础作出的判决只有固定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才具有实际意义,这一时间点即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某一行政判决既判力是基于对该基准时点上作为诉讼标的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而产生,对该基准时点前的权利义务关系未作确定,对其后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缺乏预见性,因此亦未作出确定。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翁岳生先生对此有精辟论断,“在裁判基准时点之后,为判决基础之事实及法律状态如有变更,该变更后之事实及法律状态,已非原确定判决中经裁判之事项,即为原确定判决实质确定力所不及。”[2]之所以认为在裁判基准时点之后新发生的事实与法律状态的变更不受到前诉判决的拘束,主要是由于在前诉中诉讼双方当事人“即便想主张但也无法主张”的事实,诉讼双方当事人均没有对判决基准时点之后新发生的事实及法律状态进行主张、辩论与质证,而作为居中裁判一方的法院也没有得到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机会。在当事人没有提出主张、法院没有进行审查的情况下,前诉法院审结判决当然对其不具有拘束力。
行政判决既判力理论深受民事判决既判力理论的影响。从德、日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立法实践与理论发展来看,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原则上确定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其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从口头辩论一体性的角度来看,辩论在其终结时点可以作一体性的判断;其次,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看,至口头辩论终结时点为止的所有事由应当是当事人能主张的事由。”[3]可见,在民事诉讼中判决基准时点的确定主要是从法院的判断可能性与当事人权利主张这两个角度进行考量确定的。亦即基准时点的确定首先必须满足法院对争议纠纷一体性认识及判断,此外还要保障当事人有充分表达主张的机会。综合二者的要求,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确定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那么,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为何,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此研究甚少。
二、我国大陆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的主流学说
在我国大陆地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理论研究中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总结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将其确定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与“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这两种。①除此两种外,还有“判决作出时”、“行政行为作成时”、“行政行为作成时为其一般原则,具体个案分析为例外”等不确定的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
“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说认为,“作为法院裁判的对象的法律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以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的权利义务状态作出的,判决所确定的就是该时点事实状态,因而既判力也只能以该时点为基准发生作用。”[4]另有学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在制度、原理与技术方面大多或部分与民事诉讼相通。民事诉讼中诉讼当事人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前可以根据诉讼的实际需要适时提出“攻击防御”策略,即遵循“证据适时提出主义”原则,而当事人“攻击防御”的结束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则体现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因此,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与民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相同,即同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5]
“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说认为,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当遵循“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②参见向忠诚: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效力范围[J],政法论丛,2008(1):23-27。持该学说的还有杨建顺教授。杨建顺教授认为,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的规定可以推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是“具体行政行为生效时”。在此,具体行政行为生效时实际上与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相同。详见杨建顺: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5):16-22。即行政行为的作出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材料作为其合法性的证据。“先取证、后裁决”原则与英美法系国家“案卷排他性规则”相似。“在行政法上确立了案卷排他性原则的国家,行政诉讼中也同样适用了这一原则,即法院不得接受行政诉讼被告补充的行政案卷以外的证据。”[6]换言之,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只能提交在行政行为作出时掌握的证据材料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法院在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也只能根据案卷的记载事项判断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证据充足、程序合法等。因此,认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是“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
三、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主流学说简评
第一,“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说深受民事诉讼理论影响,并最大程度上满足了法院对争议纠纷一体性判断与保障当事人的主张得到充分表达的可能。无论是从对法院裁判对象的不稳定性考察作为切入点并与诉讼双方当事人提出诉讼资料的时间要求相结合,还是从我国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这样一个法历史的考察,其对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的论证路径其实都遵循着同一个原则——“将当事人试图提出并且能够提出诉讼资料的最大限度的时间点作为既判力的基准时点较为妥当”。[3]
第二,“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说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的证明力要求,实际亦遵循了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确定规则。“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说的确定主要是根据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时对所采纳的证据标准进行确定的。行政主体主张被诉行政行为合法而提供的证据只能是在行政程序中收集并登记在案的证据。根据“先取证、后裁决”的行政原理,支持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全部证据在其作出时便应全部确定。尽管像民事诉讼一样,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也专门设有言词辩论环节,但人民法院只能根据行政主体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登记在案的案卷证据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换言之,行政法治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进行法的第一次适用时必须收集掌握了充分、确实的证据,③笔者认为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国家机关进行的法的第一次适用,行政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的审查判断是国家机关进行的法的第二次适用,而民事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进行的则是法的第一次适用。同时也已给予相对人充分申辩的机会。因此,在行政行为生效时,双方的证据资料等信息交流途径关闭,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审理也只能依据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形成的案卷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说遵循了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确定规则。
第三,上述两种学说尽管都依循民事诉讼关于确定其基准时点的理论,但其明确而划一的规定不免有些局限性。换言之,不管以“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还是以“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作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都有其合理性,但具体的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的确定则还需进行具体分析。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审理对象不同,行政诉讼的审理对象——具体行政行为极具复杂性,能否一律标准化地将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确定在某个具体时点上,还有待深入研究。此外,由于行政诉讼是当事人请求国家机关进行法的第二次适用,面对行政程序中行政主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的第一次适用,司法机关该扮演何种角色?即如何妥当地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也是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应当考量的因素。
我国台湾地区通说认为,行政裁判既判力基准时点的确定,“因受诉讼种类、实体法规定、当事人声明以及诉讼性质之影响,可能因个案而有所不同”。[2]在台湾地区旧“行政诉讼法”时代,“由于形式上仅有一种诉讼类型——撤销诉讼,实务上对于行政处分是否违法之判断基准时点,原则上采‘行为时说’”。[2]但由于“‘现行法’①指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之诉讼种类增加,对于各种诉讼种类之裁判基准时点,宜分类作较明确之原则性规范,以免因观察时点之不同,而对个案裁判结果产生争议”。[2]依此见解,确定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当考量当事人声明、诉讼种类与实体法规定等因素。同时,通过对台湾新旧“行政诉讼法”的比照可知,诉讼种类对确定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有着重要意义。因此,笔者认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既可能是“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也可能是“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具体为何,则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导向,对不同的诉讼类型分别研究。
四、各行政诉讼类型的基准时点
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未对行政诉讼的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57、58条中规定了行政判决的六种主体判决和一种辅助判决。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了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规定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第57条规定了确认判决,第58条规定了情况判决。根据这七种判决类型并结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规定可知,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变更诉讼、履行诉讼与赔偿诉讼。[7]
(一)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是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效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形式。设置撤销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溯及既往地消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使相对人的权利得到回复。在撤销诉讼中,人民法院审查的对象是原告认为侵害其权益的“违法行政行为”,亦即审查行政主体是否依法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因此,人民法院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只能以行政机关作出该行政行为时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作为判断基础,即遵循“先取证、后裁决”原则。由此可知,撤销诉讼以“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为基准时点。
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如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例如在“吉林省梅河口市木材公司不服镇江市多种经营管理局林业行政处罚及扣押决定案”[8]中,人民法院依据林业部《木材运输检查监督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5条解除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办法》第5条规定:“无木材运输证件运输木材的,责令货主限期补办木材运输证件”,只有在逾期不补办又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可以“没收所运输的全部木材,并可处以相当于没收木材价款10—30%的罚款。”在审查此案时,应以《办法》的特别规定进行审查。而根据《办法》第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以“限期补正期满时”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故不能径直以“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作为基准时点,这属法律特别规定的特殊现象。另外,我国台湾地区还认为,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持续性或者尚未执行的,则应以“言词辩论终结时”作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9]笔者认为,持续性的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可能在人民法院受理审判时还在发生作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因此,笔者认同这种观点,这样可以更有效地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同时也符合程序经济的要求。
(二)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处于争议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无效或者相关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诉讼形式。在确认诉讼中,人民法院仅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争议状态进行确认,其所作的确认判决不具创设、变更或撤销的法律效果。确认诉讼的设置目的不是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增设新的权利义务,而是再一次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确定或证明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正确与否。
根据原告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不同,可将确认诉讼分为三种:一是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二是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三是确认行政法律关系成立与否。对于前两种情形,基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不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改变。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两类确认诉讼时,只能根据行政行为生效时诉讼双方当事人所掌握并提交给法院的全部证据材料进行认定。所以这两种情形的行政判决既判力基准时点是“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而对于第三种情形,由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成立有基于法律直接规定的,也有因行政行为而发生的,所以,当有法律直接规定时依法律规定,因行政行为而发生的则以“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为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
(三)变更诉讼
变更诉讼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变更的诉讼形式。在我国现阶段,提起变更诉讼只适用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一般来说,显失公正包括“行政处罚畸轻畸重,过罚失当;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行政处罚遗漏了重要因素;行政处罚反复无常等”。[10]行政处罚在内容上多数存在量的伸展和收缩性,即行政机关在该领域享有一定的行政裁量权。
原告提起变更诉讼暗藏着一个前提条件,即承认被诉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之所以起诉,则是由于对行政处罚的合理性不服。有学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变更诉讼中实际上扮演着双面角色,即在履行司法审查职能的同时也在履行行政执法职能。该学者认为,在变更诉讼中人民法院“不但要审查行政处罚是否合法合理,而且要在肯定行政处罚合法但不合理的前提下行使司法变更权;在肯定现有的行政处罚法律关系成立前提下,增加或者减少其实体内容从而形成新的行政法律关系。这个特点反映在证据方面就是人民法院必须采纳新的证据,适用新的证明标准,以新的判断取代被告行政机关的判断。”[11]即在变更诉讼中,人民法院在审查确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对原告提出其存在合理性问题作出回应。行政法治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必须遵循“先取证、后裁决”原则,因此,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所采纳的“新的证据”也只能是行政主体或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已经登记在案的证据。换言之,人民法院不能根据案卷外的其他证据来裁判被诉行政行为是否显失公正。所以,在行政变更诉讼中,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当认定在“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但也存在例外情形。在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未给予相对人充分的听证申辩等程序性权利时,在行政诉讼程序中,人民法院可以采纳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应当提交而未获行政主体允许提交的证据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显失公正的问题。此时的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是“言词辩论终结时”。
(四)履行诉讼
履行诉讼是相对人向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申请作出某一行政行为,被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致使其权利受到损害,因此相对人欲借助人民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作出相对人依法请求的行政行为。相对人提起履行诉讼的目的是希望借助人民法院的判决命令行政主体作出其在行政程序中依法向行政主体请求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诉讼类型主要适用于申请许可证和执照、申请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申请发放抚恤金等领域。履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行政不作为,而根据行政不作为的性质可以将其区分为“不纯粹的不作为”与“纯粹的不作为”。我们将对这两种不同的不作为不服而提起诉讼的判决基准时点分别进行分析。
1.对“不纯粹的不作为”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履行诉讼
“不纯粹的不作为”行政行为指行政机关明确拒绝行政相对人所提出申请请求的行政行为,通常发生在依申请的行政行为领域,是行政主体认为行政相对人不符法定条件而作出的行为。对“不纯粹的不作为”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履行诉讼,人民法院必然会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当然原告也需证明其在法定期间内向被告提出过申请等。由于被告作出拒绝行为必然有其法定理由,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提交的在拒绝时掌握的证据进行审查。由于被告只能根据当时所掌握的资料作出判断,对于后来发现或发生的事实缺乏预见性,所以人民法院只能对被告作出拒绝行为时的事实进行审查。也就是说,对于拒绝行为后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行政机关所不能预知的。因此,在该类诉讼中,应当以“被诉行政行为生效时”作为基准时点。
2.对“纯粹的不作为”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履行诉讼
“纯粹的不作为”行政行为通常发生在依职权的行政行为领域,是行政主体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权。由于行政机关消极行使甚至不行使自己的法定职权而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而人民法院在审查此类诉讼时,应当根据行政诉讼程序中诉讼当事人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查。因此,对“纯粹的不作为”行政行为不服提起履行诉讼的基准时点应确定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
(五)赔偿诉讼
赔偿诉讼无论是单独提起抑或在因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其诉讼标的均为民事法律关系,是给付诉讼的一种类型。[12]在民事诉讼中,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因此,给付诉讼的基准时点也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行政赔偿之诉实质上要解决的是原被告双方基于行政管理关系而产生的民事上的权利义务的分配,是对于受侵害一方利益进行补救的制度装置,所以,从技术性层面其更应当按照民事诉讼的思路来整合和规范。”[12]由于行政赔偿诉讼的诉讼标的是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其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状态,任何一方的行为都可能改变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状态,因此,只有在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人民法院才能作出一体性判断,当事人也才能充分提出主张。所以,这种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应当与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相同,即同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
五、结语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应当把握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这一理念在行政判决中则充分体现在基准时点上。不同诉讼类型的行政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点可能不同,相同的诉讼类型又可能因被诉行政行为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
[1]刘宗德,赖恒盈.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制度、立法与案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346,355.
[2]翁岳生.行政法(下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1476,144 9,1499,1500.
[3][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88-489,102.
[4]刘青峰.司法判决效力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23-124.
[5]王作洲.既判力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72-74.
[6]丁晓华.案卷排他性原则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障碍分析[J].法律适用,2007(6):71-73.
[7]江必新,梁凤云.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88.
[8]宋随军,梁凤云.行政诉讼证据实证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99.
[9]陈淑芳.撤销诉讼之裁判基准时点[J].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7(90):54-78.
[10]马怀德.行政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21.
[11]高家伟.行政诉讼证据的审查判断[J].行政法学研究,1997(4):26-32.
[12]章浩.行政赔偿诉讼标的再认识——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的再论证[J].行政法学研究,2004(4):105-110.
D915.4
A
1673―2391(2012)08―0091―04
2012—03—26
甘尚钊,男,广西桂平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责任编校:江 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