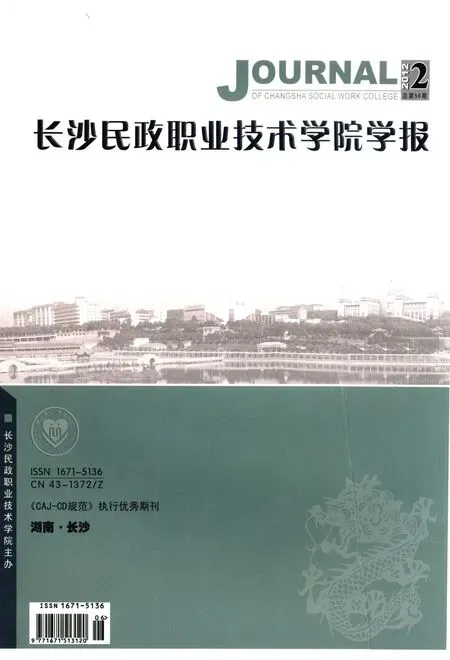我国新旧卷证移送方式下的法庭调查比较
2012-04-02曾中平唐治祥
曾中平 唐治祥
(1.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04;2.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我国新旧卷证移送方式下的法庭调查比较
曾中平1唐治祥2
(1.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04;2.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在我国传统全案卷证移送方式下,法庭调查的范围和顺序由法官在庭前审查阶段确定,对人证的询问或讯问、对物证的出示以及对证据文书的宣读等法庭调查活动,也几乎完全由法官包揽。在我国现行有限卷证移送方式下,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范围确定问题上的发言权增大,举证、质证等职责转由控辩各方承担,言词证据的调查以控辩各方询问为主、以审判人员询问为辅。
全案卷证移送主义;有限卷证移送主义;法庭调查
在我国1997年之前的全案卷证移送方式下,几乎所有的案卷和证据材料均由法官掌管,不但证据调查的范围和顺序由法官决定,而且对证人和鉴定人的询问、对物证的出示以及对证据文书的宣读等法庭调查活动,也几乎完全由法官负责。鉴于传统全案卷证移送方式下的整个庭审调查活动几乎由法官包揽的作法存在着控审职能混淆、不利于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等诸多弊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在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所移送的卷证材料进行限制的同时,还从证据调查范围的确定、证据调查职能的分工、言词证据调查的方式等角度对法官的主导作用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弱,进而使得控辩双方对庭审活动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下面拟以我国新旧《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为根据对我国新旧卷证移送方式下的法庭调查状况进行比较考查,进而表明现行有限卷证移送方式对我国刑事诉讼特别是法庭调查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证据调查范围的确定
在我国1997年之前的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的范围由庭审法官尤其是审判长在庭前审查过程中以及开庭审判前的准备阶段根据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所移送的以及自行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材料确定,控辩双方尤其是辩方几乎无法施加任何有效的影响。对于如何确定法庭调查的范围的问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由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不再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移送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只需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即可,因此,审判人员在证据调查范围问题上再也无法独自作出决断。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后文简称《解释》)的规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通常由控辩审三方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其一,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六机关”①《规定》第35—37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②第282条的规定移送的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可以使法官在庭前审查过程中通过审阅这些卷证材料初步确定需要法庭调查的控方证据范围。
其二,根据《解释》第119条第4项的规定,被告人、辩护人可以在开庭5日前向决定开庭审判的法院提供“出庭作证的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受理案件的法院由此可以初步确定需要法庭调查的辩方证据范围。
其三,根据《解释》第120条的规定,法官在开庭审判前拟定法庭审理提纲的过程中,应当把“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部分的重点和认定案件性质方面的要点”、“讯问被告人时需了解的案情要点”、“控辩双方拟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名单”以及“控辩双方拟当庭宣读、出示的证人书面证言、物证和其他证据的目录”等内容纳入其中,控辩双方证据调查的范围因此基本上定型。
其四,鉴于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可能提出超出法官事先确定的证据调查范围的证据材料,《解释》第139条不但赋予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或要求向法庭出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的控辩双方“向审判长说明拟证明的事实”的义务,还赋予审判长是否准许传唤证人或出示证据的权力:审判长同意的,即传唤证人或者由请求方出示证据;审判长如果认为与案件无关或者明显重复、不必要的证据,可以不予准许。
其五,根据《解释》第155条的规定,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公诉人可以提出出示开庭前送交法院的证据目录以外的证据的请求,无论辩方是否对此提出异议,审判长只要认为该证据的出示确有必要,就可以准许出示,在辩方提出要作必要准备的请求时,可以宣布休庭并为辩方确定必要的准备时间。
其六,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9条和《解释》第156条的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但应当“提供证人的姓名、证据的存放地点”、“说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要求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理由”,然后由审判人员根据是否“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等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总之,在我国1997年之后的刑事诉讼中,虽然确定法庭调查范围的权力仍然主要由法官享有,但因受有限卷证移送方式的影响,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范围确定问题上的发言权增大,不但可以通过各自移送卷证材料的方式对法官庭前确定的证据调查范围施加影响,还可以在庭审过程中通过请求合议庭将某一证据材料纳入调查范围的方式使法官对庭前确定的证据调查范围进行修改或调整。
二、证据调查职能的分工
在我国现行有限卷证移送方式下,法官因手中仅有“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而再也无法包揽法庭调查活动,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职责转由控辩双方承担,控辩职能因此大大增强。由于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均掌握在作为控方的检察机关手中,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相差过分悬殊,为了确保控辩双方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相对平衡,使法庭审判更加公正、合理,我国现行刑事审判方式并没有走向彻底的当事人主义,法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成为“无所事事”的裁判者,而是仍然享有讯问、询问甚至直接采取调查取证措施等职权。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5—159条以及《解释》第130—159条的规定,控辩审三方在法庭调查阶段的职能分工变化主要体现在被告人陈述、讯问被告人或向被告人发问、询问证人和鉴定人以及出示物证和宣读证据文书等方面。
首先是被告人陈述。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的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是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的第一道必经程序。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5条在保留这一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的规定。《解释》第130条和第132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如果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先由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宣读附带民事诉状,然后再分别由被告人、被害人就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法庭调查之初就可以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的作法具有多重诉讼价值:一是被告人可以借此机会向法庭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诉讼主张,进而使法庭了解对自己有利的案件情况;二是可以大大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再完全是消极接受法庭审判的客体;三是可以使被告人从法庭调查一开始就与控方展开对抗,进而增强庭审的对抗性。
其次是对被告人的讯问和发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5条虽然保留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4条将审讯被告人置于询问证人、鉴定人之前的程序步骤,但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的先由审判长审问被告人、再由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最后由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辩护人分别向被告人发问的顺序不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5条以及《解释》第133条和137条对讯问被告人或向被告人发问的顺序作了先由公诉人讯问、再由其他各方相继发问、审判人员必要时作补充性讯问的规定:①“在审判长主持下,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讯问被告人”;②“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就公诉人讯问的情况进行补充性发问”;③“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准许,可以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事实向被告人发问”;④“经审判长准许,被告人的辩护人及法定代理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以在控诉一方就某一具体问题讯问完毕后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讯问被告人。以上讯问被告人或向被告人发问的顺序不但有利于充分调动控辩双方的积极性、保障被害人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可以减轻审判人员的负担,使其在听取控辩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向被告人发问。
再次是对证人和鉴定人的询问。在1997年之前的刑事诉讼中,对于证人和鉴定人的询问,首先并且主要由审判人员进行,之后由公诉人补充询问,最后由被告人等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申请审判人员发问或经审判人员许可直接发问。鉴于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的庭前审查模式和有限卷证移送方式下,审判人员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可以在控辩各方询问证人和鉴定人之前卓有成效地展开询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6条对传统询问证人和鉴定人的顺序作了重大改变:在审判人员告知拟作证的证人要如实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之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6条把询问证人和鉴定人的主导权赋予控辩各方的作法有利于审判人员保持中立、充分调动控辩各方的积极性,此外,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6条所作的“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这一规定可以确保审判人员在听取控辩各方的发问和证人、鉴定人的回答之后有针对性地向证人、鉴定人提问,进而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最后是物证的出示以及书证等证据文书的宣读。根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16条的规定,无论是对物证的出示还是对未到庭的证人先前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的宣读,均由审判人员进行。为了解决传统由审判人员出示物证、宣读证据文书的方法所带来的控审不分等弊端,同时鉴于在有限卷证移送方式下,控方的物证、书证等证据文书均不再由审判人员掌握,审判人员无法像在1997年之前的刑事诉讼中那样可以主宰法庭审判的过程,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7条将出示物证、宣读书面证据材料的职权由审判人员转交给控辩双方:①“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②“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解释》第150条在此基础上对物证、书证等证据文书的调查程序作了如下明确规定:①“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②“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
三、言词证据调查的方式
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于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言词证据的调查,当今世界各国一般都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但由于卷证移送方式不同,对证人等的询问方式在各国存在较大差异:在英美“起诉状一本主义”移送模式下,因受“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影响,对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调查主要由控辩双方以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即首先由要求证人出庭的一方进行“主询问”,然后由对方进行“反询问”,此后控辩双方还可以分别再次进行“主询问”和“反询问”;在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因受“全案卷证移送主义”的影响,对证人的询问首先并且主要由主审法官按照事先准备的问题进行,控辩双方在征得主审法官同意后可以补充发问;日本和意大利在转向混合式诉讼模式之后,因受各自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和“有限卷证移送主义”的影响,均抛弃了传统以法官为主导的询问方式,改采以控辩双方“交叉询问”为主、法官补充询问为辅的人证调查方式③。
关于对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等人证的询问方式,与日本、意大利一样,因受新旧卷证移送方式的影响,我国也经历了由以法官为主导向以控辩双方为主导的演变过程:在我国1997年之前的刑事诉讼中,与“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和1988年之前的意大利一样,因受全案卷证移送方式的影响,也是首先并且主要由审判人员进行询问,之后再由控辩双方补充询问;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考虑到法官庭前所能接触的卷证材料范围极为有限、法官再也无法主导法庭调查活动等因素,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6条对控辩审三方在言词证据调查过程中的作用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明确规定为以控辩各方询问为主、以审判长询问为辅。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等人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以控辩各方为主导进行询问,但对于应由何方首先询问的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为了确保对证人等人证的询问有条不紊地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在借鉴英美法系“交叉询问”规则以及日本和意大利人证调查方式的基础上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询问的顺序和规则等作了补充性规定,进而初步确立了“交叉询问”的框架④。
关于对证人等人证的询问顺序,《解释》第138条、第140条、第143条、第145条和第148条作了如下规定:①对于由公诉人提请审判长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以及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先由公诉人发问,再由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补充发问,然后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问;②对于由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请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先由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问,再由公诉人补充发问,然后由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问;③对于由辩方提请审判长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应当先由辩方发问,再由公诉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问;④以上无论是何方提请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审判人员认为有必要时都可以提问。
关于询问规则,根据《解释》第146条的规定,控辩各方对证人和鉴定人等的询问或者发问,应当遵循相关性、禁止诱导性询问、保护证人等规则,即“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的事实相关”、“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不得威胁证人”、“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为了确保以上询问规则有效实施,对于内容与案件无关或者方式不当的询问或发问,《解释》第147条不但为控辩双方确立了异议这一救济途径,还赋予了审判长主动进行纠正、制止的权力:①“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②“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
[注 释]
① 本文中的“六机关”《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等“六机关”在1998年1月19日联合出台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简称。
② 该《规则》于1998年12月16日获得通过。
③ 陈瑞华.理想与现实—从实证的角度看中国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A].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治的理念建构》[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96.
④ 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J].中国法学,2000,(4):86.
D925.113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标识码] A
A
1671-5136(2012)02-0041-04
2012-04-25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刑事卷证移送制度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820068)的研究成果之一。
曾中平(1968-),男,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等;唐治祥(1969-),男,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证据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