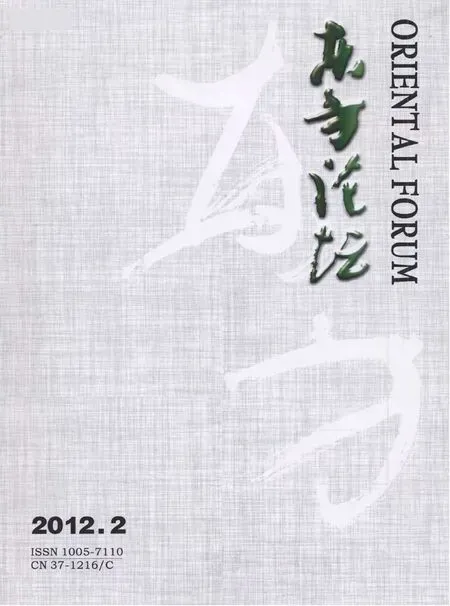孟子性善论的缘起、论证及其意义
2012-04-01
孟子性善论的缘起、论证及其意义
申 鹏 宇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人性善思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从先秦人性论的发展,到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是一个发展过程,孟子性善论的提出是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殷周之际人文精神的反省,孔子仁的学说,中庸的天命之谓性都包含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并对性善做了种种深入的论证。他通过人禽之辨,与告子的仁义之辨等深入论证了人性善观点。人性善思想的提出后成为了中国文化人性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文化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性善论;人禽之辨;仁义之辨;中国文化
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道德的情境中,并以善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人性善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中国文化的脊髓中。那么这种性善的观念是如何确立的呢?仅仅是孟子偶然提出的吗?本文试图将孟子的性善论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梳理其脉络,追溯其源头及发展过程,同时着重论述孟子对性善论的论证及其历史意义。
一、性善论的提出
性善论的提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紧紧围绕着天命与道德的关系展开,首先是殷周之际道德的重要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凸显出来;其次是孔子为代表的仁道思想,让道德从政治层面走向了个人的修身,道德进一步深化;再次是《中庸》将人性与天道直接相联系,为人性解决了来源问题。这个过程蕴含着儒家用道德转化不可知的天命并为道德寻找最终的源泉的努力。
(一)殷周之际的人文精神跃动
在殷周之际这个大变革时代出现了一种人文精神跃动,在精神的反省中,道德的重要性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更开启了一种从蒙昧向道德、文明前进的大方向,这体现在从天命不易、祈祷祖宗保佑到天命靡常、修德以俟天命的转移。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周代殷之后, “殷人尚鬼”但政权却转移成为周人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周人渐渐有了天命靡常、修德俟命的看法。《尚书·洪范》正是武王向箕子问治国之道的方法,箕子为其陈洪范九畴。洪范九畴中的“五事”、“八政”、“皇极”、“三德”等制度方面的建设中蕴含了很多道德的成分,修德成为统治者保有天命的重要手段,其他篇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如“克明德慎罚”(《尚书·康诰》)“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等,这些说法总括起来是“惟命不于常,……明乃服命”(《尚书·康诰》)。这一转变使神权所代表的威权转变为人间的道德理想规范。强调的不再只是神秘之天的主宰性,更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有了“天命之降于人,后于修其德”[1](P326)的看法。重视道德体现在制度的施设上,从《周礼·周官》中看出周公制礼作乐,经邦建国,其政典、治典、教典、祀典都蕴含着很大的道德成分。
(二) 孔子的仁道思想
孔子作为儒家的始祖,他的仁道思想在性善论提出过程中是重要的一环。孔子的道德学说使道德从政治层面走向个人修身,并以仁为基础扎根在人心中。
春秋之际,社会纷乱,民不聊生,德治开始没落。孔子正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天命的塌落已不可避免,中国文化中的宗教精神没落,开始被收摄到人文精神中。孔子作为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他致力于恢复周公之道。在继承的基础上,向前推动道德向内转化,开出广被人间在生活之道。孔子经过仁的学说把人的生命从生理的限制中超拔出来,使抽象的德性向人的生命中凝结,而成为可以把握的有血有肉在的存在。人的行为规范均从自身中求,即是“为仁由已。”
孔子面对天命下坠,但同时要执守道德的情况下,必须处理好天命与人自身道德的关系。依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解析,孔子之天命思想实乃根于义命合一之旨。“唯是孔子先认定义之所在,为人之所当以自命,而天命斯在。……行道是义,天使得我得其行道是命。此回是命义合一……然当无义以行道时,则承受此道之废,而知之畏之,仍要义也。”[1](P332)人在依自己仁义精神奋发不已的同时,感到天命之流行,一种敬畏之感产生。由此来敬畏天命,可见孔子在处理命与人的道德上,是由站在道德的角度上审视天命。在处理鬼神的问题时,孔子以义来代替一般人对鬼神的依赖,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对待祭祀已不在求一种神秘性力量降临,而是重一种报本返始,崇德报功在意义。殷周时天命不可知不可测,在孔子这里则在道德上知晓天命,努力用道德来转化不可知的天命,使天命从人格神向道德法则性的天命转化,这直接为后世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打下基础。
(三)《中庸》的天命之谓性
尽管孔子努力用道德来转化不可知的天命,但是要想说性善还需要解决性的来源问题,要找到人性的终极源泉必须推到天那里,这就需要在性与天命间建立直接联系。
今有典籍可查,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有子思的《中庸》一篇存。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直接在道德上建立人与天的关系,解决了道德的来源问题。由天命到人性,在中国人性论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从中也可看出孔子以后天命下落为人性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说其是一个里程碑,是因为《中庸》为孔子之后,性与天道解释提供了一种模式。《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是天命下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即由天所命,人性的最终源泉是天。因为天命无所不在,因此它具有普遍性,人受命的个体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天命的普遍性与个体的特殊性相结合,使个体的“性”具有了普遍存在的意义。天命之谓性,不但解答了人性的来源问题,同时赋予其形上的超越的根据。《中庸》中关于性的阐述正是孔子思想进一步发展。既解决了性的来源问题,又给予其普遍性,是人人所同的。性来自天命,自然是善的。
从上面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从人修德以俟天命的《尚书》,到孔子用仁转化天命,再到《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从人格神的天命到法则性的天命,由法则性的天命向人身上凝集而为人之性;由人之性而落实于人之心,由人心之善,以言性善: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经过长期曲折、发展,所得出的总结论。”[2](P141)
二、性善论的论证
性善之说的提出,既是先秦儒家论性路线的必然发展,也是时代的需要。孔子之后,论性并非只有性善这种学说,王充在《论衡·本性篇》说:“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性书》一篇。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性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有善有恶。”可见性可善可恶在春秋战国之际十分流行,孟子面对这种情况标性善之旨,可算是重新匡正儒家发展的路向。战国作为一个衰乱之世,道德价值倒塌,时代精神堕落,文化理想黯然不彰。可重新树立道德价值标准,孟子的时代使命非常明确。他高举仁义,标以性善,虽有帝王嫌其迂阔,但孟子真正树立的是为百世立法的道德心性,挺立的是一种道德生命。先秦儒学由孔子的仁开端到孟子的性善论,才完成了儒学的内圣之学基本形态。
孟子对性善论的论证在《孟子》一书中很多地方都有提到,本文主要从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论述,首先是孟子的人禽之辨,其次是与告子关于性的论辩。
(一)人禽之辨
孟子为点出人性的独特之处,在人与动物之间划出一界限。只有找出这细微的差别之处,才找到人性不同于动物性所在。孟子认为人性所有,而动物所无的这“几希”之处才是人之真性所在。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孟子以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并不在饮食生理上,而是在十分微妙的地方。这“几希”之处就是仁义。人要在这“几希”之处来认识真正的人性所在。再把它存养扩充,成就人之为人的真正所在。孟子这样论人性是以道德性为人性。这与告子之辩中同样提到过。“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何谓生之谓性,这即是董仲舒所讲的“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如此说性即是从人的生命所来的自然禀赋、生理来言说性,告子、荀子、董仲舒言性均有这个特点,在宋儒讲来亦可说是以气言性。以自然生理言性的一个问题是性没有绝对性,是可受自然环境在影响改变的。例如,荀子虽说性恶,但强调后天教化可以化此性恶。以仁义言性则不同,以仁义言性,这性是超越的,有永恒价值。是根植于人心内部不可改变的,所以孟子讲人之恶时,只是说放逸了本心,陷溺了人心,而人心则本是好的。
(二)与告子之辩
孟子以仁义为性,同时代要面对其他学者的论争,告子便是其中的一位。孟子的许多观点都是在和告子的论争中体现的。孟子与告子的争论主要见于《孟子·告子上》这篇中。孟子与告子争论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性善及性无善恶,二是义内义外问题。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讲的。
1、性善与性无善恶。告子的人性论以生之谓性为起点,他把人性比喻为“杞柳”,把义比喻为“杯棬”,意思是性可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可为善也可为恶。告子重视人之自然性,比喻为“杞柳”,本无价值内涵,仁义道德有待于后天的斧凿,如同将杞柳制成杯棬。在告子思想中人性与仁义之间的关系关非内在具足,一定要由后天来完成。客观的说,告子并未给人性以价值,而孟子则赋予了其人性善的价值。“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袂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赵岐章句》注此句为“告子以喻人性若水也。善恶随物而化,无本善本不善之性也。”[3](P218)伊藤仁斋注此句为“告子言性本无善无不善,其有善恶皆出于习,而非性之本体。”[3](219)可见告子这里性是中性的,没有必然的善恶之分。孟子则认为“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把握人性上,总是在经验上再进一步,要抽离掉经验上东西,直接把握本质,他认为水的方向是与地势相联系,抽调这些,水是向下,正如人性是向善的。焦循注此句为:“且水之东西,无分优劣,而人之善不善,则判若天渊。”[3](P220)从孟子的角度水向东向西流是不分优劣的,人的善于不善则是判若天渊的,所以用水分东西来比人性并不恰当,这是孟子必须澄清的。
2、仁义内在与仁内义外。孟子认为仁义内在,而告子则认为仁内义外,实际上这是关于前面人性论论争的具体化。若仁义内在,则即是赋予了性以善的价值,所以仁义是否内在是论性问题上进一步的延伸。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告子以生之谓性,即指食色一类的自然之性。说义外是把价值判断标准放在了外面,以为义是外在客体决定的。是“彼白而我白之”。但孟子突然转到“不识长子之长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由动物之长到人之长,这已经加入了道德性,即是对于动物的年长还是认识问题,到人之长已成为道德问题。当我们认识到“长马”并无敬意,当人认识到“长人”则内心产生了敬意。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由认识问题引到了道德问题,而且从内心自然生长敬意,即是义出于内。从知识到道德,是从实然到应然的一种转变,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主张仁义内在并不是否定与客观事实的相应性。实然与应然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是道德问题。顺告子之说,一方面是以客观之事实为依据,得出恰当行为,这与道德无涉。另一方面是认识客观对象后升起了道德行为,如认识到人的年长而生出敬义,所以义全在客观对象的存在上,即是由认识产生道德。但把道德全放在客观对象上会招致这样的批评,如王阳明说如果孝之理全在父上,父没难道孝之理不存。顺孟子之义讲,道德上的行为一定由本心自发的,由内心仁义发出,再关联到事物实然得出恰当行为。孟子讲性善而未忽略环境,同时讲义为内时,关注到具体的环境,把客观对象统摄到德性心的要求之下实现道德的活动。孟子很好的处理了实然与应然的问题,而告子在这个问题上则混淆了二者。而且顺着告子的讲法会出现很多弊端,告子将仁义比作杯棬,并非对仁义持否定立场,而是强调后天塑造的重要。告子以食色之性为本根而追求仁义,必先识仁义,同时强调认识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已开荀子先河。凡是不以性为善者,必重外在教化作用,告子正是以仁义为教,而不为性。“靠外在的强制之力以为仁义,则只有人类自由意志作为牺牲。其结果。其结果:一是为了保持自由而不谈仁义,……另一则牺牲自由而戕贼人以为仁义。”[2](P171)前者是很多道家的态度,后者如秦始皇、法西斯。同时讲义外容易导向功利主义,墨家思想正是这样。
三、性善论的意义
自从孟子性善论提出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后来有说性恶的荀子,性有善有恶的董仲舒,善恶混的扬雄,性三品的王充,然而这些都未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以性善论为支撑的中国文化,影响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孟子性善论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孟子看人不再是从外在环境上看人,而是从道德上看人
这是看待人的一个极大转变。孟子从道德上来看一个人的存在,把应然的道德性看成是一个人的本性,而非饮食之欲望,孟子这样讲,让我们看人都从自觉向上,愤悱不已的心情上看,人生最终的目的是成为一个德性的人。人通过修德,不断的善化自己,先天的遗传,后天的环境,都不能对人真正的决定。从善的角度看人,一方面要自己改过迁善,强调自身的修养,另一方面彼此信任,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同时从精神的角度看人,可以淡化物质的牵绊。不管富与贵,能做到贫贱不移,富贵不淫,而这正是以人的善性做基础的。这种对人德性的要求,减弱了功利主义的倾向。中国读书人在修孔孟之道,脊梁开始挺立起来,不为五斗米折腰,用精神来弥补物质的不足,这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灵上。
(二)孟子点出善性为人所固有,是内在人心的
孟子点出人是德性的存在,接下来必须点明这个善性是为所固有的,因为从外在求来的,不足以保证其是必然的人性。孟子这样讲,解决就是人成德的动力所在。道德实践是人人可能的,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的能力不够,这是一个人的义务所在。他讲仁义内在,则把一切价值之根,道德之源安放在人心。一切道德行为的发出是由内具的仁义驱动,是自主自发而非强制的,行仁义本身,不必再问理由。有了内在价值之源,则顺性之要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有本有源,发之向外而沛然莫之能御。孟子指出人性本善,那么恶在孟子这里就没有了必然性。恶只是因为一些气质的掺杂产生的,如同浮云遮住太阳,终要散去,而善则是这太阳,即是光明的德性。
(三)孟子讲性善论引发出的是自律道德,而非他律道德
孟子把仁义定为人性,赋予了其价值,则一切道德之事均是自作主宰而非强制,即自律而非他律。孟子在两千年前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人要“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在道德的行为上,个体应该凭借自己的良知来判断是非,而非一些外在的教条。而且当外在的教条与内心发生冲突时,人应该遵从自己的本心而行,这样方成为一个自作主宰的人。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可见当时人有把耳目之欲称为性的说法。孟子认为这是求在外,得之于命的,主动权不在自己的身上,宁谓之命,不谓之性。当人们把仁义礼智称为天命时,孟子认为这性“求则得之”,“求在我者也”,可为吾人真实把握,孟子宁谓之性不谓之命。
(四)在德性上贯通天道与人道,内圣与外王
孟子讲人性善的时候,纵向是尽心知性而知天,横向是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从纵向上来看,人的成德不只是有限的人间之事,同时也是无限的天理之事,而天理的无限意义又在人的当下尽心活动中彰显,即内在而超越,超越而内在,这一点使儒家学说具有了宗教的作用。从横向上看,人要成己成物,内圣外王。孟子以成己来统摄成物,内圣来统摄外王。把生活中的事情都纳入的德性之中,赋予了人日常生活的价值,同时对于背离德性单纯的霸道行为予以批判。孟子认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有人民来决定,政治都在德性范围之中。
由此可见,性善论提出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孟子提出性善并非突兀,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尚书》、《论语》、《中庸》中,隐隐含着一条性善的线索,把这条线索梳理清楚,可以见到孟子人性善是儒家义理发展的必然。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后,对性善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为中国文化建立了一个基石。他的性善论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脊髓,让中国人以善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参天地化育,追求天人合一。在中国人生活的情境中,到处都透露着“善”的气息,这体现着性善论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5.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3]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一)[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责任编辑:郭泮溪
Mencius’ Theory of Human Good Nature: Origin, Argumentation and Signif i cance
SHEN Peng-yu
(Philosophy Depart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Mencius is the pre-Qin Confuci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and his theory of human good nature has had great influence over China.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we fi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s inevitable.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humanistic spirit introspection, Confucius’ theory and the Heaven-endowed Nature of the golden mean were indispensable elements. Mencius clearly explained the theory of human good nature. Since then, the theory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thought in China and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ver Chinese culture.
Mencius;theory of human good nature; culture
B22
A
1005-7110(2012)02-0104-05
2012-02-12
申鹏宇(1984-),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