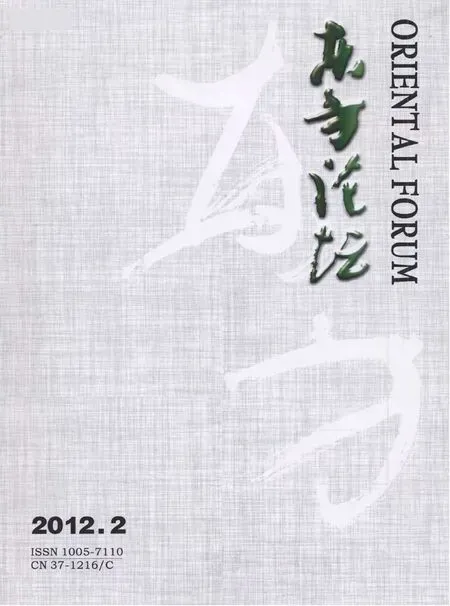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
——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评介
2012-04-01
《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
——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评介
尹 锡 南
由于巨大的国际影响、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复杂的思想构成,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一直受到世界的关注。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曾经说过:“泰戈尔可能是仅次于甘地、最为我们西方世界所知晓的名字……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诗人。”[1](P119)东西方学术界长达一个世纪的泰戈尔研究足以构成事实上早已成型的“泰戈尔学”的坚实基础。
印度学术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泰戈尔研究业已成为印度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看,在泰戈尔与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缅甸和泰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学关系,以及泰戈尔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宗教哲学等研究方面,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学者由于语言和资料的优势,也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迄今为止,印度学术界的泰戈尔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进行分析。20世纪初期即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到1947年印度独立的30多年,为泰戈尔研究的初级阶段,也是第一个时期;独立后到1970年代末的30年左右为泰戈尔研究迅速繁荣和发展的阶段,19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30年左右,为泰戈尔研究不断深化和取得突破的第三阶段。目前,印度的泰戈尔研究仍然处在非常活跃的时期。第二、三阶段的泰戈尔研究最有特色之处在于比较文学研究模式的广泛应用,这使泰戈尔研究在世界文学的框架内得以进一步深化。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S.巴塔查利雅的《泰戈尔与世界》、S.K.查特吉的《世界文学与泰戈尔》、《哥德与泰戈尔:东西方对话的回顾》等带有比较文学意识的著作。1980年代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如A.毛利亚主编的《印度与世界文学》第十一章标题为“泰戈尔与世界文学”,对泰戈尔与克罗齐、T.S.艾略特等西方作家或文论家进行比较研究。有的学者主编出版《世界文学中的泰戈尔形象》,把泰戈尔在苏联、法国及阿根廷、墨西哥等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反响和泰戈尔在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伊朗等西亚及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反应进行系统梳理。
与印度的泰戈尔研究一样,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为第二阶段,1980年代至21世纪初为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的泰戈尔译介和研究渐入佳境。值得一提的是,随着20世纪后期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勃兴,学者们开始以比较研究模式来分析泰戈尔及其作品。学者们在泰戈尔研究的多个层面都有所开掘,发表或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并积累了很多研究经验,为泰戈尔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从世界范围来说,中国的泰戈尔研究是除了印度的泰戈尔学以外最为丰富的一支。正是在中印学术界泰戈尔研究不断深化和创新的前提下,侯传文40余万言的新著《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简称《比较研究》)既凸显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也反映了国内外泰戈尔研究的转型趋势。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入的阐释。关于泰戈尔诗学观亦即文学理论的研究,印度学者有许多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就思想内容而言,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主要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神秘主义、自然主义等角度探讨文学理论问题,其后更侧重于后殖民主义、东西方关系等文化批评角度。
就中国学术界而言,关于泰戈尔诗学观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张闻天的《太戈尔之“诗与哲学”观》等论文。侯传文的《比较研究》则显示出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和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泰戈尔诗学是在近现代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不仅跨越了传统与现代,而且跨越了东方与西方,因此适于进行比较研究。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是以比较诗学为主要方法,以本体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为基本思路的学术研究。
所谓本体研究是以泰戈尔诗学本身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任务是整理其有关诗学的著作文献,梳理其诗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探讨其诗学范畴的基本内涵和逻辑体系,从而对泰戈尔的诗学观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系统的把握。该书第一章“思想历程”从诗学思想发展的角度,把泰戈尔诗学分为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认为,从诗学思想体系的角度看,经过长期思考和探索,泰戈尔诗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主体性特征的诗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人格论”为核心的文学表现论、以“情味论”为核心的文学美感论、以“韵律论”为核心的文学创作论、以“欢喜论”为核心的文学目的论、以“和谐论”为核心的审美价值论。[2](P12)该书第二章“本体研究”即以“人格论”等为论述对象,深入探讨了泰戈尔诗学观的精髓。第三章“各体诗学”则对泰戈尔的诗歌论、戏剧论和儿童文学论等进行探讨,这是对泰戈尔本体诗学观的补充说明。
所谓比较研究包括纵向和横向比较两个方面。从整体看,全书论述的重点还在泰戈尔诗学纵向历史比较和横向东西比较研究的四章。第四章“传统继承”和第五章“现代定位”集中体现了古今纵向比较的研究旨趣。第六章“西方影响”和第七章“中国情缘”则凸显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旨趣。在此基础上,最后一章即第八章“启示与反思”则探讨泰戈尔诗学建树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及比较诗学研究的深刻启示。
从该书第四、五两章内容来看,纵向主要涉及泰戈尔诗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他对印度传统诗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他与近现代各种文学思潮的关系,均涉及印度民族诗学乃至东方诗学话语转型的研究。印度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泰戈尔通过对文化传统的探索、民族精神的弘扬和民族话语的重建,贯通了印度民族的精神血脉。印度古典梵语诗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且自成体系。泰戈尔诗学的审美意识、超越精神和语言情结都是梵语诗学的继承和发展。泰戈尔的“情味论”、“欢喜论”等都有印度传统诗学基础。他以激活民族话语的方式实现了印度诗学话语的现代转型。从现代学者的角度看,泰戈尔与浪漫主义、神秘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和生态主义都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作者对这些关系均进行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论述和说明。
从该书第六、七两章看,横向比较主要研究泰戈尔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作者既有对具有事实联系的影响关系的梳理,如泰戈尔与老子、闻一多、T.S.艾略特等人的思想比较,也有并无事实联系的美学契合的分析,如泰戈尔与王国维、歌德、雪莱等的思想比较;既有相同相似的诗学思想的互证互释,也有相反相对的文论观点的异质性探求和跨文明解读。在作者看来,泰戈尔诗学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泰戈尔在诗学体系架构的思路和方法上受到西方现代诗学的启示。他主要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他还不失时机地走向西方,主动与西方对话,他的许多诗学著述就是这种对话的产物。从平行研究的角度看,泰戈尔与许多西方大家诗心会通。如泰戈尔与歌德在世界文学思想、与华兹华斯、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在崇尚情感、热爱自然、强调审美快感等方面有共同的思想情趣,与叶芝、T.S.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在超越性追求和象征性表现方面有相通之处。
该书认为,泰戈尔诗学与中国文论的横向比较是一个大课题,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研究。作为印度古典诗学传人的泰戈尔,与中国古代诗精神契合。泰戈尔诗学与中国的儒、道、释三大文论体系都有相通之处,不管是渊源探讨还是平行比较,都有许多有趣的值得研究的问题。在作者看来,泰戈尔诗学与中国现代诗学既有精神的契合,又有话语的激发,还有思想的对话。作为东方诗学的现代转型,泰戈尔诗学观与王国维等人的文艺思想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率先转型成功的泰戈尔诗学,对于正在兴起的中国现代诗学有一定的激发作用。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如郭沫若、郑振铎、徐志摩等,都受到泰戈尔诗学的思想影响或话语激发。作者还认为,陈独秀等人对泰戈尔文化思想的批判和闻一多等人对泰戈尔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中印现代诗学的深度对话。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国文化界在对泰戈尔的接受中出现了很多误读现象,这在对泰戈尔诗学观的接受或阐释中也有所表现。
以上诸方面的论述构成了《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的基本内容。
综上所述,《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一书的主体部分以比较研究为特色。这种比较研究既跨越了印度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时间维度,也跨越了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空间维度。其中,又以跨越中印西三大文明的比较诗学研究最有特色。环顾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出现如此以系统考察和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模式探索泰戈尔诗学的研究著作。因此,该书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它开拓和深化了传统的泰戈尔研究领域,标志着泰戈尔研究的成功转型。作者与泰戈尔及其作品神交已久,且出版泰戈尔作品赏析与评传计两部,再积八年泰戈尔诗学研究之功力,潜心思考,审慎运笔,写出了这部基于博士论文的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著作。这在国内当下浮躁功利的学术圈内是一个难得的佳例。
其次,该书也是对中国比较诗学领域某种不健康学术风气的矫正。目前,审视中国学术界的比较诗学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存在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比较中的跨越性问题没有得到恰当而合理的体现。这里牵涉到中国学者的心态问题。按理说,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但事实上,包括中国与印度学术界在内的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界要达到以世界胸怀来进行跨文明研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就目前中国比较诗学研究而言,跨越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跨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领域。这客观上形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中的 “中西中心主义”倾向。[3]限于诸多复杂的主观与客观因素,印度学者患上了与中国同行相似的“学术感冒”。中印学术界都较劲于中西比较或印西比较,在各自取得比较诗学研究骄人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令人遗憾的学术空白。这的确发人深思。这显示了当今比较诗学研究不太理想的一面。《比较研究》一书在新世纪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者的某种学术自觉和睿智清醒。在此之前的2006年,郁龙余等著《中国印度诗学比较》出版;2008年,黄宝生翻译的《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出版;2010年,尹锡南著《梵语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出版。这些译著或著作显示了对印度文学研究的实绩,对于开拓和深化中国学术语境中的比较诗学研究,矫正学术界某些不健康的研究心态,必将大有裨益或有所助益。
此外,《比较研究》还是总体文学研究的一种尝试。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Henry Remak)曾借用法国学者德利耶尔(Craig La Drière)的“围墙”比喻说明了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者的区别:“打个形象的比喻,民族文学是在墙里研究文学,比较文学跨过墙去,而总体文学则高于墙之上。”[4](P12)这就是说,民族文学在围墙内,比较文学跨过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围墙,而总体文学站到了俯视各国文学并审视其异同的围墙之上。如果说民族文学是比较文学起点的话,总体文学则是比较文学的终极目标。总体文学通过研究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的文学规律,归纳文学的普遍规律。从比较文学走向总体文学,必须在跨文明对话、比较诗学、双向阐释等学术层面和路径上展开。这一学术境界应是一种三维立体的比较诗学研究,即对中印西等各大文明圈的诗学进行融会贯通的比较,以寻找人类文学心灵的一致和差异。三维立体的诗学研究对于开拓比较诗学研究领域,研究文学理论纵向与横向发展的规律,探讨文化输出和话语对话问题,进而实现全球化、本土化与个性化相统一的共同诗学或整体诗学,都有重要启示意义。以此标准衡量,围绕泰戈尔诗学观探索东西方现代诗学共同规律的《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客观地看,该书的论述结构值得商榷。作为比较诗学性质的研究著作,该书引入两个比较研究维度,即历史纵向比较和包括中印比较在内的横向东西比较。但就学术价值而言,围绕泰戈尔诗学观的中印比较和印西比较显然应占更加突出的位置。事实上,该书只以两章处理泰戈尔诗学观的中印和印西比较,显然降低了横向比较在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中的比重。当然,瑕不掩瑜,该著在泰戈尔研究中的创新价值不可低估。
[1] Pearl Buck, “A World Poet,” in S. Radhakrishnan & Humayun Kabir, eds., A Centenary Volume: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Delhi: Sahitya Akademi, 1961).
[2] 侯传文.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 曹顺庆,尹锡南.突破“中西中心主义”学术研究范式的新尝试[J].外国文学研究,2007,(5).
[4]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A].张隆溪译.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