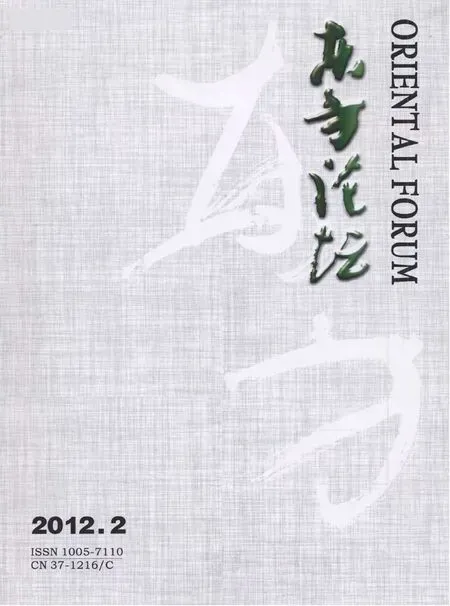马克斯・布莱克论分析悖论
2012-04-01
马克斯・布莱克论分析悖论
陈 四 海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分析方法是现代英美哲学的基本方法,正确和传递信息是对分析方法的直觉要求。摩尔把分析的对象限定在概念而不是语言表达式上,朗福德指出分析方法会陷入悖论。布莱克通过逻辑分析揭露出相似的语法形式其实表述的是不同的逻辑命题,从而消除了分析悖论。布莱克的解决方案本身已经成为分析方法的精彩注脚。
概念;语言表达式;正确;传递信息;分析悖论;
马克斯·布莱克(Max Black,1909-1988)是隐喻现代研究的奠基者,“相互作用理论”的开创者。同时他还是一位专业的分析哲学家,师从摩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曾经被认为“代表了分析哲学的最高发展”。[1](P133)布莱克是较早开始关注日常语言现象的分析哲学家,对美国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转向日常语言哲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所编选的于1950年出版的《哲学分析》论文集是这一转向的先声和预言。马克斯·布莱克对朗福德(C.H.Langford)所提出来的分析悖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且提出了一种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虽然他的方案并不足以作为定论,但激发了后来更多学者的思考,并且促进了人们对分析方法的讨论和反思。
一、分析悖论的提出
分析悖论(Paradox of analysis)和广为人知的摩尔悖论(Moore's Paradox)并不是同一个悖论,虽然两者都和摩尔密切相关。分析悖论是由朗福德在“摩尔哲学中的分析概念”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指出分析概念对于理解摩尔的哲学立场非常重要,但似乎是摩尔并没有把分析方法应用到分析概念自身,他认为如果不对分析概念自身进行系统说明的话,还有可能引起人们对分析方法的否定,因为分析方法可能会出现悖论。朗福德把分析过程中被分析的对象称之为被分析项(analysandum),把用以分析的对象称之为分析项(analysans),所谓分析就是要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恰当的陈述。朗福德指出,所谓分析的悖论就是指:
如果陈述被分析项的语言表达式和陈述分析项的语言表达式具有同样的意义,那么分析就是对空洞同一性(bare indentity)的陈述,并且是毫无价值的(trivial);但是如果两个语言表达式不具有同样的意义,那么分析就是不正确的(incorrect)。[2](P323)
20世纪英美哲学之所以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被称之为分析哲学,就是因为其对分析方法的强调。而且分析哲学家们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表达出来的一种直觉:即真正的知识应该是既能够增加新知识又具有必然性的知识。所以,如果分析是一种有用的哲学方法的话,它必须同时满足正确(correctness)和传递信息(informativeness)两方面的要求。朗福德所强调的分析的悖论实际上就是指当被分析项和分析项是同义的时候,分析不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当两者不同义的时候,分析不满足正确的要求。
用摩尔自己的例子来说就是:
(1)兄弟就是男性同胞
这里的同胞应该在“一母同胞”的本义上来理解。按照摩尔的说法这是对“兄弟”概念的分析,“兄弟”和“男同胞”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语言表达形式,通过分析能够让“兄弟”概念得到澄清。但是如果说“兄弟”和“男同胞”代表的是同一个概念话,那么它们应该可以相互替换,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命题:
(2)兄弟就是兄弟
现在问题是我们推论出来的这个命题并不能被看作是对“兄弟”概念的分析,这一点摩尔自己也承认。很明显,我们推论出来的这个句子不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因而就违反了我们关于分析方法的直觉。并且如果这个推论出来的句子没有传递信息的话,那么我们的初始句子又如何能够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呢?于是,似乎分析方法无法同时满足正确和传递信息这两种要求了。这就是分析悖论的基本内容。
朗福德在表述分析悖论时指出,关于分析的对象是什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就是认为分析的对象是观念、概念、和命题;第二种就是认为分析的对象是语言表达式。朗福德坚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分析是对两个具有同样意义的不同表达式的分析,如果分析的对象是语言表达式的话,我们就不能承认兄弟和男同胞必须是可以相互替换的。所以如果承认分析是关于语言表达式的,所以在正确的分析中也不允许完全的相互替换性。但是摩尔无法接受这种解决方案,因为把分析局限于语言表达式的话,就相当于把哲学思考等同于语言学的定义,仅仅是对两个语言表达式具有同义性的确认,并不能澄清任何东西,因而也不能称之为分析。摩尔明确指出:“必须首先强调的是,在我的用法中,被分析项和分析项都必须是概念或命题,而不能仅仅是语言表达式”。[3](P664)但是,最后令人遗憾地是,摩尔自己也承认“现在我自己也不很清楚如何解决这个难题”。[3](P665)
另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放弃其中一个直觉,即对分析方法的传递信息的要求。对于哲学家而言,通过牺牲关于分析方法的直觉来解决这个悖论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否定了哲学分析对思想所具有的严肃价值。即便消除了悖论,那么这种方法也失去了其所应具有的力量。那么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可靠的方法,在坚持直觉的同时,消除分析悖论呢?在摩尔提出分析悖论之后,有很多哲学家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二、布莱克关于分析悖论的解决方案
悖论的产生在于通过表达同一概念的不同语言表达式的相互替换所产生的陈述似乎是和原初陈述是同一个陈述,因而所推论出来的陈述也是对概念的分析,所以导致分析会违反正确或传递信息的直觉要求。解决悖论的核心就在于如何证明推论陈述和初始陈述并不是同一个陈述。摩尔虽然表示自己无法解决分析悖论,但他给出了一个解决分析悖论的建议:
如果你说“兄弟就是男同胞”,你正在作出的这个陈述既是关于兄弟这个概念的也是关于所使用的两个语言表达式的;这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个陈述和“兄弟就是兄弟”这个陈述并不是同一个陈述”[3](P665)。
摩尔在谈到关于概念分析的条件时,曾经指出,表示被分析项和分析项的语言表达式必须是不同的。有学者据以认为,摩尔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承认了分析既是关于表达式的又是关于概念的。所以如此就解决了悖论:“如果一个分析可以既是关于概念的,同时又是关于表达式的,分析悖论就可以解决。但是Max Black设计了一个精巧的推理,否定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4]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摩尔反复强调他所说的分析必须是关于概念或命题的,而不是关于语言表达式的。但是用以分析的陈述可以既是关于语言表达式又是关于命题的。摩尔明确指出:“人们必须假定这两个陈述在某些意义上既是关于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式的,也是关于兄弟这个概念的。但是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关于所使用的表达式的,我还不很清楚;因此对于这个难题我不能给出任何清楚的解决方法。”[3](P664)摩尔对于如何解决这个悖论给出了他的建议,但是他自己对于将分析过程中所使用语言表达式和概念如何加以区分缺乏技术手段,并且马克斯·布莱克的逻辑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摩尔解决方案的贯彻而不是与之相反。
布莱克拒绝上一节提出的牺牲关于分析方法的两个基本直觉来解决悖论。他认为可以在坚持摩尔立场(即分析是关于概念或命题而不是关于语言表达式的)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消除悖论。布莱克的解决方案在本质上就是通过逻辑分析表明通过替换所得到的这个命题“兄弟就是兄弟”和原初命题“兄弟就是男性同胞”虽然有着极为相似的语法形式,但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命题。因而分析的典范形式是“兄弟就是男同胞”,这是符合直觉要求的,通过推论而来的命题并不是概念分析,因而对之也就不会有传递信息的要求。从而也就消除了悖论。
布莱克的解决方案分为两步,其中第一步针对摩尔所举例子的特殊性而言,布莱克认为这些涉及到不同概念之间关系的命题,可以通过命题函项的分析非常轻易地推论出命题(1)和(2)并非同一个命题。为了让自己的理论更加稳固,布莱克更进一步指出即便对于不涉及到多个概念之间关系的概念分析命题,也可以通过语言表达式和概念的技术分离(这一点恰恰是摩尔看到但是缺乏技术分离手段的)来证明通过替换所得到的命题和原初命题并非同一个命题。
首先,来看布莱克对摩尔的分析范例的解决方案。既然摩尔认为分析是关于概念的,布莱克指出在上面的陈述(1)和(2)中分别涉及了作为兄弟、作为男人、作为同胞和作为男同胞,我们分别用符号b、m、s、和ms来指称它们。布莱克指出,我们之所以会认为(1)和(2)是同一个命题,是因为我们对(1)做了不恰当的形式化处理,即把命题(1)形式化为:b=ms,布莱克认为这并不是命题(1)的准确形式化处理。在继续论证之前,他举了一个数学的例子:21=3x7和21=21,我们并不会认为这两个算术等式是一回事,原因就在于在数学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21=3x7是关于3个数字之间关系的一个函项,对于这个算术等式的首选的形式化就是A(21,3,7)。布莱克认为,在数字等式中21是3和7的乘积(product),在命题(1)中兄弟是男人和同胞的结合(conjunct),乘积和结合都是三维关系,所以对于命题(1)的准确恰当的形式化处理结果应该是B(b,m,s)。经过这样的处理我们就会发现命题(1)涉及的是兄弟、男人和同胞三个概念之间的三维关系,是非同一性陈述,而命题(2)的准确恰当形式化是b=b,这是一种同一性论述,因而两者并不是同一个命题。[5](P263-265)
其次,布莱克指出在概念分析过程中,还存在其它一些不涉及多元关系的分析范例,除非这些范例也能够得到恰当说明,否则我们就不能认为自己真正解决了分析悖论。布莱克举的例子是:
(3)具有惯性就是具有质量。
布莱克指出这个命题是在力学研究中所承认的。因而,通过替换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个命题:
(4)具有惯性就是具有惯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成功说明在这种不涉及多维关系的分析范例中,(3)和(4)并不是同一个命题,我们就会重新陷入悖论之中,这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
布莱克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命题(3)进行恰当的形式化处理,从而让我们看到命题(3)既是关于概念的,同时又是关于语言表达式的,而命题(4)仅仅是关于概念同一性的,所以悖论就消除了。布莱克首先把(3)改写成下面的形式:
(5)具有惯性这个概念可以通过“具有质量”这个表达式来指代,并且具有质量这个概念也可以通过表达式“具有惯性”来指代。
布莱克认为命题(5)和(3)是同义的,因为两个概念是同一的话,那么它们就可以分别用对象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式来指代。布莱克用D代表概念和表达式之间的指称关系,用I和M分别代表概念具有惯性和具有质量,i和m分别代表语言表达式“具有惯性”和“具有质量”,于是(5)的形式化处理结果就是:D(I,m)& D(M,i)。通过这种形式化处理,我们看到命题(5)涉及到的是一个概念(I和M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和两个语言表达式。布莱克接着通过一系列推论成功地将概念和语言表达式从形式上加以分离(这正是摩尔想要做而没有完成的),他指出:如果是单纯关于概念同一性的,那么其恰当形式话结果就是
(6)I=M
如果是单纯关于语言表达式的,其恰当形式化结果是
(7)(x)(D(x,m)≡D(x,i)
于是我们可以看出命题(5)作为对(3)的改写从逻辑分析的技术处理来看既是关于概念(I和M)的,又是关于语言表达式(i,m)的,也就是说相当于(6)和(7)的合取,而命题(4)仅仅是关于概念同一性的,并不涉及不同语言表达式的同义关系,所以命题(3)和(4)并不是同一个命题。[5](P266-267)
布莱克认为第二种解决方案对于不涉及多维关系的概念分析既然是可以适用的,那么就会很轻易地适用于摩尔自己的例子。所以布莱克对分析悖论的真正解决方案应该是第二种,即通过逻辑的技术手段把概念分析过程中所涉及的概念与语言表达式进行分离,从而将涉及一个概念和两个语言表达式的陈述和仅仅涉及一个概念和一个语言表达式的同一性陈述加以区分。因而也就证明了通过概念同一性的替换得到的推论命题和初始命题并不是同一个命题,因而也就消除了分析悖论。
三、批评与回应
布莱克通过形式化处理将分析过程中所使用命题的概念和语言表达式成功地加以分离,从而显示出所使用命题不是单纯关于概念或语言表达式,而是关于两者的。布莱克的解决方案受到了同时代其他一些哲学家的关注。
莫顿·怀特指出布莱克在论证命题(1)的真正逻辑形式是一种涉及到三个概念的三元关系而不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同一性关系时,隐含了一个错误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任意两个句子,如果其中一个句子提及的关系和另一个句子提及的关系是不相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两个句子表达的是同一个命题”。[6]怀特同样举了一个数学的例子说:21=3x7和21是7的三倍。“21是7的三倍”原文是21 is thrice of 7,在英文表达中三倍(thrice)是一个单独的语词,不需要提及阿拉伯数字3,表示的是两个数字之间的一种关系,怀特认为这是一种二元关系,和21=3x7的三元关系是不同的。这两个句子提及了不同的关系,但却表达了同一个命题。
布莱克说如果自己的论证要求这个前提的话,那么自己的论证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事实上自己不曾使用这个前提,也并不需要这个前提。布莱克指出:一个涉及三个术语关系的命题可以恰当地通过一个只明确提到两个术语的句子来表达,这是非常明显的,自己同样承认。布莱克进而指出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把一个句子中的多元关系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关系特征(relational characteristic),从而用一个术语来表达。布莱克认为怀特的推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没有对准自己论证的真正假设,布莱克的真正假设是:“任何严格的同一性都不可能通过和这个句子同义的涉及非同一性关系的句子来恰当的表达。”[7]布莱克的目的是证明命题(1)所表达的是非同一性关系,不管这种关系可以改写成三元的还是二元,甚至是一元的,都不能得出命题(1)是同一性关系,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命题(1)和(2)不是同一个陈述,所以也就不会危及布莱克的论证。
在布莱克之后,分析悖论引起了英美哲学的广泛讨论,包括丘奇、卡尔纳普、塞拉斯、费耶阿本德等很多哲学家都被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思想场景。分析悖论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分析作为哲学基本方法的合法性的质疑,不管这种悖论是否得到解决,都已经播下了怀疑的种子,而怀疑的种子一旦播下,很快就会生根发芽。摩尔令人惊奇地预言了对分析悖论的讨论必定会将战火引至分析和综合的区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并且他指出,“我并不认为这两个术语有任何清楚的意义”。[3](P667)布莱克认为在坚持摩尔的前提下,分析悖论仍然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加以消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布莱克就忠于和认同摩尔分析方法,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布莱克明确指出罗素的分析方法的主要特征是“方法怀疑”和“逻辑重构”,但是其问题在于将哲学还原成了科学;而摩尔的分析方法优点在于简单和精确,但是其疏于论证,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是分析方法的正当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布莱克的推动之功,二十世纪中期英美哲学掀起了对分析方法的反思,以及对分析和综合二分法的批判,逻辑实证主义逐渐偃旗息鼓,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分析方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分析哲学在20世纪中期的转变同时也是分析方法自身的浴火重生,哲学分析仍然是澄清意义的必要工具,但何谓分析已经发生了悄然的改变。
[1] [英]伊丽沙白·迪瓦恩.世界著名思想家辞典[M].夏基松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2] C. H. Langford. The Notion of Analysis in Moore’s Philosophy [A]. The Philosophy of G. E. Moore,Volume One [C].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3] G.E.Moore. A Reply to My Critics[A]. The Philosophy of G. E. Moore,Volume Two [C].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4] 李大强.分析悖论的分析[J].哲学研究,2006,(4).
[5] Max Black.The “Paradox of Analysis”[J].Mind,1944,(211).
[6] Morton G. White.A Note on the “Paradox of Analysis”[J]. Mind,1945,(213).
[7] Max Black.The “Paradox of Analysis” Again: A Reply[J],Mind,1945,(215).
责任编辑:郭泮溪
Max Black’s Analysis of the Paradox
CHEN Si-ha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The method of analysis is the basic method of modern British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and correctness and informativeness are the intuitive requirement of analysis. Moore thinks that the objects of analysis must be concepts or propositions instead of mere verbal expressions. Langford points out that the method of analysis will fall into paradox. Black discovered that similar grammar forms represent different logical propositions, so the paradox collapses. The solution of Max Black itself becomes the brilliant footnote of the method of analysis.
concept; verbal expression; correctness; informativeness; paradox of analysis
B151
A
1005-7110(2012)02-0100-04
2011-11-08
陈四海(1979-),河南信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