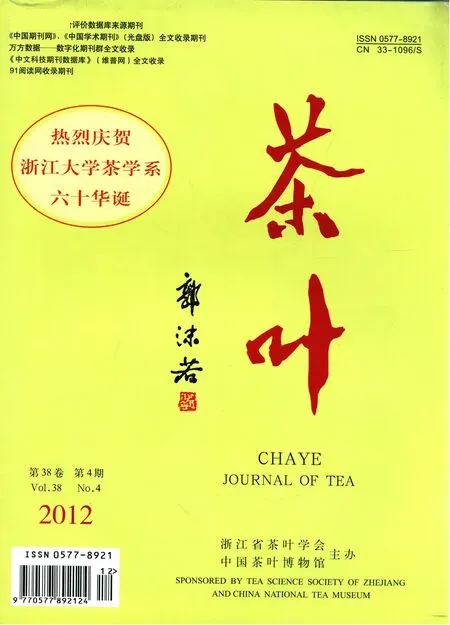“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回忆爷爷吴觉农的好友、安徽茶人傅宏镇先生
2012-03-31吴宁
吴 宁
从走访全国各大图书馆的第一天起,我就体会到收集民国时期茶史资料之难。二十世纪初,茶学还不是一个专业,少有人著书立说,就更没有专门的杂志,写茶的文章多是散落在各种出版物里,又经过了多年的战火和1949年之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以至“文化革命”,去去寻找那些茶文章常有大海里捞针之感。从早到晚,我在缩微机前一页页地翻阅那字迹模糊的旧杂志,读得头昏眼花,却找不到几篇关于茶的。我常想,要是有人编过一本茶文献目录就好了。终于有一天,在爷爷的老友钱梁先生留下的茶资料里,我找到了傅宏镇先生在1940年整理的《中外茶业艺文志》,里面分门别类地列出大量的茶叶资料,从此这本书就成了我寻访图书馆和资料库的伴儿。
爷爷的朋友安徽茶人傅宏镇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走了,我没有见过他,对他的印象是在很多年里慢慢形成的。
一
第一次听到“傅宏镇”这个名字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爷爷把傅先生的《茶名汇考》手稿交给来北京看他的王泽农先生。爷爷说,傅宏镇先生1966年四月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傅显明把傅先生的这本《茶名汇考》手稿送到我家,可那年的八月里我家三次被“抄”。幸亏爷爷在混乱中把这份老友的遗稿塞进了顶楼阳台的废报纸堆里,红卫兵烧掉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而宏镇先生的这份手稿却保留下来了。爷爷希望王爷爷能在安徽农学院找人编辑修订,整理出版。
在这之后不久,上海的姚光甲和向耿酉先生来北京看望爷爷,。爷爷见到他们很高兴,爷爷告诉他们,他正在为祁门茶场写一点三十年代的回忆他们也都是最早在祁门茶场工作的人,可以帮他回忆些旧事。爷爷还说,傅宏镇先生和他的表弟潘忠义更早,1932年就到祁场了,他们比胡浩传先生还要早,可惜他们两位都不在了。
那天,他们回忆起许多在祁门的往事。讲到傅先生,爷爷说,幼文(傅宏镇先生的字)做事有股“痴气”。1933新年前,他和潘忠义去西乡的历口、闪里做调查,竟没赶回来过年。1932年的最后一天,本来讲好的,那天中午大家都要到的,请了平里村的章家师傅做了“千层锅”那是徽州名菜,从早晨就开始煮了。鸡鸭鱼肉各一层,都煮在一锅里,底下垫着萝卜、白菜,汤里还有香菇,干菜和粉丝。傍晚时,只有傅先生没到。左等右等,天都黑了,大家饥肠漉漉,爷爷让场里的人先吃了,自己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算算路上的时间是有余的怎么人还不到呢?那时的祁门一带也不大安全,有匪盗,还有豹子、老虎,不会出什么事吧?据平里的章老先生说,上年冬天,有人在山上遇到了老虎,村里的人是谈虎变色。等呵,等呵,结果幼文他们到了第二天中午才赶回来,在路上过年了。去西乡路远,要走上百里,过溪的桥被封了,所以绕来绕去,耽搁了好多时间。历口和闪里有好多家茶农种茶和制茶的,幼文想想来一趟不容易,所以每一地都不放过,这样就赶不上过年了。
姚先生笑着说,是呵,傅公工作认真,而且脾气特别好。我和傅公一同去访有秘方的制茶人,有的制茶人很保守,有的很“牛”,开始总不愿意让我们看他们怎样制茶的,但傅公都和他们聊的来。傅公栽培和制茶在那时都是很有经验的,但他总是耐心听别人讲,细心地写笔记。他在访问时,每一与茶有关人的姓名,住址都记得清楚。还记了茶谣,谚语,好几个线缝的毛边纸本。
爷爷说,幼文收集茶资料包罗万象,可一点都不私有。你们还记得徐方干先生吧?1935年初,徐先生刚从台湾学制茶回来,正要去祁门。我介绍幼文与徐方干认识的。那时候,傅在祁门近三年,走遍了祁门的茶区,对祁红的土壤,茶的栽培和制造都极为熟悉,积累了不少资料。他把自己的笔记厚厚的几本祁门制茶笔记都给了徐方干。那天,胡浩川也在,他开玩笑说,“幼文,你把秘密都公开了”,幼文笑笑说:“没有什么秘密,里面都是些失败的经验。”
二
1980年夏,錢梁、陈君鹏先生来北京,帮助爷爷整理《茶经述评》的第二稿,在聊起传统工夫红茶,从广东、福建到江西到安徽的经过和各地的制茶方法时,爷爷又一次提到傅先生,他说,“三十年代,傅宏镇先生在祁门的时候从收集到很多红茶制作的资料,那是些来自茶叶世家的“活传统”。我们那时候多想的是科学兴茶,只注意新技术和机械制茶,想想传统小作坊制茶没有前途,所以传统的制茶方法最多只是作个参考而已。傅先生不同,他对各种茶制茶的方法和传承,包括每种茶名的历史演变就特别有兴趣。”
爷爷还说,“傅先生的茶资料多是手抄的。在祁门茶场那两年,大家都忙,空下来,也在一起打打牌,抽香烟娱乐一下。傅先生很少参加,推说他打不好,总是输。其实是借口,他的时间就都花在抄写资料上了。他也向我借过不少。那时茶书、资料少,宝贝,很多人来借书就不还了。可傅先生讲信用说哪天还,一定送还。记得有一天,下大雪,冷得不得了,他从一位老先生那里借来了一册古书,里面有茶文章,手僵得握不住笔,砚台也结了薄冰。他烧点水,温手温砚,还是把书抄完了,晚上冒雪又把书送归主人。“那时傅先生的工作常常变动,安徽秋浦、祁门、屯溪,浙江的篙坝、三界,所以他每次回家,总是把抄好的资料带回去,都存在安庆家里。1938年夏,日本人打进安庆时,他正从三界茶场赶回安徽,多年的资料来不及运走,都烧掉了,可惜呀,不然他所收集的传统制茶的活资料,今天都是宝,要派大用场了。”钱梁先生在1944到1945年曾在屯溪做香港富华公司的经理,1946年又在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做襄理,而傅先生在屯溪负责兴华公司的茶厂,他们常有往来。他说,每次到屯溪都得到傅公的帮助。傅公对安徽的茶叶了如指掌,人缘极好。特别是在1946年,皖南收购茶叶。抗战期间,皖南有很多屯积的茶叶,收购茶多是一个仓库,一个仓库的购买的。傅公威信很高,只要是他看的茶,估的价,茶商从不还价,他们信任他。傅公说起,他年青时,曾徒步去了黟县、歙县、屯溪、婺源、休宁、绩溪。一家家茶栈、茶行,一户户茶农去调查。所以很多茶人他都熟悉。
钱梁伯还说,在皖南的时间,他曾在傅公家吃饭,尝到过傅公妻子邦尧嫂做的梅干菜筍肉和清川丸子。安徽菜盐重油多,而傅公家的菜却是清爽鲜滑,很合钱伯伯的口味。钱伯伯喜欢古诗文,与傅公趣味相投。晚饭后,他们最有兴趣的是在屯溪旧货摊上、旧书店里买两本茶书,古代诗文,那时小摊上常可以买到小古玩。胡浩川先生来屯溪,也会和他们一起到旧书摊上去“淘”古书。胡浩川先生还喜欢和傅公在一起神聊老子和庄子。
钱伯伯印象深的一件事,是傅公讲起他小时在安庆读私塾,他的老师也是桐城人,教学生没有用过当时所流行的桐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他只要学生读孔孟和老庄,所以傅公背过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他根本不懂,却背下来了,以后一辈子,慢慢咀嚼,像牛一样反刍。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反刍”这个词。以后,我才懂得,反刍牛吃草,吃草,没嚼就吞下去储存在胃里,不停地返回口中咀嚼,然后把磨碎的食物,送回胃里,这种反刍不断直到食物被充分分解为止。
三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爷爷、姚光甲、向耿酉和钱梁先生都离去了。可我在收集爷爷和他的朋友们的资料之时,又听到了几位还在的老人们提起傅先生。
浙江绍兴的郑仲仙,是我爷爷的侄女。她的丈夫吕增耕与傅宏镇先生是多年好友。仲仙娘娘讲,增耕与傅先生从1932年相识。增耕还刚刚二十岁,傅先生已是三十五六了,按说应是他的长辈,可傅先生看上去年轻,眉清目秀,一口安徽音的普通话,两人都是三界茶场的辅导员,所以,增耕还以为他们的年龄、经历相近。后来才知道,傅先生是和爷爷同辈的人。
仲仙娘娘那时只有十八岁,是三界茶场的第二期学员。她记得傅先生是个很耐心、温厚的老师。她说,“那时教制茶的有两位,傅先生和徐方干,徐先生。以徐先生为主,傅先生协助他。徐先生是你爷爷用重金从祁门请到三界的,他懂英文、日文、法文,在日本静冈和台湾帝国大学与日本的红茶专家做过研究。他讲课生动,可傲得很,咄咄逼人。茶场人都把他当成技术权威的。所以我们都怕他,有问题都是去问傅先生的。我们去实习,制茶动手都是傅先生带着,他总是有问必答,耐心。时间长了,我们才发现,还是傅先生制茶经验丰富,珠茶、眉茶、龙井怎么做他都熟悉。“有一次,傅先生带我们几个学员去淳安做调查,学制眉茶,每一道工序,他都要我们一样样试过来,所有的制法,筛法细节,他都让我们记下来。眉茶的工序好复杂,那一次我们很累,傅先生更累,时间短,我们白天制茶,晚上写报告。我们的报告,他一页页读过,改过,又让我们抄写整齐交给徐先生。那份调查报告,多少心血,可是徐先生看了之后,却在课上说,我们收集的资料多而不当,用的是笨方法,但总算是有苦劳吧。他讲这话好像在讲笑话,我们听了都不大高兴,傅先生人也在,却不生气,还与徐先生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增耕(仲仙娘娘的丈夫)喜欢打抱不平。他说,他和两位高班的学生从祁门学茶回来,听那里的人讲闲话,徐先生初制祁门红茶还是傅先生教的。在祁门徐先生目中无人,和大家都相处不好。增耕为傅先生抱不平。说傅先生太软弱了,逆来顺受的。
你猜猜傅先生说什么?他说徐先生讲的有理。他读了徐先生在调查报里加的评语,挺有收获。学生得益,学会制茶就好了,与徐先生争论笨不笨没有什么太大意思。
徐先生后来为了争当场长,闹得三界茶场鸡犬不宁,你爷爷只好又把他请去湖北做场长。离开三界的时候,他和别人都翻了,但他和傅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好。三界茶场出茶叶专刊,还有傅先生和他合写的茶业调查报告。在三界只有你爷爷和傅先生捧着他。你爷爷像请神仙那样请来,送神仙那样送走,傅先生供着他。”
仲仙娘娘停了一下又说,“不过那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今朝也没什么意思了。那时所有的人都走了,我也快九十岁了。傅先生对了,现在看来,那时争的谁对谁错,谁出风头,真是没有意义的,傅先生那时就懂了。”
上海老茶人郭柽先生1941年曾到屯溪学制茶参加茶叶运销。他说,“傅公是在屯溪安徽茶叶管理处做副处长,方君强先生是安徽管理处的处长。他们的分工是,方处长对外,出面做省里的事情。傅公对内,屯溪茶界的事都是他管。几次茶叶运销,订价的集会都是傅先生出面的。在会上,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傅公先听大家说,然后,平稳,慢悠悠的讲几句话,就把事情搞定了。我们去过屯溪的人都知道,傅先生在皖南茶界威信高,经验丰富,理事公平,人人服气。有时碰上不讲理的人,出言不逊,傅公也不动气。他好像从来没有过误会和冲突。”
安徽老茶人韩燮康先生是在1946年参加兴华公司时与傅公往来,他直到傅公去世。他说“傅公人寡言、谦和、一辈子淡泊,与世无争。1949年,你爷爷请他去北京中茶公司,可他想到安徽茶区需要人,就留下来了,三十年代末,傅公就是安徽茶叶管理处付处长,在安徽茶界的名望除了方君强、胡浩川、就数傅公了,到了五十年代,许多在三十年代参加祁门茶训练班的茶人如陈季良,汪瑞琦,董少怀先生,或是大学茶学系毕业后来安徽工作的如左纪谷、徐楚生先生都与傅公共过事,然后成了他的领导。他不仅不在意,看到有为的年轻人升上去,他总是很高兴的。无论在哪里做,他总是很乐意地拾起别人都不做的工作,从没有怨言。
“1950年,傅公在皖南中茶公司做了一段,他去做安回茶叶推广所所长,然后去创建和负责过商山茶叶示范场、省公安厅黄山茶林场和茅山农场。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茶界,傅公却是位往低处走的人。虽然他的官就越做越小了,可在安徽茶人中的威信却越来越高。
“傅先生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他与你爷爷那一代老茶人做了一辈子的茶,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就是大家都看不惯,很不讲理的事情,他也不说一句。所以他的人缘特别好。在抗战时期,安徽茶业管理处的人集体参加过国民党,在五十年代,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个污点。但上海复旦大学要保送他的女儿去当时的苏联留学,派人来调查,就连常常无中生有,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人事处都说傅先生好,没人提起他加入过国民党这件事,政审顺利通过。”
四
经过了几年的寻访,我终于找到了傅先生的女儿显华和显明,她们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我希望能从她们那里找到傅先生四十年代写的书和资料却落空了。1966年傅先生刚刚去世之后,文革就开始了,因显华的丈夫是归国华侨,所以她家多次被抄。傅宏镇先生留下的遗物和手稿、书籍一劫而空,家里连一份傅先生的简历都没有存下。文革之后,显华曾写信给傅先生在安徽的单位和省档案馆,而信却如同石沉大海。
在显华给我的信中,她简单地介绍了傅先生的生平:1901年5月28日出生在安庆。祖籍是江苏句容县人,“不知何时定居在安徽安庆。”他的父亲在安庆城里开文具店。上过一点私塾,1920年到1922年傅先生在安徽省茶务讲习所学习,1923年毕业之后,即到安徽省立秋浦茶场工作。1932年初,他与妻子肖邦尧经人介绍相识、结婚。同年八月,秋浦茶场合并到祁门,也是在那一年秋天,傅先生与爷爷在安庆认识,参加祁门茶场的筹建和祁门的茶业调查。
回忆她的父母亲,显华这样写道,“母亲肖邦尧是家里的独生女,很受父母宠爱,也略通文墨。经媒人介绍和父亲结婚。婚后,父亲在浙江和安徽的茶区工作,母亲留在家里,父亲寄钱回家维持家用(祖父去世早)。父亲对母亲十分体贴。母亲身体欠佳,总是要打针吃药。只要父亲在家,总要陪伴母亲,父亲性格极温和,对家人很好,细致,在那一代男人里是很少见的,从来没见过他们争吵。晚年,父亲退休后,回到屯溪居住,两老常牵手出去走走,周围的人都很羡慕他们。
“我和大姐均在安庆出生,还有一个弟弟,傅显松,在逃难中出麻疹,夭折。正因为这,母亲常为未能替父亲生个儿子以延续傅家香火而自责,整天都郁郁寡欢。安徽管理局的局长是方君强先生,他的妻子常来抱怨方先生的小老婆。母亲要父亲再娶一个小老婆,能生个儿子。父亲却对母亲说:‘你不是信命吗?如果命里注定我有儿子,显松就不会死了。我有三个女儿,我要把她们培养好。’父亲对我们三姐妹疼爱有加,从未打骂我们。夏天亲自为我们灭蚊,深夜叫醒我们回房休息。生怕我们在天井竹床熟睡受凉。父亲也带我们去茶场玩,稍大一点,也要我们下制茶车间学习拣茶,体会工人的辛苦。”
关于傅先生来1966年4月的突然去世经过,显华写道:“1965年9月,父亲退休了。国庆节过后,我们准备接父母亲去山东同住。真的要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屯溪,母亲在感情上依依不舍,可能是因为母亲长时间整理搬家又十分劳累,在临行前的饯行宴会上,亲友们的祝福,感情地热烈,母亲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父亲遭受严重地打击可想而知。此后,我们只好将父亲一人接到山东泰安。但他老人家对母亲的思念时刻地折磨他。下一年的清明节前,我要带学生下乡实习,正在整理行李,他过来帮我时说:后天就是清明节了,你妈妈——”一阵剧烈的头痛就倒了下来,原来父亲也患了脑溢血,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跟随母亲去了。一生恩爱,相隔半年去世。我们姐妹三人,失去了至爱的双亲,”
五
傅宏镇先生的为人处事常使我联想到老子在《道德经》里的一段话:“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忧。”
老子以水喻人生:水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争高下。水往低处流,乐于停留在被人所恶的卑下之处,水性至洁,晶莹剔透。傅先生不正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的智慧之人,他懂得人生中“不争”和“利万物”之道。正如仲仙娘娘所讲的,傅先生在所经历的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是非、高下和名利在今天看来是多么遥远而没有意义,而作为当事之人的傅先生能够看清这一点,却是极为难得的。
记起钱梁伯讲到的傅先生小时背过老子,而他的人生是一个慢慢“反刍”的过程。他的为人处事难到真是“反刍”老子哲学的结果吗?还是他的天性呢?我不能判断。但有一点我知道,傅先生的一生如水,滋润万物。他在七十多年前收集和编纂的这本《中外茶业艺文志》直到今天仍对我和许多希望了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茶史的人有着无可估量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