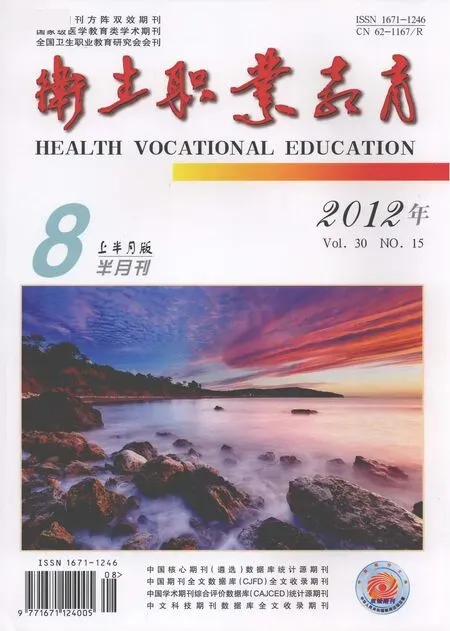“万古愁”如何能销
——从李白的《将进酒》说开去
2012-03-20马真明
马真明
(兰州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万古愁”如何能销
——从李白的《将进酒》说开去
马真明
(兰州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万古愁”是一个经两千多年时空积淀而成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意象。李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诗人,“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一高标准的人生理想成了李白悲愁喜乐的关键点,他想通过痛饮狂饮“销”掉万古以来志士仁人共同遭遇的、挥之不去的悲愁,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只有解开了这个万古以来的“结”,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灵世界才会展示在我们眼前。
万古愁;独善;兼善;销愁
“万古愁”语出李白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其末句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历来对此句的解释多为豪言壮语,周啸天先生在《唐诗鉴赏大辞典》中说:“即便千金散尽,也当不惜将出名贵宝物──‘五花马’(毛色作五花纹的良马)、‘千金裘’来换取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尔’,口气甚大;而且具有一种作者一时可能觉察不到的将宾作主的任诞情态。……情犹未已,诗已告终,突然又迸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而‘万古愁’的含义更其深沉。”[1]自古有志之士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安顿自己的灵魂。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这里的“为己”和“为人”被孟子推演为“独善”与“兼善”的穷达矛盾论,李白之“悲”也即未能够恰当处理这一关系,这是历代志士仁人共同遭遇的问题,李白将其概括为“万古愁”,欲以痛饮狂饮“销”之,然而“万古愁”果真能“销”?进路如何?本文试做解颐钩沉。
1 “借酒销愁”——普泛化的意象
1.1 难销之愁
“借酒销愁”是一个普泛化的意象,历代抒情言志诗中多有此意象表达,“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伤”[2];“驾言出游,以写我忧”[2];“深藏欲避愁”(庾信《愁赋》);“欲上高楼去避愁”(辛弃疾《鹧鸪天》)等等。当然,消愁的途径除了“借酒”还有很多,或读书,或吟诗,或作画,或书法,或游览天下名山胜景以销愁,或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者。而太白此处独以“万古愁”与“销”(非“消”字)搭配,在销愁之上更翻出一层深意。“销”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为“铄金也”,与“铄”、“铸”同义,泛指为熔化,总与金石有关。太白用此“销”字,认为他的愁是万古以来凝聚而成金石般坚硬之“块垒”,没有足够的火力、温度是无法消解的。“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襄阳歌》。以下所引李白诗皆出自郁贤浩《李白诗选》,不再一一注明出处)[3]唯有这样的痛饮、狂饮之烁金之火才可消解万古冗愁,这是太白用心之处。张潮说:“心中小不平,酒可以消之;胸中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饮中八仙令》)
1.2 道之不行
“闻道”而“行道”是志士仁人共同的理想,李白也不例外。此诗的首联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揭橥天地自然状态之不可逆转,循环不已而万古依然,相对应的是生命的有限和短暂。面对天长地久、出生入死的宇宙洪荒和生命本质,个体的渺小和无奈便油然而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夫子临河而叹,有感于大河之永恒而生命之短促、不可把握,而又激发起夫子欲以生命的有限对抗无限之天命而求得永恒的精神气度。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4]欲以生命为代价“闻道”(夫子之“闻道”即包含“行道”),因而“蔬食饮水”、“箪食瓢饮”之窘状也不减孔颜“闻道”之乐。李白是深受儒家理念濡染之士,“闻道”而不能“行道”,致使朝暮间青丝变白发,生发出无限的愁绪。
2 醉与醒:现实与理想的分离
太白之所以是太白,关键是永不泯灭的治平天下的政治热情,接下两联弃烦就乐: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认为“人生”句的语序解为“得人生意须尽欢”似乎更符合太白独特的性格,人生本来就是追求幸福快乐的,老子曰“出生入死”,生之初即死之始,结果非常明确,何必自寻烦恼呢?“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李白《襄阳歌》)“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这里,酒超越了天地神仙。酒不但是他生命力的生动体现,而且成了他追求幸福快乐的极佳途径。幸福快乐是生命的本质,故不论在“造次”、“颠簸”的失意中,或功成名就的踌躇中都应“一以贯之”——金樽对明月,何等的疏朗,何等的洞明人生!
2.1 醉中“至乐”
“天生”句是沉淀着历史厚重意味的哲学表达,“天生我材”亦如《论语·子罕》中子贡答太宰之问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又如《离骚》中“唯庚寅吾以降”。诗人认为,有天生之材不愁没用,更不必为时散时聚的身外之物介怀。李白在骨子里从来不把自己等闲视之,而是像大鹏一样等待时机搏击风云,期盼着“金高南山买君顾”,确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因此,“烹羊宰牛”非显排场,只求一“乐”,但此“乐”非“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的魏晋名士之“乐”,是用情于天下苍生福祉之“乐”。“乐”而歌是最自然不过的,但时隔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听清歌中“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悲情。并非乐极生悲,而是诗人治平天下之志(“乐”)与“冰塞川”、“雪满山”的现实境遇的严重冲突,诗人之志途幽暗不明,志向抱负难有施展空间。而展雄才、治平天下(“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是诗人“至乐”的根本所在,因“至乐”难极,故退而求之他途,愿“常醉不复醒”,醉而生幻觉,“至乐”也会幻化演绎,岂不快哉!
2.2 醉之寄托
诗人“但愿常醉不复醒”不能简单归结为麻醉自己,而是愁苦至极无法消解而纵酒与愁告别,欲将自己沉溺于无知无欲之境的、耽求“至乐”幻象的“狂人”之举,诗人自己也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但失望绝望的愤激并未影响其对人生的深层思考,传统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希圣希贤”,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大命。但诗人却发现,自古以来所谓圣贤都是在孤独寂寞中走完一生的。圣人如孔子者,14年周游列国不见用于世,落寞归鲁,只能整理古籍、教授学生,表达“后生可畏”之愿景;欲以“王道”治平天下的孟子自信“舍我其谁”,却被当世君王讥讽为“迂远而不近世情”;屈大夫欲以“属贞臣而日嬉”的途径在楚国实现美政,挽救颓势日炽的国运,却遭疏远、流放终至没水而死;司马相如只能当炉卖酒;“穷途之哭”的阮籍只能以“猖狂”自保,更不用说当世诸多志士仁人仕途的凄凉。由此更凸现出专制社会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对人才的浪费与摧残,从中不难体会诗人理想破灭后无法消解的哀愁。
“惟有饮者留其名”句可作两解。其一,中国传统骚人与酒有难解之缘,酒是乐时的锦绣,愁时的慰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不能无酒,好诗好书也不能无酒,无论是自处还是处人都不能无酒。在李白看来,圣贤之寂寞也与不能纵酒狂饮而暂时与愁告别有关。李白向来有“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理想,他希望做帝王的辅弼之臣,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然后像范蠡、张良那样,舍弃卿相之贵,浮游江海,栖隐山林。“功成名就”和“栖隐山泉”两相对立的路径在这里很清晰地统一在诗人身上。其二,按当时语境,这自是诗人纵酒狂饮的忘情之言,他拈出陈思王曹植“斗酒十千”的掌故,陈思王的文采与政治运途皆与酒有关,当他政治颓败后更离不开以酒和诗文宽解,最后郁郁而终。而李白表现得比陈思王曹植更狂放、更具有想象力,“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更超乎贺知章解金龟换酒的豪举,诗仙李白在这里简直不顾一切了。
3 独善或兼善:艰难痛苦的抉择
3.1 知音难求
此诗最后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如一苇防澜,让此前一切非常之举真相大白,诗人痛饮狂歌非只为一时之乐,而是心中积淀了万古以来志士仁人难以消解之愁。正途难以消解是这些志士仁人之通例,然李太白很清醒,“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和“举杯消愁”对举,说明所用的工具、路径皆与所为者不对应,以酒消愁的结果只能是愁上加愁,非能消愁也!柳永《雨霖霖》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庾信《愁赋》说:“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陆游的《春愁》曰:“春愁茫茫塞天地,我行未到愁先至”;临清人商调《醋葫芦》云:“几番上高楼将曲栏凭,不承望愁先生在楼上等。”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难以消解。
3.2 隐逸销愁
但“万古愁”真的难以消解吗?李太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最后一联给出了答案: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俗语云:“人生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因“不称意”而生愁者也就非太白独有,而是万古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所共同遭遇的不幸。因此,“明朝散发弄扁舟”就不仅仅是太白给自己所设计的出路,而是给普天之下志士仁人所设计出的通途。“散发扁舟”是与入世之“束发戴冠”对应的“相忘于江湖”的人生态度,是将生“愁”之路径从根本上斩断。因为李太白之愁都源于其凝结于胸中的挥之不去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情结,解除了这个心结,以“独善”悠游,也就不必以自己瘦弱的肩膀扛着万古以来志士仁人之愁而不得逍遥,岂不就可以“放浪形骸之外”,逍遥而游了?
当然,这对太白来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选择,他曾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表述了自己一生的生活理想: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太白看重的是“功成”,须俟功成后方能甘心引退。因此,“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不是太白走投无路时的哀诉,而是一个深陷痛苦之中的强有力的灵魂的怒吼。
李白还是隐居了,在庐山屏风叠上坐看风云变幻。“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猛虎行》),“吾非济待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但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毕竟是他终生执著的理想,当永王李璘率军沿江东下,慕太白大名而再三邀请时,太白便欣然前往。到761年秋,61岁高龄的诗人还打算前往临淮入李光弼幕府,参加防御安史残余势力南侵的工作,始终怀抱报国壮志而至死不渝。临终前所作歌云: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
李白常以大鹏自比,但他的“大鹏”形象与庄子的“大鹏”形象是有区别的。庄子的“大鹏”是一个“九万里而风斯在下”的、消隐了终极目的性的、无为而逍遥的大鹏;而李白眼里的“大鹏”是一个带着浪漫色彩的、非凡的英雄形象:大鹏展翅远飞,振动了四面八方;但刚飞到半空就翅膀摧折,无力翱翔。后人得到大鹏半空夭折的消息,以此相传;但如今孔子已经死了,谁肯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大鹏的夭折而流泪呢?豪迈自信的李白不但终其一生未能实现人生理想,临终也未能觅见知音,其间流淌的是对人生无比眷念和未能才尽其用的挥之不去的忧伤。因此,“万古愁”无论如何是“销”不了的。
[1]杨旭辉.唐诗鉴赏大辞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陈俊英,蒋建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郁贤浩.李白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杨伯峻.论语译注[M].2 版.北京:中华书局,1980.
I207.2
A
1671-1246(2012)15-015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