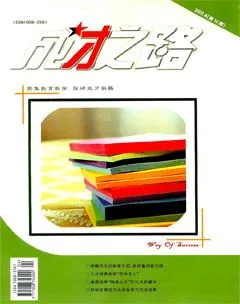王振义: 在爱中行走
2011-12-29余晓洁
成才之路 2011年10期
他,一身白衣,俯身细细为病人查体,静静倾听他们诉说。慈祥的眼神,时时传递着无限的怜爱;温暖的话语,点燃患者重生的希望。这是每周四,上海一家医院一道特殊的风景线:87岁高龄、鹤发童颜的老医者在给白血病患者看病。
白衣上的蓝色胸牌透露出他的身份: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医师王振义,工号10005。
2011年1月14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这位勇敢向白血病宣战的仁医,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捧回烫着金字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为医:深如江海是仁爱
“人老了,回想起来常常感觉很幸福。这种幸福源自我一生担当的角色——医生。特殊的工作,使医者的灵魂每天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不断得到净化与升华。”王振义说。
一个医生,应该把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最大的动力就是为病人服务。这是王振义自勉的信条。从医一个甲子,他做到了。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爱情剧《血疑》风靡亚洲,人们在慨叹主人公的生死不渝爱情的同时,也记住了一个可怕的病魔——白血病。这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种类繁多,死亡率极高。因为缺乏有效疗法,在与死神角力中,医生和患者,总是失败的一方。正是王振义,改变了这个死亡游戏的结果。他找到了白血病中一种类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临床最佳治疗方法。
冰山,终于被阳光融化了一角。
1986年,5岁的小静本该像快乐的小鸟在父母怀里撒娇。然而不幸从天而降,APL把她逼到了上海儿童医院的病房里。相比其他类型的白血病,APL发病急,更凶险。病人从诊断到死亡往往不过一个礼拜,不给医生留一点机会。
小静病情迅速恶化,高烧不退、出血严重,死神正悄悄地向这个小姑娘逼近。父母的心,被撕成了片片。“就在所有人觉得孩子没救的时候,王老从死神手里把她夺了回来。”小静母亲说。
王振义得知小静的病状后,大胆提出一个国际上独创的治疗方案——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由于从未在临床应用过,方案提出之初,遭受到极大的压力。“我有勇气,我尊重科学。”这是王振义当时说得最多的话。很快,奇迹出现了。几个月后,小静病情完全缓解。
“25年过去了,她健康地活着,马上就要当新娘了。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老说。此后,这种疗法开始在临床上推广。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从上海到全国,再到全世界,奇迹一个个发生,生命一个个得救。
人们说,王老的眼睛常含着泪水。病房里,医生束手无策,亲人生死离别的时候,他会流泪;患者得救,健步出院的时候,他也会流泪。谁能说,这不是因为爱?医乃仁术,大医精诚,大医至爱。绝症面前,医患之情亲如手足,水乳交融。王振义,以他深如江海的仁爱之心,驱散病魔肆虐的黑暗,让患者看到一片光亮。
2. 为学:重如泰山是使命
患者们大多是从胸牌上知道王振义的,殊不知10005号胸牌背后,掩藏着一大摞响亮的头衔:医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这位被世界医学界誉为“癌症诱导分化第一人”的人物在国际上获得了一系列殊荣……
在中PrHRHJniYxndYFdie9F+ig==外血液学科学史上,王振义的名字注定将因护卫全人类生命而作出的杰出贡献而流芳后世。他成功实现将恶性细胞改造为良性细胞的白血病临床治疗新策略,奠定诱导分化理论的临床基础;他确立白血病治疗的“上海方案”,阐明其遗传学基础与分子机制,树立基础与临床结合的成功典范,他建立我国血栓与止血临床应用研究体系。
“促成您有如此多的建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记者问。
“是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使命。世界上没有哪个职业像医生这样离生死这么近。患者的生命重于泰山。拯救一个个原本鲜活却濒临凋亡的生命,是我投身研究的原动力。”王老说。
整整80年前,祖母患伤寒辞世的一幕刀刻般印在他的脑海里。为什么这个病不能治呢?7岁的小振义第一次有了从医的萌动。1942年,勤奋好学的他免试进入震旦大学学医。五十多年前,救人心切的王振义曾提出要“3年征服白血病”。但由于条件不成熟,当年他眼见多名白血病患者先后撒手人寰。
“光有热情不够,还得靠创新,靠真本事。”王振义说。
细品医魂,“求真创新”,贯穿王振义一甲子医学科研生涯的始终。
让癌细胞“改邪归正”!王振义查阅到,以色列科学家证明白血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逆转,分化成熟为正常细胞。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癌第一人参悟儒家哲学思想。他一改放疗、化疗杀死癌细胞,也对正常细胞产生损害的方法,独辟蹊径。他首创的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成功运用于临床,给病人带来了生的希望。
太多的故事,随着斗转星移流逝。人们能够忆起的,是灯光。王振义办公室的灯光,实验室的灯光,资料室的灯光,从一个个深夜到黎明。再有,就是那辆数十载里骑得快散架的脚踏车。无论酷暑寒冬、刮风下雨,这部“宝马”驮着他匆匆行进在去医院、去病人身边的路上。
人们说,他对科研有发自内心的痴迷。谁能说,这不是源自使命?科学的探索,是一条漫漫长路。一个真正科学家的快乐,是创新和奉献。王振义,背负救死扶伤重如泰山的使命,披荆斩棘,攀上一个个学术高峰。
3. 为师:甘为人梯是奉献
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所,这个在病房边一个灶间开张,超过三个人就转不了身的巴掌大的地方,居然走出了3位院士。一脉相承的师生,合力把中国血液学研究推上国际水平。
开创者王振义,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高徒陈竺、陈赛娟夫妇分别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外,王老先后培养博士21人,硕士34人。陈竺夫妇此生不会忘记,王老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王老每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第一、第二作者,自己排在最后。“看到学生超过自己,是当老师最大的幸福。”王老说。
1996年,陈竺的研究日臻成熟。此时的王老没有考虑名利得失、地位动摇,主动推荐他当血液学研究所所长。在学生眼中,王老是谦逊豁达的长者,严谨求实的学者,爱才惜才的老师。
科技部“973”计划项目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之一的陈国强是王老另一位得意门生。 “当时没电脑,我的学位论文王老先后改了10遍。多次把我叫到家一起吃晚饭,一放下碗筷,师生俩就一头‘扎进’论文。”陈国强说。
“他是我们学术上的楷模,精神上的榜样。对学生,他总是倾囊相授,倾囊相助。当一个人把私利放下的时候,他自然变得崇高。”王老的学生、瑞金医院主任医师糜坚青说。
“为师,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积累的学术财富传给年轻人。”王振义说。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如今,87岁的王振义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叫“开卷考试”。临床医生“出”平时实际碰见的疑难杂症。他用两天的时间查中外文献,亲自做PPT(演示文稿),带领学生一起探讨交流,教学相长。
耄耋之年,王老身后,是徒弟们一片崇敬的潮涌。
人们说,王老慧眼识才,大义让贤。王老自己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读懂了人生的成功——鼎盛——衰落的“抛物线”。在我这条“抛物线”快要衰落时,立即让位。让有能力的年轻人上,避免“抛物线”下降阶段给国家带来的损失。
谁能说,这不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王振义,老马识途甘为人梯,培养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血液学研究俊才。
4. 为人:坚如磐石是忠诚
家里客厅墙上那幅《清贫的牡丹》是王老的最爱。“画里有清静向上的意思。做人在事业上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又要正确看待荣誉,对身外之物要有自我约束的力量。”他说。
“我们家没什么好东西。爸爸最宝贝的,就是这两捆袜子。”王老的儿子说,这些袜子爸爸舍不得穿。
原来三十多年前,王老治好一对夫妇的白血病患儿。当时没电话,也没留联系方式。王老工作几经调动,夫妇俩找了他三十多年。三年前,他们带着儿子登门感谢。“我们儿子的命是您老捡回来的。他现在身体棒棒的,没什么大出息,靠卖袜子维持生计。这些袜子给您暖暖脚。”夫妇俩朴素的话语,震撼着王振义。
当然,让王老牵挂的,还有与他结发一甲子的妻子谢竞雄教授。“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对爱人缺乏同情心。当年她生小孩,我都没在身边,对她关心不够……”王老看着老伴遗像,眼睛湿润了。
6年前,老伴得了老年痴呆。这让王老十分心痛:她和他在医学事业中相识、相恋、相伴,她是在他失意时鼓励他、支持他的爱侣。
痛,渗入他的心底。在她生命的尽头,他只想好好陪陪她。过去6年,王老没出过差。早晚陪在老伴身边,跟她讲话,尽管她越来越没有回应。中午,他回来看她,打一盆热水,拧一条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抬起手,轻抚老伴稀疏花白的发丝。半个多世纪的相濡以沫,两颗心早就长到了一起。老伴喜欢孩子,他把3个孩子从小到大的照片拷到光盘里,在电脑上一遍遍放给她看。
王老说,最高奖也是给我妻子领的,军功章啊也有她的一半。
病人说,王大夫是我们心中的灯盏;学生说,王老师是我们脚下的石级;妻子说,王振义是此生无悔的依靠。谁能说,这不是一片赤诚?妙手仁心,大医精诚。王振义,一辈子忠为衣兮信为裳,一辈子在大爱中行走,温暖着身边所有的人……
2011年1月15日,上海交通大学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王振义教授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登台发言时,王振义擦拭眼泪说:“今天非常感动,其实我的工作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方向、一个药、一种病。现在我获得这个大奖,回想起当年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搞研究,不能忘掉这么多同志的努力和协作,其中有我们研究人员、团队付出的辛苦和许多医疗机构的帮助,否则的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证明这个药是有效的并在全世界迅速推广。”
王振义激动地说:“人生有终了的时间,我已经接近古稀,回想起当年作为血液科的医生,看到白血病患者非常痛苦,家属背负沉重的包袱,才将白血病作为研究方向。现在我仍要努力,再做对人民有贡献的事情。”他谦虚地说:“过去是我领导我的团队,现在是跟着团队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