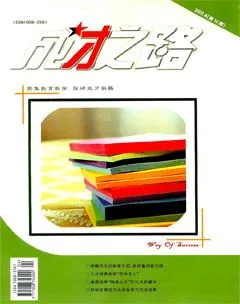凭什么成就卓越
2011-12-29张在军
成才之路 2011年10期
二、初试啼声
2.秀才
(一)
秀才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上小学时就喜欢谈古论经,就有了“秀才”的雅号。
上完高中,秀才再没上大学二学,背一捆书回村了。
秀才还常谈古论经,有时就抱着几斤沉的书本子猛啃,啃够了,就做庄稼活路。耕刨播锄都干,和村里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常见他上山做活时手里常拿着个书本子边走边看。很多人都怀疑秀才会不会做庄稼活路,就去偷着看。于是,村里马上就传出一条叫人笑掉大牙的新鲜事:秀才做庄稼活竟看起书来。播种了,看一看播一播。于是,好几天村里都有了笑谈。
(二)
村里出了件大事。
小学校里的魏先生死了。这里的人是把老师叫先生的。
这事叫村里人难受得要死。多好的先生!咋说死就死了。真应了那句好人不长寿的话。
魏先生就是这村人,年纪还不大,才六十多岁吧?教书的年头可长了。大约是土改的第二年,上边叫村里办学堂,他就当先生了。那年还不到20岁。魏先生也从没进过校门,只是跟他那上过私塾的爷爷学过些字。那年他爷爷七十多的人了,耳背眼花是不能再当先生的了,就让他当了。魏先生是极用功的,晚上跟爷爷学一些,白天再教给娃们。就这么“教学”了一年,他爷爷死了,魏先生就买了一部大字典边学边教。一教教了这几十年,村里识些字的哪个不是魏先生的学生?秀才自然也不例外。魏先生对秀才可不怎么喜欢,这娃机灵倒机灵,就是鬼儿花哨,常问得先生下不了台。也多亏像他这样的学生少,要有两个三个,他还怎么教?
魏先生教学生,村里人是极放心的。他脾气好,从不大声呵斥学生。学生解手了,他给解腰捆腰。学生流鼻涕了,他给擦洗擦洗,是从不嫌脏的。
最叫村里人满意的是魏先生的上课。娃们进了校门,他就大声喊道:解手了解手了有手没手解手了。之后,便聚到屋里,这一上午是再不叫出屋的,他魏先生自然也不再出屋。他身体不好,常坐着上课。教一会,学生十遍二十遍写着生字。他就捂揉上一烟锅子烟,打着火镰点上;吃透了,再脱下一只鞋,把烟火磕进鞋里,再捂揉上一烟锅烟,把烟锅扣在鞋洞里的烟火上再吸着。一上午下来,烟灰往往是磕半鞋的。吃透烟了,娃们也把字写二三十遍了,他便一个个批,再叫娃们改错。
对改错字魏先生要求是极严的,每回他都要求学生把错字改一百遍,之后他再一个个打一百个对号或错号。
一天少下三节课,就多学十个字。一年多少?二年呢?五年呢?这笔账,家长是极会算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古人早有哲言。
多好的先生!说死就死了。不知道得的什么病,一下子死在讲台上,那会,他刚给一个学生画完一百个对号。
(三)
学校是不能没先生的。管学校的干部来了。这里太偏远,公家人不常来。干部问你村有没有高中生?村主任说有一个。干部说叫来我看看。
秀才来了。干部一眼就看中了。这后生很精明的,公家也没多余的先生派给你,就叫他干吧。又问秀才:“你愿意当先生?”
秀才说:“愿意。”
“那好!你干了。”
秀才就当先生了。
(四)
死了一个老先生,来了一个嫩先生。娃们都觉得新鲜。
秀才先生一上任,一天就不再上两大节课,改上五节六节。这秀才再不像魏先生那样整天板着脸。教认字,教算题,还教娃们唱歌跳舞。最使娃们新鲜的是秀才先生竟教他们说广播里的话。娃们觉得好新鲜,纷纷跟先生学撇腔。
秀才说,不会说普通话将来做事是很妨碍的。说山里话人家就不懂。比方咱说“早已来霎”,外边人就不懂,要说“以前”。秀才教娃们,“秫秫”叫“高粱”,“家衬子”叫“麻雀”,“姐留”叫“蝉”。教一句,娃们就撇着学一句,就笑一阵。
(五)
学校里的新鲜事,娃们家总是喋喋不休的。于是,家长们都知道了秀才教娃们撇洋腔了。这可不是小事。头些年讲“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那是指大学生,现如今刚上小学就撇上洋腔了,你说了得不了得?
带着怀疑,带着不满,狗剩和活神仙吆喝家长们来看新鲜。无事不进学堂,就在学校远处瞅吧。里头正在上课,嘻嘻哈哈赶集一般。先前学生听魏先生的课,气都不可大喘的,这回呢,光听娃们嘟嘟讲,先生才讲三两句。
下课了。这一霎就下课?看,真跳舞了!男娃女娃手拉手,笑眯眯地对眼瞅。跟电影上没两样。
要血命了!以前山民们看电影上有这场面都是低下头合上眼的,只有不正经的下三滥才干那活儿,现今好,八九岁的娃娃学会了!
“坏了坏了,我就说这小子不地道,做庄稼都看书本子呢。”
“昨夜里还带娃们钻玉米地呢!半夜五更的,说什么看夜猫子逮老鼠回来写文章,这不是疯了?”
“唉,今下午就没上课,领娃娃爬山了!有背锅的,有拿米的,一个个疯疯癫癫搞野炊去了……”
村里开了锅。
(六)
家长们呼呼拉拉蹿到村主任家。
村主任正在吃饭,来福、坤明带头呼吁:快换!
村主任很为难:“人家公家叫干的呀。”
“还要不要咱庄的娃?”
大伙七嘴八舌,唾沫星子差点把他淹死。
村主任只好点点头:“找个先生也不是易事,咱村数他学问高了。我去劝劝他,他若改了邪,就算。这娃我有数。”
众人齐嚷,快劝!
(七)
村主任来到了学校。秀才正在上课,洋腔果然猛撇。先生撇,学生撇,直撇得老主任浑身起鸡皮疙瘩。听完课,他又亲自点:“听说娃们还会跳舞。”
“会会会。”秀才忙不迭地点头。
“跳跳可中?”
“中。”秀才便叫娃们跳舞,男娃女娃手拉手,脸对脸儿眯眯笑。
主任来到了办公室,吧嗒着旱烟开了腔。
“秀才娃,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家长的反映满我耳朵了。你想想你先生老魏先前是咋教你的,你就照他那么教吧,别再折腾娃了。”
“不行!”秀才斩钉截铁,“我的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主任沉起脸:“还这么教?”
“还很不够!”
主任叹口气。“秀才娃,你当先生也是公家来点头的,可家长有大意见。实在没法,明日咱开村民会表表态,多数同意,你就再教!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八)
第二天,村里召开了村民会,老主任给每位村民发了票纸,同意秀才当先生的,画对号,不同意的画差号。秀才在主席台上讲了话,大家只顾忙着画票,讲的什么谁也没心思听。画完票了,秀才还在讲呢,有日本人重视教育就飞了,有未来的社会什么样什么样,直讲得大家都打呵欠。老主任收票了,他还讲得起劲。票的结果出来了,他才“咯噔”打住不讲了。
他只得了一个对号。这个对号是谁打的,实在无须动脑去想了。
村里又让来福当了先生,来福上过小学。人老实巴交,因为老实,订婚几年的未婚妻都跟一个养蜂的远走他乡。社会发展了,再不能找个晚上学白天教的先生了。来福刚上任,村民们又去远远地瞧新鲜,瞧过之后,都一致评论,比秀才强多了,只是比魏先生还差得远,不过时间还长,可以慢慢锻炼。众人评论着往家走。于是大家更怀念魏先生,像他那样的好人好先生是绝不应该走那么早的。
秀才呢?村里不常见了,整天骑着一辆破车子满山转,转了这村转那村,还不时掏出本子记上些什么,看阵势八成真疯了。
3.山这边山那边
单人教师学校,所有课程由我一个人上。
我最挠头的是音、体、美等课程。美术课要搞剪纸,要画简笔画,这简直是赶鸭子上架,我得一点点学会了,再教给学生。体育好说,队列、队形、体操、正步走、做游戏。几个年级先集中在一起跑几圈操,再分年级进行活动。这样的课孩子们喜欢上,兴致很高。
村子小,村人们文化生活贫乏,一听学校里吹哨子加“一二一”的口号声,大男小女的就奔走相告来学校看热闹。校门是不能进的,只好搬块石头坐在西边的坡上往这边看。
这时候,往往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跑的跳的喊口号的,无不竭尽全力。一个院墙隔开两拨人马,但喜怒哀乐的情绪往往是相互牵动的。
我最棘手音乐课。
上小学、初中、高中时,正值特殊时期,除了数理化断断续续开设一些外,学校里很少开音、体、美这样的课程。记忆中也就是李春溪老师忙里偷闲地为我们上几节二胡欣赏课。自己脑子里没有这样的积蓄,很犯愁这课怎么上。要撒播阳光到别人心里,自己心里多少总得有点吧。请教周围老教师,都说这课开不开无所谓,联考统考又不考这样的科目,不如腾出时间来多教学生几个字实惠。
我总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我苦苦思索着路子。
这天傍晚,我到山那边锥子崮南的云头峪小学找赵焕祥老师交流。
为招待我,赵焕祥安排他上初中的四弟赵焕军去好几里路远的王庄镇上买来几斤肉。
赵焕军灵活、机敏,跑前跑后地忙活烫酒端菜。一边吃,我们一边交流条件落后的学校如何开全课程的话题。
我说了其他教师的看法,什么上音体美课不如让孩子多认得几个字实惠等等。
赵焕祥不同意这个观点,说孩子从入校门到离校门,老是摁着语文、数学课不放,孩子厌烦了,学校也太沉闷。童年应该是百灵鸟,要飞翔,要歌唱,要舞蹈才行。
吃过饭,太阳要落山了,小鸟们啼叫着归巢了,我要回去。赵焕祥让我住下,我说不行,我快回去要誊抄书稿。赵焕祥问是什么书稿,我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一本书《怎样辅导小学生作文》,我白天上课,要靠晚上抽空誊抄,出版社催了好几次了。一边在吃煎饼就大葱的赵焕军说,我给你抄吧,我正好没事。我说,十多万字,你也要抄些日子。赵焕军说,没事,你把稿子捎过来,我保证一个星期交给你。
第二天,我托人把书稿带给了赵焕军。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天,他就把干净、漂亮的誊抄稿送来了。我问他这么快啊。赵焕军说,你认为我自己抄啊,太累了不说,时间真来不及。我班里很多写字漂亮的,我让大家帮忙誊抄的。我问大家都听你的?赵焕军说,怎么不听,我有办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动动脑子指挥指挥就行了。你别问什么办法,暂时保密。能给你抄写文章,对他们是个荣誉啊。我笑了。
就是这个机敏、智慧的赵焕军,从小就显示出不俗的管理才能。后来,他一路打拼,成了某传媒集团的总裁。这是后话。
一天夜里,赵焕祥在我学校住下,我们正闲聊呢,一阵山风隐隐传来悠扬的笛声。循声音听了听,声音来自东边的东西棋盘。东西棋盘与我村相距二里路,中间是崎岖的碎石小路。我村子在纱帽崮的东坡,东西棋盘在东汉崮的西坡XzkXmmkzFIQBdVOKM0jfLg==,西村中间是一条小河。每年汛期,四周山崮的流水汇集到这条河里。汛期一过,河里没有了水,只剩下一河底七大八小的碎石。两山相望,一河横中,两村的房子零零落落宛如颗颗棋子,两座山就像下棋的老人,干河就是河界,东棋盘,西棋盘因此而得名。
我身上的哪根神经被这笛声轻柔地撩拨了一下,遂约上赵焕祥,拿上手电筒,循着声音而去。
走过干河底,就是东汉崮的山坡,上坡行走几百米,笛声、二胡声渐渐清晰了。
声音出自东西棋盘学校。
手电筒晃动的亮光把我们引进了校园。院子里,几十个村民正围着两个乐手听他们的演奏。地上星火点点,驱蚁草散发着苦艾的野草味。办公室里面窗台上如豆的油灯透过玻璃发出微弱的光。今夜风大,在外面是点不住灯的。
见我进来,二位乐手停止了合奏。年龄大点的这位是张厚元老师。年轻的是李京峰老师,刚从师范毕业参加工作不久。
握手,打招呼。是你们悠扬的乐声把我引来的。我和赵焕祥说明来意。
张厚元老师离家近,回家去提水。李京峰和我们闲聊,村民们饶有兴味地听着。
听了我和赵焕祥的话,李京峰很有同感。他说学校没歌声还叫学校吗,连音乐课本也没订啊,先从教歌开始吧。赵焕祥说,我听到你们的曲子了,是“桃花盛开的地方”,孩子学这个难度有点大吧。李京峰说,广播里唱,大人们也哼哼,孩子们有点基础了,好教,今下午教会了两个年级。
东棋盘学校有五个年级,张老师教二四年级,李老师教一三五年级。
说话间张老师回来了,沏茶倒水继续闲聊。我拿过笛子,开始练习国歌的旋律。半个小时的时间,有个大概的意思了。
第二天早晨升国旗仪式上,在孩子们行队礼的时候,多了笛子的伴奏。《国歌》的旋律使得平常的升旗仪式多了几分庄严、肃穆。
从这个月开始,西棋盘学校有了歌声,村子里多了一只只快乐的百灵鸟。我教孩子们唱哪首歌,不过几天在全村大人们中逐渐传唱开来。开村民会,常会叔总不忘让学校的孩子们到场来几支大合唱以活跃气氛。小山村开始有点生机了。
在赵焕祥的努力下,云头峪小学也开全了音体美课程。后来,因工作需要,赵焕祥去了省报社。再后来,他去了北京,先后在多家报刊任职。凭着独有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在新闻界已经有了一片属于他的天空。
赵焕军也先我们一步来到北京发展,干出了骄人的业绩。京城节奏紧张,我和焕祥、焕军总忘不了忙里偷闲聚一聚。
焕军也是他哥赵焕祥的学生,一次焕军问他哥,教书的日子是不是很乏味啊?赵焕祥说,教了十来年书是幸运的,一是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二是结交了张在军这么一个好友。赵焕祥的话也是我的内心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