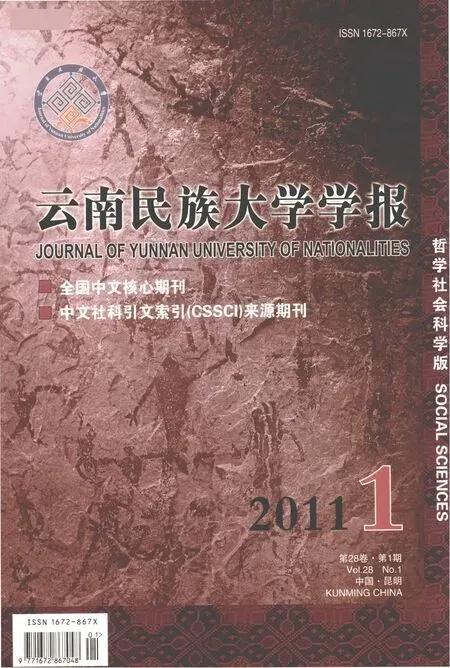“品式”和西晋 《户调式》研究
2011-12-10张尚谦
张尚谦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031)
“品式”和西晋 《户调式》研究
张尚谦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031)
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视作“常事”,制订有“品式章程”。“式”即“样”,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用作“比”,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式”方面的规定,与“户品”等配套,作为划分户等、按等纳税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包括“户样”和“调样”两项内容。杜佑写《通典》,不知“品式”为何物,把西晋《户调式》中“占田”、“课田”规定误为土地制度,从“式”中抽出,放在其《田制》篇中,剩下的内容生硬缝缀,当作赋税的“令”,归入《赋税》篇。 《通考》沿袭杜佑的错误观点,仍视“占田”为国家授田,虽认为“课田”系“租税”,按户缴纳,有一些进步,但无法解释“式”。现今治史者或是遵从杜佑的思路和方法,或是遵从马端临的思路和方法,也有进步,却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品式;户调;样;占田;课田;混通;户品;比照;折算
一
西晋赋税不入“律”、 “令”,而是作为“常事”,即一般事务,制订有“品式章程”。
“品式”流行于两汉, “式”即“样”,一种制度的标准和典型模式,与“品”制结合,遂有“品式”的称谓,和“故事”一齐,同为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书·孔光传》: “光以高第为尚书,观故事、品式,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魏晋时期,“品式”制度臻至顶盛,西晋将汉代以来的律、令、故事、品式等进行了整理订定,修订出“律”、“令”和“品式章程”三大部分,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章程”,又称“故事”,即是说原先的“故事”已被“品式”取代,援“例”而行吏事已基本不用了。
“品式”的普遍化是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现象,可惜留下的资料太少。前、后《汉书》未留下“式” (样)的实例,无法见识两汉的“式”具体是什么样子。魏晋时期的“品式”留下来的也不多。围棋有“品式”,分为九品,一品的“样”为“神化”,但围棋“品式”不规范, “神化”作为一品的“式”太过笼统,看来那只是仿照“品式”制度而有的仿制品。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唯一规范而又较完整的“品式”实例,是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其内容十分丰富,从现在能见到的史料看,它至少包括:
1.户品制,亦即户等制。征收赋税时先要将民户划分为“九品”(九等),按等纳税。
2.《户调式》,即《户样》和《调样》(赋税额样),规定“一夫一妻占田百亩丁男作户主”的“户”为民户的标准户型, “女及次丁男当户者”为“半标准户”。“赋税额样”为“标准户”每年缴纳的税额,国家抽收标准户“占田百亩”之半,即“课田五十亩”,而有的“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这是一种标准税额。
3.赋税征收的“九品混通”法以及“比照”和“折算”的方法。
4.官品式和荫客式:以“官品式”为基础的“荫客式”,规定免税范围的标准。
5.诸侯王封地租调收入划分的原则章程。
以上诸规定是相互关联的,基本上是“配套”的措施,其中又以《户调 式》最为重要,是核心内容且独具特色,既展现了西晋独具一格的赋税制度的特点,又展现了“式”制的风貌:
1.“式”作为“样”,用作“比”,要求“比照”而不是“遵照”执行。 《户调式》亦用作“比”,是赋税征收中划分户等,按等交纳租调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依样定户上下”是其主要功能。
2.“式制”不仅是等级制度发展的产物,也是形式主义盛行的结果,因此,“式”都有形式方面的规定,“装样子”的规定。《户调式》中“占田一百亩”就是装饰“户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汉代以来政治理论家都宣传一夫一妻的五口之家,拥有一百亩土地,是一种最理想的编户情况,因此《户调式》中“户样”的制订才有“一夫一妻占田一百亩”的说法。这是一种理论上形式上的规定,无实际意义。西晋将赋税列为“常事”而制订“品式章程”后,赋税征收,至少主要项目“租调”的征收,已不考虑民户土地占有数量的多少。“比照”,进行户等划分时也不考虑土地的数量,也无法考虑,“土地数量”无法“比照”。当然交纳租调的编户都是有土地的,虽然多少不等。西晋“女则不课”,只有“当户”的女子才代表一种“半标准户”纳税,因此,进行“比照”来划分户等时,“丁”(包括次丁)的数量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但赋税是按户缴纳的,“比照”是“户型”之间的“比照”, “丁的数量”是不能直接进行“比照”的,须要把“丁”折合成“户”或户的一部分,这就有了一个“折算”问题。西晋“折算”方法是:每户除了“当户”的“丁” (或次丁)外,如还有一个“次丁”的,户等上升一个等级。两个“次丁”折合一个“丁”。
“课田五十亩”也是一种理论上和形式上的规定,是“赋税标准额”理论上的“依据”,而实际上“标准额”(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的制订不是“履亩而税”而有的。它是参照历史上“租调”征收的数额、国家财政需求以及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等因素而确定下来的。
西晋以“标准户”为“中中户”的基样,“五等户”交纳“标准税额”(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半标准户”为第九等户的基样,交纳“标准赋税额”之半。中等以上户租调递增,以下户递减,每一等的级差为“租五斗、绢一丈二尺”,结果,一等户和九等户 (二等和八等……)租调相加再平均,仍为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和“标准额”相同,即仍然是“标准”、 “理想”的税额和民户纳税情况,这就是“九品混通”法。“混通”之制不限于赋税征收,繁琐又碎而难行,却也是形式主义盛行的反映,带有形式主义色彩。
西晋按户收租调,不考虑编户土地数量,关注的只是人丁数。这影响到后来,构成了长达三个多世纪古代国家赋税制的突出特点,但“九品混通”却较早被废弃了。
二
“式”制演变至唐代有了很大变化,唐代仍然有“式”,《唐六典》:“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令、格、式,四项并举,足见“式”制亦相当重要,但将“式”界定为“轨物程事”,表明原先“样”的含义已十分淡漠了。这种情况可能影响了唐代人对两汉魏晋“式”制的认识。唐代还能见到一些有关西晋《户调式》等“式”制的史料,但许多情况说明唐代大多已对以前的“式”不甚了了。唐人为《后汉书》作注,作“样”解的“式”都注为“法”。《后汉书·马援传》: “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 《注》: “式,法也”。唐初编纂的《隋书》在《经籍志》中收录了当时尚能见到的西晋以来称之为“故事”、“旧事”的25部著述的书名,部分有作者姓名。这25部著述虽已看不到内容,从书名看,既不是两汉作为“决事比”的“故事”,也大都不是西晋作为“品式章程”的“故事”,它们实际上大都是史学著作或史料编纂之类的著作。《经籍志》将其归于“旧事篇”混同于两汉的“故事”,又与西晋“品式章程”的“故事”拉扯在一起,说明编书者已经不清楚“故事”的演变以及“品式”的意思了。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关于西晋《户调式》的直接史料有两种:其一是唐初编的《晋书》,在《食货志》中记述了西晋统一之后“又制”的《户调之式》:
及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
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女丁男当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宗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田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见从武贵、殿中武贲,持锥斧武骑武贲,持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这份史料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直接引用的,使人们得以见到《户调式》原貌。由于《晋故事》这种档案材料早已佚失,它就成了唯一的一份历史资料,记载了西晋《户调式》的具体规定内容,但也有严重的缺陷。西晋在泰始三年已经有了收载常事“品式章程”的档案——30卷《晋故事》,其中自然包括有赋税的“品式章程”。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意思应该是只对赋税“品式章程”中的“式”制作了修订,虽然它是最重要的,却毕竟不是全部内容。《晋书·食货志》在“又制户调之式”后引述的应该只是《户调式》的规定,但却在《户调式》引述完后紧接着又引了“官品式和荫客式”的规定,而且只多引了赋税“品式章程”中的这一项。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引述,表明《晋书》的作者似乎已不太清楚“式”的意思以及《户调式》都有哪些规定内容。这也影响了后人对《户调式》的认识。另一缺陷是在引述“其丁男课田五十亩”后漏引了“亩收租八升”或“收租四斛”等字眼。漏引是如何造成的,也还难以确定,是否传刻时出的问题,也未可知。漏引使得《户调式》中关于“租”的数额规定不见了,或者说含混不清了,同样增加了后人对《户调式》理解的困难。
另一份材料是唐徐坚《初学记》中转引的《晋故事》中关于西晋赋税“品式章程”的部分规定内容:
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
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升,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候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候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匹、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
这是一份难得的史料,价值极高:
1.《晋书》等史书明确记述西晋的“常事”有“品式章程”,收载于《晋故事》档案之中,但未明确说西晋的赋税属“常事”。这份史料则明确说西晋赋税规定是收载在《晋故事》中的,证明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而是作为一般事务,制订有“品式章程”,而“品式章程”为“故事”。能证实这一点,意义重大。
2.这份史料概括性地转引了西晋《户调式》,虽然从中无法了解《户调式》的具体条文,但《户调式》的要点都概括出来了,抓住了《户调式》精神实质。概括转引表明“官品式和荫客式”不是《户调式》的内容,还证实《晋书·食货志》引述西晋《户调式》在“丁男课田五十亩”之后确实漏引了“亩收租八升”或“收租四斛”等规定内容。
3.概括转引的《户调式》,不仅表明西晋赋税按户征收,“租”和“调 ”都按户收,而且把“式”的特点也凸现了出来。 “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显然不是“履亩而税”,表明“课田”规定无非是一种理论上和形式上的说法,并无其他什么实际意义。另外,西晋时称“户样”(标准户)为“丁男之户”,这是一种简便的称呼,有时甚至简称为“丁”。这则史料中说的“凡民丁课田”,意思也就是指“标准户课田”,并非每户只有一个男丁,或每户以“一丁计”。对“户样”的概括叙述中,不引“占田一百亩”的规定内容,也显示“占田”规定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无实际意义,不关紧要。
4.这则史料表明,诸候王封地租调的划分是以《户调式》为基准的,在“样”上分割。按“三分食一”的原则,“标准户”交纳的“标准税额”“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应划给诸候“租一石三斗、绢一匹、绵一斤”。可能考虑到划拨给“绵”这类原材料,诸候难以处置,就用了不划给绵而增加“租”的变通办法,结果实际划分给诸候的为“租二石五斗、绢一匹”。这表明《户调式》的功能还不限于划分户等和按等定税额,其用途还多。
5.这则史料表明,西晋赋税“品式章程”中还有诸候王封地租调 分配的原则章程, “赋税故事”内容十分广泛。
6.这则史料明确指出西晋赋税征收有“九品混通”的方法。
7.这则史料和《晋书·食货志》关于《户调式》的记载相互比较,相互印证,使许多含混不清的问题清晰起来了。
总之,唐代能有这两份关于西晋赋税“故事”的材料,特别是其中“户调式”的史料留了下来,已是很难得的了。
遗憾的是唐代史学家杜佑写《通典》并未同时使用上述两份史料,依据的只是“正史”的记载,即《晋书·食货志》的记载。 《晋书·食货志》的记载,如前面已指出的,已经有问题了,而杜佑也不懂“品式”,不知道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而是作为“常事”,制订有“品式章程”,又称“故事”,不知道“式”作“样”解, 《户调式》就是“户”和“调”的“样”,结果在引用《食货志》的记载时,把西晋《户调式》任意裁剪分割,从而弄得它面目全非。首先, 《通典》将《户调式》中修饰“户样”和“赋税额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 “占田一百亩”、“课田五十亩”,从“式”中抽出,放到其《田制》篇中,无中生有,制造了一个作为土地制度的“占田、课田制”:
平吴之后有司奏王公以国为家,京城不宜复有田宅……今可限之:国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处,近郊田大国十五顷,次国十顷,小国七顷,城内无宅城外有者皆听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其官品第一品五十顷,每品减五顷以为差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依品之高卑荫其亲属……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
《田制》篇基本上是史料堆积,而且即使从收集史料的角度看,质量也很差,杜佑并未对史料作起码的甄别。西晋统一之后制订的关于“国王公侯”在京城及京城近郊拥有宅第和土地数额的限制规定,目的在于促使诸侯王就国,也有维护中央皇权的意思,不是什么重要的土地制度,严格来说还算不上是土地制度。官品占田规定是“官品式”,官的“品样”,官分九品而一品的“样”就是拥有五十顷土地。这和实际上一个一品大员拥有多少土地是两码事,也不是规定一品官可以占五十顷土地。“官品式”根本不是土地制度。至于“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等等,则分明是杜佑不懂西晋的“式”制,不知道那只是装饰“户样”和“调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看见有“田”的字眼就当作土地制度而收入“田制”篇中了。杜佑不懂“式”,从而编造了一个“占田、课田制”假命题,贻害无穷的假命题。
抽掉了形式方面的规定, “样”已经受了损害,一个重要的特征不见了, 《通典》将剩下的《户调式》内容归入其《赋税》篇中:
晋武帝平吴之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当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宗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不课田者输义米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这些记述虽都是《户调式》里的话,但经过杜佑的剪裁和重新缝缀,已完全扭曲了《户调 式》的面目而且文理欠通,让人难以读通:
1.杜佑不知道“式”作“样”解,把西晋平吴之后“又制”的《户调式》误解为西晋赋税的法令了。
2.“户调”一词原指按户抽收的绵、绢等实物税,后来“调”有更广泛的含义,指包括“租”在内的赋税。《户调式》名称中的“户调”意思又不一样,指“户”和“调”两项,《户调 式》就是这两项的“样”。 “调样”以“户样”为基础,包括了两个“子样”:一是作为狭义的”调”的“样”;一是“租样”。杜佑把《户调式》理解为狭义的户调的法令,即按户抽收“绢、绵”的税令,结果不仅显现不出“样”,特别是“户样”,也把“租”排除在赋税“法令”之外了。西晋不收“租”税?
3.《户调式》中关于夷人“不课田者输义米”的规定是和一般民户的“课田”规定相对应的,有“课田”者才有“不课田者”。《通典》把“课田”规定抽出后,对夷人“不课田者输义米”的规定难以处理,因为很难把“夷人输义米”也算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不得已只有留在他认定的“户调令”规定之后,结果这份记述就无法读通了,怎么在“户调令”之后冒出了一个“不课田者”呢?没有“课田者”就无法理解什么叫“不课田者”。这是一道文意欠通的“赋税法令”。“法令”中有对夷人征收田税的规定却唯独没有对一般民户抽收田税的规定,这是不可理解的。
南宋郑樵写《通志》,抄录了上引《通典》的记述。元代马端临写《文献通考》,基本上沿袭了杜佑的观点,但他可能看出《通典·赋税》篇对西晋赋税“令”的记述文意欠通,又缺乏“租”税的规定,因此在引述西晋《户调式》时方法有所改变,《文献通考·田赋》:
晋武帝平吴之后置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夷人输宗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又限王公田宅及官品占田
《通考》的引述遵循了《晋书·食货志》的记述层次,未再分割和缝缀。同时,马端临认识到“课田”规定和“租”税有关联,对上述引文作“按语”说:
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付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似合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
显然马端临认为《户调式》中有“租”的规定而且也是按户抽收的,这比杜佑高出许多。马端临还指出西晋“无无田之户”,就缴纳租调而言,这是实情,但他也把“式”理解为“法”, 《户调式》就是西晋赋税的法令,并把其中“占田”和“课田”的规定理解为土地制度:
按夹祭郑氏言,井田废七百余年至后魏孝文帝纳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然晋武帝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则亦非始于后魏也,但史不书其还受之法,无由考其详耳。
可见,马端临也是把“占田”等规定当作土地制度来看待的,认为那是国家授田制。这样《通考》也留下了一个大难题:何谓“户调之式”?它究竟包括了哪些规定内容呢?照《通考》的记述和理解,又制的“户调之式”下面,先有一个“户调”方面的规定 (令),即户出的绢,绵以及夷人输的宗布,然后是国家授田令:“占田”和“课田”的规定,再后又是“租”方面的规定,最后还有“又限王公田宅及官品占田”一句话,一个“户调之式”怎么能包括如此广泛,不同项目的内容呢?这个“户调”又该作何解?“式”作何解?《文献通考》对此未作交代,它的这个“户调之式”也是一个不伦不类的、说不清楚的东西。
《通典》和《通考》都涉及了西晋的《户调式》,都误解了它。
三
近现代的历史研究中,两汉魏晋的“品式”制度被忽略了,甚至根本没有提到过它,历史研究者也未注意到西晋的赋税是当作“常事”来看待的,制订有“品式章程”。倒是《户调式》吸引了众多治史者的眼球,论述之多,让人难以卒读。遗憾的是所有关于《户调式》的著述都接受了杜佑的错误观点和解说,尤其是杜佑编造的“占田、课田制”这一假命题,虽然具体的解读多种多样,但任何赋予“占田”、“课田”这种形式方面的规定以实际意义,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仔细地分析,现今对《户调式》有两种解读:
(一)一种遵循了《通典》的思路和方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晋武帝户调式研究》一文最具代表性。
1.接受《通典》的观点,把《户调式》第一大项目的规定界定为“式”的全部内容,不了解“式”即“样”,结果《户调式》不过就是按户抽收“绢、绵”,等实物以及向夷人征收“宗布”的规定。唯一进步的地方是不敢明确地把“式”解释为“法”,指出“户调式见于《晋书》卷26《食货志》,文意极其含混。”但又说:“《晋书·食货志》只提到户调式,紧接着叙述田制”。可见实际上和杜佑的观点一致,只不过弄不明白“式”的意思,不愿明确指其为“令”而已。
2.沿袭《通典》,也把“占田”、“课田”规定与《户调式》切割开,当作“田制”来解读,但不再把“占田”解释为“国家授田”,而是说“占田有限田的含义”、“是对一般庶民拥有田地限额的规定而决不是政府对之负有授田的义务。”然而“限田”主张和“限田法”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西汉中期以后土地集中趋势明显,土地兼并盛行,小土地所有者大量破产,政治理论家认为帝国的强盛依赖于掌控尽可能多的向国家纳税服役的“编户齐民”,因此才先有董仲舒的“限田”理论,后有孔光的“限田法案”。虽然无法实行,却都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西汉以后“限田”思想还存在,但古代国家再也没有“限田”的政策措施。把“占田”解释为“限田”,却避而不说西晋统一之后是什么样的社会历史状况、条件,什么原因,促使国家再次面向全国颁布“限田”令呢?西汉“限田”是限制官僚贵族大土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西晋却要限制的是“一般庶民”占有土地,一般庶民不可能占田“逾制”。他们往往是被兼并的对象,根本不存在对他们实行“限田”,防止他们“兼并”土地的问题。“占田为限田”说是随意编造出来的,它还带来了许多新麻烦。
对“课田”的解释就更为离奇。《户调式》中“丁男课田五十亩……”的意思是清楚的,说明“丁男”要缴纳五十亩土地的“租税”,国家要征收“丁男”五十亩土地的“租税”,这当然是对向国家纳税服役的编户而言的。如同“占田”的概念一样, “课田”一词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动宾结构”来使用的,不是一个普通名词或专有名词,即使不懂“样”,不知道“丁男”指以丁男为户主的“户”,甚至不知道“课田五十亩”的租额为四斛,但“课田”是一个“动宾结构”,这一点还是明确的。《晋武帝户调式研究》①宫崎市定《晋武帝户调式研究》,日本学者大多推崇此文,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 (中华书局,1993),编译者称“选译”的是日本一流学者的一流文章。国内高志辛同志有《西晋课田考》一文。(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借用宫崎市定的说法,称“西晋课田是由魏的屯田转变而成,它是西晋政府承袭了屯田的农民和土地”一文却解释说“课田是授田”,援引《晋书·傅玄传》付玄说的一段话:“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突然得出结论说: “这里的课田,无疑是指分配给屯田兵督其耕种的田地。”这不合付玄说的话的意思,傅玄说“魏初课田”指的就是魏初征收田租,实际上是把“课田”当做一个“动宾结构”来用的。 “课田是田地”曲解“课田”的含义,把“课田”由一个“动宾结构”篡改为一个普通名词,傅玄话的意思就不通了。另外, “课田”作为一个“动宾结构”并未涉及到所“课”之“田”的性质。屯田兵当然耕种的是官田,但“课田”一词中不包括土地性质的内涵,向屯田兵征收田租叫“课田”,向一般民户征收租税也可以称作“课田”。未查到把“课田”当作普通名词使用的史料,即使有,也只能解释为“课税之田”不包含土地归属的内涵。西晋以后有“课户”的术语,是普通名词,意思是“纳课之户”,但把田分为“课”和“不课”也不好理解。宫崎 市定用屯田兵耕种的是官田这一事实为掩护,采用蒙混的手法,不仅将“课田”曲解为一个普通名词,“课”用来修饰“田”,而且给这个“课”增加了一层意思:“分配给屯田兵督其耕种的”(田地),这样“课田”似乎就成了“屯田”中的专门用语了。宫崎市定又说:“这里的课是 [科派]的意思,因为是屯田,其土地收获量的一半必须上缴,这种义务也称作课。”这是又把“课田”当作“动宾结构”来解释,和指“课田”为“田地”的解释相矛盾。但宫崎 市定并不在乎逻辑混乱,他正是一会儿把“课田”当作普通名词,一会当作“动宾结构”,含混使用,交替使用,让人难以琢磨,使人们糊里糊涂地接受“课田”是“屯田”中的专用语的说法。这是他为进一步的推论编制的“前提”。经过这番铺垫之后,推出结论说:“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是政府的授田规定”,理由呢?解释说咸熙元年“屯田”被废除,屯田兵变成了一般百姓,但这类一般百姓耕种的还是原先国家用以“屯田”的土地,原先向国家交纳至少收成一半的租,成为一般百姓后国家不可能骤减其田租,“即使减轻,也不至于降到五成以下”,这不同于原先郡县民交纳的租税,这样西晋的一般百姓就分为两类:“以前屯田的土地用以课田,以前郡县编户的土地成为占田,以前的屯田兵适用课田法,以前的郡县民依占田法”,“课田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以一般百姓为对象的土地分配制度”。显然,这些解说东拉西扯,毫无逻辑,荒诞不经,其一,推论的大前提不真实,“课田”不是“屯田”中的专用语,大前提不真实,进行的推论是无法站住脚的;其二,推论的大前提含混不清,“课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作为“动宾结构”意为“征收田租”呢还是作为一个“普通名词”意为“分配给屯田兵督其耕种的土地”呢?两种意思差别太大,付玄话里的“课田”一词不能兼而有之,不能同时有两种意思。在大前提“含混不清”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合乎逻辑的推论;其三,推论的大前提不确定,一会把“课田”当作“动宾结构”来用,一会又当作普通名词。大前提不确定情况下进行的推论,只能是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其四,推论没有史实的依据。曹魏“屯田”由于史料限制,许多情况难以说清楚,但有几点是明确的,“屯田客”租种的是官田,不是小土地所有者,交纳的是“地租”,不是赋税。曹魏“屯田”虽然一度规模空前,却仍是社会经济自发发展的补充,当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后就不再需要它了。从曹睿时期开始,用来实行“屯田”的国有土地,特别是肥沃的良田,就日渐被官僚贵族侵占,而国家也把大量的“屯田客”赏赐给公卿。咸熙元年的废“屯田”,主要是指撤消管理屯田的行政机构,而那正是屯田制堕坏的结果,就整体而言,不存在把“屯田客”改变为小土地所有者的问题。“军屯”是另一回事,更不存在把士兵改成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一般百姓的问题。撤销管理屯田的行政机构在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户调式》颁布在“平吴之后”,即公元280年之后,两件事相隔起码16年之久,不能说“废屯田”和拟订《户调式》是“同时制定出来的”;推论出的这种“课田民”不伦不类,国家把他们当作“一般百姓”授田,他们是不是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呢?宫崎市定不肯明说,只指出“他们获得了移居的自由,即使离开课田,也不至于依军法问逃亡之罪”。又说“课田民”的“田租”不低于“五成”,这意味着交纳的是“地租”,不是“赋税”, “课田民”似乎又成了国家的“佃客”。《户调式》规定“丁男课田五十亩,”缴“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①文中所引《晋故事》史料是经过校正后的文字规定。,宫崎 市定显然未见到《初学记》引《晋故事》的材料,但也表明“课田民”交纳的“田租”不低于“五成”的解说是没有史实根据的主观臆断;其五,整个推论不仅逻辑混乱,还常常缺乏逻辑,许多话文意欠通。例如说“课田制”是对“课田民”的“授田制”,那么“丁男课田五十亩”就应解读为“丁男授 (或“受”)田五十亩”,“课田”又可作“授田”解,总该有一番解释至少该有一些逻辑的演绎,但文中未有任何的逻辑上的演绎。不作解释,也没有一点点逻辑的演绎,表明编造上的“乏力”。又如,先说“占田”为“限田”,又说“占田是土地”,存在有“占田民”,不仅自相矛盾,“占田是土地”的话也不通。
3.《通典·赋税》篇中记述的西晋“赋税法令”,是对《户调式》任意切割后缝缀起来的,重新缝缀时省略了几个字。宫崎市定抓住这点大做文章,提出《户调式》中“远夷不课田者输义来……”的规定中“远夷”两个字是“衍文”:“从文义上看,最初是‘远夷’,接着是‘远者’,另外还有一个‘极远者’,远字不能三次重叠构成文章。”这是故意挑毛病,因为最初的“远夷”是就整个夷人而言的,是相对于汉人等非夷人而言的,以后的“远者”和“极远者”,是就夷人本身而言的,意思清楚,可以“构成文章”。当然也可以不用“远”字,但“夷”字不能取消。宫崎市定实际上是想把“夷”字去掉,去掉“夷”字后,“不课田者输义米”就不是针对夷人的规定了。“不课田者是占田民,即在原来屯田土地之外,占有私有土地的百姓”。但是,如果把“夷”字去掉,“课田”和“不课田”两类并列了, “课田”即“有田纳租”是一般情况不加界定就是清楚的,“不课田”如果也是一般情况,不加界定也应清楚,但问题在于不加界定就不清楚,谁是“不课田者”呢?最后的“远者”和“极远者”都无法理解。“不课田者”不可能是一般情况,也不能有两个一般情况并列,它只能是特殊情况, “夷”字不能少。原记载说的“远夷不课田者”就指的是特殊情况,记述清晰,意思明畅,“夷”字不可能是衍文。《户调式》中“租样”和“调样”规定是相对称的,都是先规定“丁男之户”的税额,再规定“半标准户”的税额,最后才是对夷人作为特殊情况的赋税规定。而且如果“租样”是西晋统一之后“又制户调之式”时修订而有的,那么这修订明显是比照“调样”的结构而有的。总之,两者规定内容在结构上的对称是明显的。而且,如果“不课田者”不是指夷人,则《户调式》只有对夷人征收“宗布”的规定,没有收取夷人谷物的规定,这也让人无法理解。
宫崎市定又以《通典》记述中没有“远夷”两个字为根据,指“远夷”两个字是衍文,从而论证“不课田者”非指“夷人”,说是《通典》用的是“善本”,上面没有“远夷”两个字。从哪里出来的“善本”?宫崎 市定说不出来,解释说“可能”如此。按《通典》并非简单地照抄《晋书》里《户调式》的文字,而是切割其文字规定,然后重新缝缀。在切割和重新缝缀的过程中,略去几个字是正常的,不引“远夷”两个字显然是因为把夷人不课田而输义米的 规定系在“夷人输宗布”的规定之后,都是对“夷人”的规定,缝缀时可以省略也就省略了,压根扯不上什么“善本”问题。这本来是简单、一目了然的事情,而宫崎市定却从一个再简单、清楚不过的事情中制造出许多蹊跷来。还要指出,《通典》说:“不课田者输义米三斛”,省略了一个“户”字,这也清楚地表明,“远夷”两个字是省略了的,才又可以省略“户”字。宫崎市定不提《通典》还省略了“户”字或者说还有“户”字这个“衍文”,显然是有意迥避。
《通典、赋税》篇留下了一个让人读不通的西晋赋税“法令”,宫崎市定重新作的解说,更加无法读通。
(二)另一种遵循了《文献通考》的思路和方法,以已故史学大家唐长孺为代表。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以及何兹全先生编的《中国通史》也都沿了这种思路。唐先生在《西晋户调式的意义》一文中说:
式是一种法令 的名称.《唐六典》卷六刑部说:“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令、格、式是四种“文法之名”。照《食货志》所说,似乎所载的文件就称为户调式,但也可能所谓“户调之式”乃是后人综合相关法令而加以“式”的名称。不管怎样,《户调式》的内容包含了三个部分:一是户调之制;二是占田,课田制;三是荫族荫客之制。 《唐六典》刑部的注称:“晋命贾充等撰令四十篇……九调、十佃、十一复除”。户调式的内容实际上超出了户调的范围而牵涉到佃令,复除令的一部分。
这里,唐先生先是按唐代人的观点把“式”视之为“法”, 《户调式》就应是“户调”的法令,但又说:“不管怎样”,户调式包括了三个部分:一是户调之制;二是占田,课田之制;三是荫族荫客之制,“不管怎样”四个字把关于“式”的解释一下子勾销了,还是按照《通考》的思路和方法,解释《户调式》包括了几个不同项目的规定,结果还是说不清楚《户调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晋书》的作者写《食货志》,记叙晋平吴之后“又制户调之式”,表达清楚,怎么可能是“后人”综合相关法令而加以“式”的名称呢?而且“综合相关法令”而加的“名称”,不是“式”,而是“户调式”,加“式”的名称在逻辑上还说得通,而加“户调式”在逻辑上也讲不通了,唐先生显然有意含混。尽管如此,唐先生的解释还是被广泛接受了,许多涉及西晋赋税的论著,包括大学通用的教材,都认定《户调式》包括上述三个内容。例如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太康元年 (280年),西晋颁行户调式。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家制三部分。”
1.关于“占田”。唐长孺先生解释说:“我认为占田只是空洞地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危害最小的解释。大多数治史者还是把“占田”解释为“限田”。也有学者解释“占田”系土地限额申报制度,本义是“个人通过口授形式向政府自报土地数目”,“据有土地”只是其引申义,西晋占田规定了土地登记的标准额度,通过申报登记的法令程序,由实际占有变为合法占有。但是,即使“占田”有“自报土地数”的意思,也还有“拥有土地”的意思 (就算是“引申义”也罢), 《户调式》中说的“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显然用的是“引申义”,没有“申报土地”的意思,而且是描述性的。另外“申报土地”就是如实报出拥有多少土地,怎么会有“限额申报”呢?也还有人解释说“占田”就是“名田”, “名田”就是“私田”,“占田既不是授田而是私有土地,由占田法令所反映的占田制度就是关于私有制度”。这种解释太过牵强,不合逻辑。说“占田”和“名田”是一个意思,也还说得通,但说“占田是私田”或“名田是私田”,就文理不通了。“占田”是一个动宾结构,意思是“占有土地”,不包含对土地性质的说明,判断词“是”后面不能跟一个作为普通名词的“私田”。
对于“课田”,流行的解释是“课田制为赋税制度”,这是沿袭了马端临的观点,但说得要清晰一些。但也还有不少含混不清的说法,如说:“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督课耕田”是什么样的赋税制度呢?又说“课田是课税之田”,这是又把作为动宾结构的“课田”曲解为一个普通名词了。
比较而言,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和何兹全先生编的《中国通史》 (卷7)对“占田”、“课田”和“赋税制度”作了更好的解读。虽然也说“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官品占田荫客式三部分 “,但指出;“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土地数量的一个假定的指标,所谓课田则是指农民应负担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无关”。说的稍显含混,但“假定指标”、“同每户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无关”等说法已经朝认清“占田”、“课田”系形式方面规定的方向走了一步。又指出西晋的田租和户调都是以户为单位来征收的,“把田赋变成户调,不再履亩而税”,这些都是正确的。还提到“西晋田租和户调实际上大概都是一户以一丁计,按户征收租调时,官吏还预先把纳租调户按贫富分为九等,按等定数,而以《晋故事》所述定额为平均指标,这种征收租调的办法,叫做“九品混通”①治史者经常提到西晋赋税征收的“九品混通”之法,但并未弄清楚“混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些学者未弄懂“混通”却大谈什么“九品混通”是中国社会封建化的标志等等。。 “一户以一丁计”当然是不正确的。西晋划分户等、按等征税时主要考虑的是每户“丁”的多少,虽然不是直接计丁,而是把“丁”数折合成户“品”的一部分来确定“户等”,但“户样”却只有一个“丁”,是一个“当户”的“丁”。虽然如此,一户以一丁计“的说法向认识“户样”的方向迈了一步。“平均值”的说法含混不清,唐长孺先生曾对“平均值”作过一番解释:
既然以家赀为标准,就应有贫富多少之差,为什么曹魏西晋却规定绢绵每户征收额呢?我认为这一定额只是交给地方官统计户口征收的标准,其间贫富多少由地方官斟酌,但使每户平均数合于这个面额而巳。
唐先生的解释含混不清。 “地方官斟酌”,如何“斟酌”?不得要领。而将户“按贫富分为九等”,“按等定数”,以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为“平均指标”,这就是“九品混通”等说法,较唐先生解释清楚了一些,却仍然含混。怎样“定额”?怎样才能达到“平均指标”?“混通”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显然不了解户“样”制、 “样”用作“比”,不了解“比照”和“折算”的方法以及“混通”的真正意思,就无法说清楚西晋赋税是如何征收的。但是“平均值”、“平均指标”的说法仍然意味着朝正确认识“样”、“赋税额样”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中国史纲要》和《中国通史》两本书的解说代表了现今对西晋《户调式》研究的进步虽然还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尚未摆脱杜佑编造的“假命题”的束缚,未能认识到“式”作“样”解,用作“比”,不知道“比照”、 “折算”、 “混通”之法,但抛弃“占田”、“课田”为“授田”的观点,仍然是值得肯定的。《晋武帝户调式研究》一文把西晋《户调式》中装饰“标准赋税额”的“课田”规定,一种形式方面的规定,曲解为国家对“课田民”的“授田”规定,编造了一个古代国家以一般百姓为对象的土地分配制度,宣传它“上承曹魏的屯田制,成为以后直到隋唐土地制度的样板”,“正是魏晋的土地制度,才是将中世纪与古代区别开来的划时代的重大事件”。这样,文章就不仅曲解了西晋《户调式》,还歪曲了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史的真实情况,这对正确认识中国古代中世纪史起了负面作用。
1.剪伯赞.中国史纲要 (上册);何兹全.中国通史 (卷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Abstract:This is a study of the household tax system in the West Jin Dynasty and a commentary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s in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records.It traces the causes of the misinterpretations in some famous history books and offers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s,which should be of much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studie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standard;household tax;pattern;farming tax;comparison;convert
(责任编辑 王东昕)
A Study of the Household Tax System in the West Jin Dynasty
ZHANG Shang-qia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China)
K237
A
1672-867X(2011)01-0106-09
2010-05-23
张尚谦 (1935-),男,云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