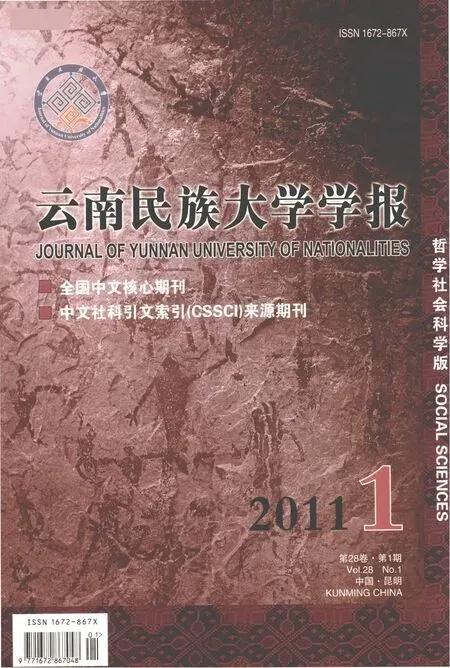论南诏入犯安南对唐代国家安全的影响
2011-12-10陈国保
陈国保
(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唐代晚期,南诏趁唐朝国势日衰和其南疆边备空虚之际,出兵入侵安南。持续十余年的战争,对岭南地区乃至整个唐朝,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于南诏侵犯唐安南都护府的战事,较早就有涉及,并一直备受越南古代史、南诏大理史、云南地方史等相关领域研究学者的关注。如黎正甫先生的《郡县时代之安南》、吕士朋先生的《北属时期的越南》、张秀民先生的《立功安南伟人传》、尤中先生的《云南民族史》、陆韧教授的《云南对外交通史》等,都在相关章节或专题中论及唐朝与南诏在安南都护府的争战。方国瑜先生就南诏与唐朝、吐蕃之间或敌或友的历史关系做过较为深入详实的考察。[1]乌小花、李大龙的《有关安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一文,以编年的形式阐述了安南都护府的兴衰历程,讨论了南诏对安南都护府的争夺,略及南诏占领安南都护府后对唐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所构成的威胁。但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南诏兵犯安南的战事梳理或战争过程的描述,且视野往往拘泥于南疆一隅,而谈到南诏所发动的这场战争,则多着墨于南诏的扩张性,忽视了从晚唐国家所面临的内外形势以及唐帝国边疆防务策略的角度来进行审视和检讨,尤其是对战争影响到的唐代国家全局问题的认识,则更显不足。西方学者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如英国学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即看到了南诏占领安南都护府后对整个唐代形势的影响,颇具见地。然受所掌握的中国历史文献的局限,所以论证单薄;又因缺乏对中国疆域形成历史的全面了解,故其观点又难免有失偏颇。
一、内外交困的晚唐时势与南诏伺机内犯
缘于边疆与内地不可分割的整体联结,边疆安危往往与国家形势紧密相关。以唐朝国势的盛衰演变来说,表现在边疆形势上即为治与乱的交替更迭。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盛转衰,中央集权大为削弱,逐渐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其初跋扈陆梁者,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而其后戡定祸乱者,亦足以称祸而致乱。故其所以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2]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升安南管内经略使为节度使;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置柔远军于安南都护府;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又升安南都护为静海军节度使。唐王朝本欲以此南疆方镇“镇遏夷僚”,但据张国刚先生所划分的唐代藩镇的四种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安南都护府属第三类[3](P81),“供馈不足与藩帅苛刻是边疆型(即边疆御边型)藩镇的共同特点,由此而引发的兵乱是藩镇动乱的主要内容”[3](P98)。所以,唐代后期的安南都护府也同样发生了政府驻军的叛乱。驻兵之乱,本已损及唐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而晚唐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又进一步削弱了唐帝国在安南都护府的军事部署力量。
就其内部军事局面而言,尽管唐王朝为达到有效抑制藩镇割据而殚精竭虑,但迫于无奈,玄宗以后的李唐统治者,基于缓和地方形势的考虑,多对藩镇势力采取姑息之策,“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故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盖姑息起于兵骄,兵骄由方镇,姑息愈甚,而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击,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代非其有;又其甚也,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灭。[1]”尤其如唐穆宗,“上于驭军之道,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戎臣。故即位之初,倾府库颁赏之,长行所获,人至钜万,非时赐与,不可胜纪。故军旅益骄,法令益弛,战则不克,国祚日危。[2]”
而其外部边疆形势,“四郊多垒,连岁备边,师旅在外,役费尤广,赋役转输,疾耗吾人,困竭无聊,穷斯滥矣。下庶暗昧,不见刑纲,戎士在军,未习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实繁。”[3]特别是西南边疆的吐蕃,趁安史之乱唐朝国力大为消耗之际,从西域、云南、河陇三面全线出击,进犯唐土,直接威胁到大唐帝国的生死存亡。曾经唐王朝为改变“外重内轻”的被动军事形势,加强中央集权,“国家自禄山构乱、河陇用兵以来,肃宗中兴,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吞噬无厌;回纥矜功,凭陵亦甚。中国不遑振旅,四十余年”。”[4]本是出于良好愿望,但却正中吐蕃下怀,更给了其可乘之机。穷于备战的唐王朝,为守住李唐江山的根本,“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边,中国无武备矣。”[5]
在这种内忧外患交织困扰的复杂形势下,疲于应付的唐王朝根本无力顾及南部边疆的边防问题,从而导致了南疆边备的空虚。其实,并非南疆如此,自唐中期以后,整个国家的边防问题都很严重,如元和八年(813年)宰相李绛就曾言于宪宗曰:“边兵徒有其数而无其实,虚费衣粮,将帅但缘私役使,聚其货财以结权幸而已,未尝训练以备不虞”[6]。若以南疆而言,“交州,汉之故封,其外濒海诸蛮,无广土坚城可以居守,故中国兵未尝至。及唐稍弱,西原、黄洞继为边害,垂百余年。”[7]虽稍有言过其实,但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后期南部边疆防务的松弛,而这正好给了地邻安南的南诏可乘之机。所以说,南诏对安南的骚扰,除因其自身力量壮大而致扩张欲望膨胀的因素外,亦与唐朝国力衰落及其南疆边防的空虚等外部客观环境不无关系。
雄踞于唐帝国西南的南诏是唐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方民族政权,“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4]。周旋于唐与吐蕃之间的南诏,利用唐与吐蕃长期争战而致彼此损耗的时机,逐渐发展壮大,如陈寅恪先生言:南诏“强盛之原因则缘吐蕃及中国既衰,其邻接诸国俱无力足与为敌之故,此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也。”[5](P347)方国瑜先生亦曰:“(南诏)虽然受唐朝宠渥,但是'开门节度,闭门天子',非服服帖帖地听命于唐朝,利用唐朝与吐蕃的矛盾,日益强大起来。”[1]随着南诏势力的迅速强大,其扩张野心自然也更加膨胀。因此在天宝战争大败唐朝之后,南诏便在频繁侵扰唐境剑南西川的同时,亦将目光盯上了唐帝国的南部边疆。
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南诏出兵袭击安南都护府,开始了对唐朝南部边疆的侵扰。不过,在宪宗、穆宗二帝当政期间,南诏虽趁安南防备相对空虚及岭南局势动荡之际,零星骚扰唐朝南境,但尚不敢公然与唐为敌,姑且维持着对唐帝国貌合神离的臣属关系,“是时,黄洞蛮屡叛,邕管间连岁被兵,嵯巅乘衅,遂东寇安南,然朝贡犹每岁不绝”[6](P136)。其实,当时南诏觊觎唐土的野心,重点仍在西川一线。太和三年(829年)冬,南诏命王嵯颠大举进兵西川,轻易地攻陷了巂、戎等州,次年一月攻破成都,在大肆掳掠之后撤离。南诏的突袭,敲响了唐朝西南边防的警钟。太和四年(830年)十月,唐以李德裕为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云南安抚使。李德裕到任后,致力于西川边防的巩固和提高,使唐帝国西南边疆的防御能力不断加强,并在形势上与安南都护府架构成唐帝国西南、南部边疆的两大军事防御屏障,由此对南诏的北上或南下的扩张之路形成阻挡之势。更令南诏坐卧不安的是它担心唐朝借此以安南和西川作为反击的基地,对其形成钳制之势。为改变这一不利的被动局面,南诏再度出兵入犯安南,“南诏知蜀强,故袭安南”。[7]虽然当时安南的边备相对薄弱,但唐朝尚未因“苍洱之盟”后二者结成的盟友关系而完全松懈南疆一线对南诏的防范,尤其是凭借维系在唐帝国边疆秩序之中的安南都护府辖下散布于南疆西北沿边之羁縻州形成对南诏的天然屏障。《旧唐书》卷17《文宗纪》即有记载云:“太和七年三月己酉,安南奏:蛮寇当管金龙州,当管生僚国、赤珠落国同出兵击蛮,败之。”为突破这一防线,南诏试图招诱安南羁縻州部落首领的归向,策划安南内应。开成三年(838年),安南都护马植奏称:“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南诏的企图引起了马植的警觉,也使他意识到了这一边疆隐患,故“自到镇以来,晓以逆顺。今诸首领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8]以此提升南部边疆的防卫能力。在此时期,南诏虽间或寇犯安南,但因唐朝尚有一定的防备,其入侵阴谋屡屡未能得逞。
然自大中七年(853年)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当时以行贿权僚得以出任安南都护的李琢,为政贪暴,苛刻逾求,导致安南土著居民的反叛。史云:“大中时,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李琢“贪于货贿,虐赋夷僚”而导致的安南内乱已使南疆呈现离心之象,而其又错误的裁撤南疆边防,更加重了安南都护府的危机。《云南志》卷4《名类》载:“南蛮去安南峰州林西原(即林西州)界二十二日程。自大中八年,安南都护府擅罢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独等七绾首领被蛮诱引,复为亲情。日往月来,渐遭侵轶。罪在督护失招讨之职,乖经略之任。”又曰:“桃花人,本属安南林西原七绾洞主大首领李由独管辖。亦为境上戍卒,每年亦纳赋税。自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状与李涿(琢),请罢防冬将健六千人,不要来真登州界上防遏。其由独兄弟力不禁,被蛮柘(拓)东节度使书信,将外甥嫁与李由独小男,补柘东押衙。自此之后,七绾洞悉为蛮收管。”[9](33~34,45)李琢不顾当时唐与南诏对立的边境实际,听信峰州刺史一面之词,盲目撤销唐在安南都护府西北边境一线驻扎的主要用来防备南诏的政府驻军,仅仅依靠当地部族兵力防守,致其首领李由独孤立无援而生弃唐之心,加之南诏百般诱引,并与之结成姻亲之家,李由独因此背唐而投奔南诏,从安南都护府的前卫将帅变成南诏侵犯安南的先锋。唐朝的南部边疆藩篱尽撤,堂奥洞开,南诏势力不断推进。所以黎正甫先生说:“南诏攻陷安南,李琢先撤去防守,实启其门”。[10](P107)自此以后,南诏对唐帝国在南部边疆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双方兵争不断,直至咸通七年(866年)十月,高骈击败南诏,收复安南,战火绵延十余年。唐与南诏在安南的争夺,虽最终以唐帝国收复安南而结束,但唐王朝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连年战争,不仅对其南疆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也使已是强弩之末的唐帝国遭受沉重的创伤并由此导致唐代整个社会的严重危机。
二、安南残破,南疆离心
南诏趁唐与吐蕃衰落之际,不顾吐蕃的威胁,与唐为敌,频繁发动对唐朝安南、西川的侵犯,虽屡有得逞,但也因此困乏,最终导致灭亡。而唐朝的南部、西南边疆亦因南诏的寇扰变得残破不堪,“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厉,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杨收言:“南蛮自大中以来,火邕州,掠交趾,调华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南诏在安南的肆扰,导致当地居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民生极度凋敝,以致无力承担国家的赋税义务,当地社会矛盾亦随之激化。为稳定唐帝国在南疆的统治,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不得不颁布《救恤安南流人制》,“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将吏官健走至海门者人数不少,宜令宋戎、李良瑍察访人数,量事救恤。安南管内被蛮贼驱劫处,本户两税、丁钱等量放二年,候收复后别有指挥。其安南溪洞首领,素推诚节,虽蛮寇窃据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闻溪洞之间,悉藉岭北茶药,宜令诸道一任商人兴贩,不得禁止往来。廉州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遂绝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11]《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传中·南诏下》也云:“安南之陷,将吏遗人多客伏溪洞,诏所在招还救恤之,免安南赋入二年。”
长期的战乱也导致了安南交州港的衰落。交州自汉代以来便担当了古代中国海外贸易不可或缺的中转角色,成为中原王朝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说:“交州(安南)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幡,道里不可详知。自汉武以来,朝贡皆由交趾道。”所谓朝贡,实则是经济贸易的一种政治表现形式。[12]隋唐时期的交州、广州已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两个繁荣的海外贸易基地。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海外贸易逐渐兴起,与唐朝发生贸易的国家逐渐增多,给交州港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交州港的对外贸易达到了鼎盛。当时同唐朝联系最为频繁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是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南亚天竺、狮子国,东南亚沿海国家蒲甘、昆仑、扶南、真腊、占城等等。到唐代后期这些国家几乎都通过海道,起帆波斯湾,取道马六甲,或直接从东南亚沿海北上交州、广州,同中国进行贸易。”[13](P118)不过,交州的繁荣显然离不开当地和平的社会环境。唐王朝通过安南都护府,对南疆地区实施着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强有力的军事控制,既维护了安南都护府与今两广及内地传统水陆交通线的畅通无阻,也为唐帝国南海海上交通线路的稳定与拓展提供了保障。于是交州凭借它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地处水陆交通要津之地的区位优势,不但在唐帝国的海洋贸易中占据特有的商业发展优势,为唐王朝南海交通和贸易的门户,而且对于唐帝国的整体经济利益存在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或许也是后来唐朝与南诏在安南展开长期争夺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即如西方学者所认为:南诏进攻安南,给唐朝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四川,朝廷关心的是可能失去一个与朝廷有密切政治联系的富饶地区。在安南,关心的性质则全然不同,它更多是为了威信,特别是贸易。因为南部港口是通过繁荣的海岸贸易而和长江下游港口联系起来的国际海运贸易的中心。中国对经过中亚通往西方的陆上交通的控制仍很不稳定,朝廷对丧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认真考虑”。而南诏对安南的频繁骚扰,则使得交州港在唐代中国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急剧下降。自“李琢失政,交趾陷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13](P123),战乱“严重地损害了交州港的正常秩序和外贸环境,自咸通四年,南诏攻陷安南后,原来在安南从事贸易的客商和外地人,多转移到广西沿海,或寓寄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战争还阻断了安南经云南与内地的陆路交通,交州港失去了南诏和西南内地市场。从此交州的海外贸易一蹶不振。”
唐朝虽击退了南诏,收复了安南,但因战争的消耗,中央王朝对南疆的控制力度却渐趋微弱。我们知道,唐为维护和加强中央王朝对南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在安南都护府境,既置十二正州管理交通沿线地区,又于沿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广泛设置数十羁縻州,以此实现对归附少数民族的统辖。唐代所推行的这种酌依其俗、灵活制宜的羁縻政策,并不强行国家权威在岭南边隅的一蹴而就,而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旨在通过羁縻州制渐进式的推进国家秩序在南部边疆的渗透,无疑有利于州县制度在南部边疆的贯彻实行,有助于实现中央王朝对它的有效牵制,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在南部边疆的巩固和发展。但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保留了当地部族土长“自治”的特权,也就等于削弱了中央王朝委派在南疆最高军政长官安南都护等“流官”在当地的实际控制权,由此埋下了地方势力与国家权威之间矛盾冲突的隐患。
于是,在唐代国家盛衰演变与南疆土流势力消长变化的连环效应下,中唐以后安南都护府境内的土族大长的势力获得了迅速发展。以耿慧玲教授等人所著《唐贞元安南〈青梅社钟〉铭文考释》及毛汉光先生的《中晚唐南疆安南羁縻关系之研究》两文的分析,根据在越南河西省(今已并入河内市)青威县青梅社所发现的立于唐贞元十四年(798年)的《青梅社钟》铭文,记录了当地青梅社民242人,其中最大的姓是杜氏,有65人;其次郭氏,42人;黄氏,22人;高氏,21人;阮氏,14人;王氏11人;陈氏,9人;李氏,7人;其余郑、吕、杨、苏、江、魏、张、冯、黎、僧、周、吴等姓氏或不过5人,或仅有1人。若将官职与姓氏作比较,则拥有各类官衔者总计有65人,结果大致与姓氏分布相似,以杜郭二氏最强,超过半数39人。若再以所任官职之层级观察,刺史及刺史以上职务,杜氏3人,他姓皆无;其下较重要之职位为左厢兵马使,则为姓氏排序甚低的杨氏。至于各级中下级文武官职,大致与姓氏分布相当,以杜、郭、黄三姓居多。[14](P282)当时安南地方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时入晚唐,因随国势的衰微和南诏的入犯,南部边疆的地方势力应机而兴,更为壮大,“五管为南诏蛮所扰,天下征兵,时有庞勋之乱,不暇边事。……,北兵寡弱,夷僚棼然”。①《旧唐书》卷158《郑余庆传》。按:郑从谠,余庆之孙,咸通六年出任岭南节度使。安南都护府的离心力亦由之更加增强。尽管咸通七年(866年)收复安南后,出于主观愿望的唐王朝为恢复南疆地方秩序,加强国家对安南的控制,提高南部边疆的军事防御能力,升安南都护为静海军节度使,但“静海军”,不过空有名号而已。如乾符四年(877年),当南诏新主隆舜提出与唐和亲时,朝臣卢携为说服唐僖宗答应南诏的和亲之请,即以对南疆边防的忧虑为说词,“今朝廷财匮兵少,安南客戍单寡,钞冬寇祸可虞,诚命使临报,纵未称臣,且伐其谋,外以縻服蛮夷,内得蜀休息也。”可谓实情。所以安南都护府也并未因为名义上的军事升格,而避免动乱的发生,僖宗广明元年(880),安南军乱再起。
自唐懿宗时期起,唐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尤其是唐僖宗乾符元年中原内地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以后,既要固本又须安边的唐帝国应付严重的内忧外患已是捉襟见肘,因此无力亦无能顾及南部边疆,甚至授命的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使),亦几乎是徒有虚名,未能到任。如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任命独孤损为安南都护,充静海军节度、安南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其实就根本没有到达安南。这样,远离帝国中心的安南都护府便因淡出国家的视野,而致实际控制权逐渐旁落于地方豪族大长手中,成为后来安南脱离中国地理版图的直接原因,“随着中国中央对于地方控制力的逐渐转弱,唐末五代,越南原本在中国政治力摶合下的政治集团,也逐渐开始淡化在中国的中央体制中,被中国行政制度强化了的地方政治集团,失去中央的强力控制后,开始尝试争取各个地方势力的独立权力,客观的情势使得越南地区得以游离出中国的政治统治圈”。如《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5“属唐昭宣帝天祐三年”条载:“春正月,唐加静海节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曲氏,洪州人,世为巨族,承裕宽和爱人,为众所推,因乱以土豪自称节度使,请命于唐,唐因授之。”唐中央王朝被迫承认安南土长在南部边疆的最高军政地位,致使自秦汉以来即为中国王朝直接管理下的地方行政辖区,初现由郡县统治走向藩属册封的端倪。故曲承裕死后,其子曲颢“据州称节度使。颢凭旧业,据罗城称使,分定各处路、府、州、社,置令、长、正、佐,均田租,蠲力役,造户籍,编记姓名、乡贯、甲长之帅,政尚宽简,民获苏息,辰梁以广州节度使刘隐兼静海军节度使,封南平王,隐据番禺,颢据州称使,志在相图。”[15]如方国瑜先生言:唐与南诏的十年争扰,“虽(南诏)主力被高骈击破,但(安南)地方势力当更发展,唐朝衰替已无能挽回。唐亡,南汉并有交州,但州人杨廷艺、矫公羡、吴权、杨主将、吴昌文,遁相争自立,以致丁部领称南越王,宋时,南越只为朝贡之国了。”[1]西方学者亦云:“公元9世纪,因越南地方势力的复兴,不断冲击着唐朝的最高统治,并与唐朝展开了长期的冲突,尽管冲突最终得到了有利于唐朝方面的解决,但此时的唐王朝已日趋衰弱,越南地方势力趁机将安南引向独立发展的时代。”[16](PP209)
三、邕州被扰,殃及五岭
安南都护府与同为岭南五管之一的邕州都督府是互为维卫、共同筑建在唐帝国南部边疆的重要军事防线,“唐设安南都护,以邕州为支柱,……。邕州与安南互为犄角,唐兵守安南,当加强邕州,南诏占安南,也要进取邕州。从安南事件发生,邕州即受威胁,安南事定,邕州始告安全。”[1]所以说,安南与邕州同样是矗立在唐代南部边疆唇齿相依,存亡相连的边疆防御系统。安南固然以邕州为支柱,震慑南疆,邕州乃至岭南也以安南为藩篱,安南为邕州以及整个岭南的稳定提供军事地利上的保证。因此当南诏占领安南都护府后,挥师东北、兵犯邕州时,波及五岭,形势更为严峻。
早在咸通元年(860年),南诏首度攻陷安南都护府时,即已举兵进犯邕州。 《资治通鉴》卷250《唐纪六十六》“懿宗咸通二年”条:“七月,南蛮攻邕州,陷之。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入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盗。”边镇戍卒向招募的转变和唐廷对边情的无知,被藩帅的私欲所利用,致使岭南边防空虚,南诏趁此长驱直入,攻陷邕州达二十余日方才撤出,“城邑居人,什不存一”,邕州几乎被焚劫一空。
邕州虽失而复得,但其因此而遭受的巨大创伤和造成的危急形势,也迫使唐廷意识到加强邕管防守,对于堵截南诏扩张之势、控扼五岭、固卫疆垂以及屏藩内地的重要性。基于此,唐王朝吸取邕州疏于防守轻易丧之敌手的教训,决定实行岭南道东西分治的治边策略。唐懿宗咸通三年十月《分岭南为东西道敕》云:“敕:岭南分为五管,诚已多年,居常之时,同资御捍,有事之际,要别改张。邕州西接南蛮,深据黄洞,投两江之犷俗,居数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轻,军威不振。境连内地,不并海南,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别择良吏,付以节旄。”[17]唐王朝试图通过此举加强邕州的边防军政要位,并对赴任岭南西道的封疆大吏寄以厚望,委以重托。如以郑愚为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而作《授郑愚岭南节度使制》曰:“朕以郎宁地分零、桂,共控夷蛮,将以重城镇于两江,壮服岭于西道,俾崇旄节,用固疆陲。……(尔)既懋师节,仍长宪台,勉承顾遇之荣,伫观缉柔之绩。”又《授蔡京岭南西道节度使制》云:“滨海而南,邕为重地,城临瓯骆,俗本剽轻。居常则委经略之权,有事则付节制之任。是用改其旧号,建以新军,一时之革,千古无对。尔其颁惠养以驭众,亦宽严以训兵,济活乡闾,保安谿洞。”然本是一剂治世良方的改弦更张,邕、广分治不仅没有给弥留之际的李唐王朝带来一丝慰藉,相反却成了地方官员张扬权势、抑压同僚的尚方宝剑,防守之诫不过一纸空文。所以咸通五年,南诏再度轻易兵临邕州之境,只因其“知边人困甚,剽略无有,不(复)入寇”,由此更可见邕州所受蹂躏之深。但南诏此势已非仅仅危及邕州,而是直接威胁内地,岭南诸州,“一有不靖,湖南且乱”,南疆一隅已不再只是边疆失与守的问题,而成为关涉唐王朝国家存亡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如顾祖禹言:南宁府“内抚溪峒,外控蛮荒,南服有事,此为噤喉重地。唐置邕管于此,为广南唇齿之势。……盖地居冲要,势所必争也。”[18]所以一时唐廷上下慌乱,调兵遣将,御敌深入,力图收复岭南。如此,南疆边吏的授任是否得人便成为能否让唐朝重新获得对南疆主动权的制约瓶颈。所以因夏侯孜的力荐,骁卫将军高骈被任命为安南都护、本管经略招讨使,率兵抗击南诏的侵犯。临危受命的高骈不负重托,取得胜利。
唐朝为反击南诏的入犯,连年用兵岭南,战争不仅直接摧毁了岭南居民的家园,而且国家军队的给养也成为了当地百姓的沉重负担。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云:“关要之外,声教至遥,每念疲人,尤多横役。访问五岭诸郡,修补廨舍城池,材石人工,并配百姓,至于粮用,皆自赍持。既不折税钱,又全无优恤,永言凋瘵,实可悯伤。……(交战)累载已来,亦颇校科征纳,主持军将十余辈,摊保累数百家,或科决不轻,或资财荡尽。典男鬻女,力竭计穷,尽虚挂簿书,徒为羁絷。”当然,南诏陷没交趾,北寇邕容的军事扩张,非但导致了岭南地区的民不聊生,同时也给其相邻地带乃至唐代全国的社会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破坏。如高骈《回云南牒》言:“云南,顷者求合六诏,并为一藩,与开道途,得接邛蜀。……复穷兵再犯朗宁,重陷交阯,两俘邛蜀,一劫黔巫。城池皆为灰烬,士庶尽为幽冤。”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岭南用兵德音》曰:“如闻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凋伤转甚,宜有特恩。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文,以助军钱,以充馆驿息利本钱。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与置本钱。”又《咸通七年大赦》云:“应三道(安南、邕州、西川)兵士,经过累路州县,供应顿递,征配里闾,水程船夫,陆路车役,劳弊斯甚,疲瘵可哀。其岳州、湖南、桂管、邕管、容管内,沿路州县,今年二月二日德音,已蠲放今年夏秋两税各一半,尚恐乡村未悉,更要加恩。宜于今年夏税正钱,每贯量放三百文,沿路州县,亦甚凋伤,先未霑恩,今须优假,宜于来年夏税正钱,量放一半。”可见,安南战事,地方经济遭受巨创的地区首当其冲的是岭南内部及相邻的今湖南、湖北、江西、贵州等地,同时损及全国,“累岁以来,岭南用兵,多支户部钱物”,“自从近岁,颇欠丰年,百姓凋残,四方空竭。邕、交防戍,邛蜀征行,租赋罄于东南,衣粮耗于西北。”岭南用兵对于唐代全国经济的沉重打击由此不言而喻矣。
四、神州震荡,唐室残喘
唐与南诏争夺安南的战争,其破坏并不局限南疆一隅,这在上文的论述已有体现。范祖禹《唐鉴》卷21《论高骈破南诏》云:“唐室之衰,宦官蠹其内,南诏援其外,财竭民困,海内大乱,而因以亡矣。”《唐摭言》载:“时属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联翩,寇乱中土。”[19](P21)南诏之犯,不仅危及唐帝国南部边疆的安全,也波及全国,造成中原内地的局势动荡,加速了唐朝的灭亡。尽管南诏攻破安南、兵犯邕州的嚣张气焰,因高骈的大兵压境而稍有抑制,但迫于严峻形势,为防止南诏再度突破岭南邕州防线并北上寇扰内地,咸通三年唐调徐、泗戍兵镇守桂林,防备南诏。唐懿宗咸通三年(862)五月《岭南用兵德音》云:“徐州土风雄劲,甲士精强,比以制驭乖方,频致骚扰,近者再置使额,却领四州,劳逸既均,人心甚泰。但闻比因罢节之日,或有避罪奔逃,虽朝廷频下诏书,并令一切不问,犹恐尚怀疑惧,未悉招携。结聚山林,终成诖误。况边方未静,深藉人才,宜令徐泗团练使,选拣如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城,待岭外事宁之后,即与替代归还”。此即为《旧唐书》卷177《崔慎由传》所说的:咸通“六(当作三)年,南蛮寇五管,陷交阯,诏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桂州,即桂林,为岭南隘口,亦是岭南西道通向内地的要冲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桂林府,府奠五岭之表,联两越之交,屏蔽荆、衡,镇慑交、海,枕山带江,控制数千里,诚西南之会府,用兵遣将之枢机也。……隋唐之初,皆置军府于此,盖天下新定,岭南险远,倘有不虞,燎原是惧,故保固岭口,使奸雄无所觊觎也。”这实际也是当时唐分兵戍守桂林的原因所在。
依唐代的军事制度,戍卒镇守边疆三年一换,那么咸通七年唐收复安南后,镇边四载的徐、泗戍兵当被轮替,但因战争刚刚结束,担心南诏利用唐岭南换兵之机,趁虚再犯,而此时的唐朝实已无兵可调,所以要求岭南戍兵尚且严守封疆,待形势完全好转以后,再作打算。同时为稳定军心,又许以种种承诺,“安南、邕管、西川三道军士,皆逾山越海,擐甲荷戈,志切勤王,诚深报国,固内侵之封域,收已失之城池,尽欲捐躯,咸思贾勇,险阻数历,终始一心,言念忠勤,诚用嘉叹。今南蛮已加招抚,冀就弭宁。日下但严守封疆,且备要害。虽未用更图攻讨,亦未可便绝训齐。其将士等义感风云,志谐金石,屯营既久,立效已多,大功将成,恳节无夺。俟其归款,别有指挥。……其赴府三道行营兵,有亲老及妻子在家者,各委本道切加存恤,勿使冻馁恓惶,俾无回顾之忧,以励当锋之志。其诸将士勇敢用命,当锋殁身,义节可嘉,孤弱是念,并委本道节度使,据所申报,各须安存。如血属单弱,不能自存者,即厚加给恤。遗骸在野,深可悯嗟,今春已降德音,尽令优给收葬,尚虑暴露,未契幽阴,今更举明,用慰泉壤。宜令所在长吏,访寻收殓,如法瘗藏,仍以酒醪殷勤奠酹。”然当时已是满目疮痍的唐帝国,根本无法兑现这些承诺,所谓“恩宥”,不过徒托空言,这从后来的庞勋事件即可充分说明。咸通九年(868年),已经镇守南疆六年的徐、泗戍卒仍不得返籍,故请求替代,“尹戡以军帑匮乏,难以发兵,且留旧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飞书桂林。戍卒怒,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时亡命者归贼如市。……九月十四日,贼逼徐州。……十八日,庞勋自称武宁军节度使。”镇守岭南之徐、泗兵卒的军饷及返乡补给国家尚且难以筹措,又何能安抚存恤戍卒在家亲老妻儿?“勿使冻馁恓惶,俾无回顾之忧”无疑只是冠冕之言,而“戍卒家人飞书桂林”,其内容当为苦诉家乡窘境之情。正是在这样一种回家无望、军饷无期、亲人顾盼的多重因素的刺激下,进退无路的徐、泗戍卒举兵起义,并推庞勋为将,倒戈反唐,震动江淮。起义虽被镇压,但它却发黄巢起义之先声,成为导致唐朝灭亡的直接诱因之一。甚至宋代的修史者总结唐亡的教训云:“懿宗任相不明,藩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桂林之祸的根源即在于安南被扰,可见南诏侵夺安南对于唐朝全局的深远影响。故西方学者认为:“868年以后这个偏远的南方安静下来了,但是这个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价才获得的。……唐王朝这时正被许多内部叛乱所困扰,而且不久又经历了由一个名为庞勋的军官所领导的兵变的柔躏——他严重的扰乱了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另外,王仙芝-黄巢的大叛乱仅在5年以后也开始了。”从此,李唐王朝的局势更趋穷蹙,日薄西山的晚唐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做苟延残喘的最后挣扎。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安南都护府对于维护唐代国家安全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和作用。作为唐朝设置在南部边疆的重要管理机构,安南都护府的主要职责是“抚尉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因此,它不仅是唐王朝实现南部边疆稳定、巩固南部边疆统治的最高军政机关,也是防御外敌、镇重边陲的重要军事屏障。依持设置在南部边疆的安南都护府,唐王朝有效稳定了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凭借安南都护府及其互为犄角的邕州都督府与矗立在帝国西南边疆的南宁州都督府共同构建的唐帝国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边疆防御体系,则又为唐帝国统治在南部边疆的不断深入提供了保障。如果说唐代前期以南宁州都督府作为经略安南的据点,亦以安南作为经营西南的基地的话,那么当南诏坐大,与唐为敌,安南都护府则为唐朝用以对付南诏的前沿阵地。故云安南都护府既是唐王朝用以经略西南边疆的军事基地,也是防范南诏内犯的边塞铁篱。然而正因为唐朝南疆治策乖违,边吏贪暴,土酋倒戈,致使唐帝国南门洞开,南诏趁机而入,战火兵燹绵延十余载,安南遭劫,岭南涂炭,大唐国势益受虚耗。南诏的兴起使安南都护府失去其西北的屏藩,唐朝的南部、西南边疆也因此无法保持彼此制约的平衡。而南诏对安南的频频进犯,则直接击溃了自唐初以来帝国精心构建的边疆防御体系。所以就在南疆战火的烽烟尚未完全淡去的时候,驻扎在桂林防备南诏的徐、泗戍兵因久不得更代,而发生庞勋起义,骚动江淮,内忧外患频仍相继,帝国震荡,国势日危。安南失陷,成为加速唐朝走向尽头的催化剂。
[1]方国瑜.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和战,方国瑜文集(第二辑)[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8《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宋]王应麟.玉海卷25《地理·议边》[M].广陵书社,2003.
[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M].上海:三联书店,2001.
[6][清]冯甦撰,李孝友,徐文德释.滇考校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9《四裔考六·南诏》[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8][宋]王溥.唐会要卷73《安南都护府》 [M].北京:中华书局,1955.
[9]云南史料丛刊卷2[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0]黎正甫.郡县时代之安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11]希泌.唐大诏令集补编卷20《仁政·赈恤》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周伟洲.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2,(3).
[13]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14][台]耿慧玲.七至十四世纪越南国家意识的形成、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研究[M].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
[15][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 [J].“唐天祐四年”条,越南建福元年1884,5.
[16]Keith Well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J].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1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99《政事·建易州县》[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0《广西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9][清]王定保.唐摭言卷3《散序》[A].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740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