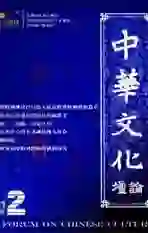灾难焦虑
2011-10-21苏宁
苏宁
[摘要]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思想统辖下,自我、社会、自然和天道构成灾难发生不可分割的四维关系。儒释道都反对孤立的看待自然灾害,而主张将其定位在人天关系之中。本文认为,当今各种灾害已经形成一种具有群体文化精神反映的灾难记忆。由于全球化和发达资讯技术的叠加效应,灾难感已经复制到全球各个角落,成为超过社会发展问题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键问题,灾难焦虑成为重要的生存焦虑。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灾难问题的思考,应对其进行细致的辨析、释义,寻找思想的启迪和现实的意义。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1.天人之和灾难观的本体论命题:物我一体,天下有道;2.“天人之和”灾难观的认识论命题:内外之和、自然与人的整体性问题;3.方法论:天地为万物之根,圣人学习天地,人身运度是天地之模拟;4.生态伦理:善恶报应与天、鬼、神、天神;5.灾难焦虑感:征服,还是守望自然?
[关键词]天人之和与灾难焦虑;内外之和;四维关系;生态美学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046-5
继“5·12”汶川大地震、海地大地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新近的新西兰地震之后,各种自然、人为灾难似已形成一种具有群体文化精神反映的灾难记忆。借助全球化和发达的资讯技术,灾难焦虑已经复制到全球各个角落,成为超过社会发展问题的人类生存状况的关键问题之一。站在今天的角度审视可以救治灾难焦虑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其辨析、释义、重构,也许可以找到某些思想的启迪并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从物我一体的思想中剥离出人的本体立场
在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思想统辖下,自我、社会、自然和天道构成灾难发生不可分割的四维关系。儒释道都反对孤立的看待自然灾害,而主张将其定位在人天关系之中。儒家和道家都有类似的思想:通过修身(包括行善),人可以感悟天道,建立天人之和。
中国古代从《周易》开始的天人一体观具有人文思想。它把个体性自我统一于宇宙整体之道,人与自然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真正的“物我一体”的关系。此说类似海德格尔的“共在”理论,对人类的灾难生存状况给予人类学意义的浪漫主义假设,其根源在于有一个符合最高理想的天道,所谓“人乃天之所赋”。在这种天人一体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交融的关系。人是自然万物中的人,自然是属人的自然。人生活在世界之中不是选择的,而是被规定的。这就根本不存在存在主义的选择,自然万物乃至灾难也成为了人的规定性。
道的本体和自然万物本来是不同的。本体是形而上的,万物是形而下的;但在传统天人·体观念中本体和万物是统一的。本体生成万物,万物显现本体。儒家天人·体观从人的角度来探求宇宙自然的和谐,人能通过自我教化而“参天地”,既然人能弘道,仰观俯察之间就不应盲目扩张人的自我实现的能力。道家则从道的角度来探求宇宙自然的和谐,解决之道有阴阳平衡之说,老子认为人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之所以能够和谐在于保持天人存在之间的平衡。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阴阳二气,通过相互激荡、相互作用而“烟煴”出和谐之物。
儒道都认为发生自然灾害是人类自身造成的,其分歧在于神的介入。神有多种形态,神所体现的超自然力量在何种关系中与人有关是重要分歧。另一个分歧在于天地鬼神到底对人有没有惩罚作用。道教劝善书与《周易》相同的是:都有善恶报应思想;都有关于天、鬼、神、人关系方面的论述。《周易》中鬼神的态度是助善不助恶,但无惩罚人之善恶作用出现。道教《太平经》则发展为承负说,明确讲到惩罚作用。“承负”说认为,人之善恶报应,与祖先后代皆有密切关联,承祖先之福殃,恶的力量可以数代相承。而“天”就是善恶的监督力量。因此,强调要靠一己之苦修才能达到完善的道德境界,并获得神赐之福。这里讲了监督作用,也涉及到惩罚作用。董仲舒人副天地论也涉及惩罚之说:“行有伦理副天地”,即人的行为伦理与天地相符。这个道德命题是儒家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将人类的伦理视野推广到天地之间,即认为道德伦理不仅存在于人际之间,也存在于天地生态系统之间,所谓“命与之相连”。董仲舒和《太平经》所言善恶惩罚说的出现,使伦理关系上升到“生态伦理”层面。
儒道二家实际上都肯定了人的自身给予性,即人本立场。但这里“道”的立场与神的立场是可以转换的,自然一旦被赋予了“道”的立场,人本立场就成为神性立场的奴仆。站在神的立场从自然、天道的解释中见出天人·体灾难论,如此仅能做到人在灾难面前的顺从、忍耐、坚韧、自强不息,与天地共施仁义道德以抗击灾难。但如果以人为尺度,从物我一体的思想中剥离出人的本体立场,“人是万物的尺度”,则必须经过从原始的主客融合,到主客二分,再到新的或后主客二分的天人之和状态,即黑格尔所说“彻底摆脱自然束缚的精神性”状态,逐渐从万物融通的传统中走出来。这里,关键在于对灾难的解释应如何摆脱人与万物融通的宗教感情和神学目的论,如何在构成人类社会空间的天道中寻找并顺应自然的内在灵性,强化人类的“超物”责任意识。
二、认识论命题:自然与人的整体性问题
从认识论角度看,天人之和思想在认识关系中提出了自然与人的整体性问题。从宇宙之和(天地、阴阳、,四时之和)、天人之和等角度,通过对自然地体认,求得自然的规律,并顺势而为。这样来阐述儒家理想的生态社会思想,往往把灾难的起因归于人与天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因此,一种观点主张顺应自然之说,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天道自然与人无干:“黾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天人关系不仅仅是统一的,也有疏离、冲突和对立。如荀子就突显人为的意义。他反对听命自然,而要求以人治天。
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入地思考:抽象地、孤立地讲天人之“和”与灾难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反命题也可以成立,同大自然作斗争,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同样是与天道“大化之流行”。如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老百姓进行农耕;尝百草,察成苦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曾与蚩尤大战于琢鹿之野。这些同样是天人之和的表现。只说“和”,看不到与天地奋斗而抗击的一面,显然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文学中的灾难描写,从古代神话开始就建立了“人与天斗”的宏大叙事母题。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都是描写天灾中人与自然的抗争。光和不斗不行,光斗不和也不行。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本身即是以人与自然界共同存在为出发点的。人不再只是从自然界里直接地获得生活资料,而是通过对于自然界的改造加工间接地获得生存的所需。所谓生产就是人通过工具从自然界中制造出人所需要的产品,这就要承认自然有其客观规
律。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人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整体才能去改造自然。在一个整体中,人作为类的整体与他物之整体的关系是多重性的,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和谐与斗争是分不开的。
因此。天人之和灾难论的认识论基础应该是“和而不同”,是“兼和”,而不是“同”、“和合”。从哲学角度来看,如何才能“和”既是现实问题,又是理论问题,起码还有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前科学认识论的语境下,对如何达到“和”的认识与把握仍然只能通过悬置或还原来达到,悬置或还原的结果是回到意识之中的意向对象本身。随着悬置或还原的层层深入,最终将现象追溯至纯粹意识的观念论。但这不是一个消极的否定步骤,悬置产生了一种关注态度的改变,即从自然态度转变为观念论态度。悬置把世界从自然的经验变为哲学和历史的经验,灾难史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历史共生。
三、方法论:天地为万物之根。学习自然本身存在的既显露又遮蔽的智慧
灾难与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紧密相联。追问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是中华民族的信仰与思想。灾难是生命的天敌,也就是信仰的天敌。抗拒灾难的人本理想其实具有科学性、实证性。在强大的灾难感中,它能既为脆弱的个体疗治苦难又能为民族与灾难的抗争贯注力量。
在中国古代天人·体思想中,理想的实现要靠学习天地,但不是普通人,是“圣人”学习天地。因为“圣人们可以替天言说,代天立道。“圣人”位于天地自然与大众百姓之间,并将天地之道传达给大众。天地自然本身存在一种既显露又遮蔽的智慧。灾害的发生往往由于天地的真相被遮蔽了。它之所以遮蔽,是因为人们没有发现它,认清它。“圣人”在体悟天地之道时,能将天地的遮蔽的道理变得清明。
之所以学习天地,是因为“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从历史上灾难的精神形象中,我们看到对天地的敬畏:“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
通过“圣人”学习天地,完成整个社会的修身、修心、修神之旅。这个观点将灾祸归于受“天命”所辖的人道之中,含有对于神学目的论的解脱,影响深远。人天关系各种类型,存在于天道伦理。社会运转中,甚至人体身心内外,都在天道伦理中相互渗透,不断地形成、变化和消失。这些远离科学主义的神秘主义逻辑,作为精神形象被显现出来,长时段的占据着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成为灾难焦虑的形上基础。
怎样学习天地之法?总的来讲即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之法,它承认客观事物有自身的规律。具体来讲可以举一些圣人学习天地的例子:
之一:顺道而行的方法。
顺道而行的关键在于“顺承天道”、“顺动”、“奉天时”(《周易》)等。
之二:反修自身与道感通的方法。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
“中正以观天下”。“中正”、“养正”都是一种修己方法。
反修自身的目的是求与天地之道感通。《易》讲道无所不在、感通天下,“《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感通”或“感应”也可以从两个主体角度之间来讲,如天与地;“刚”与“柔”:“刚柔相摩”,“刚柔相推”;“圣人”与“人心”;“圣人感人心”等。
之三:“圣人教化天下之法。
“圣人”观象、法道与象道之余,以“道”“教”、“化”“天下”。一方面是与自然偕同参与了天下之化成;另—方面是“神道设教”。
“圣人教化天下之人,主要方法是依循“神道”之大道,追求“顺动”,顺天地人之道、之理,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人可以贯通天地,法道修德;还可以感天动地,灾难自然就能得到治理。
这些方法让人从自然中体悟天地之道,在“圣人”的积极作用下,灾难自然会减少,这仍是效法自然变化而得出的哲理,贯穿着中国文化既重人伦、又重内在之心性之学的理念。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可以从自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些方法的实现坚定了我们对治灾难焦虑的信心。它既重人事,又重自然与宇宙之理,艰难的做到主客二分使其“尽人之性”之外,还存“尽物之性”。
四、征服,还是守望?
黑格尔曾提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调合。调和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自身。黑格尔解决问题的作法,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去寻找避难所。在他之前罗马人也曾企图通过自我深化来摆脱社会分解为原子个体的状态。从斯多嘴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论的流行,都是试图探索人对于现实灾难中发生的一切抱回避的态度。问题在于割断了同客观现实的联系,灾难仍然会在内心生活中复制,甚至生成无限的精神主观性。所以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通过天人和谐而对治灾难,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世界各民族文化中都有此思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世界各大宗教都有摆脱各种灾难的关于“天国”的种种设想,虽然是虚幻不现实的,但也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对没有灾害的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中国传统天人一体思想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从精神、观念的层面维护了两千多年的政权、神权对灾难危害的统治意识,此次序与天道相通。而当下对治灾难焦虑而建立的生态观,就核心价值体系而言,与中国传统灾难伦理观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抗灾难主体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不同,哲学本体观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时代精神不同。
我们可以将天人-体的生态伦理思想与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联系起来思考。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个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产生于自然界并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人化自然界,这是一个根本事实。自然界作为对象世界是一个自然和历史结合的存在者的整体,人和世界的主客体二分关系将是人设立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前提。这是抗拒灾难的人本主义理想。这个观点与前文所述与人与自然一体、万物融通的观点,不仅是概念的不同,二者背后有深远的文化背景差异。无论人本体还是神本体,从其背后的思想内涵来看,对自然界所持的道德境界仍然停留在“推己及人的俯视境界。惩善杨恶的神是创造主,是洞晓世界生灭的因缘。
那么,有没有可能并且如何通过人的行为对世界进行拯救?灾难意识中强烈的角色焦虑感来自于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和位置:应该从人的主体性寻找支撑点还是从我们尚未认知的自然界寻找支撑点?一方面,人被天地自然的普遍规律所规定;另一方面,人又有其超出天地自然的特殊法则。中国传统天人之和理论含有的人作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马克思人化自然思想相通。它并非人类中心主义,不主张人统治万物,征服万物,而是看守天地,顺应天地规律。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应该把握的生态伦理意识。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这个思想开启了治疗灾难焦虑症新哲学的广阔思路,尽管实现的路途还很遥远。它启发我们将灾难启示带来的理性与自信变成一种稳固的精神“常态”,学会在差异、矛盾、斗争的关系来研究灾难意识,在内心自由的层面上守望自然,并重新定义人在自然法则中的位置。
(责任编辑李明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