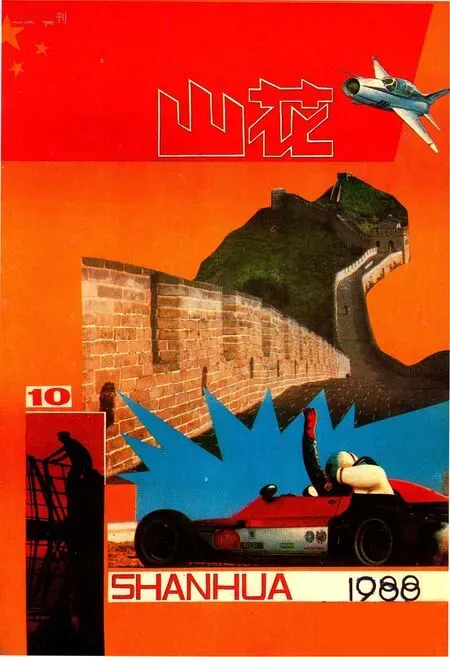论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女性形象的他者气质
2011-08-15唐美华
唐美华
论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女性形象的他者气质
唐美华
“在最纯粹的男人的角度里,即使最独特的见解,也往往笼罩着社会规定的意识和影子,她沉迷于美妙深化的瞬间,却把日常的沉沦期间的现实变成虚无。于是女人消失了,成为寻求美的抽象手段。”在男性本位创造的神话中,女性是一种被动、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是被男性享用和欣赏的。哈代威塞克斯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女性形象,哈代虽然对女性怀有不同于其他男性作家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但也无法彻底真正摆脱男权意识的束缚,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依然渗透着男性的主观意识和偏见。
德里达认为:“西方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所有的形而上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蓝本先于摹本等”这种二元对立在社会中表现为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倾向,他将这两种倾向符合成一个词——菲逻各中心。在菲勒斯中心的社会里,男人和女人的二元对立意味着男性为正面价值,代表男性价值的菲勒斯则是一个超验的能指,女性只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用以证明男性价值的“他者”。“也许她是代表着男人身上某种东西的一个符号,而男人需要压制这种东西,将它逐出到他自身的存在之外,驱赶到他自己明确的范围之外的一个安全的陌生的区域”。
另一位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从意识形态、生物学和社会学几方面论述了所谓女性的气质、角色、地位的问题。她认为,女性气质的依据是占统治地位的群体的需要和价值观,是其成员根据自身的长处以及可轻而易举的在从属身上获得的东西规定的。男性的个性是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女性的个性是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在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作品中,女性人物也具备这种他者的女性气质。
1.虚荣善变的个性缺陷
波伏娃早在《第二性》中就说过:“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的所谓‘女性’。”她用存在主义观点对女性进行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历史的考察,她认为并不存在先验的“女性气质”,两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比两个单人之间的差异更大。正如波伏娃所发现的那样,在过去许多作家,特别是男性作家那里,“女性形象变成了体现男性精神和审美理想的一种介质,由于女性形象在文学中仅是一种介质,一种对象性存在,一个空洞的能指,所以她们总是被她们的男性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削足适履的扭曲变形”。玛丽·埃尔曼在《想象妇女们》一书中指出,西方文化各个层次上充斥着一种“性别类推”的思维习惯,即人们习惯于以男性或女性的特征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分类。她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男性批评家笔下的妇女作品中总结出十种模式,即“无形”、“被动”、“不稳定”、“封闭”、“贞洁”、“物质性”、“精神性”、“非理智性”、“依从”以及难以改变的形象“悍妇”和“巫婆”。这种思维习惯造成了女性形象的不真实的表现。受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哈代笔下的女性人物也被或多或少地贴上了带有这些性别偏见的标签。见异思迁、虚荣冲动、软弱、矛盾而不合逻辑等一些在男性价值观中受轻视的个性特质总会如影随形地出现在她们身上,甚至在哈代看来,这些个性弱点也成为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因素。在《远离尘嚣》中,作者多次借男主人公奥克之口对女性这种特有虚荣心的品质进行批露和讽刺。当芭思希芭第一次被奥克注意到时,她正对着镜中明媚生动的倩影微笑,而这一举动在一直暗中注视的奥克眼里却成了具有传统男权文化审美趣味的“女性被公认的弱点”。当芭思希芭对奥克的帮助并未有任何表示的时候,奥克对她作出带有男性偏见的评价“她有缺点,是虚荣心”,这是明显的因为男性尊严遭到女性漠视而表现出的恼怒。芭思希芭的高傲和虚荣使她对奥克的求婚不屑一顾,她在冲动之下给农场主波德伍德寄一张情人节匿名卡,其原因就是懊恼于他对她的冷淡与漠视,挫伤了她的虚荣心。她的轻浮行为虽然终于吸引、征服了波德伍德,但同时也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她为特洛伊英俊潇洒的外表所吸引,却对特洛伊所说要娶别的姑娘信以为真,在虚荣心和嫉妒心的双重作用下,她匆忙草率地嫁给了他从而酿就了一出悲剧。她所有的痛苦与不幸似乎都是所谓虚荣心造成的。而游苔莎的悲剧多少也是因为她对繁华都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如果不是强烈的虚荣心作祟,她和克林的婚姻似乎应该有个美满的结局。聪明灵秀的淑明明是对裘德有意,因为得知他有过一段婚姻,一时冲动赌气而嫁给她根本不爱的裘德的小学老师,正是这一冲动的行为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而在感情上她们也常常表现出犹豫不决、轻率冲动或见异思迁。范西·戴被一时的虚荣心遮蔽了眼睛,没有坚定地选择自己的所爱;芭思希芭虽然有主见,敢作敢为,却弄不清楚真正的爱情;游苔莎为摆脱荒原周旋于韦狄和克林两个男人之间;淑面对裘德的感情若即若离,不能果断地作出抉择,以及艾拉白拉对男人的轻浮放荡。以男权为中心的道德标准判断,这些品质是女人的弱点,是被否定的。哈代自己也承认这些矛盾的性格特点是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从女权主义观点的角度来看,她们的种种矛盾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父权制思维方式和菲勒斯的批评标准的反抗。
2.永恒的弱者
法国当代女权主义作家埃莱娜·西苏在《新生儿》中列出了一些二元对立项:主动性/被动性、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白昼/黑夜、父亲/母亲、头/心、概念的/感觉的、逻各斯/情感因素。这些二元对立都与潜在的男女二元对立相一致。在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以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创造出来的男女主人公。
《远离尘嚣》男主人公奥克和女主人公芭思希芭是男人和女人二元对立关系的最好体现。首先,奥克和芭思希芭这两个名字都来源于《圣经》的人物名称,奥克在《圣经中的人物》伽百列意为“上帝的大能者”是基督的使者,他代表了基督的精神,因此他拥有男权社会所赞赏的男性的优秀品格:忍让、真诚、坚定、谦卑、诚实、仁慈博爱和富有牺牲精神。芭思希芭在《圣经》里的同名人物是拔士巴,代表着耽于享乐,傲气轻浮,好冲动这些与男性文化要求格格不入的女性品质。这种带有男性文化偏见的名称指称,正好符合父权制社会对男女角色的界定。奥克从第一次见到芭思希芭,对她的感情始终坚定不移,哪怕被拒绝,依然默默付出,这与芭思希芭在感情上举棋不定、反复无常的个性正好相反。他具有极大的忍耐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遭遇破产后并没有消沉下去,依旧诚实努力地工作,保持着乐观进取的生活态度。他宽容忍耐,对情敌波德伍德给予同情和无私帮助。奥克的这些传统美德反衬了芭思希芭的女性弱点。正如波伏娃所分析的一样,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为一个低下的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高尚。芭思希芭虽然高傲要强,追求独立自主,但在强大的奥克面前她依然只是一个弱女子。她因奥克的冲撞,一气之下要将他赶出农场,而当她的羊群遭难时,她又不得不放下她的自尊,低声下气地求助于奥克;暴风雨之夜,他的丈夫酩酊大醉,是奥克及时出手挽救了麦堆,避免了巨大的损失;当与特洛伊婚姻破裂之后,又是奥克帮她经管农场,种种一切表明,芭思希芭是离不开奥克的。在菲勒斯中心的社会制度下,男人必定是强者,女人只能是弱者。苔丝从一个无知少女被亚雷诱奸,到因失贞而被安吉尔抛弃,再到最后杀死亚雷,整个就是一个受尽欺凌的弱女子反抗父权社会道德伦理压制的血泪史。同样遭受世俗社会压迫的裘德和淑,他们曾在一起并肩作战,共同对抗不公平的陈规旧俗,然而面对坎坷的命运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裘德最后一次见到淑时对她的转变发出了这样的责问:“我曾经有幸看到你那些充满希望的现实人性的才智,然而你现在却成了一个又可怜、又悲伤、又软弱、又忧郁、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人!你对世俗的鄙视到哪里去了?我可是宁死不会屈服的!”裘德从一开始对基督教义的认同到最后的彻底反叛,淑从最初的坚决反叛到最后的无奈妥协,这样的情节安排恰恰印证了父权制下男女二元对立的思想,男人是强大的,女人是脆弱的。苔丝、露西塔、游苔莎和淑无一能逃脱弱者的悲剧命运。因此,伍尔夫在《论托马斯哈代的小说》中这样论述到:“芭思希芭就是芭思希芭,但她是个女人,是游苔莎、露西塔、淑的妹妹;加布里埃尔·奥克就是加布里埃尔·奥克,但他是个男人,是亨查德、维恩和裘德的兄弟。不管芭斯希芭多么可爱迷人,她仍然是个弱者;不管亨查德多么顽固不化、上当受骗,可他仍然是个强者。这就是哈代想象力的基础部分,也是他许多作品中的主要成分。”
女性现实中低下地位以及她们的种种弱点,常成为男性轻视她们的理由。对这种颠倒因果关系的推论波伏娃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她认为,事实上,是以男性为主宰的父权制文化体制压抑着妇女,使妇女变得地位低下,而不是因为妇女地位低下而应受支配。社会各方面都限制妇女同男性一样成为独立自由的人,却要用各种方式证明女性不适宜独立,只能从经济上和精神上依附于男性。凯特·米利特也说过,正是由于父权文化对男性优越这一偏见的普遍赞同保证了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使妇女成为弱者的不是她们自己而是整个父权社会制度。受父权文化影响的哈代,虽然同情妇女弱者的遭遇,但同时却是认同妇女在男权社会中不可改变的弱者身份的。因此,在笔者看来,哈代对女性的同情是出于认同妇女本身就是弱者的观念上给予的同情,这种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是难以超越的。因此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也难免带有男权意识的影子。
3.主体地位的缺失
哈代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妇女是被看做依附于男性的另一个性别,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男性身份的双重局限,他所描绘的那些女性人物,无论是恪守传统、逆来顺受的,还是背离传统,离经叛道的,都摆脱不了受支配的客体地位。她们可以被随意玩弄、践踏和抛弃,毫无个人意志和能动选择性可言。范妮、朵荪和苏珊便是这样一类女性。美丽纯洁的范妮和中士特洛伊相爱,献身于特洛伊,而风流的特洛伊并未打算真正娶她,她被特洛伊抛弃而毫无怨恨,仍旧执著地忠贞于爱情,苦苦地寻找特洛伊,没有任何依靠的她,在贫病交加中悲惨死去。她生存的唯一信念就是找到爱人,实现自己的爱情。对于自己命运她从未怀疑和抗争过,最后终究沦为所谓爱情的祭献品。朵荪的结局似乎没有范妮那么悲惨,却同样被用情不专的浪荡公子韦狄所骗,比范妮幸运的是她实现“爱情”梦想,与韦狄结为夫妻,可婚后发现了丈夫的不忠,虽然无比痛苦,却默默忍受,全力维护她的“爱情城堡”,而最后韦狄和游苔莎私奔落水而亡的现实将她极力掩饰的爱情谎言彻底击碎。面对命运的不公,她选择了默默忍受,这一点上她和范妮的命运没有差别。另一位逆来顺受的女性苏珊,同样是绝对服从命运安排的婚姻。她被酒后的丈夫以五个基尼卖给了一个水手,出于对丈夫的愤怒或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她赌气跟随水手而去。然而对于这一荒唐的行为她内心不仅没有任何质疑,反而认可了这个被卖的事实,心甘情愿地跟随水手四处流浪。在她看来,水手付了钱买了她,他在道德上就获得了正当的权利。尽管她后来对这种交易具有的神圣力量表示怀疑,但她始终未能走出这种困惑。在父权制社会下,女人是男人的财产,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这些妇女完全屈服于男权主义的统治,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默默忍受着不幸的命运。人们对待她,像对待一具活娃娃,她得不到自由。“一种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因为她越不运用她的自由去了解、捕捉与她周围的世界,她的源泉便越枯竭,而她也越不敢将自己肯定为一有主见之自我。”她们将父权制标准自觉内化,成为被男权意识形态所异化的典型女性。她们的全部身心都是奉献给家庭和男性的,在思想和生活上以付出自己的权益与独立为代价。
哈代终究没有塑造出一个彻底不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独立女性,没有提出给女性的主体性地位,对女性的同情依然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同情,如同对物的同情与爱惜,而物与人终究是不平等的。
[1]罗婷.女性主义文学和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5
[2]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14
[3]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16
[4]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5
[5]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23
[6]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7
[7]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65
[8]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16
[9]哈代.无名的裘德[M].刘荣跃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363
[10]陈涛宇.哈代创作论集[M].北京: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214
[11]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2
[12]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7
唐美华(1974—),女,湖南永州人,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湖南师大2008年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毕业。专业方向:翻译学与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