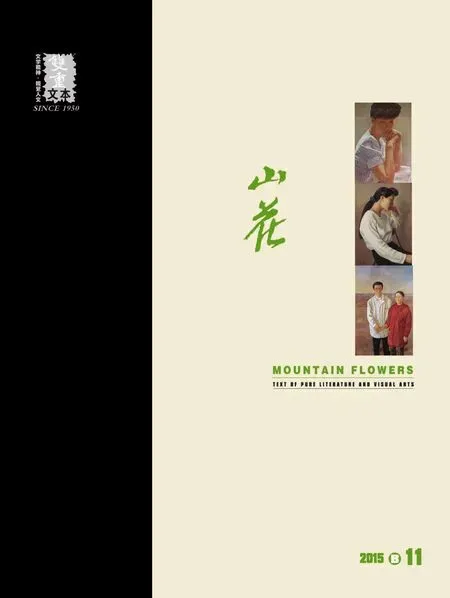以两部灰阑记为例,浅析中外戏剧创作原则之异同
2011-08-15
在东西方戏曲与戏剧的创作过程中,作家都遵循着一定的创作原则,也就是按一定的剧目体制要求进行创作。在不同年代、不同民族,这些创作原则可能截然不同,可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都代表了一个时期内一个民族的主流文化思想。如今,回过头来将同源作品的不同创作原则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些原本毫无关联的相似点。本文将以《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与《高加索灰阑记》为引,探讨元杂剧的“一本四折”、欧洲的“三一律”以及现代戏剧复杂的创作原则,发掘其中的相关之处,感受东西方戏曲戏剧在场次安排上的不同特点。
元杂剧注重尊崇严格的传统体制
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曲赋,自古皆遵循一定结构体制,如作诗就要求有平仄,讲韵律,求意境等,元杂剧亦如此。人们常以“一本四折”来概括元杂剧的传统体制,“折”与唱词相关,一些同一宫调中的不同曲调连缀构成一个套曲,而一个套曲就为一“折”,通常四个套曲往往就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也存在五折构成一个剧目的情况。除了四折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故事开始最初或两折间增加“楔子”,它原指在木器制作过程中,在木榫缝里插入的以增强牢度的小木片,用在元杂剧中能起到介绍人物、补充故事内容、连续剧目情节的作用。
《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就是一部严格按照标准体制创作的元杂剧,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马致远的《破幽林孤雁汉宫秋》,郑光祖的《迷青锁倩女离魂》等也都是如此,以一本四折加楔子的体制敷演一个完整的故事。当然,并非所有的元杂剧都按这个体制来写,如《赵氏孤儿大报仇》一剧就包含了五折,而关汉卿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一剧则没有楔子。不论折数多少,每一折都为一个固定的场景,在该场景会引发一个或多个矛盾,通过这些指向主人公的矛盾的层层堆砌,推动情节的发展。
《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的开场楔子中,剧中部分主要人物悉数登场。通过张海棠之母刘氏之口,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张家有一儿一女,儿子张林,女儿张海棠。时运不济,这个原本祖传七辈的科第人家如今无以营生,女儿为家人谋生计而入风尘。当地有一位财主马员外马均卿,看上了张海棠,欲娶她作妾,而张海棠也原有此意,双方便在张家碰了面,商讨嫁娶事宜。张海棠的兄长张林认为妹妹出入风尘有损门风,因此看不起她。然而,他自己却着实没有为家庭作出任何贡献,因此他一气之下决意独自前往汴京投靠舅舅创出一番事业。“大浑家”,也就是此时未出场的马员外正室的性格通过楔子中人物对话可见一斑,实属蛮横泼辣之辈。而对话中提到的“若是令爱养得一男半子,我的家缘家计,都是他掌把”,①为下文“二母争子”的情节埋下了伏笔,成为“争子”的根本缘由。
第一折发生在马员外家中。大浑家与奸夫赵令史合计给马员外下毒,以谋其家财。同时,张林投亲无主,又连遭灾祸,不得不回来投靠妹妹。张林不听海棠的劝说,只求海棠能给他些盘缠使使,谁知这件事恰好被大浑家撞见,挑拨离间,不仅将张海棠给其兄的衣服头面说成是自己的,加深二人之间的矛盾,又骗马员外,说张海棠有奸夫,连衣服头面都给了他。还将准备好的下了毒的汤嫁祸给张海棠,夺走五岁的海棠之子寿郎,嘱咐赵令史在衙门打点,一切似乎志在必得。
第二折发生在公堂。郑州太守苏顺糊涂办案,因张海棠曾经的下等身份而一再怀疑她的论词。而大浑家与奸夫早已买通相关人士作假证,苏太守甚至在未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对张海棠动刑,使其屈打成招。
第三折发生在押解至开封府的途中。海棠与兄长张林在一家酒馆偶遇,昔日误会解开,张林如今已是开封府五衙都首领,表示定要为妹妹讨回公道。这时恰逢大浑家与赵令史,他们本给了两个押解张海棠的衙差银子,让他们在半路杀了张海棠,如今未得手,故前来看看情况。两路人马在一番口角与厮打后收场,一同前往开封。
第四折发生在开封府的公堂之上。包待制在询问了张海棠相关案情后,传一干人等上堂,当堂以灰阑断案,识破大浑家与奸夫合谋杀夫、夺子、嫁祸的实情,还了张海棠一个公道。
通过以上四折主要内容的概述可以看出,每一折均只有一个固定场景,从马员外家中,到当地公堂,再到押解途中的一家酒馆,又到开封府的公堂,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尤为紧凑,高潮迭起,种种真相与谎言交杂在一起,接二连三地激化人物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内容安排上可谓环环相扣,起承转合,缺一不可。同时,推动该故事的矛盾主线,都与张海棠密切相关,所以毋庸置疑,张海棠是全剧的核心人物。
元代戏曲文本结构与欧洲古戏剧“三一律”
“三一律”是指在戏剧剧本创作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时间、地点、行动的一致性,故事必须发生在一日之内、同一个地方,有着单一的故事情节。这种理论最初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被提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他指出“所模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意在指出戏剧行动的一致性,当然,虽然他重在关注主要情节,但也并非排斥所有次要情节。此外,他还提到了“以太阳的一周为限”,这些说法都为后来“三一律”的理论表述提供了参考。后来,该理论由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家进一步确定与推行,一度成为欧洲戏剧创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到了16世纪,基拉尔底·钦提奥与洛德维加·卡斯特尔维屈罗先后在曲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后明确指出剧情发展应以一日为限,而戏剧行动必须限于一个地点,次要情节必须排除,只能有一条情节线索。这种最终被确定下来的戏剧创作理论于17世纪在欧洲剧坛大放异彩,占据主要地位。这得益于它对剧本结构集中、严谨的要求以及在艺术上简练、紧凑的优点。这一时期产生了不少精良之作,莫里哀的《伪君子》便是其中的佳作之一。
然而,纵使在“三一律”指导下,戏剧创作领域得到了一定的规范化,但也正是这种约束作用,严重束缚了剧作家的创造力。因此,随着18世纪浪漫主义的兴起,作家开始抨击、反抗“三一律”,并最终得以突破,戏剧创作从此开始走向多元发展的自由环境,更多矛盾、更为复杂,情节更为扑朔迷离,人物性格多样化的故事开始出现在观众面前。
将元杂剧的创作原则与“三一律”相比可以发现,两者虽没有什么源流关系,在对时间、地点的处理上也有异同,但在故事情节的要求上,即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与“三一律”要求单一的故事情节,两者产生了较多的相似点,具体分析如下:
从故事发生的时间长度来看,元杂剧的故事发生时间没有限制,可以是事隔几日、几年甚至几十年不等,通过密切内容片段间的关联,同样可以达到紧凑的效果,如《梁山泊李逵负荆》的故事事隔三天,《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的故事时隔五年不止,《赵氏孤儿大报仇》的故事则横越二十多年,然而这些作品并未因为故事发生时间的长短而影响其故事性。
从故事发生的地点来看,正如上文所述,元杂剧对地点的处理也有它一定的要求,一折为一个场景,即一个地点。而且,这些场景通常为定点,是实实在在的某一处地方,一般不会出现某一折的场景不停地变换,并且不知何处的情况。因此,虽然没有固定在同一个地方,但是与后来更为现代的戏剧相比,元杂剧对地点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与“三一律”有一定相关之处。
从故事发生的情节来看,由于每出戏的演出时间有限,其中大部分又为唱词,时间消耗量大,因而为了能在有限时间里将故事讲清楚,情节安排必须高度严密,主要情节会通过演、唱来表现,而次要的情节则将通过某位主人公之口叙述表达。因此,全剧只保留了与故事核心有关的绝对不可剔除的内容,这一点与“三一律”的故事情节创作要求比较相似。
譬如《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中,第一次在公堂,街坊邻居作证孩子是大浑家所生,其实他们事先是被收买了的,而这件背地里收买的事没有在剧中真实演绎。大浑家曾说:“(搽旦云)他无过是指望着收生老娘和街坊邻里做证见,我已都用银子买转了。”②更具体地提到也只不过是通过街坊在上堂作证前私下的话语来展现:“(二净扮街坊、二丑扮老娘上,净云)常言道: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如今马员外的大娘子告下来了,唤我们做证见哩。这孩儿本不是大娘子养的,我们得过他的银子,则说是他养的,你们不要怕打,说的不明白。”③同样是在背地里做的事,大浑家下毒谋杀马员外这一情节因其重要性,有着不同的待遇。在大浑家与赵令史商讨合谋算计他人之时,已提到:“(搽旦云)赵令史去了也。我且把这毒药藏在一处,只等觑个空便才好下手。”④而在挑拨了张海棠与马员外之后唤张海棠去拿汤拿盐酱,并趁机下毒:“(搽旦云)前日这一服毒药,待我取来倾在这汤儿里。(做倾药科,云)海棠快来。”⑤可见,元杂剧中的表演空间也只为情节的重中之重准备,这一点,不能说与“三一律”无一点瓜葛。
西方现代戏剧追求复杂的综合结构
《高加索灰阑记》创作于20世纪,早已突破“三一律”创作原则的限制,沿用了“故事套故事”的传统叙事手法,从文本结构上来看更为复杂,因而故事容量也更大。作为“故事套故事”手法运用的佳作在欧洲文学史上数不胜数,短篇小说集《十日谈》这部薄伽丘最优秀的作品便是该手法运用的典范之作。《十日谈》的创作背景是意大利佛罗伦萨1348年发生的一场瘟疫,这部作品的诞生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场灾难。在作品开始之初是一个楔子,也就是作品结构外围的大故事:7位少女和3位男青年为躲避1348年的这一场瘟疫,逃到了乡下,为了打发难熬的时间,决定在这10天里,每天定一个主题,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作品的核心部分就是这100个故事。使用故事套故事的手法可以有效地将不同的故事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虽然故事与故事间由于各自的主题不同而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它们在思想内涵上都闪耀着人文主义的的光辉,旨在揭开教会神圣的面纱,对其腐败、虚伪、奸诈进行有力批判,颂扬人类敢于战胜一切,讴歌爱情,讴歌人性。
《高加索灰阑记》也是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传统手法。“加林斯克”农庄原本是山谷的主人,由于战火不得已离开。在这片山谷暂时脱管阶段,“罗莎·卢森堡”苹果栽植农庄完成了这一地区的水利灌溉工程设计,使山谷能更好地得到利用。然而,毕竟他们不是山谷真正的主人,当原来的主人在战事平息后回来,山谷又该归谁所有?最终,经过双方协商,山谷归“罗莎·卢森堡”苹果栽植农庄所有,成全了一项伟大的设计。为了庆祝双方这一和解,特别请了一支乐队前来表演改编自中国《灰阑记》的故事。这便是全剧的楔子部分,它所套的故事也就是歌手所表演的这一段“灰阑故事”,而“灰阑故事”中又嵌套着两个母亲与孩子的故事以及“另类”法官的故事。在全剧的最后,开头楔子中的故事不仅收了尾,还与所套的故事作了关联性的阐述:
“……但是《灰阑记》故事的听众,/请记住古人的教训:/一切归善于对待的,比如说/孩子归慈爱的母亲,为了成材成器,/车辆归好车夫,开起来顺利,/山谷归灌溉人,好让它开花结果。”⑥
布莱希特通过这种手法,不但能使戏剧结构与内容看起来更为新颖,而且也符合他戏剧理论“间离效果”的要求。首先,一般来说,自己看演出与看别人在看的演出是不同的,相比较,前者更为直接,因而更容易受剧中人物角色的影响,容易深陷故事情节与思想中;而看别人在看的演出时,由于中间还有中介人,情感上有着一定的阻隔,观众往往只能将自己的情感直接投射到第一对象,在本剧中也就表现为讲故事的歌手,而对于故事中的故事,观众将会投以更为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而不是跟着角色的情感走,这样一来,通过“陌生化”处理,使观众对灰阑故事更多地产生合乎自己逻辑的观念想法;第二,中断情节的发展,尽量避免观众产生共鸣也是“间离”的一大特色。如《高加索灰阑记》中第三幕末,格鲁雪与西蒙的误会加深,铁甲兵带走了米歇尔,等待他们的是法官的判决,这时歌手唱到:“铁甲兵带走了孩子,宝贝孩子。/不幸的女人跟他们进了城,危险的城。/生身的母亲要讨回孩子。/过养的母亲被送上法庭。/谁来审案?孩子会断归哪一个?/谁来当法官?清官还是赃官?/城里起了大火,法官座上坐的是阿兹达克。”⑦故事讲到这里已是紧要关头,歌手的歌唱似乎也在昭示下一幕的内容。然而,“事与愿违”,第四幕从开始到结束前的一大部分可以说都在介绍阿兹达克的故事。虽然这部分内容对把握阿兹达克的性格很有必要,但是客观地来说,故事在这里的确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大断点,原本紧凑的情节、观众紧绷的情绪在这里突然中断,从“间离”的角度来讲,是去除观众已融入其中产生的紧张感,换一个暂时完全无关的场景,以保证再次回到前一场景时,观众会用一种理性的思维来对待所表演的故事,而不是紧张地进入演员的情绪,被剥夺应有的冷静思考。
本论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课题《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灰阑”——两种灰阑记文本的解读》科研基金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