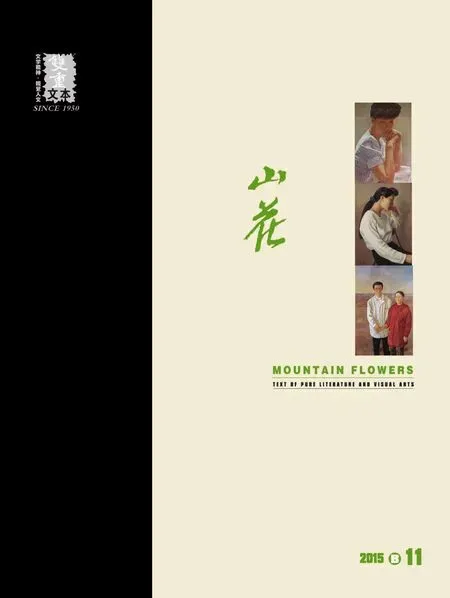文学翻译中再创造的“理”和“度”
2011-08-15薛海滨
薛海滨
凡事皆有度,文学翻译也不例外。文学翻译的标准向来被认为是最具模糊性、最具争议性的,有人主张译文力求忠实,原文至上;有人主张发挥译语优势,超越原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来争去,终无定论。当然,争论的焦点无非是译文有没有权力偏离原文。本文所议论之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即指译文有意或无意偏离原文的现象。再创造是文学翻译中的常态,如许均先生所说:“一种是‘主观性’的创造,即主动的创造,另一种则是翻译过程中实在有很多无法逾越的困难,于是译家必须‘不得已而为之’,加以变通,进行创造。”但是,这种再创造的行为是否真要与忠实的翻译行为分庭抗礼,另起炉灶,产生新的翻译标准?果真如此,那么这种再创造还叫翻译吗?与普通的文学创作又有何差别?其实,再创造只是译者在复杂的翻译过程中作出的合理选择,并没有完全撇开忠实的原则,所谓“创造”并非天马行空,肆意妄为,弃原文于不顾,而是创而有度,在不脱离原文的基础上合理发挥。那么,这个“度”是什么,译者在进行创造的时候“理”又在哪里呢?
再创造的“理”
认知语言学告诉我们:意义并非直接源于现实,而是通过对现实的体验而获得的。不同的人接触同样的现实,所体验出来的意义可能会是不同的。文字是用来记录意义的,但并非意义本身,而只是一个激活码,用来激活人在体验现实世界过程中已经在头脑中形成的意义。文本是作者利用文字手段来记录自己头脑中现实生活的影像,即作者力图通过文字来留存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意义,但由于体验不同,同一文本在不同的人脑海中激活的意义可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翻译不可能百分百忠实于原文,创造是必然的。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翻译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创造性、语篇性与和谐性。体验性是指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和理解都源于体验性活动,译者必须对原文文本作体验性理解才能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互动性是指在翻译过程当中,作者、译者、读者、原文文本、译文文本以及现实世界都在进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受到自身认知、作者认知、译文读者认知、原文文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创造性是指译者是认知主体,人的认知本身就有差异,不同译者对同一语篇必然存在不同理解。语篇性是指翻译活动是以篇章为基本单位的,而不是以单个的词或句子为单位的。和谐性是指翻译必须照顾到两个世界(客观世界和认知世界)的和谐,译者的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力图在译文文本中复制原文文本的两个世界;此外,翻译过程还要兼顾作者、文本和读者三者之间的和谐。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从而使其译文不可能再现原文的原貌。
此外,不同文字能创造不同的文学美,因为不同文字具有不同的形式美。形式和内容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文学美有时源于形式美,而形式美在两种文字互译过程中有时则难以传递。例如,唐诗的美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汉语的平仄押韵,如译成英文,这种美便荡然无存。
以上理由都证明文学翻译再创造实属无奈,但有时可能也会出现像许均先生所言的“主观性”创造。我们不用去管译者为何要故意创造,我们只要弄清楚能不能故意创造。实际上,即便出现了“主观性”创造,只要是好作品,能为读者所接受,也是合情合理的。理由是:首先,“主观性”创造不是没有可能,例如,我们可以故意将诗歌体译为散文体,而不管该诗歌能否在译语中同样以诗歌面目重现。其次,原文和译文都是文学作品,一般读者对作品的认可只是基于其文学价值,只要译文具有这种文学价值,没有人会去过问译文是否违背了原文。最后,只要译文的文学价值能够促进译语文化的发展,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承认其合理性,而非得问其违背原文的罪呢?
再创造的“度”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中译者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再创造。但是,所谓再创造是否意味着译者可以脱离原文而随意发挥呢?当然不是。如果译者彻底抛弃原文,则翻译就不再是翻译,而变成译者的原创了。那么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又该如何把握再创造的“度”呢?
第一,既然是翻译,译文和原文一定存在一个共核,即统一之处。一般情况下,译者需保留原文宏旨不变。以林纾的翻译为例。林纾是清末公认的文学翻译大家,但他的翻译却总有“不忠实”之嫌,其译文很多情况下属于“主观性”创造。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一书中评论道:“林纾译述,主要是传达小说的情节,他认为无关宏旨的枝枝叶叶,往往不惜删去。”例如,如果他觉得原文繁冗,用古文翻译很吃力,就采用撮译的方法。《块肉余生述》第一章描写一个接生的医生,原文用了一百多字,对医生的温和性格进行夸张的描述,林纾只译为两句话:“医生平婉不忤人,也不叱狗。”林纾的译法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确“不忠实”于原文,但由于不悖原文宏旨,还能体现汉语的文字魅力,所以仍被后人奉为译作中的精品。
第二,不能出现误译。虽然不同译者对原文都有不尽相同的解读,但理解不同不等于对原文做出错误的解读。所谓误译,是指不合理的翻译,其译文明显有违上下文逻辑,或有违客观常理。
误译往往是由于译者语言功底不深,或对翻译不负责任的态度造成的,但有时候,译者的文化认知也可以造成误译。孔慧怡曾经对《福尔摩斯探案集》中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并撰文指出一些晚晴译者在翻译该小说集中某些西方妇女形象时有创造性扭曲。例如,其中有一个故事,名为《窟中秘宝》,讲述的是一位贵族家中的男管家突然失踪,而经常与其有暧昧关系的女仆似乎受了刺激而投河自尽,却又找不到尸体。福尔摩斯断案时发现男管家是死在这家大宅的地窖里。因此,他推断该管家是想一心谋取该家族家传宝物,而到此寻宝,然而寻宝需有人帮助,故找来曾受他感情欺骗的女仆来帮忙,结果自己却死在地窖里。到底是谁杀害了男管家呢?不言而喻,最有嫌疑便是这位女仆。原文中所描写的女仆是一位凯尔特女人,在英语文化中,对凯尔特女人有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就是热情奔放,喜怒易形于色。写到福尔摩斯对案情的推理时,作者首先有意说明她是凯尔特人,意在让读者明白,福尔摩斯认为这位女仆在协助男管家寻宝这种紧张的气氛下难免会情绪失控。然后,作者还描写了该女仆当时的心理状态,她不断想到这个男管家是如何对不起她,曾让她失去贞操,而后又无情地将她抛弃。这就更让她爆发了杀人的欲念。最后,在描述女仆杀人的情形时,作者所使用的两个英文字是“sudden”和“suddenly”(均意为“突然”),说明女仆杀人是出于一时冲动。结论是:福尔摩斯的推理合情又合理,但似乎不是对女仆杀人行为的谴责。另外一个细节让我们看到,福尔摩斯不仅没有责怪这位女仆,反而还对其有所同情,因为作者在描写时采用了一连串疑问句,均是这位女仆发自内心的疑问,她在责问自己的良心,责问自己的杀人动机。这些疑问句是一种修辞手段,意在舒缓这种杀人事件的震撼性,显示这位女仆善良的一面。因此,在福尔摩斯看来,就算这位女仆杀了人,顶多也是“误杀”,根本算不上什么“谋杀”。
然而,这个情节在清代译者严独鹤的笔下,却变成了如下的文字:“而秋风团扇之捐,固已久怀怨毒,报复之念,蕴诸于心。正如弩箭在弦,随机即发……兰儿于是时,忆往事,顿触旧恨。以为此天假我以大好之时会也,不死此伧无以泄吾愤。”其中,“秋风团扇之捐”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的一夫多妻现象,也可指男性在外金屋藏娇或与妓女交游的现象,虽说可以反映女性因地位低下而心怀怨恨之意,但并不表示对男性道德观的谴责。这已经不符合原文的意义,更何况,传统中国女性柔弱哀怨的形象与凯尔特女性感情炽烈的形象相去万里,原文中女仆可能因为性格冲动而杀人的动机则被完全抹杀。取而代之的是“久怀怨毒,报复之念,蕴诸于心”的蓄意杀人动机,也就是说女仆杀人是早有预谋,只是时机未到,现在“天假我以大好之时会”,所以为了“泄吾愤”而杀人,是不折不扣的谋杀。
原文是“误杀”,译文是“谋杀”,天壤之别,而这种质的改变势必会破坏福尔摩斯断案推理的严密性,同时也会有损于该故事文本前后的逻辑连贯性。文本是一个整体性概念,译者在翻译时切不可割裂这种整体性,而误译正是造成割裂的罪魁祸首。
第三,译文应具备文学性。文学性主要强调文学的美学概念,提倡 “文质彬彬”,反对“巧言令色”。孙建成和温秀颖在评述刘士聪先生的文学翻译美学思想时,曾指出文学翻译的三种美:音韵之美、词句之美和篇章之美。音韵之美指语言的声响与节奏之美,即文字音乐性;词句之美指选词得体,句子长度适中,能有效地传递思想感情;篇章之美指文章叙事语气、行文风格、前后逻辑等的一致性。试想,如果原文具有很高的文学性,而译文却语气生涩,诘屈聱牙,让人不忍卒读,这样的译文还有何价值可言?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语言的文学美可能不尽相同,翻译中不能随意复制原文的语言模式,不当的复制很有可能破坏译文的文学美。若两种语言模式不一致,必须用可接受的译语模式来替代原语模式。例如,汉语中旅游景点解说词的翻译往往令人很苦恼,因为其遣词造句显得华丽铺陈。某旅游景点有解说词如下:“这里三千座奇峰拔地而起,形态各异,有的似玉柱神鞭,立地顶天;有的像铜墙铁壁,巍然屹立;有的如晃板垒卵,摇摇欲坠;有的若盆景古董,玲珑剔透……神奇而又真实,迷离而又实在,不是艺术创造胜似艺术创造,令人叹为观止。 ”这段文字成语或四字格的叠用层出不穷,这是汉语独特的美,会使汉语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感强,尽显音韵之美。但是,如果译为英文,就没必要将所有的成语或四字格全部译出,因为英文词汇的音节完全不同于汉语。如果过分追求忠实,反而会使英文显得罗嗦。英文崇尚简洁之美,实在之美,只需寥寥数笔,将景点的特色描绘出即可。
翻译本身就是译者戴着脚镣和手铐在跳舞,文学翻译艺术性高,则更是如此。虽说这样跳舞很难受,但这脚镣和手铐却摘不得,只有在适合文学翻译“度”的前提下进行再创造,才能造就好的译文。
结论
文学翻译中译者再创造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必然会发生,百分百的“忠实”译文是不存在的。由于认知层面和语言层面广泛存在的差异性,文学翻译就只能通过再创造的手段来弥补这种缺憾。但这种再创造是有限的再创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种种因素的牵制,尤其是原文的牵制。如果译者任意而为,不顾原文,翻译将不再是翻译,甚至会使损害原文和译文的文本价值。因此,文学翻译实际上是在尽可能尊重原文的前提下,扬译语之长,补原语之缺,创造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1]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2]孙建成,温秀颖.翻译美学思想与译作的审美重构——简评刘士聪文学翻译美学思想[J].中国翻译, 2007:45-48.
[3]许均.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4]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