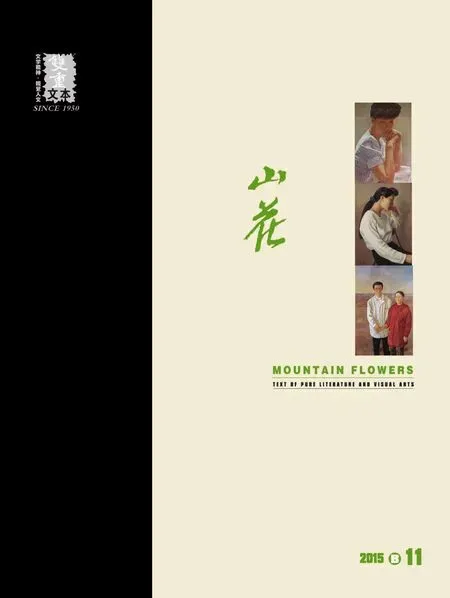从“以理化情”探寻《庄子》人生美学
2011-08-15杨菲
杨 菲
从《庄子》一书看庄子的人生美学思想,他的“情”和他的“理”是不可分割的。“情”,从心,青声,本意是感情,许慎在《说文》中的解释是“人之阴气有欲者也”,《荀子·正名》中说:“情,性之质也。”情,是一种与生俱来、不可摆脱的人性特点。庄子也明白这一点:“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庄子的情,更主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情感而非欲望;至于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在庄子看来,那是外界带给人的考验和伤害,不在他所谓的难以摆脱的内在情感的范围之内。庄子很清楚“情”于他的人生所占的分量,为了避免因情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他很自觉地用自己所掌握的理性和意志对情感发展的过程加以控制。“理”,从玉,里声,本义是加工雕琢玉石,在《说文》中被解释为“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庄子认为理对情的雕琢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通过理的规划,情才更显其美好和可贵,情给精神自由所带来的负担,以及由此导致的自我的人生困境,才可找到解脱的出路。
人生背景
庄子生活在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灾难随处可见,整个社会都笼罩着强烈的不安定感。动乱的环境也使各国政策开明,学术思潮空前活跃,各种学术流派竞相崛起。兼容并蓄的文化大氛围,使庄子特立独行的思想具有了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可能性。庄子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关注,《庄子·秋水》中就谈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礼聘庄子之事。
思想的繁荣带来的不仅有学术的发展,也有社会秩序变动、人心浮动的不良结果,这些结果给庄子等文人带来的困惑是逃避不了的。庄子认为“为政当无治”,主张“为政之道,勿庸干涉,当顺人性之自然,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庄子对统治阶级彻底失望,对旧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怀疑和批判。庄子深切体会到,作为这个庞大的社会体系里的一员,个体的人类是多么的悲哀。不止如此,政治制度不断虚化的流弊带来世俗道德的虚伪,疲于追逐外物的人们为了获取各自的利益,不惜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很多不能适应的人,在矛盾中忍受着传统思想和现实社会之间的不和谐所造成的煎熬,迫切渴望找到一种心灵解脱之道,来作为自己在这乱世之中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宿。
庄子之“痛”
庄子只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一生主要活动在社会下层,而且生活常常处于窘迫状态。有人曾将庄子的窘迫描述为“处穷闾隘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庄子·列御寇》),还有记载庄子曾“往贷粟于监河侯”(《庄子·外物》),可见其生存条件的艰难。长期穷苦清贫的生活,造成庄子长期痛苦的体验。但是,庄子不愿去做官,而且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官场往来:比如他有机会成为一名衣食无忧并且可以自主做学问的清客,但他放弃那种看似合理的施舍,更愿意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
庄子对德有着过高的期望,他刻意坚守冷峻的孤傲,不认为政治上可以救世,所以他鄙斥那些奔走呼号以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比如庄子自比为鹓鶵,讥笑惠子在梁国做相是“鸱得腐鼠”的有名故事;庄子更不愿担当救世的责任,认为整个世界最终都是不合理的,他在临死前嘱咐自己的弟子不用殡葬自己,弟子说“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却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庄子·列御寇》),他以夸张的游戏之词,道出内心对世间不平之事的彻底不谅解,表现出深深的无奈和愤恨。然而,庄子并不能做到像他所想做到的那样洒脱,他在内心为生活在底层的人们鸣不平,他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心不得冷却,他遭受着来自社会不平和自身情、理纠结的双重煎熬。以下两个问题是他困扰最多的。
(一)生与死
生与死的问题是人生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在庄子,也是如此。无论多么健康、长寿的生命,必然走向死亡,如《庄子·大宗师》所言:“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认为人不可能脱离生命有限性的限制。
然而,庄子对于生命的态度,貌似看得很开: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韬,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庄子·知北游》)
这却恰恰表明,他是深深眷恋的。他说无所谓,是因为感到悲哀且无奈,是因为不愿接受生命无情的短暂。对自然生死大限的无奈,使庄子感到痛苦。
(二)“命”与“情”
庄子在《大宗师》有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将这种非人力所能干预的必然性,称为“命”。
庄子痛苦的原因不在于他对命运的妥协,也不在于他的感性和懦弱,而在于他做不到对现实的和解。庄子对弟子说不愿被埋葬,是因为他在意不论怎样都要被那些吃食腐肉的动物所分解,对他来说不论哪种动物,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是他在用对身后事的态度,表达他强烈的不理解和无言的愤慨。
庄子内心中激烈的情感不得抑制,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极端有限,这种矛盾不得解脱,他转而寻求个人精神冲突的释放点,提出完全顺从自然的“天命”、“命定”理论。当庄子衣着褴褛去拜见魏王,面对魏王“何先生之惫邪”的询问时,庄子这样说:“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在他看来,“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是命运让人来到世上辛苦劳作,而离开人世则是造化命运安排人去歇息。天地自有公断,困苦发生在人身上,只是命运的安排。“……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庄子·大宗师》)既然命运的力量那么大,在命运面前,在人生苦难面前,还有什么可以抗争的呢?在庄子看来,能做到“安时处顺” 就已经不错了。
王圣美认为“心之美者为情”,庄子认为“情”是人的精神自由得以实现的负担。所以在《庄子》中有这样的话:
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庄子·至乐》)
喜怒哀乐,虑叹变,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庄子·齐物论》)
但是要超脱生死的束缚,摆脱命运的局限,达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的境界,就必须做到无欲无为、不为外物所牵绊。看似对生命顺从的庄子,实则是以自我的坚守认真地测量着公正的尺度。他满怀着深深的失望和痛苦。
解脱之途
庄子认为,通过真正理解自然本性,修炼自身的内在意志,做到 “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庄子·田子方》)的程度,才能达到 “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的境界。在庄子看来,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因顺于自然,相通于大道,才能不再为情所烦累,心也不再会受到外物变化带来的侵扰。
在庄子的寓言与故事中,大多存在一对相互矛盾的观点或疑问,到最后,其中符合庄子理论的那种观点被认可。这是庄子道出自己内心矛盾的另一种形式。然而,在试图说服别人的同时,谁又能说庄子不也是在说服自己呢?庄子在解决自我的思想矛盾时所实现的,正是“以理化情”的过程。
(一)以大观小——打破“我”对世界的执著
庄子通过打破自我对现实世界的执著,化解自我情感与理性的矛盾。
《庄子·秋水》中河伯的思想经历讲的就是突破“小我”视野的道理: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庄子了解了命运的无可奈何,因此选择了放弃世界,也放弃对于自身以外的一切事物的坚守,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命运。换个角度来说,知道了命运不可违抗,知道了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就既不抗拒,也不怨愤,还不颓废,而是以一种淡定达观的态度,以一种“无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遭受的一切,这正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庄子写道:“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庄子·秋水》)懂得这些,就不用为自己作任何的辩解了,只要以平静的心态对待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心中自会平衡。
处于这个世道之中,个人要改变生存的大环境,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保守自我心灵的自由与纯净还是可以做到的。在庄子这里,心灵的自由几乎成了他继续活下去的唯一追求。“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县解者,物有结之。”(《庄子·大宗师》) 如果觉得心灵不自由,那只能是因为“物有结之”而不得“县解”。既然做到了“县解”,那所有外界的干扰就不能对之产生什么影响了,也就能真正让外物成为与自己心灵无关的东西了。能达到这一点,保守心灵想要的纯粹与自由的状态,就不再是什么难事。
(二)“心斋”、“坐忘”
要以大观小首先是自己要“大”,那么如何才能通达“大”?对于人世间是非善恶的问题该怎么释怀呢?庄子认为只能通过“心斋”、“坐忘”的方法来实现。什么是“心斋”呢?《庄子·人间世》中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就是一种虚静养心、绝思绝虑的精神状态。那什么是“坐忘”呢?《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也就是说,要做到忘记形骸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的混沌状态。这和“心斋”是一样的,是“心斋”的进一步发展。总之,庄子所谓“心斋”和“坐忘”,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人们从自己内心彻底排除利害观念。利害观念是与人的心智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为了彻底排除利害观念,不仅要“离形”、“堕肢体”,而且要“去知”、“黜聪明”,要“外于心知”。
于是,虽身在世界之中,却可以无心而任化。郭象在《庄子注·大宗师》中说:“知天人之所为者,皆自然也;则内放其身而外冥于物,与众玄同,任之而无不至也。”“天之所为”,即是自然;“人之所为”,即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命至境,是“至美至乐”的境界,是高度自由的境界;通过“心斋”与“坐忘”,才能实现对这一境界的理性追求。
以理化情的延伸
出于对命运的深刻理解,庄子对穷达、生死、疾病这些困扰人生的问题,开始看得洒脱。既然无力对抗世道的不公,更无力改变生命的轮回,能坦然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举重若轻,就是最好的境界了;而这唯有德者能之。他说:“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德充符》)苦难与命运,人无法做出有效的反抗,只能顺从;庄子把这种顺从又上升到德的高度,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劝导别人,也劝导自己:要安时处顺——只有这样,才能让内心不平静的波澜,变得小一些。另外,因为上升到德的高度来理解,这种对命运的宽容与豁达具有了合理性,因此表现出来的,就是对生命的理解,就是达观安命的处世态度了,这是对庄子的人生观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的分析。同样是庄子不愿深埋地下和“鼓盆而歌”的故事,经过他自己理性化之后,在这里,也可以拿来用作他理解命运之后变得放达的佐证,这一点冯友兰先生的话点论得很精到:“吊唁死者而悲痛时,人在精神上受苦,是由于自己的感情,感情悲痛越深,受苦也越深。痛苦的根源是期望人不死,违反了自然的法则,即所谓‘遁天之刑’。人对万事万物增加理解,就可以减少由感情造成的痛苦。”这就是“以理化情”的动因。
无功利的审美起点,对理想世界的独守,对理可以化情的坚信,决定了庄子不会放弃对无碍自由的追寻;而追求个体生命绝对自由的理念,本身是一种消解理想与现实矛盾的终极理论——庄子注定在寻找精神出口的人生路上,走得很辛苦。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张少康.先秦诸子的文艺观[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颜世安.庄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廖群.中国审美文化史:先秦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7]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李天道.中国古代人生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