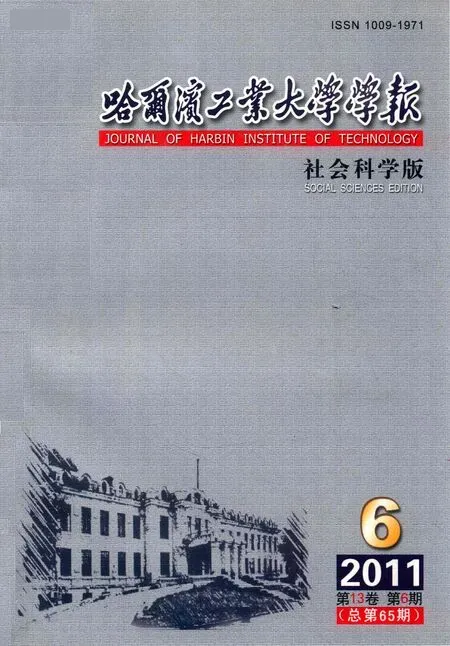明代厨婢现象的历史文化蕴涵——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
2011-04-07王雪萍
王雪萍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明代厨婢现象的历史文化蕴涵
——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
王雪萍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醒世姻缘传》是明代历史章回小说的典型代表,它对明代中下层社会生活进行了共时性、整体性的展现。以《醒世姻缘传》反映的厨婢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小说描述与各种史料的相互印证认为,明代厨婢呈现出数量庞大、分布广泛的时代特征,这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奢侈之风的盛行息息相关。奢侈之风拉动了社会对家庭服务类厨婢的需求,而商品经济的逐步深入使这种需求成为现实,它一方面健全了厨婢买卖的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上的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条件的考量冲击着传统道德的良贱分野。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透露出明代社会女性生存空间的狭窄。商品经济尽管为明代下层民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和谋生机遇,但女性却被儒家两性体系中的“男外女内”原则所阻碍,她们不得不在家庭内部的有限空间中寻求适合的生存方式,明代厨婢的大量出现正是有明一代这种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整体变迁的反映。
厨婢;明代;醒世姻缘传;妇女史
一、《醒世姻缘传》对明代厨婢研究的史料价值
婢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女性群体。有明一代,婢女显现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特征,其身份、地位以及独特的社会角色都于此时段有了不同的发展内容。对婢女群体的关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妇女构成的多样化和多层化面貌。对此项研究的开展之意义,目前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但不容忽视的是,妇女研究工作的开展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便是史料的严重缺乏,以及史料类型、内容上的格式化和重复化。对此,已在妇女史研究领域取得不菲成绩的定宜庄教授颇有感触地谈道:“我曾对清朝的‘一代国策’即清皇室与蒙古贵族的联姻倍感兴趣,却费尽气力也找不到对远嫁蒙古的公主们的生活有关的任何官方记录,即使在卷帙浩繁的满、蒙档案中也同样如此。”[1]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权往往被牢牢地操控在男性手中,这些拥有话语权的男性书写者们又都对女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加以忽视,从而造成有关妇女资料的稀缺。通过定宜庄教授的言论,可以了解到关于上层妇女资料的匮乏程度。与此相比,这些资料关涉下层妇女的更是少之又少。况且,史料类型、内容上的重复率又是相当的高。许多妇女类的史料都是贴着标签塑造出来的,如贞节烈女传、女性碑传文等。这些资料为我们勾勒出的明代妇女几乎都是一个模样:女顺—妇贞—母慈。如此,不利于中国古代妇女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事实上,对婢女这样一个拥有庞大数量的社会群体,仅从阶级压迫角度来考察未免过于狭隘。因而,有必要对婢女群体从社会学角度做更深入细致的研究。由于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多以记载政治史为主,对婢女这一低贱群体鲜有涉及。因此,发掘文学作品中的史料资源成为必需。庆幸的是,明人还留下许多正史之外的史料,其中历史章回体小说就是可供研究的重要文献之一。历史章回体小说既具有小说文学性的一面,又兼具历史客观性的特质。它的描述对象覆盖广泛,不仅有官宦女、才女、贞节烈女,还有市井女、婢女、侠女、妓女等。它的描述内容亦极其丰富,若以女性活动空间为标的物的话,它除了有对闺帷内部女性家庭活动内容的精细勾勒,还有关涉闺帷外部女性社会活动的详尽描画。
《醒世姻缘传》就是一部对研究婢女具有极高史学价值的历史章回体小说。书中时代背景为明英宗正统年间至宪宗成化年间,据胡适先生的考证,其成书于清初。此书尤显珍贵之处在于它是当代人写本朝事,对明代社会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男女社会性别秩序与家庭生活进行了共时性、整体性的描写,为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广阔的明代中下层社会生活提供了极其丰富翔实的社会史料。胡适先生曾经如此评价过《醒世姻缘传》:它包含有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和“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2]。中国近代著名诗人徐志摩也对此部作品的“写实大手笔”赞叹不已:“(《醒世姻缘传》)是一个时代(那个时代至少有几百年)的社会写生。”作者“把中下社会的各色人等的骨髓都挑了出来供我们赏鉴”,“你看他一枝笔就像是最新的电影,不仅是活动的,而且有十二分的声色”,“他是把人情世故看烂透了的,他的材料全是平常,全是腐臭,但一经他的演绎全都变了神奇的了”,“他的画幅几乎和人生的面目有同等的宽广”[3].
《醒世姻缘传》的关注目光投向了明代社会中下阶层各色人们的生活际遇,能够接近真实地反映了明代婢女群体的实际情况,这恰好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厨婢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仔细阅读,我们可从中梳理出丰富的细节和有利用价值的信息,例如,厨婢的市场运行状况、厨婢的出身、厨婢在主家的地位以及出路,等等。历史章回体小说所提供的厨婢生活的细节性资料是其他资料所无法替代的。着眼于对厨婢生存状态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婢女群体的认识。从女性史的角度来看,对厨婢群体的研究,还有助于推动中国古代下层劳动女性的研究。从社会史意义上讲,对厨婢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明代从事技艺型劳动的女性也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意在立足于《醒世姻缘传》并辅以其他相关资料对明代厨婢群体作更深入的考察,以期有助于明代妇女史的整体研究。
二、《醒世姻缘传》反映出的明代厨婢状况
婢女因其侍奉主人内容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称谓。厨婢,顾名思义,即指那些专门负责为主家提供精致可口饭食的婢女。史载:“中都下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其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集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项。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之家,必不可用。”[4]据史料记载,明代以前厨婢虽已存在,但数量较少,且多寄身于极富贵之家。如“段文昌丞相精馔事。第中庖所榜曰:‘链珍堂’;在涂号‘行珍馆’。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仆四十年。凡阅百婢独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编‘食经’五十卷,时称‘邹平公食宪章’”[5]。至明代,厨婢群体则有了新发展,这些新变化在《醒世姻缘传》中都有清晰体现。
首先,厨婢群体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十分广泛。与“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之家,必不可用”大为不同的是,在《醒世姻缘传》中,那些居住乡间的卸任、现任官员及家属都蓄养厨婢,有的监生家庭也养厨婢,甚至俗称“穷秀才”的家中都有厨婢,如“一个姓游的秀才……房中使一个十三岁的丫头茗儿,厨房中一个仆妇。家中止得六七十亩地,住着一所茆房”[6](第24回)。更值得注意的是乡间医生家里也有厨婢,如专治妇产科的萧北川家里就有个做饭的小丫头[6](第4回)。再如,《醒世姻缘传》中有个开乌银铺的童奶奶家也有个烧饭做菜的婢女[6](第55回)。厨婢在社会中下层的分布如此之广泛,在社会上层厨婢的存在就更自不待言了。可见,明代厨婢数量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完备的厨婢买卖市场运行机制。某些家庭迫于生计或垂涎利益而将女孩卖为婢女,某些家庭则因豪奢的生活而需要婢女,从而产生了厨婢的供需关系。在这种买卖过程中,专业性的团伙和中介人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专业性的团伙和中介人所作所为都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的。《醒世姻缘传》中的厨婢调羹就被卖了二十四两银子[6](第55回)。高额的利润令许多团伙专门通过蓄养、买卖厨婢来牟利。《醒世姻缘传》中有一个卖厨婢的老妈子对买家讲:“家里有这们四个哩,都是调理着卖这个的。”[6](第55回)说明这个老妈子的家庭是专以买卖厨婢而牟利的。而从她培训这些女子一些上灶技艺的情况来看,他们是一个以低价买入女子,再高价卖出的有组织性的专业团伙。除了专业的买卖厨婢的团伙以外,中介人也是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个中介人的角色一般是由社会上被称为“三姑六婆”中的“六婆”之人来充当。这些人的存在,使厨婢买卖的交易过程变得既简单又高效。《醒世姻缘传》中买卖厨婢调羹一例堪为典型。童奶奶为狄家张罗买一个全灶婢女。她先找到中间人马嫂,与她讲清楚对上灶丫头的要求。第二天,马嫂便来回话,讲有三家合适的。童奶奶提出要当面试一下手艺,马嫂便把上灶丫头领到童奶奶处。童奶奶先看了丫头的长相,又问了年龄,又问了问她有何上灶本事。接着留家二日做了家常菜及宴客酒席。试过后,全家满意,童奶奶便与中间人就丫头的长相、手艺等条件进行讨价还价。在敲定了价钱以后,又写了文书[6]。(第55回)从买卖厨婢的全部交易过程来看,中介人马嫂起到了关键作用。狄家需要厨婢,既没有专门的奴婢市场可以提供,又不能大肆张扬,以待卖家,只能依赖像马嫂这样的中介人。而卖家想卖厨婢也只能借助中介人,毕竟他们不掌握需求信息。完整的厨婢买卖利益链条的形成令厨婢买卖过程得以顺畅地进行。
再次,相较于其他粗使婢女,有一技之长的厨婢在主家的地位略高些,相应地其处境也好些。李一松的《婢诗》[7]就深刻地反映了那些辛苦从事纺织、汲水、拾薪等繁冗事务婢女的悲惨境况。这些粗使型婢女们即使辛勤劳作得到的却是“事冗日长半饥饿”,“破絮无温片板卧”;同时,还要受到“毒手老拳不知数”、“淡妆亦被娇娘妬”的不公正的待遇。而厨婢因有一技之长,在主家的地位要强于那些粗使婢女。如《醒世姻缘传》中厨婢调羹就受到狄家老少的礼遇。不仅狄老爷夫妇二人善待她,就连狄家少主人也对其另眼相看[6](第55 回)。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厨婢群体在明代社会中数量庞大、分布特别广泛。不仅官宦之家有大量厨婢存在,即使中下层的一些家庭也存在蓄厨婢的现象。厨婢的广泛存在有社会需求的动因,更重要的是完善的厨婢买卖市场运行机制保证了厨婢的供应。由于厨婢有一技之长,其在主家的地位相较普通婢女略有提升。
三、明代厨婢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
厨婢群体在明代社会中呈现出的诸多面相,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有明一代社会变迁的集中反映,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明代社会各阶层对厨婢需求日益增加的背后,是弥漫于整个明代社会奢侈之风的盛行。明朝建国之初,由于礼制的规范作用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当时的社会风气呈现出纯厚、俭朴的特征。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化,以及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的活跃,使明中叶以后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表现在崇尚金钱,追求奢靡,婚姻论财,服舍逾制,伦常失序等方面。弘治元年,马文升在《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的奏疏中称:“列圣相承,一遵成宪,恪守旧章,礼仪不紊,法令严明,人尚节俭,不事奢靡。至景泰年间,祖宗成宪所司奉行未至,风俗渐移。近年以来,群小用事,恣肆奸欺,贩卖金石之徒窃盗府库银两,供帐服饰拟于王者,饮食房屋胜于公侯,以致京城之内递相效尤,习以成风。虽尝禁约,玩法不遵。军民之家潜用浑金织成衣服,宝石镶成首饰,僧道俱着纻丝绫罗,指挥亦用麒麟绣补。其官员相遇尊卑不分,俱不回避。娼优隶卒骑坐驴马,亦不让道。违礼僭分无所忌惮,名分逾越,风俗奢侈,旧章废坠,礼制因循,未有甚于此时者也。”[8]袁帙对此现象也同样是深恶痛绝,在其《世纬》中称:“痛乎!风俗之移人,而奢靡之蠧财也……我高皇帝躬服节俭,首重农桑,服舍有等,昏丧有制,贱不逼贵,下不干上。弘治以前,纯朴未凋,禁防犹在。自逆瑾黩货,继以宁彬奸赃百万,籍没无算。暨乎今日,人有邓通之铜山,家有郭况之金穴,无和戎之策而备魏绛之女乐,蔑造唐之勋而侈令公之声伎。临食者笑何曾之万钱,执筹者嗤元载之八百。”[9]张瀚在《松窗梦语》中也称,当时“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10]。时人亦警示道:“江州陈氏长幼七百余口,少事长,卑事尊,不蓄婢仆供使,所以十三世而同居不变。余乡兄弟一两人,亦各分居,各有婢仆,生疑启爨,皆由于此。且一人而有数十或至百仆者汰侈如此。”[11]
奢侈享乐的生活增加了对厨婢类婢女的需求。明人周顺昌曾说:“长安作宦者,那一人不饮酒食肉,那一人不要美姬以自娱。”[12]陈献章理想中的闲适生活是:“富而居畎畝,体便轻暖,口足甘肥。左右僮仆,随意指挥……亲友相过,饮酒忘归。纵观山云水月,鱼沉鸟飞。引满高歌,吹竹弹丝,以相谐嬉”[13]。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澄怀录曰:‘长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鸟径绿崖涉水于草莽间。数四左右两三家,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竹篱茅舍芜处。其间籣菊艺之临水,时种梅柳霜月春风自有余思。见童婢仆皆布衣短褐,以给薪水。酿村酒而饮之,案有杂书庄周太玄楚词黄庭阴符楞严圆觉数十卷而已。杖藜蹑屐往来穷谷大川,听流水看激湍,鉴澄潭步危桥,坐茂林探幽壑,升高峰顾无乐而死乎!’”[14]在这样奢侈日风的刺激下,过去以“主中馈”为己任的主妇们也逐渐荒废了此项技能,不肯甘愿每日只是操臼织纫。时人有论:“晋书论其风俗淫僻,妇女装栉织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夫此闺中细务耳,而以为关系天下乱离之由,胡可忽也。吾郡女妇之勤苦,大异于南北都会,盖淳朴之风从来未其漓也。近日富室不知闲习女红者,渐如晋史所论矣,可惧哉!”[15]黄奂讥讽到就连一些“暴发户”都追求此种风尚:“薄俗尚华靡,下至仆厮皆然。不知淡薄雅素,正大家风味。好为丽齐整,只是三家村中暴发人耳。”[16]《醒世姻缘传》中的狄家、童奶奶、秀才三家亦如此。狄家就是个经济稍显殷实的富户,童奶奶家是个开乌银铺的,游秀才家有六七十亩地,三家都只能算是个经济能力说得过去的人家,而且三家都属于“核心家庭”类型,没有侍奉老人的负担,所以家务肯定不会繁重。这一点童奶奶自己也亲口承认操持家务其实并不算难,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得了[6](第55回)。然而,这三家却都偏偏蓄养了专门负责做饭的厨婢。可见,他们之所以找婢女代做家务就是受“有闲生活”的影响。
当然,对一些面临经济困境家庭的女孩来说,选择成为技艺型厨婢女也不失为一条谋生手段。前述“中都下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择”,表明这种选择有自发的因素存在。《醒世姻缘传》中虽然没有专门描写卖女为厨婢的动因,但提到三处亲生父母卖女为婢的想法。婢女珍珠的父亲是个皂隶,母亲是个篦头的。其父为堵上他私自挪用公款的窟窿而将女儿卖到狄家为婢[6](第79回)。珍珠的母亲是这样说的,“因为家里穷,怕冻饿着孩子,一来娘老子使银子,二来叫孩子图饱暖。”[6](第79 回)话中之意很明显,将孩子卖到本地富户家中,既缓解了当前父母的经济压力,又让孩子有个温饱之所。也就是说,孩子虽成为婢女,但能获得强于本家的生存条件。另有一对不知姓氏的父母急需用钱,拒绝了一个欲出高价买她女儿做通房的大户,而将女儿卖为婢[6](第84回)。她的想法是希望孩子最好能卖到本地的、到年纪或嫁出去或收为妾的富裕家庭中[6](第84回),认为做大户的通房婢女没有名分,能收为妾的机会少,而卖到当地为婢女,如果以后嫁出去或收为妾,这对贫困人家女儿来说是个很好的归宿。因为,妾虽然在名分上地位很低,但也有个相对而言的问题。也许对一些有地位的人家来说做妾有辱身份,但对一般小民来讲有的倒很希望能让女儿给人家做妾,如另一部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提到,“江家有一女,唤爱娘……其嬷嬷道:‘我们这样人家,就许了人,不过是村庄人口,不若送与他(一吏典)做了妾,扳他做个女婿,支持门户,也免的外人欺侮,可不好?’”[17]由此可见,在明代厨婢的形成中,除解决经济压力以外,卖厨婢之家还有考虑女儿现在及将来的生存条件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厨婢数量的不断增多亦表明明代女性谋生空间依然狭小的社会现实。16世纪商品经济的活跃,的确为女性提供了许多谋生的机会,令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经济领域成为可能。有的女性在固定的商铺内销售杂货。冯梦龙的《情史》就描写过两个青年男子钟情于卖货女孩。一个是福建的林姓男子,“福建林生,弱冠。市有孙翁造白扇,一女尝居肆中。林生心慕其美,日往买扇。”[18](卷 3)另一个也是个富家男子,“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18](卷10)也有一些妇女奔走于市井巷陌之中从事小型商业活动。像以出售金银首饰或针线丝帕为生的“珠娘”;为人说媒、接生或替人牵线的“六婆”;汲水而卖或挑盐肩木的“小商妇”,都属于此类。除小商业经营以外,女性的谋生手段还有以声色娱人的性服务行业。明末清初人张岱在游历泰山时所见便证明了性服务行业的普及,“离州城数里,牙家走迎,控马至其门。门前马厩十数间,妓馆十数,优人寓十数间”[19]。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男性经商者的长期离家,为娼妓业的普遍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需求。相对而言,目前学界对娼妓现象的研究较深入与丰富,此不赘叙。但从总体考量,女性谋生途径依然狭窄。因为儒家精英们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排斥女性走出家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尽管他们也知道女性投身小商业经营活动多为生活所迫。如万历年间,周晖曾记载金陵一位老妪沈氏,本为富家之侍妾,因年老无依,以卖翠花度日[20]。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二回中介绍开茶坊的王婆时讲到,她因丈夫过世后无法度日,只好“迎头儿跟着人说媒,次后揽人家些衣服卖,又与人家抱腰收小的,闲常也会做牵头、做马泊六,也会针灸看病”[21]。但儒家精英们依然向社会各阶层传达这样的信息:凡是在外抛头露面的女人都是不具备完美妇德的女性,应遭到鄙视。如范濂就批评道:“近年小民之家妇女,稍可外出者,辄称卖婆。或兑换金珠首饰,或贩卖包帕花线,或包揽做面篦头,或假充喜娘说合。苟可射利,靡所不为。而且俏其梳妆,洁其服饰,巧其言笑,入内勾引,百计宣淫,真风教之所不容也。”[22]虽然无法通过量化数据来说明这种思想观念对女性走出家门谋生起到多大限制作用,但从逻辑上说,其形成的社会阻力肯定不小。这一切都表明,明中叶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展是极其有限的。总体上看,女性的生存空间依然狭窄。
女性进入他人家庭成为厨婢也迎合了儒家两性体系中所要求的“男外女内”原则。古代女性一般都是依人而立,自主抗危机能力薄弱,顺境时,她们会波澜不惊地平稳完成由本家到夫家生存地的转换。但其所依附的小家庭一旦有所变故,如遭遇牢狱、破产、重赋、灾荒之灾,家内女性往往就会彷徨无助,失去家庭庇护的她们被迫地要直面生存困境。而社会领域内却未能给这些无家女性安排自谋生存的途径。因为按照中国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中的“男外女内”原则,女性的有效活动空间只是在家庭内部,即社会经济领域中没有配备一套可以容纳大量女性独立地在其中谋生的机制。当然,这并不绝然意味着社会活动中就没有女性的参与,但这类女性大多集中在小型商业活动、娱乐行业当中。其中小型商业活动者是需要一定资金的,无家女性根本不具有这个能力;况且在时人眼中,凡是那些走出家门,在外抛头露面的女性大都或是在道德品质方面有所欠缺,或是与有伤风化的色情交易相关的人。另外,充斥于这类行当之中的又大都为已婚或丧偶的妇女,并不适合未婚的自由女子。而妓女又是最为世人轻贱的群体。并且,按照常人的看法,将女性从娘家到夫家完成结婚生子的生命历程看做正常的人生轨迹的话,选择做娼妓就意味着她们严重偏离正常女性生活轨道。这并不为当时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具有强烈的家庭向心力的女性们所接受。《明世宗实录》载:“凤阳府盱眙县民何雄有二女,长年十七,次年十三岁。饥,雄欲以二女为人婢妾,不果。又欲出归乐户为娼,泣不从,以死自誓。雄强之,二女夜潜出,以帛相系其手,俱投水死。事闻,诏有司立祠死所,岁时祭之,赐祠额曰‘双贞’。”[23]可见,失去家庭依托的女性在社会中基本无法实现独立自存。
总之,明代厨婢群体的广泛存在为我们透视明代社会及女性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场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社会初期淳朴、节俭的风气消弭殆尽,奢侈之风日益盛行,从而增加了对用于家庭服务的婢女群体包括厨婢的大量需求。而商品经济的逐步深入又促使这种需求成为现实,它一方面健全了厨婢买卖的市场运行机制,另一方面,改变了社会上的思想观念,物质生活条件的考量代替了传统道德的良贱分野。而这一现象的背后也透露出明代社会女性生存空间的狭窄。商品经济尽管为明代下层民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和谋生机遇,但对女性来说,却被儒家两性体系中的“男外女内”原则所阻碍,她们不得不在家庭内部的有限空间寻求适合的生存方式,明代厨婢的大量出现正是有明一代这种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文化整体变迁的反映。
[1]定宜庄.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史料问题[G]//李小江.历史、史学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31.
[2]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G]//胡适文存.第五册,第4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0.
[3]徐志摩.《醒世姻缘传》序[G]//西周生.醒世姻缘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45.
[4]冯梦龙.古今谈概[M].汰侈部.卷14“厨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131.
[5]焦竑.焦氏类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5:193.
[6]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7]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M].卷1“婢”.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5:28.
[8]马文升.马端肃奏议[M].卷10“申明旧章以厚风化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27册:799.
[9]袁帙.世纬[M].卷下“革奢”.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子部第717册:20.
[10]张瀚.松窗梦语[M].卷 7“风俗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40.
[11]冯时可.雨航杂录[M].卷上,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6.
[12]周顺昌.忠介烬余集[M].卷2“与吴公如书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295册:427.
[13]陈献章.陈献章集[M].卷1“王徐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7:94.
[14]高濂.遵生八笺[M].明万历刻本:135.
[15]方弘静.千一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370.
[16]黄奂.黄玄龙先生小品[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子部第111册:323.
[17]凌梦初.二刻拍案惊奇[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327.
[18]冯梦龙.情史[M].长沙:岳麓书社,2003.
[19]张岱.张岱诗文集[M].卷 2“岱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51.
[20]周晖.金陵琐事[M].卷 3“识宝”.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1955:155.
[21]秦修容.金瓶梅:会评会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8:53.
[22]范濂.云间据目抄[M].卷2.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11.
[23]明世宗实录[M].卷132“嘉靖十年十一月癸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室影印本,1967:3128.
[责任编辑 郑红翠]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Implication on Cook Maidservants Phenomenon——To Center around Marriages to Awaken Common People
WANG Xue-p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vilization along Heilongjiang River Regeion,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80,China)
The daily life of middle-lower classes unfolded in"Marriages to Awaken Common People"as history chapter novel typical represents in the Ming Dynasty.This paper is based on cook maidservants by Marriages to Awaken Common People meantime verified one another with fiction depict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It considers that the tendency of cook maidservants'increase in number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luxury ethos.The luxury ethos pulled a need for cook maidservants used on domestic work and the need had become reality with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It not only had perfected market mechanism on the sale of cook maidservants but also had changed social ideas that material life impact traditional moral.The female living space's narrow had been revealed in the Ming Dynasty.The prosperity of commodity economy provided more advantages for middle-lower classes of Ming Dynasty but the female living space had been restricted with Confucian gender system on men outside and women inside.In consequence,the female only could sought suitable means to survival within the household.The tendency of cook maidservants'increase in number had reflected the whole transition on economy society and thought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cook maidservants;Ming Dynasty;Marriages to Awaken Common People;women's history
K248
A
1009-1971(2011)06-0114-06
2011-09-28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明代婢女群体研究”(09CZS026)
王雪萍(1976-),女,吉林磐石人,副编审,历史学博士,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从事明代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