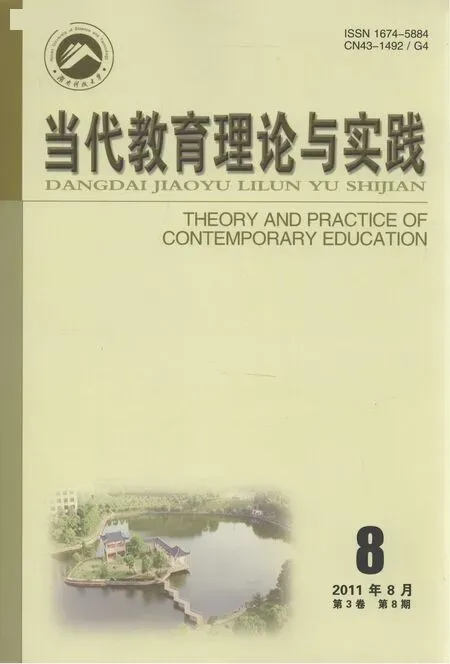新世界主义思潮对翻译的影响
2011-04-03张景华
潘 锦,张景华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新世界主义思潮对翻译的影响
潘 锦,张景华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新世界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而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论文就新世界主义思潮下翻译的新特征展开探讨,反思新世界主义思潮对译者身份带来的冲击,发掘新世界主义思潮给翻译带来的挑战,解释现象的同时补充翻译的内涵。
新世界主义;翻译的复杂性;译者文化身份
翻译是复杂的跨文化交流。翻译过程中文本由一语译入另一语的,远超于简单的符号间转化,更关乎到文化交流中权力、意识形态的冲击,以及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随着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翻译研究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杰勒德·德兰迪(2000)看来:旧式的现代意识形态—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以地缘分化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已经逐步消解和转化为新的二元对立关系,即“本我”与“他者”。人们开始反思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间的关系,认为只有保障个人平等才能保护文化间的差异,学者们也提出从理论和实践上扩大“公民”这一概念,以保障差异不被抹除。学者们开始重新定义世界主义,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现了一些新特征,而译者也有了新的身份。本文就新世界主义视角下翻译的新特征展开研究,思考新世界主义思潮对翻译复杂性和译者文化身份定位带来的冲击和反思。
一 新世界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区别
世界主义的英文是Cosmopolitanism,来源于希腊文的kosmopolitês,意为“跨越国界的对人类的博爱”的世界公民。其最早见于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世界主义思想,认为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公民”,而且首先对“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体”负有责任。如乌尔里希·贝克(2008)所说:“世界主义将差异和他性的价值判断,同建立一种新的、民主的政治统治形式的努力结合起来,而这种新的民主形式又区别于民族国家。”然而旧式的世界主义始终只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式的理想,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多元化的文化逐渐得到人们的承认和重视,学者们开始反思之前一直提倡的世界主义这个概念,发展提出了新世界主义。不同于世界主义,新世界主义更关注个人的需求。博格(2005)归纳了新世界主义核心理念包含3个基础要素:“道德关怀的最终单位是个体”、“平等的价值地位应该得到每个人的承认”、“地位平等和相互认可需要个人权利得到公平对待”。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主义和新世界主义都肯定当今世界所存在的“他者”和“差异”,而新世界主义建立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就更承认文化多元,肯定各个国家的独特价值;其次新世界主义是弃中心主义论的,承认“他者”,但并不将其绝对化,并寻找着一条使其得到普遍容忍的途径,例如建立跨国机构等等;最显著的是,新世界主义抛弃传统的文化决定论,肯定个人的自主选择,并将“他者”视为既平等又相异的伙伴来对待,认为地位平等和相互认可需要个人权利得到公平对待,体现出一种集体的关联,更具有一种个体表达的意义。
二 新世界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复杂性
翻译历来是复杂的东西。通常人们通过民族定位认知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新世界主义思潮抛弃了以往的文化决定论,转而从个体视角来认知世界,并提出新的观点,这也就为人们观察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新世界主义思潮下翻译不是更为简单,而是变得更为复杂。随着文化间的交流加剧,以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冲击,翻译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即:全球化VS.本土化、世界文学VS.本土文学、为超国家机构服务VS.为国家机构服务。
(一)全球化VS.本土化
全球化和本土化是相互矛盾的两个概念。阿里夫·德里克(2004)认为:“在当今资本扩张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通过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同质化来压制本土,并把这种压制冠以总体和普遍的美名。本土则被烙上了一种卑劣的形象,作为落后的孤立群落被排除在进步之外,被视为对抗资本主义城市、工业文明动态的停滞的‘农村’区域,作为一种排他主义的文化对抗普遍科学的理性。”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必然陷入到两难选择之中。以往翻译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为标准,将全球交流看成一个网络,所有的文化交流都通过翻译转变为标准语言进行交流,那么语言文化在交流的时候就不能体现自己本身的特质。新世界主义思潮影响下,译者更注重自身本土的表达,试图自下而上本土化(bottom-up localization)改变文化全球化的格局。译者自下而上本土化(bottom-up localization)翻译本土作品,则更注重基层和未经处理的语言,将各个民族的文化敏感性放在翻译的核心位置,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以取得合理的能够表达“他者”诉求的翻译。
(二)世界文学VS.本土文学
世界文学这一术语的提出最早见于1827年歌德和艾克曼的谈话,歌德呼唤作为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时代的到来。而今天人们将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更多的理解为“跨文化交流”,即指一系列的全球对话和交换。相较世界文学,本土文学更看重本土特色,强调本地域、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学特色。肯定本土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这就促使通过翻译使得本土文学打破本土边界的限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所以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相辅相成,并不互相排斥。新世界主义思潮下,译者更重视各国文化间的“差异”:一方面,一些国家不再单单学习本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学习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在很多国家市场占据了主流,成为本土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克罗宁(2007)所说,翻译使得民族经典文学作品有如超越时空般,将祖先美学经典展现在现代读者面前。民族文学通过翻译的传播作用,正一步一步的向世界文学转化;而世界文学转而影响着各个民族文学的发展,改变着民族文学的面貌。
(三)为超国家机构服务VS.为国家机构服务
新世界主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打破全球与本土、国家与民族的二元对立,试图在国家与民族之上建立“世界之城”。“欧盟”、“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超国家机构的出现标示“世界之城”的初步建立。这些机构的译者们代表各方利益,在利益的博弈中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又要遵守超国家机构定下来的规章制度,势必带来新的翻译规范。以学者贺显斌(2007)对欧盟翻译研究为例,在欧盟,文本的产生需要原作和译作经常互换身份;翻译以游离具体文化的交际为目的;交际不是翻译的唯一目的,捍卫语言平等是翻译的另一项重要功能,等等。由此可见,超国家机构翻译对部分传统翻译观念提出了挑战,打破了传统译论中原作/译作、原语文化/译语文化、等值等等翻译的功能。超国家机构的翻译远比国家机构翻译更为复杂,也给翻译研究带来史无前例的挑战。
三 新世界主义视角下的译者文化身份取向
对于文化身份,克拉什奇(1998)说过:“文化身份是由社会官僚机构如政府认同或成员自我认同所形成的该文化群体的成员身份。”由此可以见,文化身份表现为一个个人,一个集体,一个民族在与他人、他群体、他民族比较之下所认识到的自我形象。译者的文化身份定位往往取决于语言之外,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社会教化信念等都对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新世界主义思潮下译者文化身份取向尤为复杂,本文拟从新时期译者的3种不同的文化定位着笔:新世界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文化掮客。
(一)新世界主义者
新世界主义者指的是信仰新世界主义思想的人,不赞同将人以源于国家的传统地理划分,通常可能是推动世界政府的人士、支持国际主义的或是服务于联合国等非政府组织的个人。以新世界主义者为文化身份定位的译者必定是肯定多元文化的,期待通过翻译帮助人们站在全球的角度、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打破偏见、狭隘的观念,找寻作为人的本性,比如联合国译员。联合国的正式语言只有6种,每每联合国的正式会议,秘书处都要组织译员负责在现场将代表们的发言通过话筒进行同传,并打印成这6种语言的文稿。在联合国工作的译员就是为各国代表团服务的,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对各国代表团都要尊重,并且不得介入有争议的国际问题。例如,联合国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字样绝对不得出现在联合国的文件上;提到“台湾”时,必须加上“地区”。又如,提到“福克兰群岛”时,必须括上“马尔维纳斯群岛”,否则,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就会提出意见。由此可见,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译者,在文化身份选择上并非单一的取决于自身民族或是国家定位,更加需要摆脱个人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束缚,选择互相合作的方式为世界平等交流做出贡献。
(二)民族主义者
民族主义,亦称国族主义、国家主义或国民主义,为包含民族、种族与国家3种认同在内的意识形态,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之“基本单位”,以作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主张异化翻译的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针对译者的民族责任就曾指出:
“翻译不仅构建着独特异域文化的本土再现,它同时也参与了本土身份的塑造过程,翻译史也揭示出一些旨在借助翻译文本促成本土身份的项目,因为翻译能够有助于本土话语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一致的文化身份的塑造。”(许宝强、袁伟,2001:370一77)
在新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文化“他者”的形象不是被忽视了,而是更加得到重视;文化间的差异不是刻意的将其削弱或是丑化,而是以更为正面、客观的形象出现;以往那些文化中被视作怪异、落后的本土文化形象也成为世界文化市场中的一员。译者通过翻译将本国的文化译介到世界文化中。例如,一些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汉语词汇,通过异化译介收入英语词典,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如:儒教(Confucianism)、道教(Taoism)、磕头(kowtow)、丢脸(lose face)、功夫(kungfu)、纸老虎(paper tiger)、阴(yin)、阳(yang)、官倒(guandao)等等。新世界主义思潮下,译者更有义务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特色,宣传本国优秀文化,促进本国文化发展,增进民族骄傲感和自豪感。
(三)文化掮客
掮客(broker),或居间掮客,又称“居间人”、“代办商”、“经办商”等,是为买卖双方说合贸易,评定价格需要花费口舌的人,俗称“牙人”。掮客也被称为“托儿”,一般指为买主与卖主之间签订买卖、契约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人。而文化掮客一说来自雪莉·西蒙的《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文化掮客》,指作为在不同知识传统之间充当媒介并向强力民族(powerful nations)回报的“文化掮客”。(陈永国,2005)歌德也说过:译者是中介者,译者的任务就是要促进精神交流—一种普遍贸易,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交流。那么姑且不论译者的道德职业操守,在世界市场上确实存在着以翻译谋生的并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译者。但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掮客是具有贬义的,类似于间谍、叛徒或口是心非的人。
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军译者,他们大多属于伊拉克人,却为美国人打一场“扫清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战争。“为美军服务的译者们必须戴上黑色的面罩,太阳镜和帽子,以保证他们的身份不被他人认出。他们必须穿上厚厚的护甲和头盔以保护不受到当地武装袭击,他们甚至取个美国式的外号,常年待在美军基地里。”(斯佩塔尔尼克,2004)
这种完全违反自身文化身份的角色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局势的发展,强势文化仍然存在,弱势文化仍然受到强势文化的压迫。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刚刚摆脱殖民地状况的小国或新兴国家,仍然无法摆脱文化殖民的状况,受强势国家的控制。因此,弱势文化想摆脱文化殖民的状况,不得不加强对外交流,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以获得平等的权益。
四 结 语
新世界主义是一次思想解放,颠覆了传统的文化决定论,也为实现平等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新世界主义肯定个人选择以及文化“他者”,试图建立普遍容忍的途径,为实现公平交流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也对翻译提出新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间的矛盾仍然存在,不公平交流现象仍然多见,如何通过翻译消解各个国家、民族间的矛盾,促进合作交流仍然任重而道远。重新定义翻译复杂性和译者文化身份的定位,有助于更好的了解全球文化发展的新态势,促进全球文化的平等交流。实现既肯定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又包容和接受文化“他者”和“差异”的翻译,将是译者和学者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1] Delanty,Gerard.Citizenship in a Global Age[M].Buckib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2]乌尔里希·贝克.什么是世界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2).
[3]Pogge,Thomas.Cosmopolitanism and Global Justice[J].The Journal of Ethics,2005(9).
[4]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M].王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Cronin,Michael.Translation and Identit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
[6]贺显斌.欧盟的翻译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挑战[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4).
[7] Kramsch,Claire.Language and Cul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8]陈宝强,袁 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9]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Spetalnick M.Lost in Translation:Iraqi Interpreters Live in Fear,Reuters International[EB/OL].(2005 - 04 -17).http:www.occupationwatch.org/article.phpid=8513.
[11]尹 星.全球/本土的共融和对话——评《翻译、全球化与本土化——中国的视角》[J].中国外语,2010(1).
[12]陈秀娟.当代西方世界主义研究[J].哲学动态,2010(2).
H059
A
1674-5884(2011)08-0146-03
2011-04-01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09A029)
潘 锦(1983-),女,湖南湘潭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责任编校 王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