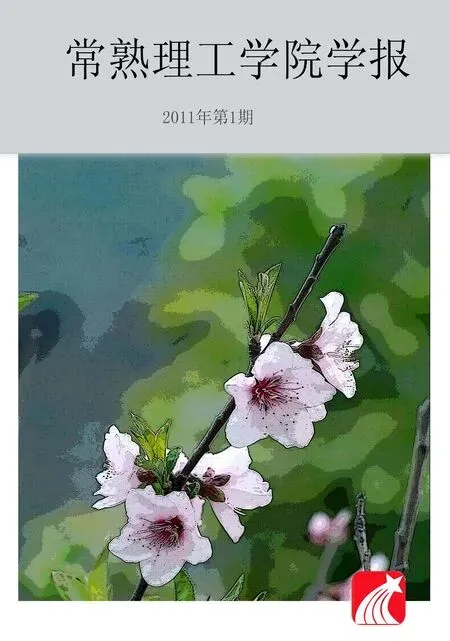《古诗十九首》抒情主人公多重身份现象论析
2011-04-02周海平
周海平
(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作品或被认作思妇念夫,或被视作游子思君(或思乡),各执异词。李善注此诗时说:“浮云之白日,以喻邪佞之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能顾反也。”(《文选注》卷二十九)[1]可见其对抒情主体身份的认定。刘履说:“贤者不得于君,退处遐远,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诗。”(《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三)度其语意,也当指游子。姚鼐说:“此被谗之旨。”(《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二)[2]言思妇之作的如方东树说:“此只是室思之诗。……‘弃捐’二句,提笔换意,绕回作收,作自宽语,见温良贞淑,与前‘衣带’句相应。”[3]明确指明思妇诗的还有清代的张玉穀:“此思妇之诗。”[4]216也有徘徊于两说之间模糊其词者,如方廷珪说:“此为忠人放逐,贤妇被弃,作不忘欲返之词。”(《古诗十九首集释》卷二)近现代,多以为思妇之作。如朱自请先生就认为“诗中的主人是思妇”[5]145。余冠英先生说:“本篇是写女子对于离家远行的爱人的思念。”[6]97马茂元:“这首诗和下面几篇都是思妇词。”[7]27也有比较圆融的说法,如郭预衡先生说:“长期漂泊在外,不胜生离之苦,游子深有感受,却托为思妇之词。”[8]208言其作者为游子,而以思妇身份抒发感受。
其实,此诗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模糊性,即游弋于多解之间,既可作游子思乡或思君说,也可以作思妇念夫解。也就是说既有游子思恋之韵,也有思妇怀夫之致,无论从哪个立场与角度去理解,都无碍通达。前人对此未作深究。其实,出现抒情主人公多解的现象,相当特别,值得细究,故而略作陈述,尤以《行行重行行》诗中的关键性句子的辨析来认识这个现象。
(1)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君,古代用作对人的尊称,多用于人与人之间互称,而于夫妻之间男女都宜。女称男,如《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对焦仲卿说:“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这是最常见的。男称女,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问归期的“君”自然是诗人的妻子。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轼铭其墓曰:君讳弗,眉之青神人。”夫妇间男称女还常常用“卿”表示亲密,如《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对刘兰芝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赴府。”但是女称男则一般不能用“卿”,认为是轻佻。只是在魏晋名士中出现过,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其妻子以卿称王戎,王戎还对她说:“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为尔。”(《世说新语·惑溺》)可见,男子称女子或者尊以呼君,或亲以称卿均可。但是用君称呼对方,则男女互相对称皆可。
至于“行行重行行”可以是游子离别远行的真实陈述,也可以是在家妻子的想象之状。前人都有所解,此不累述。
(2)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这两句以身在南方的胡马依恋北风,越地(南方)的鸟筑巢也要向着南边的树枝作比,其要义在表示不忘本。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以游子思家言,如马茂元先生释:“胡马和越鸟尚且如此,难道游子就不思恋故乡吗?”[7]显然,马先生是以思妇的视点来解读此句的,句中带着留守妇女埋怨的口气,意谓人竟不如马和鸟,微有怨夫薄幸忘家之意。靳极苍先生则释:“马鸟尚有乡土之思,何况有情感的人呢?所以我‘行行重行行’。”[9]322靳先生是站在游子的立场上来解读此句的,表明身在异乡,不得已有家难回。这两种解读都言之有理。
(3)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
“浮云蔽白日”句是造成全诗多义多解的关键,也是中国文化的特殊表现。“浮云”与“白日”(有时以月亮代白日)在古代典籍中出现频率很高,而且常常组成一对意象,表示具有特定关系的两个事物,彼此相依,形成固定的搭配,在诗文中联袂而出。《文子》:“日月欲明,浮云盖之;丛兰欲茂,秋风败之。”(《艺文类聚》卷三)“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史记》卷一百二十八)“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白日掩徂晖,浮云无定端。”(《李太白文集》卷一)关系上,总是云“蔽”日,浮云是负面的,白日是正面的。从形象上解,漂浮在空中的云将明亮的阳光遮蔽了。这种搭配,实际上是阴阳观念的反映。浮云代表阴,白日代表阳,两者构成阴阳两极的事物或人物。当然,阴阳只是规定了两者关系的性质,具体确指为哪对阴性与阳性的物象或人物并不固定,表现出相当的多样性。
其一,君主与奸臣。在古代把君主比作日是常识性的,如《楚辞·怀沙》:“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王逸注曰:“君政温仁,体光明也。”(《楚辞章句》卷四)江淹《为萧让太傅扬州牧表》:“崇绝之宠,降自白日;殊甚之礼,坠于青云。”(江文通集》卷二)君主周围如果有了奸佞之臣自然影响了他的执政英明,好象浮云遮蔽了白日的光辉、光明,所以将君主与奸臣作为一对阴阳对立的意象在古代就很常见。例如《楚辞·初放》:“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王逸注曰:“言谗佞陈列在侧,则使君不聪明也。”(《楚辞章句》卷十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因此明代的叶盛这样阐释:“阴邪之臣上蔽于君,使贤路不通,犹浮云之蔽白日也。”(《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李时勉也这样说:“谗邪蛊惑君心”。(《古廉文集》卷八)刘履说:“第以阴邪之臣,上蔽于君,使贤路不通,犹浮云之蔽白日也。”(《古诗十九首集释》)照这样理解,“白日”指君主,“浮云”指奸臣,游子当为因奸臣进谗而使君受蒙蔽进而被迫离开朝廷的忠臣良吏。
其二,将白日与浮云比作忠良与奸佞。如《罪所留系每夜闻长洲军笛声》:“白日浮云蔽不开,黄沙谁问冶长猜。”(《刘随州集》卷八)此处显见将白日比作忠良,而浮云(奸佞)将他掩蔽,使人莫辨。西汉初的陆贾说:“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非得神灵之化,罢云霁翳,令归山海,然后乃得睹其光明。”(《新语》卷上)浮云之用在于遮蔽光明,而忠良的特点就是心地光明,一旦被奸佞掩蔽,众人不能见其光辉,甚至会被误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朝廷,历史上被放逐甚至被当作奸人杀害者也不少。这样的用法古人中不乏其例。如孔融《临终诗》:“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孔北海集》)以明月代替白日的,如《九辨》:“何泛滥之浮云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愿见兮,然侌噎而莫见。”(《楚辞章句》卷八)王逸注曰:“浮云掩翳兴谗佞也。”“蔽遮忠良,害妒仁贤也。夫浮云行则蔽月之光也,谗佞进则忠良壅也。”杜甫也有这样的用法,其《天河》篇有云:“常时任显晦,秋至辄分明。纵被浮云掩,终能永夜清。”注曰:“贤人虽则为群小所掩,然终不能害其明。”(《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显而易见,将白日与浮云比作忠良与奸佞在古代也是很常见的,李善很自然地为此注曰:“浮云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徒毁忠良,故游子之行不顾返也。(《文选注》卷二十九)吴淇也说:“‘白日’比游子,‘浮云’比‘谗间之人’。”(《古诗十九首集释》)显然,这是游子的内心表白。
其三,把“白日”与“浮云”比作男女,自然其中的女子是反面形象。这种情况下,“白日”往往是男子的正式妻子对丈夫的比喻,“浮云”则用来比喻与在外的丈夫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女子。两个比喻合起来表示在外的丈夫(游子)因为受到另外女子的诱惑蒙蔽,置自己正式妻子和家庭于不顾,沉湎于这种严重违反伦理礼制的不正当男女之乐中,不想归家。清代张玉榖就是这样解读的:“浮云蔽日,喻有所惑。游不顾返,点出负心,略露怨意。”(《古诗赏析》)近现代学者也大多从这个角度来阐释这个比喻的,进而论定此诗为思妇之诗的。如马茂元先生说:“‘白日’是隐喻君王的,这里则指远游未归的丈夫。……‘浮云’,是设想他另有新欢,象征彼此间情感的障碍。”(《古诗十九首初探》)这样的设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应该说是很自然的。正如天鹰先生说:“在封建社会里,男的可以有三妻四妾,所以被遗弃或被冷落是女子不可避免的命运。”[10]因此,古代表现这种情感的诗作是很多的。南朝宝月和尚《行路难》:“(思妇)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唐朝韦应物《拟古诗十二首》其二:“白日淇上没,空闺生远愁。”(《韦苏州集》卷一)可见,以白日与浮云比作自己丈夫与迷惑丈夫的情人,也是古人习用的。这样理解,那么此诗的主人公肯定是留守妇女。
当然,从光明与愚暗的喻意看,还可以把白日与浮云比作觉悟和迷茫。如:“‘子得佛道以来,良有益否?’牟子曰:‘吾自得佛道来,如开浮云见白日,如执火炬如冥室矣。’”(《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三)古人尚有其他用法,此不累述。可见其喻意是相当广的。
从以上分析的三组比喻看,前两种的理解,可说此诗的主人公是游子;根据第三种的理解,此诗又可说是思妇诗。两种理解都与全诗的主旨不悖,也得到了古今学人的认可。
(4)弃置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两句字面意思并不难解,而联系全诗则也有多解。“弃置勿复道”,又作“弃捐勿复道”;俞平伯先生说:“‘弃捐’句,旧有两说:一说君弃捐我,‘勿复道’,是决词;一说相思无益,曷若弃捐勿道;均可通。”[11]若加以主人公的身份几说,那就可以演绎出几种不同解释。(未仕)游子:君主弃我,则不必多说了,算了!臣子被弃,再思念君主也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把这样的事情弃捐勿道。若站在思妇立场来说,丈夫(君)弃捐我,我也不抱任何希望和幻想,任他去。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相思于事无补,还不如不去说它。这样至少就有了四种理解。
“努力加餐饭”亦如此。可以是自励,说还是多吃饭,保重自己身体要紧。曹旭解释说:“与其憔悴自弃,不如努力加餐,保重身体,留得青春容光,以待来日相会。”[12]也可以是劝慰对方,希望对方多加保重。马茂元说:“下句是对对方的希望,希望他好好保重身体,留待异日相会。”(《古诗十九首初探》)这两种解释都以思妇的身份说的。靳极苍说:“祝你好好保养身体吧。(你指君主)”(《诗经楚辞汉乐府选详解》)自然是游子劝慰君主。
从上述可知,《行行重行行》的抒情主人公无论作游子解还是作思妇解都是切合诗意的,并且游子的身份可以是被逐或被谗之臣,也可以是因种种原因久离在外的男子。这种一诗有多种身份的现象并不常见,但在《古诗十九首》却不少见,还有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纬。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余冠英先生说:“这诗有人说是游子久客思妇的诗,有人解为女子闺中望夫的诗,两说都可以通。”(《汉魏六朝诗选》)从其行为与心理看,游子与思妇两者都合适。另外如《西北有高楼》等作品也有类似现象,只是表现方式有些差异。
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应该说这是文人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决定的。《古诗十九首》作为第一批文人五言诗,显然是向汉乐府民歌学习而成的,但是学习中有提高。即以“努力加餐饭”而言,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结尾有“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两者之间的相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民歌中置于思妇读信期间,身份是很确定的,没有疑义的,而《行行重行行》语言更精练,主体身份不明,且可以作多种“可通”的解释,使全诗的解读域限一下子扩大了很多,同样的语言载体,蕴含的信息量就扩大了许多倍!
这样的“含混模糊”正是《古诗十九首》的魅力之一。叶嘉莹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因为这种含混模棱的现象,造成了这首诗对读者多种感受与解说的高度适应性,因此具有更多的西方理论所说的那种‘潜能’,从而能引起更多的联想。”[13]95也就是说,无论游子还是思妇,无论是逐臣还是因恶人所逼而游走他乡的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与自己高度一致的深沉感受,并因此而发出深深的共鸣。再扩大一点,就是深深相知的朋友同学因种种不得已的原因而长期分离,无法共饮畅叙,都会在此得到相同的情感交流,这诗也似乎是为他们而写的。不得志之情与友情、爱情已经几乎涵盖了古代文人的主要情感世界,再加之以留守思妇,所能囊括的人类社群之广可以想见。正如陈祚明在其《采菽堂古诗选》里所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造成这种“人同此情”的审美效果的方式之一就是抒情主人公身份的不确定性,各种各样的人似乎都符合主人公的身份条件,这诗好象是为天下所有人写的,发出了他们内心共有的情感,由此甚至可以说人人都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一点,钱志熙先生有过精湛的论述:“古诗作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具体事件,以普遍性的人情人性,典型性的‘情意结’为表现对象,这自然反映了文人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概括能力。”[14]57也就是说,古诗的作者运用了自己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思考,在艺术上作了高度的概括,摆脱了艺术表现的人物、事件、地点、时间等具体性,使作品具有很高的涵盖性普遍性,因而产生了人同此情的艺术效果。
造成这种艺术技巧高超而又不失自然之美的原因可能也是复杂的,但其中肯定与东汉中后期文人的处境有关。汉末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士人欲助汉建功而不得,仕途被宦官或世族所把持,社会上有一大批长期游学欲仕的“游子”,还有已进入仕途也因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频遭迫害者,实际也是游子。这种社会情境,前人论述极多。范蔚宗《后汉书》尤其叙之甚详:(宦官)“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衔达。同敝相齐,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后汉书·宦者列传》)这是言宦官之害的。其实,外戚之害也与此相仿。袁宏《后汉纪》载,梁冀因李固不顺从他胡作非为,不仅杀害了李固,而且杀害了他的两个儿子,惟有幼子因仆人王成早先改换名姓,带往徐州才得幸免于难。由此可见士人的处境。这样的事例极多,我们仅举蔡邕以明之。蔡邕品行与才学都堪称一流。“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汉灵帝因阉党充斥朝廷而听不到忠正之言,密询蔡邕,邕密奏直言却被阉党曹节窃视而得,并宣示泄露。随即遭到构陷,于是下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弃市。”经人救助,免死,流放朔方。一路上遭追杀毒害不断,整整九个月。逢大赦而还。又因怠慢中常侍兄弟王智,被密告“怨于囚放,谤讪朝廷。”“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以上均见《后汉书·蔡邕传》)正直忠良之士,或者被杀甚至灭族,更多的被长年流放边鄙,或者逃逸他乡,远离乡梓,或者隐居深山僻壤,或者改名换姓,寄居蛮荒。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有如被放逐之士,与家人则长期分离,与亲朋好友悬隔永绝,欲回家则有家难回。因此,他们的处境就集中了许多类游子的多重身份。尤其是他们的心态具有多重性。因为汉代开始,中国文人的地位就处在阴阳交会点上:在家庭关系中则是其妻之阳,在社会关系中或者是阴(君主为阳)或者为阳(奸佞和小人为其阴)。表现在诗歌中,对汉室,对君王,可谓“阴”与“阳”的关系;对奸佞小人,又是“阳”与“阴”的关系;对妻子儿女,也是“阳”与“阴”的关系。当然,士子的这种处境在后代仍然还有存在,但是人数之多,比较集中地成为一个群体性的现象,应该说在汉末。所以,《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主人公的身份属于阴性无疑,但可以是思妇之阴,也可以是臣子(游子)之阴。
综上所述,《行行重行行》等古诗中的抒情主人公身份不明的现象,是其特定时期作者的身份、心境特别等原因所决定,也是作者的审美追求自觉提高的必然结果,并且收到到了令历代读者产生“人同此情”的艺术效果,也可以说造就了“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1]李善.文选注:卷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4]张玉穀.古诗赏析: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M]//古诗歌笺释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6]余冠英.汉魏六朝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8]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靳极苍.诗经楚辞汉乐府选详解[M].西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10]天鹰.中国古代歌谣散论[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1]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13]叶嘉莹.汉魏六朝诗讲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14]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