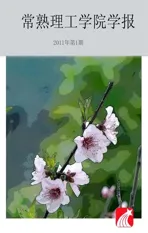论20世纪中叶的苏州弹词女声流派
2011-04-02潘讯
潘 讯
(苏州市委研究室,江苏 苏州 215004)
一、引 言
苏州弹词唱腔流派的生成出现在评弹艺术走向成熟、并逐步形成自身独特美学风格的历史阶段。从清代乾嘉间弹词艺人陈遇乾首创陈调算起,200多年来苏州弹词产生过20多种流派唱腔。各种流派既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又有亲密的血脉联系。概言之,自清代中后期苏州弹词形成了三大流派体系,即陈调体系、俞调体系和马调体系。后世众多流派都是从这三大体系中嬗变衍化而出,如俞调系统衍生出周调、蒋调、徐调、祁调等流派,马调系统孳乳了魏调、沈调、张调、严调等唱腔。
但是,直到1940年代评弹流派仍以男声唱腔一统天下,书中旦角演唱则多以男声俞调表现。至20世纪中叶,特别是1950、60年代以来,弹词女声唱腔获得很大发展,并络绎出现了徐丽仙(1928—1984)的丽调、侯莉君(1925—2004)的侯调、朱雪琴(1923—1994)的琴调、王月香(1933—)的香香调(通称王月香调)等四大女声流派。其中丽调、琴调为听众认可较早,侯调次之,王月香调最为晚出,约形成于1960年代初,也是苏州弹词唱腔体系中最后诞生的一个流派。
二、女声流派诞生的背景及原因
苏州弹词四大女声流派在20世纪中叶密集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它既是评弹艺术自身流变丰富的产物,又具有深层次的历史文化背景。
首先,20世纪中叶评弹艺术的繁兴为女声流派的诞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苏州评弹在19、20世纪之交进入大都市上海,并逐步在江浙沪一带走向鼎盛。1920、30年代评弹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期,今天评弹界最有影响的一些流派如蒋调、周调、薛调、沈调、徐调等接踵诞生,《玉蜻蜓》、《珍珠塔》、《三笑》、《白蛇传》等传承已久的经典书目培养出许多名家响档。到了1950、60年代长期的战争动乱局面已经结束,经济建设全面开展,社会生活渐趋稳定,评弹又迎来了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期。这一时期,各类书场遍布江南城乡,据有关资料统计,上海市1963年有书场262家,座位近6万个;1965年苏州城区有书场23家,全市范围内有书场近百家;同期,无锡城区有书场近30家。[1]217评弹从业队伍也有大幅度增加,据记载,1960年代初,江浙沪地区参加团体的评弹演员有800多人,未参加团体的艺人尚不在此列;即便如此,评弹演员的业务仍十分繁忙,有不少演员一年演出达600场。[1]218在苏州城区,广播空中书场开始普及,评弹通过电波传入千家万户。新编书目不断涌现,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新编传统题材书目(二类书)有近百部,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孟丽君》、《梁祝》等十余部;新编现代题材书目(三类书)70余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红色的种子》、《青春之歌》等;此外,评弹界还编了为数众多的中篇书目,如《罗汉钱》、《芦苇青青》、《三斩杨虎》、《厅堂夺子》等,大大充实了评弹文库,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2]177评弹的繁荣、听众的期待激励着艺术家的探索与创新,20世纪中叶弹词女声流派的诞生适逢其时。
其次,评弹演出形式的变化为女声流派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契机。数百年来,苏州评弹的演出形式都是以男单档为主,清末民初上海虽然零星出现了女性弹词的身影,但不久就蜕化为“妓女弹词”。至上世纪30、40年代,社会风气逐步开化,评弹女艺人渐多,在苏州出现了男女双档的行会组织——普余社,但女性弹词仍被视为非主流的“外道”,整个20世纪上半叶比较知名的评弹女艺人屈指可数。以男性为中心的演出形式束缚了评弹演唱艺术的发展,男声的性别错位更制约了流派唱腔的丰富与拓展。1949年之后这种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男女双档渐成评弹演出主流。特别是随着演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评弹艺人纷纷加入集体组织,评弹演员在团体范围内进行重新拼档,出现了许多珠联璧合、至今还为人所称道的艺术组合。如朱雪琴与郭彬卿、王月香与徐碧英、侯莉君与钟月樵、徐丽仙与周云瑞等,他们改变了传统弹词演出中上下手关系,在艺术上互相切磋、相得益彰,这种组合为女声流派唱腔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像郭彬卿的琵琶弹奏铿锵遒劲,又吸收民乐技法,为传统弹词琵琶增加了和弦、长抡及绞弦等手法,发展了枝声复调的伴奏音乐,堪称一绝,对于朱雪琴琴调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与烘托作用。周云瑞在音乐伴奏创新方面就给予徐丽仙很大帮助,对于丽调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1950年代开始与王月香合作的徐碧英,在三弦弹奏上着意创新,对于王月香调的衬托、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钟月樵是擅唱俞调的著名老艺人,他对于俞调的演唱技巧有着独特的体会,而侯莉君所创侯调显然吸取了俞调的滋养。
再次,新书的大量编演成为培育女声流派的主要载体。从评弹艺术史来看,书目与流派之间有相对稳固的对应关系,新的流派唱腔只有在创编新书的过程中才有发展起来的可能。有“评弹皇帝”之称的严雪亭早年拜师徐云志学《三笑》,《三笑》是徐调的看家书,作为一位有抱负的艺术家,严雪亭自然有开创流派的雄心,但是,说唱《三笑》显然无法逾越乃师。严雪亭便转而学习新编书目《杨乃武》,严调便以《杨乃武》为载体发展起来。在20世纪中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进入评弹界,为配合社会改造等宣传需要,开始大量创编新书。评弹艺人也积极投入到排演、谱唱中,如侯莉君先后参演了《孟丽君》、《梁祝》、《江姐》等新编书目,王月香先后参演过长篇《孟丽君》、《红色的种子》、中篇《梁祝》、《三斩杨虎》等新书,徐丽仙演出了新编长篇《杜十娘》、《王魁负桂英》、新编中篇《罗汉钱》、《情探》、《刘胡兰》等,朱雪琴参演了新编长篇《琵琶记》以及中篇《芦苇青青》、《厅堂夺子》、《冲山之围》、《红梅赞》、《白毛女》等。新书目着意塑造了一系列崭新的女性形象,既有孟丽君、祝英台、赵五娘、敫桂英、花木兰等古代妇女,又有钟老太、刘胡兰、江姐、林道静等现代女性,这些形象不仅在传统评弹中前所未有,而且人物内在的反封建、反礼教、反抗斗争等精神内涵更为传统评弹表现艺术所难以容纳。如果还是以男声俞调来演唱这些女性人物,显然已经格格不入,富有时代精神的弹词女声流派呼之欲出。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评弹书坛上相继出现了清丽阳刚的丽调、激昂高亢的王月香调、跳跃飒爽的琴调等女声流派,这些新颖流派与敫桂英、祝英台、钟老太等崭新女性形象紧密融合在一起。
最后,艺术家的杰出才华和刻意求工的努力。梳理徐丽仙、朱雪琴、侯莉君、王月香四位女艺术家的艺术人生轨迹,发现颇多相似之处。其一,她们都出生在1920、30年代,很小登台演出,在码头上磨砥历练,备尝艰辛。朱雪琴初次登台只有9岁,艺名“九岁红”;王月香幼年从父学艺,8岁起就与姐姐王再香、王兰香拼档说书;而徐丽仙与侯莉君都是无锡“钱家班”出身,从小学艺,徐丽仙11岁就在茶馆、酒楼演唱。幼年“滚码头”刻骨铭心的经历陶铸了她们在艺术探求上坚忍不拔的毅力。其二,她们都是从说唱长篇书目起步,有深厚的艺术功底。王月香的出窠书是家传的“王派”《双珠凤》,在评弹界独树一帜;徐丽仙自小登台演出的也是传统、新编长篇弹词《倭袍》、《啼笑因缘》等;朱雪琴学习过很多长篇经典书目,如《玉蜻蜓》、《珍珠塔》、《双金锭》、《白蛇传》,并与名家拼档演出;侯莉君早年与徐琴芳拼档演出传统长篇弹词《落金扇》。长篇书目培养、锻炼了她们说、噱、弹、唱的基本功,为她们日后的流派创造奠定了深厚的基石。其三,她们在艺术成长中都擅于博采众长。徐丽仙从小喜爱京戏,她在评弹表演中的一些手面动作就借鉴了京剧的程式;侯莉君创造的侯调吸收了京剧花旦演唱的俏丽流畅的音乐、表演元素;王月香则是越剧的爱好者,她以哭行腔、以情胜腔的演唱,颇具戚雅仙、傅全香的神韵。20世纪30、40年代兴起的流行歌曲、电影插曲对于这些追逐潮流的女艺人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与前辈艺人相比,20世纪中叶的弹词女艺术家具备了更加宽阔的艺术视野,他们的流派创造不再闭锁在弹词音乐自身局促的框范内,而是向周围广泛采撷,将那些可资借鉴的艺术资源化合在她们正在唱腔流派创造中。
三、女声流派的美学特征与艺术风格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代的审美标准和艺术风气始终处于流动中,评弹的流派唱腔也是如此。马调展示了清代后期的评弹美学标准,魏调展示了民国初年的评弹美学标准,蒋调则展示了上世纪30、40年代的评弹美学标准,评弹流派唱腔正是在与时代美学的吐纳、因应中实现了自身的嬗变。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弹词女声流派具有哪些共通的美学特征?哪些相近的艺术风格?
第一,追求阳刚健进之美的“花木兰情结”。1949年后,新文艺工作者进入评弹界,他们的任务是改造评弹,让这种旧的市民文艺脱胎换骨,为工农兵服务。在当时的时代气氛下,柔媚、哀婉的演唱风格已为评弹艺人所不取,评弹女艺人更力戒自己的演唱流于“靡靡之音”,而使演唱风格转向悲愤、激越、刚健、明丽。周恩来向来与文艺界有着亲密的关系,1958年,他在听了徐丽仙谱唱的《新木兰辞》后,指出对于花木兰战斗生活描写不够,作者夏史随即加上了“鼙鼓隆隆山岳震,朔风猎猎旌旗张。风驰电扫制强虏,跃马横枪战大荒”等唱词,以突出花木兰英勇豪迈的巾帼英雄形象。弹词开篇《新木兰辞》也因此成为徐丽仙前后演唱风格的转折点。[3]243此后,《罗汉钱》、《阳告》、《情探》中那种凄楚哀婉的情调不见了,丽调开始向豪放、刚健发展。鉴于谱唱《新木兰辞》在20世纪中叶评弹界的经典意义,我将这种艺术取向称之为“花木兰情结”。“花木兰情结”对于同时期弹词女声流派美学特征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无论是琴调还是王月香调都是明朗、跳跃的,都呈现出一种阳刚健进之美。在20世纪中叶四大女声流派中,唯一显露出婉转流丽之美的是侯调,侯调的成熟不在苏州、上海等评弹中心城市,而是在评弹艺术边缘化、较少政治干预的南京(江苏省曲艺团)。但是,在“花木兰情结”的笼罩下,“侯调”问世不久就遭受非议,侯莉君也自认为侯调缺乏“鲜明的时代感”。[4]459
第二,在演唱中深入心灵体验。我曾经提出,20世纪中叶以来评弹艺术发展受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影响。[5]43当然,这是一条间接的路径,斯坦尼体系首先影响了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戏剧、电影,再由戏剧、电影波及评弹。换言之,评弹是在戏剧化的过程中接近了斯坦尼体系。斯坦尼体系的精要之点在于重视演员的情感体验,其理论印痕在20世纪中叶的评弹女艺术家身上最为显豁。王月香曾在谈艺录中自述:“大道理讲讲便当,一句话:‘要说好书就要跳进角色里’去,究竟用什么办法跳,做起来会有困难的。我的笨办法就是把角色所到的地方、碰到的人、做的事……根据她全部的性格完完整整想一遍,跟了这个角色走、看、听、想、做……这样就能较快较好地变进去,跳进了。——我有时还会忘记自己的,《英台哭灵》抱牢山伯遗体推和搡,哭得呼天抢地……等这档篇子唱完,我却跳不出来,还是眼泪簌落落,吭叠,吭叠叠地吭个不停——这是大毛病,要能把眼泪含在眼膛里不掉下来,才是真本事。”[4]575-576徐丽仙亦有近似说法:“我认为唱好一则开篇和说书起角色一样重要,只有自己跳进开篇的角色中去,才能自然而然地使唱腔和伴奏融为一体,把词中人喜怒哀乐的不同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即使唱完最后一句,余音回绕,这时要使听众仍身临其境,全神贯注,流连忘返。……只有自己首先做到尚未跳出角色时,才能达到具有这种感染力的艺术效果。”[4]508“忘记自己”不正是斯坦尼体系黾勉求之的最高表演境界吗?王月香深知这种“忘记自己”的深入体验并不符合传统评弹艺术的科律,故而她一方面津津乐道自己的表演经验,另一方面又说“这是大毛病,要能把眼泪含在眼膛里不掉下来,才是真本事”。但是,王月香内心仍然尊重自己的情感体验和表演尺度,直到晚年执教苏州评弹学校,每次为学生示范王月香调代表作《英台哭灵》时,她仍禁不住潸然泪落;她并没有克制自己的感情——“把眼泪含在眼膛里不掉下来”。王月香、徐丽仙等一辈艺术家的努力,使她们所创造的流派更重视情感的投入,更重视抒情,她们的演唱呈现出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的鲜明特点。
第三,重视音乐形象的塑造。“音乐形象”一词是20世纪中叶评弹理论界在接触到西方音乐美学之后,频频引用的一个概念;是对于传统弹词说书体、叙事体演唱功能的一种救正。重视音乐形象的塑造就要求弹词演员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以人物为中心增强演唱的抒情性,充实音乐的情感内涵。男性评弹艺人因为嗓音条件的先天制约,在塑造女性人物时,只能采取“遗形取神”的方式,他无法逼真模拟女性的声色(形),只有从高一层的“神”(情感、性格、思想)去把握和表现人物,这无疑富有难度。以祁调选曲《霍金定私吊》为例,祁莲芳演绎出一种被人们称为“迷魂调”的细若游丝、恍惚迷离的唱腔,并试图以这种音乐情调来接近女主人公霍金定在未婚夫灵前悲痛逾恒的内心世界,但是,男性演唱的角色哀诉毕竟很难在听众内心呈现出一个清晰的人物形象,从直觉上仍不免有隔膜之感。而到了1950、60年代的女性评弹艺术家手中,这种努力就较容易达致成功。比如,侯莉君与王月香都曾演唱过《梁祝》选曲《英台哭灵》,虽然她们有着不同的演唱风格,但是在音乐形象塑造上却殊途同归。王月香的演绎体现出她的以哭行腔特点,她以一种壁立千仞、排山倒海的快节奏叠句来表达祝英台悲愤的心情,重在突显祝英台的反抗精神。而侯莉君的演唱则发挥了侯调婉转多姿的特点,听侯调《英台哭灵》仿佛是在听剧中人缠绵戚凄、娓娓不尽的哀诉,时而哽咽,时而沉抑,塑造出一个深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古代妇女形象,这种角色定位在侯莉君的演绎下同样是完整、丰满的。
第四,对“一曲百唱”的突破和发展。20世纪中叶出现的弹词女声流派具有鲜明的创新精神,对于评弹谱曲中某些承袭已久的观念也有所突破。比如,传统评弹中“弹唱”从属于“说表”,是说表的延伸和丰富,正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评弹以说表为主,因此,评弹中的“唱”是一种说书体或叙事体的“唱”(音乐也是如此),而不同于一般以抒情言志为主的歌唱。弹词流派唱腔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所谓“一曲百唱”,以同一种唱腔曲调施之于各种唱词,只是在演唱的轻重徐疾上略作变化。而且,在一部书中基本上只运用一种流派,翻调头则被称为“什锦调”而遭同行的诟病嘲讽。对于这些清规戒律,20世纪中叶以来的弹词艺术家们都有所突破,创造出了不同的弹词音乐板式,其中以徐丽仙的成就最大。徐丽仙的努力使得评弹唱段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于书情和说表的附庸,而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尤其是徐丽仙晚年所谱唱的丽调开篇《黛玉葬花》、《年青妈妈的烦恼》、《八十抒怀》、《望金门》、《青年朋友休烦恼》等,都是从唱词的具体内容情境出发,创造出新的音乐结构、伴奏技巧和演唱方式,使丽调唱腔显示出千姿百态的艺术魅力;她还在伴奏中大胆引入二胡、阮、筝、铙等乐器,使得伴奏音乐更加饱满、深沉,增加了弹词音乐的抒情性,拓展了评弹弹唱艺术的意境空间。
四、结 语
20世纪中叶苏州弹词女声流派的勃然兴盛是评弹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将苏州评弹的演唱、表演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对女声流派源流及发生背景的探寻中,我们还应注意听众审美心理变迁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据记载,20世纪初叶,在京剧观众的欣赏习惯中老生流派独占鳌头,而到了1930年代以后青衣、花旦演唱逐渐盖过老生的风头,成为观众的新宠,并捧红了影响至今的梅尚程荀四大旦行流派。[6]623以此参照苏州弹词唱腔艺术的发展,似乎可以寻觅出一些富有规律的线索,20世纪中叶至今,弹词女声唱腔发展大有超越男声流派之势,也不为偶然。
苏州弹词女声流派所呈现的艺术风格体现了与时代美学之间相互渗透、彼此制约的深刻联系,其中政治因素亦不可小视,如女声唱腔悲愤、激越的风格适合于表现对旧社会的控诉,而刚健、明丽的情调则多被用来歌颂新人新事。总览四大女声流派所呈现出的美学风貌,可谓得失参半,阳刚有余,阴柔不足,多少限制了艺术的表现力。这有待于后辈艺术家的再度经营,1980年代以来,弹词艺术家邢晏芝在俞调的基础上,兼收祁调、侯调、王月香调之长,创造出一种被业界称为“晏芝调”女声唱腔,“晏芝调”深情婉约,细腻缠绵。依托这一最具女声独有魅力的新型流派,邢晏芝在长篇弹词《杨乃武》中塑造的小白菜形象一改传统定型模式,别具人性的魅力,为21世纪的评弹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标准。
[1]周良.苏州评弹史稿[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2.
[2]周良.苏州评话弹词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
[3]左弦.评弹散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4]周良.艺海聚珍[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3.
[5]潘讯.评弹美学的新超越[J].曲艺,2003(9).
[6]吴小如.吴小如戏曲文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