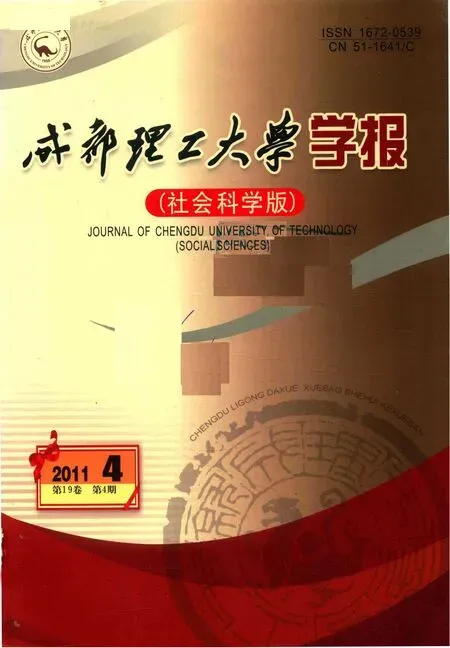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升级的理论述评——基于供给的视角
2011-03-31马子红胡洪斌崔静敏
马子红,胡洪斌,崔静敏
(1.云南大学 a.经济学院;b.文化产业研究院,昆明 650091)
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升级的理论述评
——基于供给的视角
马子红1a,胡洪斌1b,崔静敏1a
(1.云南大学 a.经济学院;b.文化产业研究院,昆明 650091)
关于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品供给和要素供给两个方面,主要涉及产品更新、产品创新、劳动力流动、资本汇聚、技术外溢和政策创新等推动的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分析。虽然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相关理论研究,都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国外理论和国内实证缺少耦合,对如何将产业转移理论与国内区域产业升级的实践相结合研究不够;现有研究更多地注重了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升级的经济因素,而对制度创新、行为决策、社会网络、社会文化、决策主体偏好等非经济因素的理论分析明显不足;研究对象上侧重于考察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研究相对较少。
产业转移;产业升级;供给;理论述评
产业转移(Industrial Transfer)是指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的变化,导致产业空间布局在不同区域(国家或地区)间进行调整的经济现象。它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区域(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转移已成为具有后发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手段。借助于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或地区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新型化,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加快实现产业发展的非资源化和高附加值化。针对这一情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本文主要从供给的视角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理论综述,旨在抛砖引玉,为我国加快推进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一、基于产品供给的视角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实际上是企业产品供给变动所推动的。产品供给能力往往受制于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供给量,许多企业为了维持产品供给能力,就必须从空间上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客观上促进调整区域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外研究者们从产品供给的角度,深入剖析了产品的转移路径、内在价值及产品创新所引起的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引起的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
(一)产品更新的外推效应
一般而言,创新型产品往往是供不应求,相应的产业实现快速发展;成熟型产品往往是供求基本平衡,相应的产业保持稳步发展;衰退型产品往往是供大于求,相应的产业逐渐衰退甚至消失。在此过程中,单个企业进行产品更新,势必会促使其他企业模仿跟进,导致整个产业链上的产品生产都受到影响。一些企业为了维持其产品供给,被迫调整生产布局,将原有产品的生产工艺或生产环节进行跨区域转移,最终带动了移入区域的产品、产业的结构调整,这就是产品更新所产生的外推效应。对于这一机理的探讨,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赤松要(Akamatsu,1935)提出的“雁行模式”是较早形成的产业转移理论,他通过对日本二战前工业发展的统计研究,总结出产业发展遵循的三个模式:第一个基本模式认为某一产业的发展是按照从接受转移到国内生产,再到向外出口的三个阶段,即按照“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模式相继更替发展;第二个模式是从一般消费品到资本品,或者是从低附加值产品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第一模式演进,产业结构不断高度化;第三个模式是某一产品的第一模式动态演化会在国与国之间传导,工业化的后来者会效仿工业化的先行者。雁行模式从产品的转移路径和内在价值方面,研究了产品的转移促进了产业升级的问题,是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产业发展路径的总结,反映了日本的许多产业包括纤维产业、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等的发展路径。小泽辉智(Ozawa,1993)通过经验研究证明日本许多产业的发展是符合该模式的。他在雁行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增长阶段模型,认为跨国公司应当在产品一上市就到国外投资生产,无需通过出口开发东道国市场,这将能帮助东道国建立有竞争力的消费品工业[1]。弗农(R.Vernon,1966)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产品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产业转移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他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产品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阶段的产品在不同国家受到的重视程度将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不同国家间的产业转移现象,这客观上推动了产业移出国和产业移入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可以说,该理论是对早期产业和产品转移理论的系统描述和总结。利柯鲁(Lecraw,1993)运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变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产业转移的行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发生在产品周期的成熟期与学习曲线的上升期的交点,并且是倾向于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跨国生产。利柯鲁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部门的下游方向的投资具有一定的解释力。Tan Z.A(2002)在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从产品系列的角度来解释产业转移现象[2]。他将产品分为高、中、低三个档次,将对应的市场结构分为直接出口(DS)、中间产品出口和当地组装(IL)、当地生产(LP)三种。高档产品对应的市场结构以DS为主,IL为辅;中档产品则以IL和LP为主,辅之以DS;低档产品则以LP为主。市场结构相对保持不变,而高、中、低档产品系列将不断变化,新的产品不断充实到高档产品系列中,一部分高、中档产品降级并充实到中、低档产品系列中去。这表明在产业转移中,外国直接投资者通常将高档产品的生产主要放在本国进行,辅之以中间产品出口和国外组装;就中档产品而言,产品在国外组装的同时,产业逐步向国外转移;低档产品的生产则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这样可以提升本国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Rober E.Lipsey(2002)考察了美国跨国公司在母国和投资对象国的产品结构,他发现,母国企业通过转移国内部分传统产业到投资对象国,促使部分生产要素转移到新兴产业,推动本国产品的不断创新。因此,母国企业会趋向于在国内生产资金密集型或高端技术型的产品,投资对象国生产低端技术型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这样不仅能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而且能通过技术外溢加速原有比较优势的转变,以达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目标。
(二)产品创新的关联效应
产业转移往往表现为由产品创新引致的产业布局的空间调整,产品创新能力越强,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就越大。然而,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必须依托于“聚集成群”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通过知识技能的扩散而产生关联效应,从而推动产业集群内的产品创新活动,而随着产品创新的不断深入,产业的更替势必成为必然,这将推动部分产业在空间布局上进行调整。Hagerstrand(1970)通过对产业集群创新优势的研究,提出了“产业集群扩散”模型。他认为,由于产业集群中行为主体间的学习是平稳的“扩展扩散”(1),植根于集群内部的知识技能扩散将确保产业集群具有可持续的创新优势,在此过程中产业集群的跨地区转移主要是由内部关联企业的产品创新所推动的。因此,产品创新的关联效应将影响一个区域的产业集群化程度,进而影响该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能否顺利实现。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考察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状况,探究了产业发展过程中,产品创新的关联效应如何影响产业的区位选择[3]。他们认为,产品创新的关联效应主要表现为外部效应(不同企业在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环节的关联度提升)和内部效应(不同企业在产品生产、内部管理、技术研发等环节的关联度提升),它们使得相关企业的联系成本日益递减,并成为了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进而推动了不同地区的产业升级和变迁。叶建亮(2001)认为,知识外溢是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集群的产品创新实质是不同企业的知识外溢过程,它决定了产业集群的规模,当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知识溢出机制将引致产业转移,进而推动产业集群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魏守华(2002)认为,产品技术创新和扩散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形成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随着产品技术创新和扩散的顺利实现,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逐步丧失,为了确保产业发展的持续性,产业集群将实现跨区域的产业转移。Jian Cheng Guan,Chiu Kam Mok ,Richard C.M.Yam(2005)探究了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以技术转移推动的一国(或地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仅推动了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而且加速了产业发展的高端化和新型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彭新敏(2007)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机制,从创新类型维度构建了产业价值链升级的体系。他认为,我国制造业已具备了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市场基础,应该利用国外的产品创新带来的外溢知识和外溢技术,推进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基于要素供给的视角
从要素供给的角度来看,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由要素供给的稀缺性和竞争性差异所推动的。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供给(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政策)条件的变化,将会影响到空间上的产业转移过程,进而影响到不同地区的产业升级过程。
(一)劳动力流动的“倒逼”效应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促使某国(或地区)的劳动力将实现跨国(或地区)的流动,一旦劳动力供给有所减少,产业转移现象必然发生,而产业转移又将推动劳动力输出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这可称为劳动力流动的“倒逼效应”。爱德华·F·丹尼森(1976)在《日本经济怎么增长得这样快》一书中,采用经济统计方法,用知识进步、规模经济、资源配置解释了总要素生产率,并对规模经济和资源配置部分进行了计量分析。他认为,劳动力从农业和手工业向大工业转移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阿瑟·刘易斯(1989)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来研究国际产业转移现象。他在研究中最早触及产业转移机制问题,提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他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产业转移的主体,并且把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的变化相联系。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于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陈计旺(1999)分析了要素流动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他认为,劳动力流动趋向于扩大区域发展差距,并导致产业转移现象的发生,进而推动转出产业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4]。石奇(2004)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总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主要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实现了产业的跨国界转移,形成了产业集聚[5]。刘艳(2005)认为,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区域集中,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使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压力加大,促进产业自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6]。王业强、魏后凯(2007)利用1995~2003年中国28个两位数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了基于产业分工的空间竞争模型,计量结果表明:传统的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产业规模对产业转移的效果并不显著。戴宏伟、王云平(2008)指出在新形势下,由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促使我国区域经济关系正由重复竞争、投资效益低下向加强协作、协调共赢转变,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产业转移有着迫切的需求,产业转移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7]。
(二)资本汇聚的驱动效应
资本在产业转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济的高速成长使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不断增加,生产要素的累积状况使要素的使用成本与报酬率发生变化,一般表现为资本供给的充足和工资的上升,在产业发展中则表现为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资本密集型产业将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发展,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平均成本上升,利润降低。这样,发达国家和地区就势必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试图通过利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廉,吸引外资,不断增加积累,改变这一生产要素的相对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化。资本的汇聚,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丰裕的资金支持,有利于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一批传统产业,有利于发展壮大一批新兴产业,最终实现产业的聚集化发展。H.钱纳里(1966)和A.斯特劳特(1966)创立了“两缺口”模型,他们认为,当发展中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所需资源的数量与国内最大供给之间存在缺口时,引进外资是弥补缺口的必要条件。引进外资会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与“储蓄缺口”,从而可以提高国内经济水平,并可以引进发展中国家无法生产的资本品,进而促使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消费结构的高级化和多样化,最终带动产业结构的变化[8]。Blom strom,M.Konan D.&R.Lipsey(2000)建立了反映FD I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发展的计量模型,结果显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助于日本企业维持在海外的市场份额,而且有助于日本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9]。Rossel V.Advincula(2000)对韩国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将低端的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从而提高了国内生产活动的技术密集程度[10]。M ajan Svetlii,M atija Rojec &Andreja Trtnik(2000)对斯洛文尼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尤其是在发展的早期,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企业特定优势积累的结果,而且是从后发劣势出发向国外学习和借鉴,进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11]。Branstetter(2001)对美、日的双向投资检证实了 FD I引起资本的汇聚,存在着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而影响产业的结构。Salva Barrios,Holger Gorg & Eric Srob(2005)通过对爱尔兰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跨国公司对于中间投入物的需求,很大一部分会从投资对象国的国内市场上获得,从而导致投资对象国的本土企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12]。
对于资本汇聚引起的产业转移现象,我国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何洁、许罗丹(1999)和耿强(2000)的研究发现,FD I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资本得以迅速汇聚,客观上推动了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进程,不仅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新技术,而且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不竭动力,促进了产业升级。张婧(2001)指出,借助于FD I的发展,我国的发达地区建立了大量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区,通过吸引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汇聚,进而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潘文卿(2003)采用面板数据,对1995~2000年投资对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进行了研究,指出了资本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积极正效应。祖强、孙军(2005)在此基础上,利用能将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包括在内的生产函数来定量分析FD I,验证跨国公司在资本集聚情况下,提高专业技术和产业配套,来促进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13]。
(三)技术外溢的扩散效应
技术创新加快了旧产业成熟的速度,并不断涌现出新型产业,使产业的产品结构不断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深化,这使得产业转移过程加快。产业转移从动态的角度反映了由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所带来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技术创新促使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地发展朝阳产业、绿色产业、高精尖产业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也不断地加快将旧产业、夕阳产业、污染产业、传统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产业转移推动了产业转移对象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并借助于“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使得不同企业在技术上相互借鉴和利用,进而推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外学者针对这一现象,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角度来进行了研究。
小岛清(Kojima,1978)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该产业先由发达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在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小岛清从日本的实际出发,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工业的投资要按照比较成本及其变动依次进行,并从差距较小且容易转移的技术开始,通过产业转移推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的深入研究,提出了“技术本土化优势”理论,从技术优势的变迁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产业转移。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成熟技术或生产工艺的应用和改进,可以使本国的跨国企业所创新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效益,以满足中低档次的消费需求,这一特定的优势将推动产业转移。坎特韦尔和托兰西诺(Cantwell,Tolentino,1990)从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的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对外产业转移的阶段性动态演进过程,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与它们对外投资的累积量高度相关,对外投资的累积量越大,技术进步就越快速,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向外转移才更可能发生。赫希曼(1991)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地区的发展必须有一定的次序,不同的地区按不同的发展速度不平衡发展,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和大城市,并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以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效益,自身增长迅速的“发展极”[14]。发展极地区的优先发展,最终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外溢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存在这种地区的不同,中心地区的产业转移到周边的地区,促使中心地区的市场不断扩大;中心地区的技术转移到周边地区,促使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Walz(1996)将赫希曼的理论延伸到了微观层面,通过对美国企业区位选择形成产业集聚现象的深入研究,他提出:技术外溢是产业集聚的主要推动力,正是技术外溢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形成了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极核”。Best(2001)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产业转移会产生知识的外溢效应,为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企业将十分重视专业技术知识的更新,这就会推动着不同企业的集聚化发展,最终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15]。H·Gorg and E·Strobl(2001)认为,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外溢促使东道国企业实现技术更新,优化了东道国技术结构的同时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着东道国产业的转型升级[15]。Lemoine and Uenal-Kesenci(2004)认为,中国出口导向型的高竞争力行业大多是依托于外国的技术和设备而发展的。Jian Cheng Guan(2006)的研究表明:日、韩两国正是借助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向它们的技术转移,才得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对经济实力的提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16]。Amy H.I.Lee,Wei-M ing Wang and Tsai-Ying Lin(2010)对台湾 TFT-LCD行业的研究表明:该行业的繁荣得益于日本的技术转移同台湾的人才、资本等优势的有效结合,大多数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随着产业转移而不断提升,并促使企业的竞争优势不断增强[17]。
(四)政策创新的“洼池效应”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减少区际收入和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许多国家对迁往落后地区和衰退地区的企业提供多种形式的津贴或其他刺激,这产生了政策创新的“洼池效应”,吸引和聚集了大量发达地区的产业进行主动转移,如荷兰、法国先后采用了相类似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认为空间上的产业转移过程,不仅要考虑影响企业决策的传统生产要素,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决策行为中的政策性因素。这使得学者们开始关注政策因素对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对鼓励产业转移的政策加以评估。
Keeble(1976)认为,区域政策是影响 1966~1971年英国区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其结论是所有政策包括区域政策都会对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影响。O rtona&Santagata(1983)研究发现,意大利都灵地区的土地使用政策对产业转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制度区位理论认为,产业转移的空间经济过程是由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形成,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是企业与供应商、政府、工会以及其他机构就价格、工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和其他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进行谈判的结果。Toshihiro Iho ri&C.C.Yang(2009)分析了税收优惠竞争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方式下,美国区域间税收竞争与地区内政治竞争的互动能够产生最优的公共品供给,进而影响产业的区位分布[18]。
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lsch,1990)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来研究产业转移现象。他认为,处于中心的少数发达工业化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依附于发达国家,难以获得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同时,由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而工业制品的需求弹性高,导致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被迫实行的用国内工业化替代大量进口工业品的进口替代战略,是国际产业转移发生的根源。普雷维什观点借鉴了汉密尔顿、李斯特等人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突出了国家行为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穆尔、罗兹和泰勒(1993)有关英国产业转移的研究表明:受援地区吸引投资的优惠条件、受援地区的工资补贴以及在非受援地区的限制企业布局政策对产业转移起到很大作用。阿什克罗夫特和泰勒建立了产业转移的时间系列模型,他们发现,总的产业转移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投资,而产业转移的空间分布主要取决于反映区位发展优势的政策性要素组合。Dupont and Martin(2003)探讨了不同地区补贴政策对落后地区产业区位、就业、收入不平等(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以及福利水平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资金来源(国家和地区层面征税)、不同的补贴方式(税收减免、利润补贴、一次性补贴、固定成本补贴、生产和就业补贴)对产业区位、收入不平等程度(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贸易成本较低时,上述所有补贴方式对产业区位的影响较强;当从地方层面融资时,补贴能够成功吸引产业;对贫困地区制造业的补贴改变了地区竞争和企业规模,这可能导致贫困地区该产业就业和生产的下降;如果存在产业区位调整成本,地区补贴则可能损害贫困地区。
三、结论
综观已有研究,对于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产品供给和要素供给两个方面,主要涉及产品更新、产品创新、劳动力流动、资本汇聚、技术外溢和政策创新等推动的产业转移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内在机理分析。虽然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相关理论研究,都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一,国外理论和国内实证缺少耦合。大部分成熟的理论主要从国家的角度来研究产业转移,对于解释发达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区域非均衡发展为背景来研究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升级的问题,很多理论缺乏相应的实践基础。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其内在机制、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和国际产业转移存在很大的区别,不可等量齐观。如何将产业转移理论与国内区域产业升级的实践完美结合,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第二,更多地注重了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升级的经济因素。上述研究侧重于考察资本汇聚、劳动力优势、技术外溢、经济政策等经济因素,而对制度创新、行为决策、社会网络、社会文化、决策主体偏好等非经济因素的理论分析明显不足。
第三,研究对象上侧重于考察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上述研究尤其是国外研究,侧重于利用技术的发展差距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研究对象上主要以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而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研究相对较少。
注释:
(1)扩展扩散:也称膨胀扩散或波式扩散,是指某种产业在其源地形成并得到日益发展的同时,还继续向外部扩散,像滚雪球一样,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像波纹一样,由核心向四周扩展。
[1]Ozawa T.“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tructural Transfo rmation:Japan as a Recycler of Market and Industry”,Business and Contempo rary Wo rld,1993,5(2):129-150.
[2]Tan Z.A.“Product cycle theor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government policy,and indigenous manufacturing in China”,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2002,26:17-30.
[3]Gersbach,H.A. Schmutzler,“External spillovers,internal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Regional Science and U rban Economics,1999,29(6):679-696.
[4]陈计旺.影响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7,(5):99-101.
[5]石奇.集成经济原理与产业转移[J].中国工业经济,2004,(5):5-12.
[6]刘艳.“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学家,2005,(3):124-126.
[7]戴宏伟,王云平.产业转移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分析[J].当代财经,2008,(2):93-98.
[8]钱纳里,等.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分析[M].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9]Blomström,M.,Konan,D.&R.Lipsey.“FD I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Japanese Economy”,NBER Working Paper 7693,2000.
[10]Advincula,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Competitiveness,and Industrial Upgrading:The Cas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KDL,2000.
[11]Marjan Svetlii,M atija Rojec and Andreja Trtnik,“The Restructuring Role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Central European Firm s:The Case of Slovenia”,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0,10:53-88.
[12]Salvador Barrios,Holger Gorg,Eric Strob,“Fo 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peti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5,49:1761-1784.
[13]祖强,孙军.跨国公司FD I对我国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5):28-32.
[14]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曹征海,潘照东,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15]Gorg & Strobl,“M 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A Meta-Analysis”,The Economic Journal,2001,111(475):723-739.
[16]Jian Cheng Guan,Chiu Kam Mok,Richard C.M.Yam,K.S.Chin.“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Technological Fo recasting&Social Change,2006:666-678.
[17]Amy H.I.Lee,Wei-M ing Wang and Tsai-Ying Lin,“An Evaluation Framewo rk fo r Technology Transfer of New Equipment i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10,77(1):135-150.
[18]Toshihiro Iho ri,C.C.Yang,“Interreg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Intraregional Political Competition:The Op timal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Rep resent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U rban Economics,2009,66(3):210-217.
The Review on Industrial Transfer’s Upgrading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e:Based on Supplying Factor Analysis
MA Zi-hong1a,HU Hong-bin1b,CUIJin-m in1a
(1.Yunnan University a.Economic College;b.Institute of Cultural Industry,Kunming 650091,China)
In the respect of all over the world,industrial transfer has becoming an impo rtant way to imp rove those countries which have lagged advantages to op timizing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By means of industrial transfer,developed countries o r areas can push continually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become higher and newer pattern,meanw hil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o r areas can push quickly industry to realize non-resource-depending and high-additional-value’s developing path.Aim to this condition,a lager different study on industrial transfer’s upgrading regional industry structure have been accomp lish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ian and all kinds of theo ries are increasingly formed.Based on the supp lying factors analysis,this paper is aimed p roviding some academic evidence to accelerate pushing our country’s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o realizeour country’s regional developing harmoniously,by meansof review ing on industrial transfer’s upgrading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transfer;industrial upgrading;supp lying;review
F269.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1)04-028-07
2011-05-0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产业转移促进西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机制分析”(10CJL044);云南大学第三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基金(21132014)
马子红(1976-),男,云南寻甸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胡洪斌(1974-),男,昆明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发展;崔静敏(1985-),女,天津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