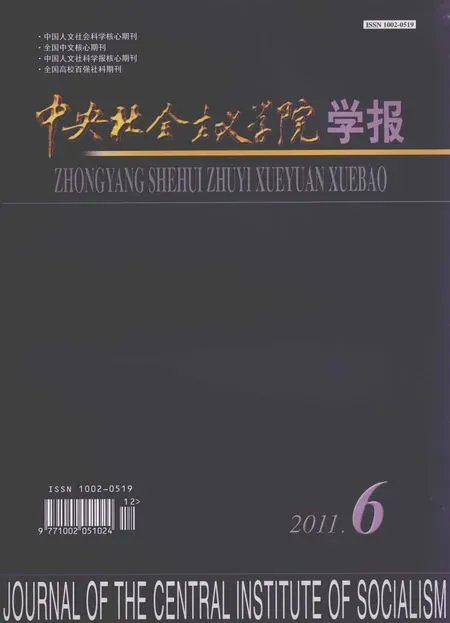试述异化劳动研究的经验转向
2011-02-18李勇刚
李勇刚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试述异化劳动研究的经验转向
李勇刚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异化是人对其本质的疏离,表现在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等方面,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此后的研究长期遵循纯粹理论研究的方向。20世纪50年代末,塞曼(Seeman)提出了异化的“五维度”:权力缺乏、意义丧失、规范缺失、社会隔离、自我疏远,对“异化”概念进行操作化定义。围绕“五维度”范式展开了众多的经验研究,形成异化劳动研究领域的“经验转向”。在这些研究中,关于异化原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和个体人格两个层面,韦格纳提出的“特定环境分析方法”则对这两个层面予以综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键词:异化劳动;五维度;经验转向;特定环境分析
一、理论的建构: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研究
“异化劳动”问题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关注并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对于异化问题的研究,始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异化的概念以及原因,初步完成了对异化劳动的理论建构。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于“异化”概念的论述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
首先,是劳动产品的外化,即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自己。劳动产品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对于工人而言,劳动产品是异己的存在物,劳动是对象固定的物化劳动,这叫做“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对象化也就是劳动的现实化,劳动的现实化则是工人的非现实化。因为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表现为被对象所奴役。于是,工人所生产的产品越多,反对工人自身的异己对象世界就越强大,工人所占有的对象就越少,内部世界就越贫乏,从而愈发受其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自然界是感性的外部世界,是工人劳动的前提,为工人劳动提供劳动生活资料和生存生活资料,以维持劳动对象与劳动力。人们本来可以通过自身劳动占有外部感性自然界,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在两方面都失去生活资料:一是感性外部世界越来越不属于工人的劳动对象;二是感性外部世界越来越不为工人提供直接生活资料,即工人维持其肉体生存的手段。
其次,是生产活动的异化。异化还表现在生产行为中,即生产活动本身之中。在劳动的时候,工人只是否定自身,备受折磨;在劳动以外,工人才能感到自在。如果没有外在强制,那么,工人必将逃避劳动而后快。因为劳动不过是一种手段,属于他人,而非工人自己。在工人身上出现一种奇特的反差:只有在动物性机能的运用中,比如吃喝、生殖等活动中,工人才能获得自由活动的感觉;而当工人运用人的机能,亦即劳动的时候,反而陷入不自由的境地。
再次,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是类存在物,这是因为人能将自身生命活动变为其意志与意识的对象。也只有这样,人的活动才能成为自由的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正因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反而把作为自身本质的生命活动,变为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这样一来,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劳动,仅仅变成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这是异化更为深刻的内涵。
最后,是人际关系的异化。虽然这一点马克思似乎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也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劳动的本质,变为异己的本质,变为维持个体生存的手段。因为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生命活动、类本质相异化,所以,也必然与他人相异化。
马克思对于异化原因的归结较为简明,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那么,它应当属于谁呢?劳动产品不可能属于神灵和自然,只能属于工人以外的他人,也就是资本家。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产物与结果,外化劳动侧重指工人相对自然界与自身的外在关系。从外化劳动、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生命、异化的人等概念出发,马克思推出了私有财产的问题。私有财产是外化的结果,更是外化的手段。
如何走出异化?马克思认为,要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而如果要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则需要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工人的解放,也就包含普遍人类的解放。
二、发展的分化:从理论到经验
韦格纳(Wegner)总结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路:在本质上,人类是有活动与创造潜能的动物,如果给以适当的自由的条件,人类可以实现这一潜能。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个人在与生产方式、劳动产品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等方面,都变为被动的客体,而与其活动与创造的潜能相疏离。也就是说,异化理论有一个未曾说明的预设:对人类创造性的假定[2]。然而,这一来自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假定本身能否成立,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另外,在从“现代”到“后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异化”理论所开创的思想方向,也必将有新的思想内容;异化理论本身要成为一个与现代学术规范契合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也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在有关异化劳动的研究中会出现“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的发展道路。
在有关异化问题的研究中,遵循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道路的不在少数,比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弗洛姆和马尔库赛的异化理论,等等。这些研究者大多结合各自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状况,用一种批判的视角进行哲学层面的探讨。尽管他们对于异化的定义仍然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但缺乏一致的理解。关于异化的原因,他们更多将其归结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而非个体的因素。
单纯的理论研究难以突破自身的窠臼,“异化”劳动研究的拓展,需要新的研究视角的加入。正如韦格纳(Wegner)所言:“作为社会科学概念,‘异化'应该与人类现实的状况相关,而不是去说明人类应该如何。”[2]作为一种“应然”色彩颇为强烈的概念,“异化”的界定有必要向“实然”转化。或者说,“异化”的概念需要“操作化”,成为经验研究的对象,才能获得更为充分的解释力。这项工作开始于美国社会学家塞曼(Seeman)。
三、概念的操作化:塞曼的异化“五维度”
1959年,塞曼总结了马克思、韦伯、米尔斯、弗洛姆、曼海姆、默顿、古尔德纳、阿多诺等理论家的相关论述,抽取出了构成“异化”含义的五个基本维度:权力缺乏(powerlessness)、意义丧失(meaninglessness)、规范缺失(normlessness)、社会孤立(social isolation)、自我疏离(self-estrangement)[3]。通过对于“五维度”的论述,塞曼提出了自己关于“异化”概念的操作化定义。
塞曼运用一种“预期”的视角来界定这五个维度。塞曼承认,可以采用的界定标准其实很多,包括预期、客观条件、对道德标准的偏离等,争论哪个因素能界定“真正的异化”并无意义。而他之所以选择“预期”,是为了避免将道德或判断特征带入异化概念。这表面上和马克思的观点相左,但其实不然。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是关于事情(affairs)的论断,即个人的自由和掌控的减少。而他所定义的异化则相反,指的是个人对于这些事情的状态的预期。在这种标准之下,塞曼对异化的五个维度一一作了详尽的说明。
“权利缺乏”指个人所持的一种预期和可能性,在这种预期和可能性之下,个人认为自身行为难以决定所产生的后果,难以增益其所追求的利益。这首先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其次,“权力缺乏”的成分除去了马克思异化观念中批判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通常容易引起争议。
“意义丧失”是一种低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之下,对于行为的结果,难以作出满意的预测。个人难以理解其所参与事件的意义,个人对其应该相信什么并不清楚,个人在作决定的时候,难以达到最低限度的了解。
“规范缺失”包含一种较高的预期,在这种预期下,如果要达到既定的目标,则必须采取社会所不允许的行为。这一概念与迪尔凯姆的“失范”概念直接相关,即是说,指导个人行为的社会规范被破坏,或难以继续成为有效的行为规范。
“社会孤立”指个人疏离于其所在的社会和文化。这一维度如果运用回报价值的观点来理解更为合适。在此种状态下,对于既定社会通常所看重的目标或信念,个人只是赋予其很少的回报价值。
“自我疏离”指在工作中内在意义的丧失,既定行为对将来预期回报的依赖程度低,个人参与某项活动,只是为了金钱,或者为了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难以在其所参与的活动中找到自身的意义回报。
塞曼进一步指出,“五维度”之间在逻辑上相互独立,但是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关系。
伊斯雷尔(Israel)对塞曼的“五维度”进行了两方面的评价[4]。关于塞曼的开创性贡献,他肯定塞曼从浩如烟海的社会学文献中提炼出异化概念的各种用法并以更为经验的形式予以说明的做法。伊斯雷尔总结了对于塞曼的四条批评:第一,没有将异化的五变量纳入过程性的理论背景之中。第二,塞曼忽略了个人期望与社会现实的落差所导致的后果。第三,塞曼试图维持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基本内核,但是,放弃了社会批评与社会变革的关怀,转而承认社会之现状,满足自己所构建的模型的“微观问题”。第四,抛弃马克思对社会过程的强调,转而关注社会心理层面的个人经验,只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而非社会学研究。
四、“经验转向”的展开:关于后续的研究
尽管受到一些批评,塞曼对于异化“五维度”的划分还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遵循塞曼开创的研究范式,许多学者对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经验研究。
经验研究的重要任务是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依照下面的思路对经验研究予以考察:第一,在因变量方面,什么是异化?第二,在自变量方面,哪些因素造成了异化?第三,在相互关系上,这些因素如何造成了异化?在这种思路下,我们发现关于异化的经验研究有如下几个类型:
首先,大量研究集中在作为因变量的“异化”各维度的关系方面,这采取的是一种横向的研究思路。因为塞曼并未说明异化的“五维度”孰轻孰重,所以,许多学者试图用经验来研究证明“五维度”中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甚至是可以省略的。迪安(Dean)用经验研究证明权力缺乏、规范缺失、社会隔离是三个主要的维度[5]。多兰(Dolan)则认为,自我疏远与社会隔离两个维度最得马克思的精髓[6]。罗伯特(Roberts)研究出关于美国雇用工人异化状况的模型,该模型为纵向二阶证实性模型,以塞曼首创的五维度概念为基础。此模型中,异化为二阶因素,与五维度息息相关。权力缺乏与自我疏远似乎为中心要素,而意义丧失、规范缺失与社会疏离似乎较为次要[7]。
其次,一些研究者从纵向的时间角度,验证异化的各个维度的稳定性与一般性。泽勒等人(Zeller)利用纵向数据,通过在1963到1971年间对334位妇女的抽样调查,研究四种异化维度(权力缺乏、意义丧失、规范缺失、社会疏离)的可靠性与稳定性。结果表明,异化的“五维度”在经验上可以分离,在两个时点上都非常可靠;在长达八年的间隔当中,各维度量表得分都高度稳定。这些研究发现,支持了异化各维度的稳定性,证实了塞曼的划分切实可行[7]。
再次,更多的研究者试图在经验层面寻找导致异化的自变量,并得出一些具有经验证据的结论。迪安(Dean)用量表测量异化与一些因素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在权力缺乏、规范缺失、社会隔离三个维度与职业声望、教育、收入、乡村背景等因素之间,存在虽然较弱但统计显著的负相关。在异化与年龄增长之间,存在较弱的正相关[9]。谢泼德(Shepard)将工作满意度作为测量异化程度的重要经验指标,为了检验工作满意度与社会分工之间的负向关系,引入了文化差异作为中介变量。为了揭示工作满意度与城乡差别的关系,引入了中产阶级规范的融入或疏离作为中介变量,并探讨了技术类型与社会分工的关系[4]。布劳纳(Blauner)对印刷业、纺织业、汽车工业、工业化的化学行业这四个行业进行经验研究,区分了手工技术、机器倾向技术、流水线技术、连续过程技术四种技术类型中不同的异化程度,建立了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模型,认为不同行业的不同技术状况,决定了该行业工人的异化状况[10]。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许多理论家遵循着理论研究的范式,对现当代社会的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异化理论此时已经走出了纯粹理论研究的藩篱,发生了一种“经验转向”。对于这种转向,泽勒等人似乎看出了某些端倪。他们指出,测量异化的各个维度是偏重经验的研究者乐于从事的事情,但是,偏重理论的研究者则质疑这一做法的可行性。泽勒等人举例说明[8]。李(Lee)甚至贴出“异化讣告”,认为指定异化的测量标准不过是出于为工业管理服务的需要,实质是为了维护社会和制度的稳定。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反对异化的社会心理学标准,认为异化是由于结构所导致,独立于人们的知觉而存在。批评者的存在,正好说明这种“经验转向”已经发展到了不能不引起人们重视的程度。
五、综合的努力:特定环境分析方法
不应忽略的是,“异化”是一种个人的主体性感受,并不是每个个体都会感到异化。具体而言,可能出现的差异是:某个群体所受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客观异化压力非常之大,大多数人也有异化的感受,但就有一些人——即使是少数——主观上始终不曾感到自己“被异化”。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需要从个人人格方面寻找原因。
一些社会学家试图区分“异化感”产生的潜在人格特征,包括动机、价值、自我印象等,尤其注重自我印象。韦伦斯基、方斯认为,自我印象包括社会性、心智、良心、独立、雄心等方面,而异化来自于个人人格的缺陷,尤其是这些自我印象方面的缺陷。麦克罗斯基和沙尔认为,认知缺乏、情绪缺陷、极端基本信念可解释异化的形成。因此,异化是权威型人格与神经质人格的反映。异化的人不过是不满者与社会不适者。这样,他们最终得出结论:异化概念无甚意义[2]。
韦格纳不赞成上述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流于片面。他指出,面对相同环境,有人感到满足,有人感到异化。因此,一方面,异化关系到特定个人的人格特征;另一方面,异化又并非纯粹个人心理或内在心理特征的产物,它与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总之,个人是否感到异化,在于个人人格与所处环境能否协调,不能笼统地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异化[2]。
在此基础上,韦格纳总结了特定环境分析方法的逻辑:第一,异化与特定人格特征有关,而不是普遍的人性的特征;第二,异化并不是和社会秩序相关的普遍倾向,而是和特定社会环境有关。在特定环境之中,社会结构与个人人格相互冲突,从而产生异化问题;第三,异化的原因,涉及独特的社会环境特征,并没有足以导致异化的普遍社会条件;第四,异化是一种多维度的问题,也是经验的问题。若要具体回答这一问题,则需在特殊环境之下,确定个人与环境冲突的不同模式[2]。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0-64.
[2]E.L.Wegner.The Conceptof Alienation:A Critique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a Context Specific Approach[J].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1975(2):171-193.
[3]M.Seeman.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59(6):783-791.
[4]J.M.Shepard.Technology,Division of Labor,and Alienation[J].The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1973(1):61-88.
[5]J.Israel.Alienation:From Marx to Modern Sociology[M].Boston:Allyn&Bacon,1971:207-215.
[6]Edwin G.Dolan.Alienation,Freedom,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1(5):1084-1094.
[7]B.R.Roberts.A Confirmatory Factor-Analytic Model of Alienation[J].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1987(4):346-351.
[8]R.A.Zeller,A.G.Neal,H.T.Groat.On the Reli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Alienation Measures:A Longitudinal Analysis[J].Social Forces,1980(4):1195-1204.
[9]D.G.Dean.Alienation: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1(10):753-758.
[10]R.Blauner.Alienation and Freedom-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
责任编辑:杨 东
F014.2
A
1002-0519(2011)06-0096-04
2011-08-24
李勇刚(1981-),男,四川阆中人,北京大学哲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