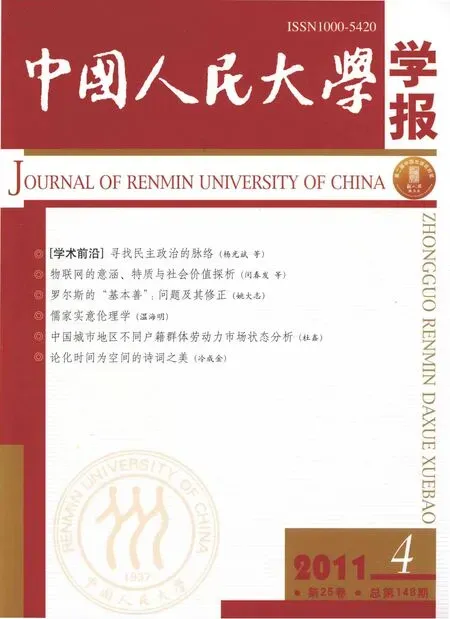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及其“过渡”性质
2011-02-10范方俊
范方俊
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清末之际,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转折期。其中,梁启超(1873—1929)无疑是这一历史时段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文化人物。作为中国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领袖,梁启超参与、主导了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使改良文学成为清末文学的主流。在戏曲创作领域,梁启超对清末戏曲的改良工作也有独特的贡献。
一、清末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与戏曲创作
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历经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并强化了以宗法制和农耕生产方式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形态。不可否认,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曾经创造出跻身于世界民族先进之列的古代文明,奠定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但作为一种植根于农耕生产方式之上的传统社会,相距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近代社会有很大的落差。同时,由于中国农耕文明形成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封闭的文化模式,从根本上抑制了自身主动寻求变革的内在动力,其发展潜力也在长期的僵化停滞和自我封闭中受到限制。进入19世纪之后,与西方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却步入封建社会的末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利和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更让中国陷入了亡国灭种的苦难深渊。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开始瓦解。早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P276-277)近代的中国社会正是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外力推动下,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化。
“文变染乎世情”。阿英对于清末的戏曲创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当时中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清廷腐朽,列强侵略,各国甚至提倡‘瓜分’,日本也公然叫嚣‘吞并’,动魄惊心,几有朝不保暮之势。于是爱国之士,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提倡民主,反对侵略,即在戏曲领域内,亦形成了宏大潮流。”[2](P1)其所编订的二卷本《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分历史、现实、传奇三个主要部类,详细地记录了清末的戏曲创作:
第一是历史类。除了少部分剧作,如感惺的《断头台》取材于法国大革命、梁启超的《新罗马》取材于意大利三杰建国史之外,基本上都是取材于本国的历史,特别是南宋文天祥抗元以及南明史可法、郑成功、瞿式耕、张煌言抗清的历史本事,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筱波山人的《爱国魂》、浴日生的《海国英雄记》、祈黄楼主人(洪栋园)的《悬岙猿》、孤的《指南梦》、虞名的《指南公》以及吴梅的《风洞山》等。从历史情状上讲,清末与南宋和南明末年惊人地相似:外部遭异族侵凌,内部又积弱难振,内忧外患,朝不保夕。剧作家们选取南宋和南明的历史说事,带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所依托的虽是过往的历史故事,但戏曲的所指分明是当时的清末现实,如吴梅在《风洞山·自序》中所言:“思宗殉国,王业偏安,东南人士,痛雪国仇,竭忠尽智,碎骨捐躯,阁部而外,莫如临桂。新亭涕泪,故国河山,慷慨誓师,从容尽节,成仁取义,君子韪焉。秋斋寥寂,旧雨不来,摭拾遗事,衍为院本,以厕艺林,瞠乎后矣。”[3](P45)
第二是现实类。直接取材于清末的社会现实,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惜秋填词、旅生等补续的《维新梦》、湘灵子的《轩亭冤》、嬴宗季女的《六月霜》、孙雨林的《皖江血》以及华伟生的《开国奇冤》等。其中,《维新梦》直陈清末的乱象已是“不堪回首”:“现在的大局,内忧外悔,交迫而来,此弱彼强,相形见绌,这真是无可如何的了!”[4](P444)而其《建路》、《采矿》、《讲武》、《劝学》、《裁官》、《训农》、《验厂》、《商战》、《立宪》和《大同》等数十齣戏,堪称是对清末维新运动的真实再现。《轩亭冤》、《六月霜》、《皖江血》和《开国奇冤》等剧作,则集中取材于清末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的英雄事迹,热情讴歌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所述清末革命运动激动人心,而去时未远,在反映清末现实方面可谓独树一帜。
第三是传奇类。传奇,本是唐代记述奇异故事的文人小说,明清以后成为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形式。清末的戏曲创作,在依托于前人传奇故事的基础之上,有意识地对传奇进行艺术的再造,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洪栋园的《后南柯》和梁启超的《劫灰梦》。尤其是《后南柯》,虽脱胎于明代汤显祖的《南柯记》,立意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环伺、种族吞灭之竞争时世,“或问于余曰:昔时汤临川先生有《南柯记》之编,而子是作又名《后南柯》,亦借蚁为喻,意者以汤意未尽,而为东施效颦乎?抑羡慕成作,而为邯郸学步乎?余应之曰:否,否。临川先生《南柯记》,大旨以世人之弱于富贵荣华,故托之于梦,欲人之以真为幻也。兹编大旨,以世人沈迷醉梦,故托之于蚁,欲人之以幻为真也……《南柯记》以解脱尘累为指归,觉后便能成佛;兹编则以大声疾呼为宗旨,觉后须有为焉。虽取譬同,而主意则处处不同,事事反对,此其所以为《后南柯》欤!”[5](P377)其题词点题百字令:“竞争时世,正列强环伺,狡焉思启。眼见中原干净土,一任鲸吞而已。蠢而微虫,御诲有心,戮力坚团体。物犹如此,为何人不如蚁?忆昔玉茗风流,南柯作记,幻想在空际。嗣响词人期救世,危语切中时弊。因幻求真,反虚课实,保种心诚矣。休云小说,人心风俗关系”[6](P376),鲜明的现实指向更是跃然纸上。
要之,反对民族压迫、宣传革命内容是清末戏曲创作的主流和特色。郑振铎称赞清末戏曲创作:“皆激昂慷慨,血泪交流,为民族文学之伟著,亦政治戏曲之丰碑。”[7](P1)梁启超则从理论上把清末戏曲的政治承担和现实指向概括为“觉世”和“救心”。
二、觉世与救心:梁启超清末的戏曲创作
梁启超的戏曲创作始于变法失败后的海外流亡时期,先写了《劫灰梦传奇》的楔子一齣,后来又完成了《新罗马传奇》的楔子和七齣戏。关于梁启超戏曲创作的缘起,他的少年同学韩孔厂(署名扪虱谈虎客)做了如下的说明:“作者初为《劫灰梦传奇》,仅成楔子一齣,余亟赏之,日日促其续成,蹉跎至今,竟无嗣响。日者复见其所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因语之曰:‘若演此作剧,诚于中国现今社会最有影响。’作者犹豫未应,余促之甚。端午夕,同泛舟太平洋滨归,夜向午,忽持此章相示。余受之狂喜,因约每齣为之评注,兼监督之,勿令其中途戛然而止也。”[8](P520)一语道出了梁启超试图利用戏曲创作“影响中国现今社会”的创作初衷。
《劫灰梦传奇》的开场,就用男主人公杜如晦的独白,直陈清末中国社会所呈现出的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的严峻现实: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自从甲午以后,惊心时局,大梦初醒,便已绝意仕进,就屋于城西枣花寺旁,读书自乐。不料去岁义和构衅,弄兵召戎,奖群盗为义民,尸邻使于朝市,卒使乘舆播荡,神京陆沈,天坛为凶牧之场,曹署充屯营之帐。咳,小生那时亲在京师,目睹两宫仓皇出走之形,群僚狼狈逃命之状,以及外兵野蛮暴掠,民间之狼藉颠连,至今思之,历历在目。
对于列强侵凌给中国造成的空前劫难,剧作者难掩心中悲愤:
[梁州序]苍天无语,江山如画,一片残阳西挂。旧时王谢,燕归何处人家?阴山铁骑,斗米黄巾,剩附渔樵话。神京有地骋戎马,中原无处起龙蛇。泱泱风,安在也?
[前调]回风砰击,怒潮倾泻,万斛艨艟东下。谁家卧榻,尽伊鼾睡纷呶?优胜劣败,竞立争存,斯事畴怜惜?百年龙战欧和亚,梦觉黄粱日已斜。英雄泪,向谁洒?
不过,在剧作者看来,列强蚕食中国还不算“中国的第一大劫”,因为“道物耻可以振之,国耻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国自今后上下一心,发愤为强,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呢”[9](P687)!但中国的现实却是国民麻木、人心不振,却是中国最大的劫难:
咳,你看今日的人心啊!
[皂罗袍]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到今儿便记不起昨日的风横雨斜。游鱼在釜戏菱花,处堂燕雀安颓厦。黄金暮夜,侯门路赊。青灯帖括,廉船鬓华。望天儿更打落几个糊涂卦。
这算是那一种守旧的咯,别有那叫做通洋务的呢!
[前调]更有那婢膝奴颜流亚,趁风潮便找定的饭碗根芽。官房翻译大名家,洋行通事龙门价。领约卡拉(collar),口衔雪茄(cigar)。见鬼唱喏,对人磨牙,笑骂来则索性由他骂。
咳,你看整日价熙熙攘攘,就只是这两类的人,想起中国前途怎生是了!
梁启超认为,要挽救中国,唯有用文艺去“觉世人”、“救人心”:
我想歌也无益,哭也无益,笑也无益,骂也无益。你看从前法国路易十四的时候,那人心风俗不是和中国今日一样吗?幸亏有一个文人叫做福禄特尔,做了许多小说戏本,竟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了。想俺一介书生,无权无勇,又无学问可以著书传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几樁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几片道理,编成一部小小传奇,等那大人先生、儿童走卒,茶前饭后,作一消遣,总比读那《西厢记》、《牡丹亭》强得些些,这就算尽我自己面分的国民责任罢了。
所以,《劫灰梦传奇》虽然只有楔子一齣,却是梁启超戏曲创作以“觉世”和“救心”为宗旨的一个纲领性说明。
《新罗马传奇》在创作宗旨上与《劫灰梦传奇》一脉相承。戏曲“楔子”一齣,借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魂灵,述说了小说、戏曲对于“觉世人”、“救人心”、挽救民族危亡的巨大作用:
俺乃意大利一个诗家但丁的灵魂是也。托生名国,少抱天才。夙怀经世之心,粗解自由之意。叵耐我国自罗马解纽以后,群雄割据,豆剖瓜分……任那峨特狄、阿剌伯、西班牙、法兰西、奥大利,前虎后狼,更迭侵凌,好似个目虾腹蟹。咳,老夫当数百年前,抱此一腔热血,楚囚对泣,感事唏嘘。念及立国根本,在振国民精神,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衢传诵,妇孺皆知,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幸上天眷顾……今日我意大利,依然成了一个欧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国了。
并以对白的形式,交代了剧作者创作《新罗马传奇》的相同“文心”:
(内):支那乃东方一个病国,大仙为何前去?
(答):你们有所不知。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什么饮冰室主人,编了一部《新罗马传奇》,现在上海爱园戏园开演。这套传奇,就系把俺意大利建国事情逐段摹写,绘声绘影,可歌可泣。四十齣词腔科白,字字珠玑;五十年成败兴亡,言言药石。因此老夫想著两位忘年朋友,一个系英国的索士比亚,一个便是法国的福禄特尔,同去听一回。
(内):这位青年为何忽然做起这套戏本来呢?
(答):人孰无情,士各有志,精禽填海,斥鷃笑其大愚;杜宇啼枝,行人闻而坠涕。我想这位青年,飘流异域,临睨旧乡,忧国如焚,回天无术,借雕虫之小技,写遒铎之微言,不过与老夫当日同病相怜罢了。从内容上讲,《新罗马传奇》尽管取材的是意大利三杰建国的外国故事,主人公的姓名、穿戴和戏曲的发生地也都沿用外国的,但正如《新罗马传奇》的批注者所指出的,此剧的最大特点是“以外国人眼来看中国戏”[10](P520)。换言之,《新罗马传奇》的性质是借用外国的人和事来描绘中国的社会情状,戏曲中的这些身着洋装的外国人,所唱之词全是中国的地域和典故,甚至直接化用中国经典戏曲里的唱词。尤其是意大利三杰中的加里波的(戏曲中的净角)对于罗马城的咏叹:
[油葫芦]一霎凉风吹酒醒,正到洛阳城。望朝霞起,午云捲,夕阳明。十丈软红尘,玉宇琼楼迥。百战旧山河,历历心头影。一个是扁舟天地无双士,一个是青史人间第一城。我便要整顿全神注定卿。
[皂罗袍]原来是乔木废池如瞑,甚黄昏清角吹寒剩有空城。阵云黯没汉家营,月华破碎秦时镜。凄凉草树,鹃啼有声。寻常门巷,燕来无情。难道我梦儿错认了黄粱境?
[驻马听]金碧飘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蓝寂静,南朝烟锁佛无灵。神鸭社鼓断肠声,兔葵燕麦斜阳影。谁记省,觚棱梦冷秋前病。
[沈醉东风]你记得昔日啊定中原铙歌健劲,你听得今日啊哀江南赋凄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尽英雄影。望一片山残水剩,都付与乌啼故国。人泣新亭,楼空夜永,把十年好梦,被风抖醒。
这更是直把罗马作洛阳了。扪虱谈虎客批注认为:“作者生平为文,每喜自造新名词,或杂引泰东、泰西故事,独此书人西人口气,反全用中国典故,曲中不杂一译语名词,是亦其有意立异处。”[11](P540-541)这里的“有意”,就是剧作者有意识地借用外国人来说中国的事。其实,《新罗马传奇》中所描述的“帝国分赃”、“农民起义”、“义士结党”等内容,也基本暗合清末中国的社会历史。而剧中《铸党》一齣对于“觉世”、“救心”的英雄自许:“我想国中积弊既深,断非弥缝補苴可以救得转来,破坏之事,无论迟早,终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那有意识的破坏,早一日还得有一日之福哩。人心腐败到这般田地,莫说平和的福分不能享受,只怕连破坏事业也不能做成,这却怎么好?……但古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操练一国人,叫他成就一个国民的资格,正是我辈责任哩。”[12](P543)也正是剧作者期冀以戏曲创作达“觉世人”、“救人心”之社会目的的真实写照。
三、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的“过渡”性质
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一文,明确地把19世纪末20世纪的中国定义为一个“过渡”时代:“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故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13](P166)在这里,“过渡”一词有些意味深长,不仅是对梁启超生活于其间的清末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也是对其包括戏曲创作在内的文学改良活动的一个绝妙写照。
关于梁启超清末戏曲改良的“过渡”性质,也可以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这个特点来谈。
首先,梁启超对中国旧的戏曲传统的因袭。“传奇”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主要的戏曲形式,也是梁启超所因循的戏曲形式。关于梁启超戏曲创作与传统戏曲的密切关联,扪虱谈虎客在批注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时,从一开始就指出其与中国戏曲经典《桃花扇》之间的因袭关系:“全从《桃花扇》出”,“从来剧本演实人实事,毫无臆造者,惟孔云亭《桃花扇》一曲,在中国韵文中可称第一杰作。此本熔铸西史……视云亭之气魄意境,有过之无不及矣。”[14](P520)具体而言,可从“考据”、“感世”、“凡例”三个方面细说:其一是“考据”。孔尚任的《桃花扇》所据的是南明本事,剧中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都经剧作者详细考据,“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实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15](P11)。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所据的是意大利的近代建国史,梁启超本人对于意大利的这段历史专门做过考订,并著《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一书,《新罗马传奇》中的人物和事件与《桃花扇》一样俱是真人实事,扪虱谈虎客所说的“演实人实事,毫无臆造者”,即是此意。其二是“警世”。《桃花扇》的写作,有着明确的“警世”指向:“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今之乐,犹古之乐,岂不信哉?《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16](P1)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同样带着明确的“警世”指向,剧中《楔子》一齣借但丁之口所述的“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衢传诵,妇孺知闻……四十齣词腔科白,字字珠玑;五十年成败兴亡,言言药石”,几可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互训。其三是“凡例”。孔尚任的《桃花扇》设凡例十六则,内容涵盖剧名、排场、各齣脉络连贯、各本填词、曲名、说白、典故、角色、上下场诗等方面,梁启超曾在《小说丛话》中盛赞孔尚任的《桃花扇》“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冠绝前古”[17](P314),他的《新罗马传奇》尽管没有按原计划的四十齣写完,但其体例脱胎于《桃花扇》,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梁启超对中国旧戏曲传统的革新。有学者在评价梁启超的近代文学改良时指出,梁启超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在内的文学改良,突出的就是一个“新”字,如“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文界革命”的“开文章之新体”以及“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之意境”,等等。在戏曲改良中,梁启超同样试图在旧的戏曲形式中引入“新”意,具体表现为:(1)新的戏曲观。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与居于正统地位的诗和古文比较而言,戏曲(包括小说)一向为人轻视,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梁启超在近代文学改良中对上述文学观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肯定了戏曲、小说一类的文体在启迪民众、塑造新国民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他尊小说为“文学之上乘”之文体;对于戏曲,梁启超不仅在文体地位上把它与小说等同视之,而且同样肯定其在振奋国民精神上的巨大功用。这一崭新的戏曲观有力地扭转了国人对戏曲的偏见,成为日后中国近现代戏曲(戏剧)创作繁荣的引路先锋。(2)新的编剧手法。梁启超的戏曲创作虽然因循戏曲“常例”,但在具体的艺术手段上并不故步自封,而是有意识地按剧情发展的需要自创“新格”。比如,《新罗马传奇》的第一齣,依照戏曲的常例,曲本的第一齣必须由本剧的主人公登场,也即通常所说的“正生”和“正旦”。但梁启超《新罗马传奇》的第一齣却不循“常例”,全齣先从奥地利大公梅特涅、俄皇、普皇等配角举行的维也纳会议开始,其后各齣才让剧中男女主人公如烧炭党首领兄妹和意大利三杰次第出场。美国当代戏剧理论家罗伯特·科恩在谈到西方剧本的结构时指出,一个好的剧本绝不能从一开端就让剧中的主角出场,因为这样的开场只会让观众一时摸不到头脑,所以通常是由剧中的小角色率先出场,“介绍前史,交代来头,为主要角色的出场铺平道路”[18](P48)。梁启超对于《新罗马传奇》的编剧处理尽管不合中国传统戏曲的“常例”,却与西洋戏剧的编剧规范暗合,谓其“新格”也算名副其实。(3)新的异域因子的引入。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西方这一异域文化因子的涌入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对此梁启超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19](P2)他明确主张:“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20](P4)在《劫灰梦传奇》和《新罗马传奇》中,梁启超不仅把莎士比亚、伏尔泰等西方剧作家引为同道,而且直接把西洋题材引入中国的戏曲创作。这种引西洋异域因子再造中国传统戏曲的做法,对于近代的戏曲改良真是别开生面,“熔铸西史,捉紫髯碧眼儿被以优孟衣冠,尤为石破天惊……以中国戏演外国事,复以外国人看中国事,作势在千里之外,神龙天骄,不可思议”[21](P520),并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创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戏曲改良,直接引发了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两个重要的戏剧理论话题:一是对中国传统戏曲的定位和评价,以后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对于传统戏曲的论争,都是以此为发端的;二是中国新戏对西洋戏剧的引入和借鉴,1906年,留日学生成立“春柳社”,以西洋戏剧为模板,开启了中国现代新戏的先声。如果单就后来20世纪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新戏的分途发展来看,梁启超带有“过渡”性质的戏曲改良,只能算是一场没有完成、也谈不上成功的戏剧改良尝试,其更大的意义是问题的提出而非问题的解决。同时,从创作水准上讲,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清末的戏曲改良并无过高的艺术成就,甚至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如片面地强调戏曲的社会教化功用而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戏曲自身的艺术规律以及大部作品多为案头文学并不适合舞台演出,等等,但是,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陈迹”的时代产物,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戏曲改良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标举的“觉世”、“救心”的戏曲宗旨代表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强音,它的新旧交织、中西杂糅的“过渡”性质,也为中国戏曲(戏剧)的近现代转型铺平了道路。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阿英:《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叙例》,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吴梅:《风洞山·自序》,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惜秋填词、旅生等补续:《维新梦·感恨》,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5]洪栋园:《后南柯·又序》,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6]洪栋园:《后南柯·题词》,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郑振铎:《晚清戏曲小说目·序》,转引自阿英:《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8][10][11][14][21]扪虱谈虎客:《新罗马传奇·批注》,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叙例》,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9]梁启超:《劫灰梦传奇·楔子》,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梁启超:《新罗马传奇·铸党》,载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传奇杂剧卷》,下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李兴华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5]孔尚任:《桃花扇·凡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6]孔尚任:《桃花扇·小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17]梁启超:《小说丛话》,载阿英编:《晚清文字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18]罗伯特·科恩:《戏剧》,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9]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