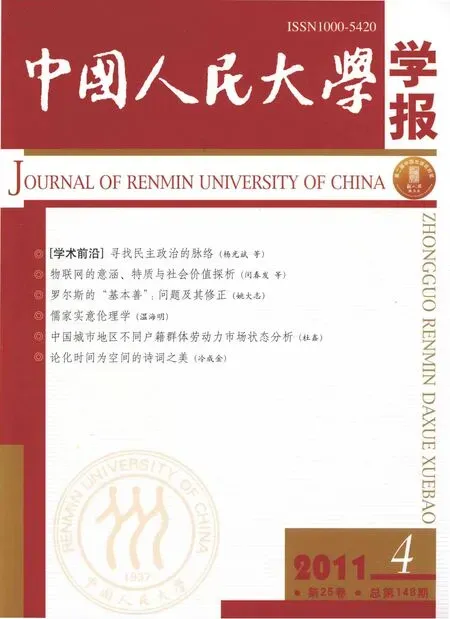知识与道德的安顿——《论语》论“学”的内在逻辑线索探微
2011-02-10陈继红
陈继红
知识与道德何者优先、如何安顿的问题,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分歧反映了中西文化之不同特质。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重视道德(“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而西方哲学则相反,不重主体性而重客体性,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1](P4)刘述先先生则以“知识与价值相统一”概括了儒家的传统观点。[2]这样的总结描绘了儒家观点的大致轮廓,亦促使我们进一步探寻其本来面目。
先秦儒家、宋明儒家以及现代新儒家分别对知识与道德如何安顿这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诠释,但是所有的讨论皆没有脱离孔子的基本框架。由是,《论语》实为理解儒家关于知识与道德关系思想的一把锁钥。本文认为,仅仅从“仁知关系”的角度解读孔子是不够的①当前以知识与道德关系问题为中心对孔子的研究皆是围绕仁知关系而展开的,如刘述先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知识与价值是相统一的,具体到孔子那里就是仁知双彰。其他的相关研究皆没有脱离这一框架。参见刘述先:《儒家传统对于知识与价值的理解与诠释》,载《社会科学评论》,2004(1)。,事实上,知识与道德如何安顿这一问题是贯穿于《论语》论“学”中的内在逻辑线索。《论语》二十篇中几乎每一篇都论及“学”,虽然貌似零散而不成体系,但是依此逻辑线索便可将之连贯成一个整体。立足于“学”这一视角把握孔子关于知识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思考,不但可以厘清后人对孔子的曲解,亦可以为解决当下的道德教育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知识系统与道德系统的分立与融通
钱穆先生曾经对诸儒论“学”下过一个断语:“宋明儒论学,必以有志适道者始谓之学,故若于游艺博文之学,皆摈之于学术之墙外。甚至自汉唐诸大儒,如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几皆摈不得预夫学术之大统,一若不可与共学焉。”[3](P82-83)这就是说,在中国思想史的主流中,“学”之内容只有唯一的道德系统,而“艺”或“文”之知识系统则被排斥在外。诸儒的立场确如钱先生所云“非孔门论学宗旨”,然而知识与道德这两大系统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钱先生并没有做特别的深究。本文认为,在《论语》论“学”中,作为“学”之内容的道德系统与知识系统既分立而自足,又内在地融通为一体。
所谓分立,意味着道德系统与知识系统因由各自的独立性与自足性而自成一体、并列共存。前者的独立性与自足性已是共识,问题在于后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按照孔子的意思,知识系统并不具有单纯的独立性。本文以为,在孔子那里,知识系统的独立性与自足性是有迹可寻的。《子罕》中有一段对话: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在上述对话中,所谓“博学”,意指孔子自身所学之内容。至于“博学”的内涵,后儒的解释是“艺”①朱熹注:“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艺之名也。”(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1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刘宝楠引皇疏:“孔子广学,道艺周遍,不可一一而称,故云‘无所成名’也。”(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3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即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②《周礼·保氏》中解释了“六艺”的内涵:“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亦即个体立身处世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虽然孔子所学之“艺”与西方的科学理性相去甚远,但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谓之为一个自足的知识系统并不过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不仅以“博学”律己,更将之推及于他的弟子: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这两则资料明确地将“文”作为孔门弟子“博学”与“学”之内容。这种内容的重合性表明,“博学”既是孔门之“学”的特质,也是一个必然要求。所谓“文”,依据朱子的解释即“诗书六艺之文”[4](P49),意谓“六艺”之文字记载。由此可知,“六艺”同样是孔门弟子所学的必要内容。就“六艺”之涵盖面来看,如此庞杂的内容体系显然具备了与道德系统相区分的独立性与自足性。
事实上,孔子并没有否认知识系统与道德系统的分立。《述而》云: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在这里,孔子提出了进学的四部分内容:道、德、仁、艺。前三者构成了层次分明的道德系统,此系统可统称为“道”③《论语》中的道、德、仁是三个既有区别又内在相通的范畴。朱子认为,“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由此可知三者之间的层次渐进关系:“道”为客观而外在的行为规范,“德”为客观而外在的“道”之内化,“仁”则为在内化基础上的行为规范之践行。三者虽各有侧重,但共同以“道”所内蕴的行为规范为其基本内容,亦以“志道”为进学之最高境界。由是,“道”自然可以涵盖“德”与“仁”。,艺则为知识系统。虽然如此排序有视“艺”为“轻”、“末”之嫌④朱子以“轻重之伦,本末兼该”概括道、德、仁、艺之序列层次,实是将艺视为“轻”、“末”。(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9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明儒则明确将“艺”排除在“学”之外,如枫山先生以艺为“末技耳,予弗暇也”。庄渠先生甚而云:“若谓此是正业,是指寻花问柳与力穑同也。”(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4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但并不能据此否认知识系统与道德系统的分立关系。所谓“轻”、“末”,仅是后儒之价值判断,在孔子那里并非如是。《先进》云:
子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为“学”之内容。依据钱穆先生的分类,若以德行为“据德”之学,则言语、政事乃“依仁”,文学则“游艺”;若以德行之科为“依仁”,则其余三科皆“游艺”也。[5](P81)以此分类,“学”之四科实为两种:道德系统与知识系统。如果说上文所列之道、德、仁、艺有序列层次区分之嫌,此处孔子所列之四科则是平铺并列,“艺”之重要性与独立性得以凸显。
综观《论语》中为数不多的有关“艺”的议论,便可进一步了解孔子的态度。如孔子曾自述:“吾不试,故艺。”(《子罕》)这显然是将“艺”作为立身之基;又如孔子以“艺”评价冉求,并进而以“艺”作为从政与成人的必要条件。①孔子对冉求的评价见于《雍也》:“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此外,《宪问》中的一段对话亦很能说明问题:“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可见,在孔子那里,“艺”并没有被作为“末技”而加以轻视,知识系统与道德系统各有侧重而不可偏废。何晏释“六艺”时将此两种系统做了优劣之断:“此六者,所以饰身耳,劣于道德与仁,故不足依据,故但曰游。”[6](P2482)刘宝楠对这一评断的批评是非常有力的:“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故周公自称‘多艺’。夫子言艺能从政,而以为不足据依,亦异乎吾所闻。”[7](P257)这就是说,知识系统与道德系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质,将两者进行价值比较不合于孔子的本意。
孔子虽然认肯知识系统与道德系统之分立,但更为看重二者之间的内在融通性。至于这种融通性的内涵,后儒的观点大体上不外乎两种:其一,视二者为不可分割之整体②钱穆先生认为,“孔门之学有其相通、有其层累,心知其意,则一以贯之,固不必一一为之分划割绝也。”又:“学之必博,而博之必能反于约,而为己、据德之学之亦不可舍乎游艺、博文以为学矣。”参见钱穆:《孔子与论语》,81~8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其二,“六艺”为“道德”之用。[8](P172)这两种观点皆有其合理之处,然而,如果着眼于二者的交互关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这种融通性。所谓交互关系,即“艺”(知识系统)与“道”(道德系统)的相互依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艺”为“道”之载体。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博学”的内容即上文所云“六艺”,“仁”在此处则为“道”之指称。③郑玄注“仁”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参见《十三经注疏》,16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所谓“人偶”,焦循解释道:“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又:“能行人恩者,人也。人与仁合而言之,可以谓之有道也。”(参见焦循:《孟子正义》,977~97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如前注,朱子注“道”为“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推而可知,当“道”、“德”、“仁”并用时,三者各有侧重;当“仁”单独使用时,亦可指称“道”,作人道解。所谓“仁在其中”隐喻了一种“艺以载道”的“学”之路向:道德之内容与精神渗透融化于“六艺”之中,“六艺”不仅是单纯的知识之学,同时亦为道德之学的载体。后儒以“道艺”连文,实是对“艺”之载体作用的阐发。④郑玄对于“艺”有一个重要的用法:“道艺”。刘宝楠进一步解释道:“‘艺’所以载道,故注‘道艺’连文。”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那么,以实用知识为主体的“六艺”何以承载道德传播的功能?以《诗》为例,孔子在教人学《诗》的同时表达了“道在《诗》中”的观点: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孔子将学《诗》的意义依次排序为修养性情、弘扬人道、广博知识。前两者皆涉及道德之学,最后才是知识之学。在此,孔子价值天平的倾斜是很明显的:《诗》的道德传播意义已经超过了知识传授功能。另一则资料亦可为之佐证: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马融曰:“《周南》、《召南》,《国风》之始。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纲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为,如何向墙而立。”[9](P2525)概言之,《周南》、《召南》的主旨并非仅仅是教人“能言”,而是着重于传播人伦日用之道,其道德载体意味是非常明确的。此外,“六艺”中的礼、乐、射、御、数皆贯通了“道”之内容,如朱子所云:“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10](P94)应当说,这种“艺以载道”的思路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内容特质上看,“六艺”不但易于理解与操作,而且具有即时可见的实际效应;相形之下,道德规范则抽象而空洞,且缺乏直接的实际效用。因此,以生动直观的“六艺”作为道德规范之载体,便可以使抽象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日用知识,不但可以激发“学”之积极性,亦可以提升“学”之总体效果。
“艺以载道”还另有一层深意,即“道”对于“艺”之反向作用。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句话一方面表述了礼乐之于仁的载体作用,另一方面则阐明了仁之于礼乐的意义所在,而后者显然是重点。以孔子的观点,礼乐的存在价值不在于外在的仪式与器物,而在于其中是否承载了仁之内涵与精神。如果缺乏道德内涵之支撑,礼乐便会沦落为失却意义的符号与形式,如黄式三所云:“夫失其义陈其数,虽礼乐,一曲技也。”[11](P172)从字面上看,孔子似乎是专就仁与礼乐之关系而言,但深究下去,其实可以将之归为对“道”与“艺”关系的阐发,是以“道”作为“艺”之旨归。关于这一点,从孔子对仁知关系的阐述中可以寻到佐证: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
所谓“知及之”,刘宝楠的解释是“政令条教足以及民也”。[12](P638)而所谓“政令条教”即君子立身所恃之“艺”,此语当指君子经由“六艺”之学后对经世之道的理论认知。推而可知,“知”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以“六艺”为主体内容的知识系统。孔子认为,理论认知与治民理想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而“仁”则是消弭这种距离的中介。所谓“仁不能守之”,意谓以“仁”(人道之概称)作为“知”(“六艺”)之内在支持,如此,“知”的价值归依便不再是单纯的理论认知,而在于彰显“仁”之内涵与精神。仁知统一,君子便可有效地将理论认知转化为治世之方;仁知分离,则“知”必然丧失其存在价值,不能成为君子立身处世之所恃而发挥功用,即如朱子所云“无以有之于身矣”。[13](P167)显然,仁知关系即“道”与“艺”之关系,亦即仁与礼乐之关系的提升。
“道”与“艺”的交互关系表明,知识之学与道德之学实为内在融通之整体,许白云认为二者“不可全然做两段看”当是就此而言的。[14](P445)孔子如此打通“学”之两大内容体系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从知识之学中开辟出道德之学的途径,在知识与道德的交融中突出道德之学的主体地位,并由此使知识之学获得应有的价值支撑。但是,此种融通性并不能掩盖二者间的分立关系,知识系统与道德系统各有其独立性与自足性,不可以相互取代,特别是以后者取代前者,二者只能在分立的基础上融通。由是,即便是以“艺”为“末”之朱子亦承认不可以德行一科取代其余三科,应“自就逐项上看”。[15](P1010)
二、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共存与选择
《宪问》中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与“为人”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之价值目标:所谓“为己”,即对自身德性的追求,所求在内;所谓“为人”,即对身外名利之追逐,所求在外。如钱穆先生所云:“孔子所谓为己,殆指德行之科言。为人,指言语、政事、文学之科言。”[16](P374)这两种目标与前述“学”之两大内容体系是相对应的:“为己”是道德之学的直接目标,意在弘扬道德价值;“为人”则是知识之学的直接目标,意在追寻知识价值。由是,所谓“为己”与“为人”之议论,其实是孔子关于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如何安顿的思考。孔子虽然仅此一论后再无明确的议论,但这种思考却贯通于其“学”论中。
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为己”与“为人”是两个相对立的目标,孔子提倡前者而反对后者。①代表性的观点如钱逊先生的评判:“孔子是提倡‘为己’,反对‘为人’的。这是孔子教育的一个基本思想。”(参见钱逊:《孔门“为己之学”》,载《孔子研究》,1991(2))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多为以“为己之学”为中心的阐发,而“为人之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被作为批判之对象。本文认为,这样的评判不免流于草率。在孔子那里,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虽然存在对立性,但是这种对立并不具有对抗的意味,亦不能据此而否认二者的共存关系。
孔子对于道德价值(“为己”)的认同已是共识,需要解释的是其对知识价值(“为人”)的基本态度。《泰伯》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所谓“志于谷”,即“为人”,以谋求功名利禄作为“学”之目标①朱熹注:“谷,禄也。至,疑当作志。为学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1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所谓“学”,着重指以“六艺”为主体内容的知识之学。孔子说“不易得”,一方面是感慨常人为学之志小,另一方面又肯定了凭“六艺”立身进仕的必然性与正当性。因此,孔子并没有将“为人”排斥于“学”之外,而是将其作为知识之学的直接目标,在对“为人”的认肯中给予知识价值以应有的地位。此外,子夏的一段话亦可视为孔子的补充:“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孔子一生都在寻求施展政治抱负之平台,对于“仕”的向往是很强烈的,自然不可能否认知识价值的实用意义。如此,“为己”与“为人”、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实为一种共存关系。而今人将这种共存关系误解为对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宋儒理学派的影响。朱子认为:“圣人教人,只是为己。”[17](P243)如果说朱子只是偏向“为己”之一端而贬抑“为人”,那么,何坦则直接将二者对立起来:“为己之学,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为人之学,徇人至于丧己,逐末而不知返本也。”[18](P3)此种对于圣人的曲解虽意在推动理学的发展,然而不免有误导后人之嫌。
值得注意的是,此种共存关系并非意味着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分立,而是指在确认目标层次序列基础上的内外相成关系。《卫灵公》中有一段话: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所谓“谋道”,即以道德价值的追求为“学”之目标;所谓“谋食”则与“志于谷”相类似,即以知识价值的追求为“学”之目标。孔子所云“谋道不谋食”并非是对“谋食”的否定,而是意在两者的价值比较之中确定目标的层次序列。孔子认为,“谋道”既是一个源目标,又是一个终极目标,而“谋食”则是在“谋道”基础上的衍生性目标。因此,所谓“不谋食”,意即不必、亦不当以“谋食”作为“学”之终极目标,因为“谋食”是依附于“谋道”这一终极目标的。换言之,在对“谋道”的追求中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谋食”之目标,此亦即“学也,禄在其中”之谓。
反向视之,“学也,禄在其中”的另一层含义是:“谋食”虽为一个衍生性目标,但是亦能为“谋道”提供一个畅遂之所。孔子肯定“谋食”,一方面是对社会现实的回应②春秋之时,学人大都以求禄作为“学”之追求,子夏所云“学而优则仕”及《为政》所载“子张学干禄”就是这种现实的写照。,另一方面则是期冀借助于禄位更为有效地推行道德理想,使“谋道”落实于“谋食”之中,不至于被悬置在半空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由是,在孔子那里,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内外相成而趋于统一,此种统一性获得的前提是对目标层次的确认,即以道德价值作为知识价值之正当性获得的依据,坚持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为己”与“为人”、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是一种共存关系。
但是,此种共存关系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状态。孔子清醒地认识到,在具体的境遇中,道德价值之终极意义不可避免地会遭受质疑与背弃,共存关系总是被现实无情地打破。孔子与子张之间有一段对话: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所谓“言寡尤,行寡悔”关乎道德价值追求,孔子以此作为获得功名利禄的前提与基础,这显然是对前述“学也,禄在其中”的进一步阐发。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看,孔子此语亦是对古时选贤之法的解释。③刘宝楠曰:“古者乡举里选之法,皆择士之有贤行学业,而以举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禄之道。”参见刘宝楠:《论语正义》,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而子张之问并非完全不解古法,更多的是出于对现实的焦虑与疑惑。据刘宝楠的分析:“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世卿持禄,贤者隐处,多不在位,故郑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禄。”[19](P63)孔子本人便是“寡尤、寡悔有不得禄”的真实写照。由此看来,“禄在其中”并非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取决于现实境遇。当具体的境遇能够认同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时,“禄在其中”便能够成为现实,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统一亦具有必然性;反之,当具体的境遇不能认同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时,“禄在其中”只能是一个虚幻的理想,由于知识价值不能从道德价值那里获得支持,二者便由统一走向了分裂。
在前一种境遇中,由于不存在价值对抗,对道德价值的坚守并不会使人产生心理冲突,但亦不排除一种可能:由于“禄在其中”的诱惑,道德价值会沦丧为一种工具性目标而失却其终极意义。①《孟子·告子上》云:“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此即是对以“为己”为工具性目标的现实描述。然而这并非孔子讨论的重点,真正使他担忧的是,在后一种境遇中,学人会因为看不到“禄在其中”的功利性结果而放弃对道德价值的坚守。这样一来,对知识价值的追求便由一个衍生性目标上升为终极性目标,从而导致了两种价值目标的对抗。他设想了三种具体的对抗情境,要求学人无条件地选择以道德价值的追求作为“学”之终极目标。
其一,当“天下无道”之际,在守道与求禄之间的选择。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所谓“天下有道”,即前述之第一种境遇,无须作出价值选择;所谓“天下无道”,即前述之第二种境遇,由于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对抗,只能在二者之间作出一种选择。坚持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则安贫乐道而德性长存;以知识价值作为终极追求,则利禄可得而德性不存。孔子认为,在此种情境之下应“守死善道”,以“富且贵”为耻,固守“为己”之目标,不以道德价值的沦丧作为谋求利禄的代价。
其二,当生存遭遇困境之际,在守道与生存之间的选择。《卫灵公》中有一段记载:“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路之问是有缘由的。如前所述,孔子曾经说过:“学也,禄在其中矣。”子路认为,此言对于解释当下的生存困境并不具有说服力。究其实质,一方面,子路是曲解了“禄在其中”的内涵,将孔子所云之理想状态视为一种必然的结果;另一方面,子路一行面临着“学而不得禄”的困境,此时守道与生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求生的欲望使得子路对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产生了怀疑。孔子及时地纠正了子路的错误,认为一个对德性有期望、有到达的君子即使是面临生存的困境,亦不应该放弃对道德价值的坚守;如果转而向生存目标妥协,则意味着以知识价值取代道德价值的地位,如此便颠覆了“学”之目标的层次序列,其后果是严重的:君子与小人的身份秩序将在道德理想的迷失中被完全消解,而身份秩序所代表的社会秩序亦将由此趋于混乱。
其三,在面临成名的诱惑之际,在守道与求名之间的选择。在“学”之目标设定中,常人不免有对成名的渴望。孔子并没有否定求名的正当性,认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但同时又为求名设置了一个限定条件:“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意即身外之名唯有在内在德性的支持下才能获得价值认同。然而,现实的境遇往往使守道与求名之间存在着价值冲突,这就要求学人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至于应当如何选择,孔子在多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
这三句话虽在表述上有差异,但内涵却是一致的。所谓“己知”,即“名”为人所称道;所谓“知人”与“能”相通,即德性与才能的完美统一。孔子虽未明言“学”,但实为阐释“学”之价值目标选择。“己知”所求在外,以知识价值的追求为“学”之终极目标;“知人”所求在内,以道德价值的追求为“学”之终极目标。孔子认为,当二者面临价值冲突时,应当放弃对“知人”的追求,选择以“己知”作为“学”之终极目标。
孔子提倡“为人”而反对“为己”,当是指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对立状态下的价值选择而言。这种对立虽然并非孔子的理想状态,但却是不争的现实情状。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在确认序列层次的前提下,将知识价值的正当性构筑在道德价值的基础上,坚持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以此避免“学”之目标导向在社会现实的冲击下误入歧途。
三、知识接受与德行训练的权重与互动
如前所述,孔子的理想目标是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共存。依此目标,学人不但能成就德性,亦能在此基础上立身济世。如此,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皆有安顿之所。那么,如何才能使理想目标转化为现实?孔子认为,知识接受与德行训练是“学”之过程的两个重要环节,对二者之间关系的正确把握是实现此种转化的关键所在。
所谓知识接受与德行训练,在孔子那里分别对应于“学文”与“行”。《学而》中有一段话: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所谓“行”,注家们在这里并无特别的解释,但邢昺在别处释之为“德行”。①《论语·述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邢昺疏:“行为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48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此种解释虽然不无道理,但这两个范畴之间并非完全的等同关系。由前述可知,所谓“德行”,在孔子那里是指道德之学。孔子为何不单言“德”而以“德行”并称?郑玄与邢昺的解释是一致的:“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20](P730)朱熹亦云:“德行,得之于心而见于行事者也。”[21](P1010)可见,德不仅是存于内心的道德律令,亦是一种实践理性。孔子以“德行”并称,意在阐明“德”之特质,明确德与行之内外合一的关系。由是,“德行”只能表达一种特质,表明“行”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而不能指称具体的行为过程。“行”则不然,“行”偏重于“德”之外在践履,强调“入则孝,出则悌”等具体道德行为的施行。由于此种施行具有反复持续的特点,“孝”、“悌”、“信”等美德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得以强化,因此,“行”其实是一种德行训练过程。而所谓“学文”,即以“六艺”为主体的知识之学,亦即知识接受过程。孔子的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
其一,知识接受与德行训练之间应有所侧重,以此凸显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非仅仅是阐释了“学”之先后次序,亦明确了“行”之于“学文”的相对重要性。如前所述,“六艺”的主旨在于“艺以载道”,而“六艺”皆为可操作的实用知识,相较于“德行”而言,其实践意蕴更为直接与明显。只有在“行”的推动下,“六艺”才能发挥“载道”的功能。舍去“行”之环节而专注于“学文”,仅仅是解决了对于道德的理论认知问题,距离“学”之终极目标——德性养成还有相当的距离,如邢昺所云:“若徒学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则为言非行伪也。”[22](P2458)反之,专注于“行”而舍去“学文”,虽有“质胜而野”之嫌[23](P49),但却能为德性养成提供直接的支持。关于后一点,子夏说得很明确:“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学而》)此处所言之四德,皆是从“行”上讲。以子夏的观点,“行”可以由天生的美质而引发,无需经由“学”之环节。此言虽有废学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经由“行”这一德性训练环节,外在的道德规范可以自然地转化为内心的道德律令,直接促成德性养成目标之实现。孔子所云“学文”虽是子夏所云“学”之一端,但二者的内在意蕴是相通的。由是,德性训练与知识接受这两个环节虽不能以“本末”而论,然实有轻重之分。此种权重旨在突出道德价值目标向现实转化的优先性与重要性,这与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是相呼应的。
其二,知识接受与德行训练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知识价值与道德价值由此而皆有所归依。孔子虽然强调“行”的相对重要性,但并未如子夏一般认为“行”可脱离“学”而自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另一层含义是:知识接受与德行训练同为“学”之环节,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一方面,知识接受是德性训练的内在支持。知识接受过程同时蕴涵了“道”与“艺”之接受,推而可知,由此不仅可以掌握知识与技能,亦能够提升对于道德的理论认知。那么,理论认知对于“行”的意义何在?孔子在《阳货》中对此做了深刻的阐释: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这段话列举了与六行相关的六蔽,其共同特征是道德行为与道德内涵相背离。孔子认为,造成六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好学”,即徒有对于道德的经验感知而缺乏对道德内涵及其必然性的理论认知,如此则使德性训练由于无法获得正确的理论指导而流于偏失,最终必将消解其对于德性养成之作用,如钱穆先生所云:“但专重德行,不学文求多闻博识,则心胸不开,志趣不高,仅乡里一自好之士,无以达深大之境。”[24](P10)“好学”虽亦蕴涵道德之学在内,并非单指知识接受,但是亦可从中体悟“学文”之于“行”的意义所在。由是,德性训练虽然可独立于“学”之外,然而孔子却郑重地将之归为“学”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用意是很明确的:通过知识接受过程提升德性训练的境界与效用,以知识价值推动道德价值。
另一方面,德性训练是知识接受的最终落实处。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学而》)所谓“重”,指“重言、重行、重貌、重好”。所谓“威”,指“威仪”。[25](P21)合而言之,“重”、“威”皆与礼仪举止相关,当指“六艺”在日常生活中的践行状态。推而可知,此处所谓“学”,主要是指知识接受。孔子认为,经由知识接受而达成的理论认知只有落实到德性训练中才能获得价值归宿,此种落实不但可以促使“道”得到价值认同而实现向内之转化,亦可为“艺”寻求到安顿之所。
孔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此语是对“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进一步阐释,不但使知识接受与德性训练的双向互动关系得以明确,亦隐设下一个问题:实现此种双向互动的推动力何在?《述而》中的一段话给出了答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结合前文来看,作为美德的“忠信”之学当是涵容在“学文”与“行”之环节中,如朱子所云:“不是当学文修行时,不教之存忠信。”[26](P894)那么,孔子何以又将二者从“文行”中抽出来单独强调?深究下去,此言的重点并非是解释“学”之先后次序,而在于“文行”与“忠信”之间关系的辨析。所谓“忠信”,邢昺认为:“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27](P2483)以此来看,“忠”与“信”是两种具有共通性的美德,二者共同指向于内心之“诚”。这一点在朱子的解释中尤为突出:“蕴之于心无一毫不实处,方是忠信。”[28](P894)由此,“忠信”对于“文”与“行”的意义便非常明确了:相对于“学文”,“诚”包含了对美德的诚心向往,要求学人于致知尽心尽力而有所成;相对于“行”,“诚”含有内不欺于心、外不欺于人之意,要求学人于美德之躬行持久而无所懈怠。若缺乏这个“诚”字,学人于“文”则无法深入,于“行”则不能坚持,其后果是:理论认知不足以指导德性训练,德性训练亦不能使理论认知得以巩固与内化。唯有心存“忠信”,“学文”与“行”才能达到自身的圆融而具备彼此支持的基础。程子云:“忠信,本也。”[29](P99)此言道明了孔子的立场:以“忠信”作为“学文”与“行”双向互动的基点,最终推动“学”之两个层次的目标向现实转化。
综上所论,孔子在对于“学”的思考中将知识与道德做了合理的安顿,虽然其价值天平倾斜于道德,但绝无轻视、否定知识之倾向。尽管孔子所云“六艺”中并没有太多科学理性的成分,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人类理解力的局限,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遗憾的是,在后儒那里,孔子的思想被片面地加以取舍,以道德取代知识成为“学”之主流。张载虽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之分,但后者的境遇如牟宗三先生所云“没有得到正视”。[30](P103)于是乎,知识价值被淹没在对道德价值的过度张扬中,这就引发了近代以来对于儒家文化阻碍科学理性的批判。现代新儒家试图建立一种道德的知识学、以内圣开出外王(民主与科学)的观点,其实是在孔子基础上的深化与发展,并没有偏离孔子思想的基本路向。由是,还原孔子思想的本来面目,不但有正本清源之功效,亦可以为摆脱当下的道德教育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路。当前,以道德取代知识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相反,道德已经让位于知识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在不同层次的教育过程中,由于对“为人”目标的推崇,知识与道德的融通性遭到人为割裂,道德价值的终极意义正在被知识价值逐渐消解。针对此种偏蔽,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孔子那里,反思知识与道德的安顿之所。
[1][30]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刘述先:《儒家传统对于知识与价值的理解与诠释》,载《社会科学评论》,2004(1)。
[3][5]钱穆:《孔子与论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
[4][10][13][23][2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6][9][20][22][2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3。
[7][12][19][25]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
[8][11]黄式三:《论语后案》,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4]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17][21][26][2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2007。
[16][24]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8]何坦:《西畴老人常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