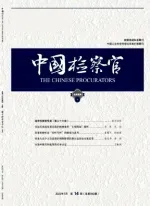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的认定
2010-08-15裴广川
文◎裴广川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的认定
文◎裴广川*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10年5月7日所作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10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在5000元以上的应当追诉。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公布以来,在司法界和学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的认定,一直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这些模糊认识直接影响对这一类案件的追诉。基于此,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就这一问题谈谈本人的一孔之见,以供大家参考: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概念及其演变
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第八条分别对刑法第163条和第164条作出修正,将原条文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应如何准确表述这一罪名,起初存有不同认识。第一种意见认为,对刑法第163条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应当采用“商业受贿罪”和“商业行贿罪”罪名,本人认为这样的表述也不够准确。因为“商业”二字不能准确概括刑法罪状规定的情形,因为这类犯罪主体的身份不一定都属于商业性质,其受贿或者行贿行为也不一定都发生在商业活动中,况且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对商业贿赂尚无统一明确定义。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采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罪名。本人认为这样表述虽然直接反映了刑法罪状的规定,但由于是选择性罪名,可能出现“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或者“对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罪名,从字面上不好理解,所以这一表述不够周延。第三种意见认为应采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罪名。最后两高的司法解释采用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罪名,这样一来,刑法第385条受贿罪的主体和第389条行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刑法第163条、第164条规定的受贿主体是“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这后两条的犯罪主体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非国家工作人员”。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国关于对商业贿赂犯罪惩治的历史。在1979年的社会背景下,当时商事主体基本上都是国家干部,因此,1979年刑法没有商业犯罪的规定。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首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这是商业贿赂构成犯罪首次见之于法律法条。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受贿罪。”这是刑法上首次规定商业方面的贿赂罪。最高人法院在1995年发布在《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构成商业受贿罪。”从此,在我国刑法上正式确立了商业受贿罪的罪名。
1997年修订的刑法吸收了上述单行刑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之外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在规定了一般行贿罪之外,规定了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将这两个犯罪修正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直到2007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确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罪名,取消了公司、企业受贿罪的罪名。自此,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罪名正式统一适用。
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将商业贿赂罪规定为八个罪名。同时这个司法解释还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和一部分非从事公务的人员从受贿罪的主体中分离出来,将刑法所规定的受贿罪中的“职务之便”,仅限于履行国家公务之便。自此,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资格有了明确界限。
二、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的区别
《刑法》第385条的规定的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以受贿论处。根据这一规定,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即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区别,目前在学界普遍倾向“公务说”,即将是否执行公务作为区分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唯一标准,但本人认为这种片面强调公务的观点不够准确,应将“身份”和“行为”两者统一起来进行判断。
我国《刑法总则》第93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从事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其中就既包含了身份特征,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也包含了行为特征,即“从事公务”。这就是说,受贿罪的行为主体既要求具有“身份”特征,即“国家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同时也要求具有“行为”特征,即“从事公务”。也就是说,只有既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又是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才可能成为受贿罪的主体。据有人统计,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真正有可能成为受贿罪犯罪主体的工作人员只可能占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数的50%左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人们往往只注意了行为人的身份特征,而忽略了行为特征,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
《刑法》第93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同时也是坚持了“身份”和“行为”特征的统一。对于身份特征的表述是“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对于行为特征的表述也是“从事公务”。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也应该坚持其 “身份”和“行为”的统一,其身份特征表述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其行为特征表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概括为“从事公司或单位业务”。
上述分析说明“公务说”是比较片面的,认定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应坚持“身份”和“行为”两个特征的统一,这样才能正确体现立法原意。
三、非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资格法律效力范围的辨析
在司法实践中,坚持“身份”和“行为”相统一来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主体资格,遇到有关法律效力范围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规定,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问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依法组建的评价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中国家机关或者国有单位的代表有上述行为的,按照受贿罪定罪处罚。在评标活动、竞争性谈判采购以及询价采购活动中从事完全相同的工作,由于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是从事公务,即构成受贿罪的主体。而不具有该种身份,其行为又不是从事公务,只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
如果用“公务说”来分析这一司法解释,就出现了同样是从事“公务”却构成了不同罪名的情况,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以“身份”和“行为”相统一的观点来分析,则很容易理解。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为维护国家利益或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的而参加招投标活动,因此,在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他们从事的是公务。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这些活动是为了非国有企业或者单位的利益,因此在这些活动中所维护的是非国有企业或者单位的利益,在招投标等活动中,他们从事的不是公务,如果他们有受贿行为就只能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由于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了“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将凡是有人大代表的身份、陪审员身份、基层组织人员都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准国家工作人员,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把准国家工作人员都列入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主体的范围,也有失偏颇。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就贪污贿赂罪的主体和渎职犯罪的主体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刑法》第93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具体人员包括: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
上述内容的表述已经明确了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被认定为受委托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时必须同时具备“身份”和“行为”两个条件。如果将两个条件割裂开来,就会将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主体范围无限扩大。只有坚持“身份”和“行为”相统一的标准,我们才能对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的主体范围作出正确的判断,如从工人、农民或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中推荐或者选拔的人大代表、陪审员或者村委会、居委会的基层组织人员,在他们履行公务的过程中,如果受贿就应当定受贿罪。如果不是在履行公务的过程中,而是在履行公司、企业业务或财务过程中收受财物的则应当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于“公务”的概念,学界的通说是指具备法定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行为或者国家权力派生的行为。我国修正后的刑法第93条所指的公务是指国家公务,其他公务已经排除在外。人大代表、陪审员、村委会、居委会基层工作人员,他们在履行由国家行为或者国家权力派生行为的过程中,如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行使法律赋予的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人民陪审员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审判权,村委会、居委会的基层工作人员行使协助乡镇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权利的时候,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此时他们才是准国家工作人员。换言之,如果他们只有上述身份,而没有履行公务的时候,他们也就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此时他们受贿就不能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应该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三)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效力范围的限制
任何事物都会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时间是指产生、发展、消灭的过程所在的时间段,空间是指事物在某种客观物质条件下产生、发展、消灭的环境。我国《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是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这仅仅是一种过渡性的规定,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规定就会被废止,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会在我国刑法中长期存在下去。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主体资格的认定,我们必须首先细致的研究其具体受贿行为发生时的时空状况。确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要根据犯罪行为发生时是否正在被委派从事公务,而不应根据历史上是否有过被委派或被委托从事公务来判定。
没有国有股份的企业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经理,他们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管理的是企业的业务,属于公司业务范围,不属于国家行为或国家权力派生的“公务”的行为,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不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93条的规定,对这类人员在履行本职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受贿行为应当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来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本文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资格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希望在司法实践中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资格的认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人深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题目,因此,本文疏漏再所难免,希望业内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10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