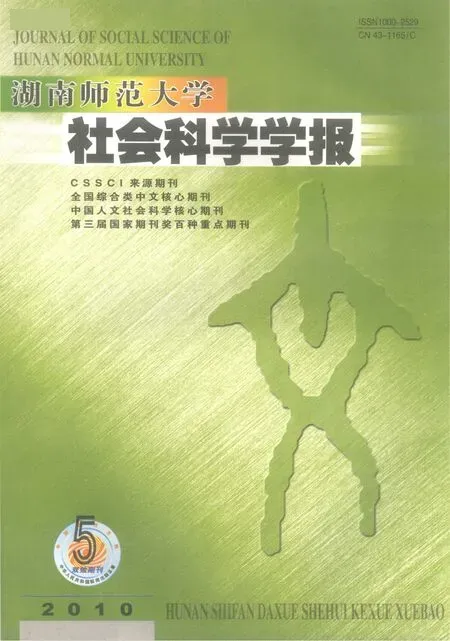唐代话本小说娱乐功能探析
2010-04-11陈怀利樊庆彦
陈怀利,樊庆彦
(1.贵州凯里学院 中文系,贵州 凯里 556000;2.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唐代话本小说娱乐功能探析
陈怀利1,樊庆彦2
(1.贵州凯里学院 中文系,贵州 凯里 556000;2.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唐代话本小说的产生与民间艺人的“说话”和寺庙僧人的“俗讲”、“转变”等说唱技艺密切相关。这些说唱艺术满足市民娱乐,成为广泛流行的通俗文艺形式。而其本身所带有的娱乐功能也同样影响着唐代白话小说的娱乐功能。因而,这时期的白话小说由文人化向世俗化转型,呈现出与文言小说较为“雅化”的娱乐功能殊为不同的情趣。
唐话本;“说话”;“俗讲”;“转变”;娱乐功能
人类创造文学,是因为文学对人类有积极作用。文学的功能就是探讨文学对社会、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影响与作用问题。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属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有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学的功能是多元的,要而言之,是娱乐和教育两大功能。娱乐功能则主要分两个层次,低级的层次是快感,高级的层次是美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同样教育功能也包含思想、道德、知识等多个方面。而且,越是优秀、成熟的作品,诸种社会功能越是结合得紧密而恰切。而在诸种文体中,因为小说本是供人们茶余饭后休闲消遣的读物,它的基本层面是故事,首先要以故事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因而小说的娱乐性尤为突出。
但小说自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不同时期、不同文体的小说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娱乐特点。中国古代小说最初是以文言的形式出现的,因而其娱乐功能较为“雅化”,表现出一种内容“奇幻”、情趣“高雅”却又语言“谐谑”等相互融合的特征。伴随着文言小说的发展,大约自唐代开始,小说创作领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在民间艺人的“说话”和寺庙僧人的“俗讲”、“转变”等艺术的基础上产生的白话小说。这些说唱形式本身所带有的娱乐功能也同样影响着唐代白话小说的娱乐功能。因而,这时期的白话小说由文人化向世俗化转型,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与文言小说大异其趣的娱乐功能。
一
白话小说的产生与中国的说唱技艺紧密相关。“说话”是唐宋元明一直存在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故事之腾于口者,谓之‘话’。取此流传之故事而敷衍说唱之,谓之‘说话’。艺此者,谓之‘说话人’。”[1](P29)“说话”即叙说故事,“话”即故事,是叙说的内容。说故事可谓源远流长,劳动之余休息时说故事就是一种很好的消遣手段。唐以前,以“俳优小说”为代表的“说话”,主要是为宫廷和社会上层服务的滑稽娱乐,以短小的谐趣故事和议论逗人笑乐,有时也暗含讽喻。王公贵族有时也说故事讲笑话以自娱,《三国志》裴注有记载说曹植曾“诵俳优小说数千言”①。而“说话”作为一种技艺为人表演,现在所知最早的记录是《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侯白《启颜录》:“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遇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启颜录》是一部笑话,侯白所讲内容与其后的说话有差异。但是,“话”的语义相同。最早出现“说话”一词,见唐代郭《高力士外传》。传中有云“:太上皇移杖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自扫除庭院,芟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另外,诗人元稹《元氏长庆集》中《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的诗句,其自注云:“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②可见这时的“说话”也是以逗趣取悦为主,但已经向长篇故事转变,而且还主要属于贵族官僚、文人墨客的娱乐方式。
但是“说话”成为民间娱乐,却是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的事。中唐以后,城市商业经济飞速发展,人口集中,既有贵族、官僚、豪商富贾等上层居民群体,也有为这些人服务的庞大的市井居民群体。市井居民群体的谋生途径、生活方式、理想情趣,乃至审美观点等等,均有自己的特点与要求,与贵族、官僚有所不同。此时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市井群体在紧张的劳作之后,为了娱乐,得以消遣,就要寻求能适合自己口味、表现自己思想感情的文艺活动,而内容通俗、演出简便、既能反映社会现实、又能排忧解难、陶冶情趣的说唱艺术,往往就受到他们的青睐。
因而,为满足市民娱乐需求的戏曲、说唱等民间艺术成为广泛流行的通俗文艺形式。唐代长安有东西二市,本是商贸之地,后又成为群众性的娱乐场所。而当时活动与市场,从事营利性表演的民间艺人,则被称为“市人”。而“市人”表演的“说话”技艺,即“市人小说”或称为“人间小说”,也就是艺人说书,其间夹杂着逗趣搞笑成份③: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与‘褊’同声,云世人皆误。”余意其饰非,大笑之。④
且他们还被富贵官宦人家邀入私宅表演,又如:
唐营丘有豪民……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⑤
上述资料表明此时说话艺人已经职业化。而在这伶伦百戏之中也应包括有“市人小说”。元稹在白居易寓所新昌宅听艺人“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能够演说如此长的时间,也应该属于民间职业艺人的演说故事。
但这些职业说话艺人更多的时候还是在街市上演出,从李商隐《骄儿诗》中也出现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表明“说话”还是普通市民的娱乐方式。而且,“此前处于时隐时现的说唱表演,出现了独具特色相当成熟的表演形式,取材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走出宫廷贵族、官僚豪家之门,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和庶民大众。此时已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演出场所和演出时间,有了以演出为谋生手段的专业演员,有为了娱乐消遣观看演出的一批观众,有了一批可供演出时用的成熟底本,演出有了一定的程式。”[2](P106)而说话艺人为便于讲说参考或师徒传授,或有爱好者为之记录,于是便出现了用文字将“说话”所讲的故事记录下来的底本,这种底本称之为“话本”,由此标志了白话小说的诞生,于是也就表明了其娱乐功能的诞生。
二
美国汉学家韩南先生认为:“唐代白话文学与佛教的关系密切……佛教和民众娱乐的关系很密切,唐代寺院往往也是民众娱乐的中心。两方面的因素必然推进白话文学的发展,也会刺激那些原已存在的世俗口头文学的发展。”[3](P6)佛教在传入中土后,为扩大其影响必然要进行宣传。⑥唐代寺院本已设有戏场,并有百戏演出,成为当时市民观看表演的娱乐场所。⑦但深奥难懂的佛教经义对于文化水平甚低乃至完全不识字的普通百姓来说仍是个巨大的障碍。为了“至使人主临观”⑧,就需要一种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在“为一笑之乐”的同时让最大多数人了解经义。“俗讲”就是寺院僧侣为宣讲佛经教义和故事所创造的一种说唱艺术。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化缘集资。⑨正如元代学者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唐纪·敬宗纪”宝历二年六月“观沙门文淑俗讲”条所指出的:
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⑩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4](P95)
俗讲的一种主要形式就是“转变”。而“转变”的底本就是变文,“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佛诸菩萨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⑪“变文”实际上是一种说唱结合的长篇故事,它以浅近文言说白,七言诗句演唱,加以俗讲僧人生动形象的表演:
导师则擎炉慷慨,含吐抑扬辩出不穷言应无尽。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感则洒情含酸。⑫
很容易打动人心,为民众接受:
四众专心,叉指缄默……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锺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人迫怀抱载盈恋慕。⑬
因而遇到有俗讲活动,则“百千民拥听经座”⑭:
远公入寺安居,约经数月,便有四远听众,来奔此寺……前后一年,听众如云,施利若雨。⑮
唐姚合亦有诗云:
一住毗陵寺,师应只信缘。院贫人施食,窗静鸟窥禅。古磬声难尽,秋灯色更鲜。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赠常州院僧》)⑯
无生深旨诚难解,唯是师言得正真。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听僧云端讲经》)⑰
俗讲僧人为迎合听众的需要,也在原有所讲经文的基础上,加入世俗故事,增添娱乐成分,从而更加激发了世俗男女听经的激情:
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⑱
但因为寺院本身受场地限制,即使在如此盛大的场面下,只能采取限制人数的办法:
时愚(遇)晋文皇帝王化东都,道安开讲,敢(感)得天花乱坠,乐味花香。敢(感)得五色云现,人更转多,无数听众,踏破讲筵,开启不得……是时有敕:“若要听道安讲者,每人纳绢一疋,方得听一日。”当时缘遇(遇)清平,百物时贱,每日纳绢一疋,约有三二万人。寺院狭小,无处安排。又写远(表)奏闻皇帝:“臣奉敕旨,于光福寺内开启讲切(筵)。唯前敕令交纳绢一疋,听众转多,难为制约,伏乞重赐指挥。”当时有敕:“要听道安讲者,每人纳钱一百贯文,方得听讲一日。”如此隔勒,逐日不破三五千人,来听道安于东都开讲。⑲
这样仍会有大量的民众不能够到现场观听俗讲,就需要读本来供阅读,由“喜闻”而“乐见”,也必然地促发了变文书录本的产生。
而且,俗讲或转变对语言的初步革新,它的叙事规模和形式,都对以谐趣逗乐为基本特点的传统“说话”产生了影响,使“说话”也朝着通俗叙事的方向发展。二者之间逐渐发生了关系,孙楷第先生认为:“唐朝转变风气盛,故以说话附属于转变……宋朝说话风气盛,故以转变附属于说话,凡伎艺讲故事的,一律称为说话。”[5](P4)这种形式后来为民间艺人所接受,除寺庙外,还在民间娱乐场所演出,并走进私家府第,甚至深入宫禁。[6](P106-112)于是讲唱变文就从一种宗教通俗宣讲变成了大众娱乐形式,最后逐渐发展为白话小说的话本。⑳
三
依据敦煌石室发现的文献,唐话本现存《庐山远公话》、《韩擒虎画本》、《师师谩语话》三种。但由于变文与话本的本质勾连,二者应属于同一系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叫法,即使按照文体特征来衡量,当时题作“变文”或研究者拟题为“变文”的作品,其叙事方式也如同话本。因此,《降魔变文》、《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叶净能诗》等也可以话本视之。其他如《丑女缘起》、《晏子赋》、《燕子赋》、《孔子项托相问书》等不少以说(散文或骈文)为主的叙事作品,也可被看作话本。
为吸引读者,变文的创作者还对题材来源——原有经文中的佛传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常常在博采众经的基础上,进行择决、融汇、想象,以达到理想的艺术效果”[7](P23),使其更符合民众的审美趣味。如《破魔变文》写如来显神通降服魔王、魔女之事。孙楷第先生指出:“诸经记降魔事皆先举魔女,次举魔军,变文以魔军居前,次第稍异。”[8](P243)对此,傅芸子先生认为:“魔女惑乱世尊事,在释典中,本在魔王迫害世尊之前,变文乃颠倒次序用之,盖经变作者,想利用此种香艳性的材料,作为变文的结局,趣味浓郁,使听者忘倦也。又经典中,魔女惑乱世尊,亦较变文所写细致,如《普曜经》第六《降魔品》十八,魔女作态弄姿有三十六样。《佛本行集经》第廿七《魔怖菩萨品》,所写魔女的肉体美,文字都比变文所写为细致,我们反而觉得变文虽形貌朴俗而实恰到好处。”[9](P502)而且变文句式对仗,平仄协调,在均衡的对称美和抑扬顿挫的听觉美里,充分发挥了骈四俪六琅琅上口的特色,读来令人目眩神迷,受到感染,呈现出它的审美娱乐功能。
比较而言,“缘起”不再严格遵循讲唱经文的固定套式,而是选取佛典中故事性较强的段落加以发挥,或者依据僧传故事加以铺陈排比,补缀成说,目的当然还是通过此类故事,诱俗悦众,弘扬佛法。[10](P412)但由于突出了故事,因而“缘起”的文学性有所增强。《丑女缘起》又作《丑女因缘》,研究者认为其所叙故事是在《贤愚经·波斯匿王金刚经》所记载的故事基础上敷衍而成。与本经相比,《丑女缘起》不仅增加了夫人的活动,又增添了两个公主,还为丑女夫主添上王姓。而且在情节上更富有变化:夫人私下为丑女择夫,王郎成婚后发现受骗后忧愁怨怪,另两个公主劝慰之,待到王郎宴请诸官时,王郎惧妻丑陋难堪,丑女询问实情后,落泪而礼佛,旋即变美,王郎大喜。整个故事显现出浓郁的人情味,中间穿插着人物的心理变化,增添丑女因得知王郎为轮流宴请朝官却惧妻丑陋难堪后落泪礼佛变美这一故事情节,虽有不切实际处,但比起原经中丑女无缘礼佛来要显得更为有趣,且具体描写异常生动,如写丑女外貌“双脚跟头皴又僻,发如驴尾一枝枝”、“十指纤纤如露柱,一双眼子似木槌离”,“上唇半斤有余,鼻孔竹筒浑小”等等,语言通俗,俏皮生动,夸张诙谐,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也体现出艺术虚构的美学色彩。
其他如《孔子项托相问书》中写孔子出游,遇七岁项托,彼此问答,项托穷难孔子而为之作师。《晏子赋》写晏子使梁,因相貌极其丑陋,梁王欲辱之,屡次问难,但晏子机智善辩,巧为答词,应对自如,反使梁王自取其辱。都是源于民间传说的智慧型辩斗小故事,富有情趣。而《燕子赋》有似于寓言故事,用游戏笔墨虚拟了一场发生在燕子和黄雀之间的巢穴争端,后又彼此相安,犹如邻里间之争宅地,最后以和收束。《茶酒论》则采用对话体的形式,摹写茶酒争功,最后由水进行调解,虽颇似御前佛道二教论衡:水是皇帝的化身,用以提出论题和仲裁胜负,茶与酒则是佛道两教的化身,其任务是就皇帝所提出的论题进行答辩。[11](P28)但作品采用民间广为流传的争功题材,以拟人化的手法及通俗化的语言,与正统诗文的抒写对象颇不相类,风格往往带有谐谑特点,颇具民间趣味,表现出作品的娱乐性。
唐代话本小说的娱乐性与它的语言的通俗性有着莫大关系,作品撷取逸事趣闻,吸收有关民间传说,夸张渲染,不仅杂用俚语方言、谚语成语,还经常游戏笔墨,玩些文字游戏,大大增强了故事性与趣味性。如《伍子胥变文》中,伍子胥仓皇出逃,乞食竟入自家门,与妻室对起了“药名诗”:
其妻遂作药名(诗)问曰:“妾是仵茄之妇细辛,早仕于梁,就礼未及当归,使妾闲居独活……妾忆泪赤石,结恨清箱。夜寝难可决明,日念舌乾卷柏……”子胥答曰“:余乃生于巴蜀,长在藿乡,父是蜈公,生居贝母。遂使金牙采宝,支子远行……留心半夏,不见郁金。余乃返步当归,芎穷至此。”[12](P10)
虽然充满悲情,但作为俗文学,仍具有娱乐化倾向。
此外,唐话本开启了后世话本、章回小说的一些民族化艺术传统。如讲究故事的完整连贯,有头有尾、有条有理、脉络分明地叙述故事,清清楚楚地交待情节。而《庐山远公话》中讲述白庄抢掠、远公被劫为奴一节,《韩擒虎画本》中表现在朝廷上韩擒虎与任蛮奴争先锋一节,说明唐话本已注意讲究设置悬念,使故事波澜叠起,夭矫变幻,扣人心弦。话本还注意运用误会、巧合等手法,突出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和言语行动,随情节的展开来刻画人物,发展故事。如《秋胡变文》中桑园会一节,正是因为秋胡夫妻分别九年后偶然相遇而又不相识,在此巧合下发生了误会,引出了调戏与被严正斥责的冲突,表现了秋胡性格的卑劣丑恶,以及秋胡妻的忠贞高尚品格。这些体式特征已经成为后世小说所效仿的规范。因此,唐话本的娱乐性与文言雅化的唐传奇迥乎不同,而呈现出由文人化向世俗化转型的情趣。
注 释:
①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
②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19页。
③ 《唐会要》卷四《杂录》载:“元和十年……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
⑤ 《太平广记》卷二七五引王仁裕:《玉堂闲话》。
⑥ 印度古代也早有发达的说唱艺术,隋那曲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一三曾提到当地演于“戏场”的“歌舞”、“相嘲”、“漫话”、“谑戏”、“言谈”等,这些表演伎艺可能也随佛教传入中土。参见廖奔:《从梵剧到俗讲——对一种文化转型现象的剖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
⑦ 宋钱易《南部新书》戊卷谓:“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尼讲盛于保唐;名德聚之安国;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见《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0页。
⑧ 王 灼.碧鸡漫志:卷五。
⑨ 与俗讲相对而言的是僧讲。《大正新修大藏经》载日本僧人园珍所撰《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云:“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讲,安居月传法讲是。(不集俗人类,若集之,僧被官责)”。
⑩ 资治通鉴:第17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50页。
⑪ 孙楷第.读变文·变文“变”字之解.载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
⑫ 《高僧传》卷一三《唱导篇·论》,载《大正藏》第50册。
⑬ 《高僧传》卷一三《唱导篇·论》,载《大正藏》第50册。
⑭ 贯休:《蜀王入大慈寺听讲》,《全唐诗》卷八三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43页。
⑮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第四册《庐山远公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8页。
⑯ 姚合.赠常州院僧,《全唐诗》卷五○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60页。
⑰ 姚合.听僧云端讲经,《全唐诗》卷五○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71页。
⑱ 赵璽.《因话录》卷四“角部”。
⑲ 李时人.全唐五代小说:第四册《庐山远公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9页。
⑳ 王重民先生认为:“有说无唱的变文,实际上已经转化为话本。但较早的作品仍然沿用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是九四九年写本,若稍晚,也许改称为《舜子至孝话》了。《庐山远公话》是九七二年写本,若稍早,也许就题为《庐山远公变》了。为什么在名称上可以这样的转化,是因为在九七二年的时候,有说有唱的变文已经衰微,而话本的含义已转化成为讲故事的书本,由于这种新兴的文体,重说不重唱,所以话本便取变文而代之了。”见《敦煌变文研究》,载《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
[1]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2]姜 昆,倪锺之.中国曲艺通史:第三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美]韩 南.中国白话小说史(尹惠珉译)[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4]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5]孙楷第.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6]姜 昆,倪锺之.中国曲艺通史:第三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项 楚.敦煌文学丛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8]孙楷第.读变文·唱经题之变文[A].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傅芸子.关于《破魔变文》[A].周绍良,白化文.敦煌变文论文录[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0]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11]王昆吾.从敦煌学到域外汉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王重民.敦煌变文集:上册卷一《伍子胥变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An Analysis on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of the Tang Dynasty’s Scripts for Story-telling
CHEN Huai-li1,FAN Qing-yan2
(1.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Guizhou Kaili College,Kaili,Guizhou 556000,China;2.The Research Centre of China’s Ancient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ia 200433,China)
The emerge of the Tang Dynasty’s scripts for story-telling was closely concerned with the“telling”of folk artists and a technique consisting mainly of talking and singing like“popular telling”,“transferring”etc.of temple monks.These arts catered to citizens’entertainment and became a widely popular artistic form.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contained in it also influenced the entertainment function of the Tang Dynasty’s colloquial fictions.Therefore,the colloquial fictions at this period transformed from literatry circle to the popularized and showed a sentiment which was different to the“elegant”entertainment function of classical-Chinese fictions.
The Tang Dynasty’s scripts for story-telling;“telling”;“folk telling”;“transform”;entertainment function
I207.41
A
1000-2529(2010)05-0121-04
2010-01-05
陈怀利(1965-),山东莘县人,男,贵州凯里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山东大学访问学者;樊庆彦(1975-),山东鄄城人,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责任编校:谭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