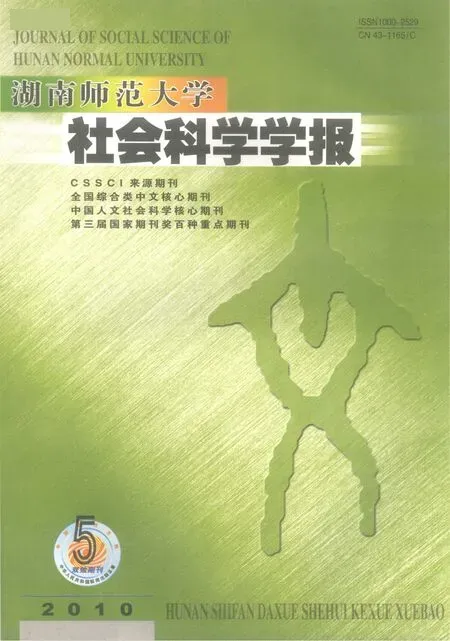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的意象生成观
2010-04-11张文刚
张文刚
(湖南文理学院 武陵学刊编辑部,湖南 常德 415000)
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的意象生成观
张文刚
(湖南文理学院 武陵学刊编辑部,湖南 常德 415000)
在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建构中,就意象的生成来说,主要有艾青的感觉生成论、臧克家的生活赐予论、梁宗岱的心物契合论和朱光潜的想象创造论。艾青的感觉生成论和臧克家的生活赐予论都侧重人与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强调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对生活的感受能力与感应能力,强调人的生活态度和情感态度。梁宗岱的心物契合论是建立在象征主义“契合”论的哲学基础上的,更多地强调个人的经验和内心体验。朱光潜从想象方面来阐释意象的生成,是建立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现代;诗学;意象生成
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对意象的本质、功能、生成和鉴赏等诸多方面广为涉猎,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诗学理论体系。就意象的生成来说,主要有艾青的感觉生成论、臧克家的生活赐予论、梁宗岱的心物契合论和朱光潜的想象创造论。下面试分述之。
一、感觉生成论
感觉生成论是著名诗人艾青的观点。艾青的著作《诗论》虽然没有朱光潜的《诗论》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但充满了睿智的眼光和灵感的火花,不少论述既是诗人自己的经验之谈,也是对诗歌创作的一种智性描述和理论提升,具有跨越时空的指导意义。
艾青赋予意象一种感性形态,认为意象的生成是感官的、感觉的。作为学绘画出身的艾青,对创作主体感官和感觉的重视和强调是情理之中的,诗歌中的意象如同绘画中的物象一样首先是要靠创作者去敏锐的观察、感知和捕捉的。他描述道:“意象是从感觉到感觉的一些蜕化。”“意象是纯感官的,意象是具体化了的感觉。”“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所采取的材料的拥抱,是诗人使人唤醒感官向题材的迫近。”[1](P25)在描述之外,他还用诗的形式来进一步形容:“意象:/翻飞在花丛,在草间,/在泥沙的浅黄的路上,/在寂静而又炎热的阳光中……/它是蝴蝶——/当它终于被捉住,而拍动翅膀之后,/真实的形体与璀璨的颜色,/伏贴在雪白的纸上。”[1](P26)这些论述形象地阐释了意象生成的过程性、具体性和心灵性,既强调诗人的感觉,又重视客观材料;既强调具体化的艺术表达,又重视诗人感觉和心灵对对象的拥抱和化入。这样从感觉中得来的意象,被诗人的感觉和生命温暖了的意象,就像“蝴蝶”一样是真实的、灵动的、形色兼备的,是富有生命力的。
既然意象是纯感官的,是具体化了的感觉,那么要生成意象,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就是多方面的。从艾青的诗论中,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五种能力。一是感觉能力:“诗人应该有和镜子一样迅速而确定的感觉能力——而且更应该有如画家一样的渗合自己情感的构图。”[1](P20)只有对客观对象的敏锐感知,获得具体而鲜明的印象,在这个基础融合自己的情感,方能生成意象。二是感应能力:诗人“必须把自己全部的感应去感应那对象,他必须用社会学的、经济学的钢锤去锤炼那对象,他必须为那对象在自己心里起火,把自己的情感燃烧起来,再拿这火去熔化那对象,使它能在那激动着皮链与钢轮的机器——写作——里凝成一种形态……”[1](P23)感觉到的,还要去感应它;感应是用自己的“知”和“情”去锤炼和熔化对象,然后定格为“意象”。这里要求诗人具有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情感和卓越的表达。三是理解力:“用正直而天真的眼睛看着世界,把你所理解的,所感觉的,用朴素的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诗人必须比一般人更具体地把握事物的外形与本质。”“形象塑造的过程,就是诗人认识现实的过程。”[1](P22)感觉和感知到的事物,还必须上升到认识和理解;只有认识和理解,才能把握事物的整体和本质,从而塑造出美而且真的意象。理解是诗人对对象认识的加深,是对自己潜意识的一种理性的照耀,就如唐所说的在意象的生成中有一种“意识的理性的光”。四是想象力:“想象是由此岸向彼岸的张帆远举,是经验的重新组织;想象是思维织成的锦彩。”“诗人愈能给事物以联系的思考与观察,愈能产生活的形象;诗人使各种分离着的事物寻找到形象的联系。”“联想和想象应该是从感觉到形象的必经的过程。没有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是不可能有丰富的形象的。”[1](P94)这里,从主观方面讲,他强调了诗人的“经验”,想象是经验的重新组织;从客观方面讲,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想象是打通事物内在关联的钥匙;从主客融合方面讲,想象是锻造丰富的意象的必经之途。可见,想象力是意象的再造、变形和重组的催化剂和粘合剂,所以在创作中我们要唤醒自己的联想和想象。由此,他批评了诗歌创作中的“摄影主义”和浮面的描写。[1](P41)五是创造力:“诗人的劳役是:为新的现实创造新的形象;为新的主题创作新的形式,为新的形式与新的形象创作新的语言。”“在万象中,‘抛弃着,拣取着,拼凑着’,选择与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能糅合的,塑造形体。”[1](P37-38)在诗人看来,只有创造,才能有新鲜的意象,才能走向完整,到达至美、至善、至真。这种创造,是离不开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和现实的,诗人只有敏感于现实,用诗歌感应、呼应现实,才能创造出新的意象,为时代和现实造型。这种创造,还体现在一种选择性,即在社会万象中选择,用自己的“情感与思想”去选择,“万取一收”,创造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灌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意象”。
艾青强调意象生成中感官和感觉的作用,是在强调诗人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强调诗人和时代的联系,希望诗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敏锐地感知和感应,并从中受到感染和感动,用新鲜而饱含情感的意象谱写出时代的诗篇。在《诗与时代》一文中,他指出,诗人的感官比平常人更敏锐,“他生活在中国,是应该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着怎样伟大的事情的”,“每个日子所带给我们的启示、感受和激动,都在迫使诗人丰富地产生属于这时代的诗篇”,“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正在期待着、剔选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1](P54-55)。可见,艾青的意象感官论,不是局限于诗人个人的小感觉、小感受,不是从凡俗的世界中寻求感官的快感和刺激,而是大胸襟、大视野,把个人的感官和感觉升华到时代的高度,从而创造出属于时代的诗歌意象和诗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艾青的诗歌,其意象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感,他的抗战前后的“北方组诗”和“太阳组诗”,那些携带着苦难和伤痛、充满了热切向往和美好憧憬的诗作,是怎样从时代的血脉里产生,又怎样呼应着、激荡着一个时代的脉搏!
二、生活赐予论
臧克家认为意象是生活给予的。“生活”是他创作的土壤和源泉,也是他论诗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他在上世纪80年代回顾自己写作的文艺随笔时谈到,由于对生活的认识,对文艺的看法,加上长期从事创作的一些经验,才有了个人对文艺、对诗歌的一些见解。而这些见解,从内容方面概括地说来就是:“新诗必须表现现实,表现人民的生活;必须与时代精神结合,富于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2]可以说,这是他的文艺观,也是他的人生观。“生活”以其丰富的内涵编织在他诗歌创作的锦缎里,闪耀着他诗格和人格的华彩;“生活”以其沉甸甸的分量贯穿在他诗论的字里行间,铸就了他诗论和文论的风骨。在《生活——诗的土壤》一文中,他从文字入手,谈到意象和意象的形成:“字句的推敲,意义不在它本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单是在字句上追求漂亮,而是求其一丝不差地去表现诗人心中的意象,而这个意象,是生活给他的,活在他心上的,它生动、有色、有声,像满了月份的胎儿,非要求一个独立的生命不可。”[3](P43)他在《诗》一文中又说:“‘诗’,从生活里萌生出来,带着生活赋予的声音、光彩和意义,它再以它的声音号召,它再以它的光彩闪耀,它再以它的意义显示。”[4]这些话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意象是生活赐予的,带有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和生动性;二是,这个意象是诗人“心中的意象”,“活在他心上的”,包含着诗人的意念、愿望和情感;三是,由生活在诗人心中受孕而产生的意象,是一个独立的有声有色的生命体;四是,这个生命体又回归于生活,发挥它的作用,显示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切,“生活”是源头,是起点;离开了“生活”,就没有诗歌的意象,也就谈不上发挥诗歌的艺术作用和社会作用。可见,臧克家把“生活”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既然意象是生活给予的,那就必然牵涉到诗人对生活的态度问题。在诗人和诗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臧克家看重的是“生活”:“诗人,他不是为了写诗活着,而是为了生活。以诗为生活的人,他没有诗(有,也只是他自己的),因为他没有生活。只有懂得生活的人才懂得诗,生活对他有多深,诗对他有多深。只有能把握生活的诗人,才能产生有意义有价值的诗。”[3](P38)这是对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的一种概括。要懂得生活、能把握生活,首先就得深入生活:“‘深入生活’,入到生活深处,去观察、体会、摄取。”[5](P67)“一个诗人须得先具有一个伟大的灵魂,须得有极热的心肠,须得抛开个人的一切享受,去下地狱的最下层经验人生最深的各种辣味。还得有一双灵敏得就要发狂的眼睛,一转之间便天上地下,地下而又天上。”[6](P9)这就对诗人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要求诗人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具有高尚的人格、火热的心肠、敏锐的眼光和经受生活考验的胆识。臧克家还进一步要求诗人“必须带着认真的、顽强的、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强烈的燃烧的感情。从一定的立足点,从某个角度里去看人生,爱憎分明,善恶昭然,这样,客观的事物才能在感情、思想、感觉上,起剧烈的反应作用,而使诗人和客观的事物结合、拥抱、亲切,而不是立在漠然不关的情形之下”[5](P67)。在这样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支配下,诗人去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体味生活,生活就会赐予他灵感和想象,赐予他缤纷的意象和动人的诗篇。他列举自己的诗歌《难民》为例,说明自己由于对农村生活的贴近、熟悉和热爱,在创作中“一字之易”,结果使诗境大变。《难民》这首诗的头两句,最初是:“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里还辨得出归鸦的翅膀。”诗人不满意第二句诗,因为他觉得还没有完全表达出他心中的诗意的“黄昏”,于是后来改为“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这样苦苦推敲,是“为了求其不‘隔’,求其恰切地表达出心中的意象,也就是自然与生活的真实情景”[3](P44)。这是艺术的推敲和打磨,更是生活赐予的神来之笔。
正因为意象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他以“生活”作为衡量和评判诗歌的标准,批评了那些与生活隔离而躲在个人的小世界中歌唱的诗人。他认为徐志摩“坏的影响多过了好的”,“他只从英国贩过一种形式来,而且把里边装满了闲情——爱和风花雪月。他那种轻灵的调子也只合适填恋歌,伟大的东西是装不下的”。他还批评了戴望舒的诗歌,“从法国搬来了所谓神秘派的诗的形式”,“我觉得这样的形式只好表现一种轻淡迷离的情感和意象”。他基本肯定了闻一多的诗歌,“在内容上表现健康的姿态”[6](P6)。姑不论他对外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态度,单从“生活”这个角度看待徐志摩、戴望舒和闻一多等诗人,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三、心物契合论
梁宗岱认为意象是心物契合的结果。梁宗岱的新诗批评文章集中在《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分别出版在1935年和1937年。他1924年赴法留学,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尤其是瓦雷里的人格和诗学影响,诗学主题是捍卫和发扬诗的纯粹性。梁宗岱论诗时视野开阔,感觉细腻,文辞华美,可以说,他的诗论,是诗之论,是论之诗,是诗论中的散文和美文,是散文和美文中的诗论。“梁是诗人,他是以诗笔的触须去探涉理论问题的,因而整个论述过程,意象纷披,元气淋漓,甚至颜色妩媚,姿态招展,显得既华美又铺张。”[7](P296)他所理解和追求的“纯诗”,就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8](P100)纯诗与象征的联系就在于“暗示”这一点上。这种象征不是一种传统的修辞手法,而是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艺术思维渗透在整体创作中。在这种象征中,诗人力求捕捉的,并不是单纯的主观情感,也不是纯粹的客观表象,而是主客相融的境界。[9](P60)“而且这大宇宙底亲挚的呼声,又不单是在春花的炫熳,流泉底欢笑,彩虹底灵幻,日月星辰底光华,或云雀的喜歌与夜莺的哀曲里可以听见。即一口断井,一只田鼠,一堆腐草,一片碎瓦……一切最渺小,最卑微,最颓废甚至最猥亵的事物,倘若你有清澈的心耳去谛听,玲珑的心机去细认,无不随在合奏着钧天的妙乐,透露给你一个深微的宇宙消息。”[10](P86)这可理解为宇宙万象与诗人心灵的契合而产生的艺术意象或意境。
梁宗岱心物感应和契合的观念,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特别是波特莱尔的影响。“契合”(又译成“对应”、“交响”),原为波特莱尔的一首诗名,是“象征派的宪章”,集中体现了象征主义诗学的核心内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包括客体和主体之间,都处于一种互为交流、互为契合的状态之中。波特莱尔的《契合》就是这种观念的形象说明。梁宗岱准确地把握住“契合”论的要质,认为这首诗带来了近代美学的福音,它“启示给我们一个玄学上的深沉的基本原理,由这真理波特莱尔与十七世纪一位大哲学家莱宾尼兹遥遥握手。即是:‘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10](P80)
而这种和谐之景,常人是难以看到和难以感应到的。因为常人在生活的尘土里辗转挣扎,“宇宙底普遍完整的景象支离了,破碎了,甚至完全消失于我们目前了”;“只有醉里的人们——以酒,以德,以爱或以诗,随你底便——才能够在陶然忘机的顷间瞥见这一切都浸在‘幽暗与深沉’的大和谐中的境界”[10](P81)。诗是另一种醉态,带领人进入到另一种精神状态,并渐渐沉入一种“恍惚非意识,近于空虚”的境界,在对外界有所放弃的同时又有所得,有所悟,正像老子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时候,“在没有什么阻碍或扰乱我们和世界底密切的,虽然是潜隐的息息沟通了:一种超越了灵与肉,梦与醒,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同情韵律在中间充沛流动着。我们内在的真与外界底真调协了,混合了。我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我们在宇宙里,宇宙也在我们里:宇宙和我们底自我只合成一体,反映着同一的荫影和反应着同一的回声。”[10](P82-83)这样,物我同一,万化冥合,意象乃生。实际上,这时候诗人放弃了理性与意志的权威,把自我完全交付给事物的本性,“站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粒细沙,一朵野花或一片碎瓦,而是一颗自由活泼的灵魂与我们底灵魂偶然的相遇:两个相同的命运,在那一刹间,互相点头,默契和微笑”。[10](P87)梁宗岱在论述心物相契的心理机制时有大量的细微而诗性表述,也列举了许多例证。
心与物的感应和契合,就要求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正如风底方向和动静全靠草木的摇动或云浪底起伏才显露,心灵的活动也得受形于外物才能启示和完成自己:最幽玄最缥缈的灵境要藉最鲜明最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进一步说,二者不独相成,并且相生:洞观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8](P96)心与物、意与象乃相成相生,互相彰显,互相深化。这涉及他文艺思想的重要话题,即“诗与真”。他自己说诗论集的名称是受了歌德的自传暗示,歌德是指回忆中诗与真即幻想与事实之不可分解的混合,是二元对立的。梁氏说自己毕生追求的是对象的两面:“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11](P5)一般论梁氏诗论,都注意到他内倾的一面,由他提倡纯诗主张抒写心灵世界,而认为他的诗论是唯心的。其实,他非常重视诗人的生活,重视对客观现实的认识。[9](P67)
心物契合而产生诗歌意象和象征灵境,梁宗岱也拿这个标准来衡量诗人和作品。他指出莫里哀、拜伦、歌德、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是文学史上伟大的象征作品,但又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象征一种永久的人性,“实在因为它们包含作者伟大的灵魂种种内在的印象”[10](P76)。这种浸润了作者灵魂的印象,亦即意象,“在我们心灵里激起无数的回声和涟漪”。他还比较分析了屈原的《橘颂》和《山鬼》,认为《橘颂》是寓言,《山鬼》是象征,因为在《山鬼》中,诗人和山鬼“移动于一种灵幻飘渺的氛围中”,作品的意义“完全濡浸和溶解在形体里面,如太阳的光和热之不能分离”[10](P77)。
既然诗歌的意象和灵境来自于心物相契,那么对诗人来讲,就得从多方面加强修养和陶冶性情,他除了像康白情和宗白华等人强调到外部生活中亲历、感悟之外,也更注重自身的体验和精神涵养。“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底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的灵魂里去……”[12](P33)在诗学观念上,梁宗岱反对灵感说,反对自我表现说,而赞同瓦雷里等象征诗人的经验说。他十分强调经验对创作的作用,说“单要写一句诗,我们得要观察过许多城许多人许多物,得要认识走兽,得要感到鸟儿怎样飞翔和知道小花清晨舒展底姿势”[8](P36)。生活经验愈丰富,愈有利于诗人创作,创作是经验的结晶。他从象征主义的经验论出发,强调回忆、忘记,“当它们太拥挤的时候,还要有很大的忍耐去期待它们回来。因为回忆本身还不是这个,必要等到它们变成我们的血液,眼色和姿势了,等到它们没有了名字而且不能别于我们自己了”[8](P42)。在这个基础上诗人在创作时需要“纵任想象,醉心形相,要将宇宙间的千红万紫,渲染出他那把真善美都融作一片的创造来”。
四、想象创造论
朱光潜着重从想象方面展开分析了意象的生成。他谈的想象,主要是“创造的想象”。他认为创造的想象含有三种成分,即理智的、情感的和潜意识的。就理智的成分来讲,根据“分想作用”和“联想作用”这两种心理作用,创造的想象对意象加以选择和综合。“分想作用”是选择所必需的,能够把某意象和其他相关的意象分裂开,“艺术的意象有许多并不是综合的结果,只是在一种混乱的情境中把用得着的成分单提出来,把用不着的成分丢去,有时也能造成很完美的意象,好比在一块顽石中雕出一座像一样”[12](P194)。可见,“分想作用”也能造成新的意象,是一种创造。但文艺上的意象大多数还是起于“联想作用”,特别是其中的类似联想。类似联想可以把许多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生发出某种关系,产生新的意象。朱光潜用大量的诗句对“拟人”、“托物”和“变形”三种类似联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同时,朱光潜还谈到象征,“‘象征’就是以甲为乙的符号,也可以说是一种引申义,它也是根据类似联想”[12](P195)。由于象征大半是拿具体的东西代替抽象的性质,所以体现在文艺作品中就是以具体的意象来象征抽象的概念,不过“在文艺中概念应完全溶解在意象里,使意象虽是象征概念而却不流露概念的痕迹”[12](P196)。朱光潜指出,“分想作用”和“联想作用”只能解释意象的发生如何可能,却不能解释在许多可能的意象之中何以某意象独被选择。这样,他就从“理智的”分析转入“情感的”分析:“情感触境界而发生,境界不同,情感也随之变迁,情感迁变,意象也随之更换。”[12](P197)从境界到情感,从情感到意象,情感是“某意象独被选择”的深层原因之所在。情感不仅能够生发与之相谐的意象,而且还能“把原来散漫零乱的意象融成整体”[12](P198)。正因为情感生发意象,连缀意象,情感是意象得以被选择、被贯通的内因,没有情感当然也就没有新鲜的意象,也没有完整的意象,所以朱光潜反对沿用和剽窃意象,“意象可剽窃而情感则不能假托。前人由真情感所发出的美意象,经过后人沿用,便变成俗滥浮靡,就是有意象而无情感的缘故”[12](P198)。“理智的”和“情感的”两种成分属于意识的范畴,朱光潜还从“灵感”的角度,亦即从潜意识的角度对意象的生发进行了分析。依照近代心理学家的说法,灵感大半是由于在潜意识中所酝酿成的东西猛然涌现于意识,那么,“有时苦心搜索而不能得的,在无意识中得到灵感,顿时寻求许久的意象便涌上心头”[12](P202)。这就足见意象和灵感以及二者和潜意识的密切关系。他分析说,在潜意识活动中,想象更丰富,情感的支配力更大,这样在意识中得不到的东西往往可以在潜意识中酝酿成功。在指出意象是凭借潜意识酝酿而成的这一现象之后,他接着分析了意象为什么会在某一时刻涌现于意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意识作用弛懈时,潜意识中的意象最易涌现;而创作时的心境往往“有如梦境”[12](P205),当然意象也就最容易涌现。关于这点,梁宗岱在论述意象的生成时也看到了,即诗人有别于常人,诗境有别于常境。正因如此,艺术家为了招邀灵感,或听音乐,或饮美酒,或喝咖啡,意在造成一种“梦境”,使潜意识中的意象得以涌现。潜意识的酝酿作用,还能带来“意象的旁通”[12](P206)。即诗人和艺术家寻求灵感,往往不在自己“本行”的范围之内而走到别种艺术范围里去;在别种艺术范围之中得到一种意象,让它在潜意识中酝酿一番,然后再用自己的特别的艺术将其“翻译”出来。朱光潜用剑术和书画等之间意象的旁通来进行了说明,并希望艺术家不宜专在“本行”之内做功夫,应该处处玩索,在对灵感的培养中获取生动的意象。
朱光潜从想象方面来阐释意象的生成,是建立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与艾青、臧克家和梁宗岱对意象形成的分析有所不同。艾青的感觉生成论和臧克家的生活赐予论有些类似,都侧重人与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强调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对生活的感受能力与感应能力,强调人的生活态度和情感态度,这也是他们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诗论中的体现。而梁宗岱接受的是波特莱尔、瓦雷利和里尔克等象征派诗人诗学观念的影响,他的心物契合论是建立在象征主义“契合”论的哲学基础上的,更多地强调个人的经验和内心体验,强调人的潜意识、梦境和醉态。在对人的心理特别是人的潜意识的关注方面,梁宗岱和朱光潜是相通的。
[1]艾 青.诗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臧克家.五十年间学论文[A].吴 嘉.克家论诗[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3]臧克家.生活——诗的土壤[A].吴 嘉.克家论诗[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4]臧克家.诗[A].吴 嘉.克家论诗[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5]臧克家.新诗常谈[A].吴 嘉.克家论诗[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6]臧克家.论新诗[A].吴 嘉.克家论诗[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7]李振声.编后记[A].梁宗岱批评文集[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8]梁宗岱.谈诗[A].诗与真[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9]许 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10]梁宗岱.象征主义[A].诗与真[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1]梁宗岱.诗与真·序[A].诗与真[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2]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Views of Formation of Imagery in Modern Chinese Poetics
ZHANG Wen-ga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Changde,Hunan 415000,China)
In th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ics of imagery,there are mainly four views of formation of imagery:Ai Qing’s perception formation view,Zang Kejia’s life-giving view,Liang Zongdai’s correspondence of heart and material view,and Zhu Guangqian’s imagination creation view.Ai Qing’s perception formation view and Zang Kejia’s life-giving view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ife,men and time,attach importance to man’s subjectivity,creativity and ability to perceive life,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man’s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feeling.Liang Zongdai’s correspondence of heart and material view is based on the“correspondence theory”of symbolism and stresses on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inner feeling.Zhu Guangqian’s imagination creation view i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explains the formation of imagery from the aspect of imagination.
China;modern;poetics;formation of imagery
I0-02
A
1000-2529(2010)05-0116-05
2010-01-05
张文刚(1959-),男,湖南安乡人,湖南文理学院武陵学刊编辑部执行主编,教授。
(责任编校:谭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