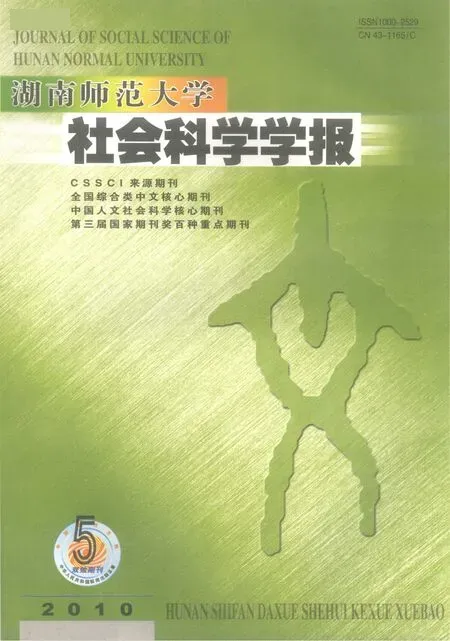公民权与公民社会之建构
2010-04-11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教授王小章
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教授 王小章
公民权与公民社会之建构
浙江大学社会建设研究所教授 王小章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一直是我国学界所热议的一个话题,在当前以社会建设为主题的讨论中也再次成为学界热点。公民社会之所以引起关注,与人们对它在现代社会政治发展、在社会成员个体权利的增进维护、在社会福利的促进等方面的作用的期待有关。作为既有别于国家也有别于市场,以非营利性的公民组织或者说自愿结社为核心要素的“第三领域”,现代公民社会在其健康发展的情况下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功能。支撑起现代公民社会之基本架构的各种公民组织,不仅可以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上有效地为其成员以及需要帮助的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各种服务,从而促进其成员的福利,更能在比较一般的、更为基础的层面上维护和促进社会成员的权利,维护和促进现代社会和政治的良性运行、健康发展。举其要者,第一,它可以有效地抵御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权势——无论是政府当局的权力还是市场组织的强势——对于个体的可能侵犯和压迫,从而保护个人的正当权利和独立自由。也就是说,在所谓身份平等的现代社会中,通常很难产生特别有影响力的人物能够起来有效地抗拒当局对他们的独立自由的可能侵犯(就像欧洲以前的贵族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如若社会成员陷于原子化的状态,当局的权力就很容易成为专横的权力,个体的权利则很容易成为脆弱的权利。而结社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软弱无力,从而有效地维护个体的正当合法权利和独立自由。当然,在今天,公民不仅要通过结社来应对政府当局权力对个体自由独立的可能压迫,还要通过各种自愿、自由的公民组织,如消费者权益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工会等等,来抵抗市场组织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可能侵犯。第二,通过有效地维护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公民组织可以成为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释放消极对抗情绪,维护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解压阀”。通常,社会成员之所以会产生不满、怨愤情绪,往往是因为其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强势者的侵害而无力捍卫。作为受侵害者个体,这种情绪很容易转化为各种消极的、反社会的行为。而当这种情绪与其他人同样由于其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类似情绪汇合起来,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在外界特定条件的刺激下,就可能酿成各种群体性事件。这时,一直逆来顺受的“顺民”就会转化为“暴民”。而公民组织通过有效又有序地保护个人的正当权益,可以防止和消除这些由于个人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不满、怨愤情绪,净化社会心理氛围。第三,公民组织为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了渠道,所以它还是培养公民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由于结社是自由、自愿的,社会成员的这种参与、进入也就是独立自主的。尽管最初人们往往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而参与公共事务的,但是,通过这种独立自主的公共参与,人们逐渐会认识到,除了那些使他们与其他个体分离开的利益外,还有能够使他们彼此联系、联合起来的利益,而且这种共同利益,完全依赖于他们每个人共同参与的努力。由此,人们逐步地就会像关心自己的利益那样关心公共利益,从而培养出仅仅通过几年一次的、在对于切身利益的感觉上无关痛痒的选举投票所永远不能真正培养出来的公共精神。第四,公民组织本身可以有效地避免和防止现代社会的涣散或者说原子化,而通过公民组织培养出的公共精神则可以进一步为社会培育、积累起深厚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各种社会事业、公共项目能得以高效地、事半功倍地举办的重要基础。
就以各种自愿结社或者说公民组织为基本骨架的现代公民社会所具有的上述诸多功能而言,人们对公民社会的关注和热议无疑是可以理解并应该肯定的。不过,多少有点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关于公民社会的议论中,对于“公民权”(citizenship),即公民身份以及与这种身份相关联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的直接的、正面的讨论却处于一种相对缺席的状态。近年来情况尽管有所改变,但对于公民权的探讨和关注依然处于一种相对薄弱的状态。更准确地说,关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建设和公民权(citizenship)之关系,许多人的认识处于一种单向的思维中,即往往只看到公民社会对于公民权的作用,却常常忽视一个正常运行的、健全的公民社会也是以公民权的形成和确立为前提的。
作为相对独立于国家的一个范畴,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是从17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而其原型,则是欧洲中世纪晚期那些作为“特别的市民身份团体”的工商业自治城市。一如李猛所言,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一开始就有多重涵义。侧重于经济涵义,是“市民社会”;侧重于文化涵义,是“文明社会”或“礼貌社会”;侧重于政治涵义,则是“公民社会”。三重涵义,明显对应着、昭示着作为civil society之主体的那些成员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们是“经济人”,是可以独立自主地支配使用自己的财产并通过市场而合法正当地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消极意义上的个人自由是其最基本的性格特征。作为“文明社会”的成员,他们是能够控制自己那些危险的、不确定的激情冲动的人,即他们愿意、也能够在一个由法律、契约以及各种文明习俗所构建的稳定秩序中以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追求可预期的自我利益的可预期的人,理性自律是最基本的性格特征。作为“公民社会”的成员,他们是在法治架构、民主体制下拥有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和影响政治过程的权利、动机和能力的人,出于对自身权益和公共利益(也就是和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有关的利益)的关怀而介入公域是其最基本的性格特征。显而易见,作为“市民社会”、“文明社会”和“公民社会”成员的人,作为具有上述诸方面性格特征的人,事实上也就是既有别于古代城邦之政治公民,也有别于在人身上依附于封建领主的中世纪农奴的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没有这样一种拥有各种消极(如免于外来干涉的自由权利)和积极(如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的法定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的理性公民,就没有civil society的形成。
当然,如上所言,今天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是指既有别于国家也有别于市场、以非营利性的公民组织或者说自愿结社为核心要素的“第三领域”,其所指已不完全等同于古典意义上的、包括市场在内civil society,但是,正如哈贝马斯等所指出的那样,前者是起源并从属于后者的。如果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就没有古典意义上的 civil society,那么,没有这种公民权,同样没有今天所指的那种健康的公民社会。
由一系列消极和积极的法定权利来体现的现代公民权是现代公民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至少是两者互为前提,因此,要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不能不关注现代公民权之基本形态的确立与维护。而要确立现代公民权的基本形态,需要付出的努力当然牵涉到方方面面,关键的,如法治秩序和观念的形成、民主制度的确立等,但联系现代公民权的历史起源,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形,同时也针对我国学界的一些言论,笔者以为,第一步是要确立个人的本位性,即要使个体成为自己的主权者,并且作为特定共同体的成员,个体是一系列权利和相应的义务的承受者。个体本位的诞生与确立,既是近代公民权的首要特性,也是它得以诞生的前提条件。就近代公民权的起源而言,这一点十分重要。当然,对强调个体本位,有人可能不以为然,并援引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来加以驳斥。确实,社群主义所批判的那种自由主义对于公民权的理解是有偏颇的,其最主要的偏颇在于,它过于、甚至是单方面地强调了个人的自由权利,而忽视了这种权利本身是在一个“共同体”中的权利,忽视了公民权首先意指的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成员身份,而个体本位也是相对于一个“共同体”而言的。社群主义与此不同,它强调如何让社会发挥有效和公正的功能,认为“好社会”的建立,靠的是相互支持和集体行动。它对于自由主义之批判的基本的矛头所向主要也就是上述这一偏颇。鉴于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实践中,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正是这种自由主义,并且已确实导致了社会的原子化,凝聚力的弱化,导致了社群感(共同体意识)的失落,即使从矫枉过正的角度出发,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只要稍稍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今日的社群主义事实上并不忽视个人权利,无非只是鉴于西方社会政治之特定的语境而更强调公民个体对于共同体的义务、责任罢了。但是如果把社群主义在西方特定语境中对于自由主义之片面强调个体自由权利的批判照猫画虎地搬到我们这里,就形成了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错误。我以为,对于我们这个至今尚未完全确立起个人本位地位的社会来说,今天更为迫切的是确立个人作为自身的主权者。
个人的本位地位是现代意义的公民权得以诞生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它的首要特性,同时也是不同于宗族或传统自然村落的、现代意义上的健全的公民组织或公民社会得以诞生和形成的一个基本前提。道理很简单:第一,只有当个体是自己的主权者时,他才有能力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促进自身的或公共的福利而主动地、自觉地组织或加入自己的社团,也即,他才有现实的结社权(就此而言,笔者以为,如果说中国社会目前也存在原子化的潜在威胁,威胁的主要来源不在于个体权利的过度,而恰恰在于个人权利发展的不足。第二,只有这种基于个体自决的、自觉主动地加入或组建的组织,才能(在法治秩序和民主制度下)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要素,而不致蜕变为凌驾于个体成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