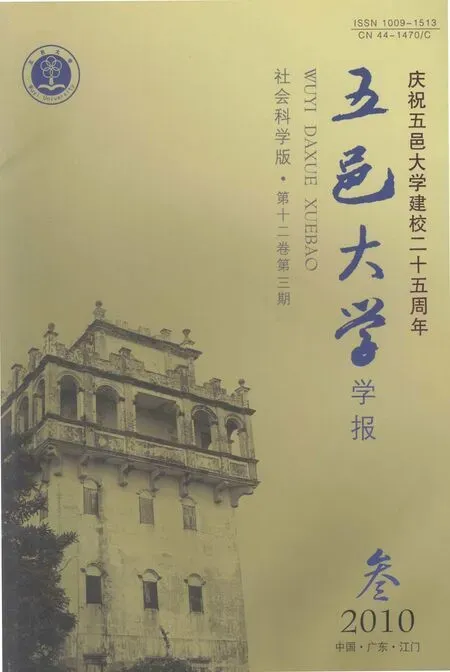隋代“巫蛊之术”新探
2010-03-21李荣华
李荣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191)
隋代“巫蛊之术”新探
李荣华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191)
隋文帝统治晚期,宫廷中“巫蛊之术”盛行,主要有“猫鬼”之术、偶人和毒药等。这几例“巫蛊之术”都以伤害他人为目的,属于黑巫术。借用人类学和古代医学的相关理论对相关史料进行新的诠释,不仅对隋代“巫蛊之术”有全新理解,而且有利于深化对隋代宫廷中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
隋代;宫廷;巫蛊之术
中国古代社会使用“巫蛊之术”较为常见。隋文帝统治晚期,宫廷之中存在着“猫鬼”、偶人以及蛊毒等“巫蛊之术”。它们发挥着独特作用,从而便于使用者实现个人目的。
关于隋朝宫廷“巫蛊之术”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一些成果。有学者专门研究了隋朝宫廷中的“猫鬼”之术,认为杨秀、杨俊之死都与“猫鬼”有关。①不过,另有学者认为杨俊之死与蛊毒(蜘蛛蛷蝼蛊)有关。②笔者拟从人类学和医学的角度,就隋朝宫廷“巫蛊之术”进行新的诠释。
一、“猫鬼”:役魂盗财的巫术
关于“猫鬼”,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卷二五《猫鬼候》中写到:“猫鬼者,云是老狸野物之精,变为鬼域,而依附于人。人畜事之犹如事蛊,以毒害人。其病状,心腹刺痛,食人府藏。吐血利血而死。”“猫鬼”是“老狸野物”精魂的化身。《说文·豸部》中对“狸”的解释是:“狸,伏兽,似貙。”段玉裁认为狸“即俗所谓野猫。”[1]《广韵·之韵》:“狸,野猫。”《太平广记》卷一三九:“隋大业之际,猫鬼事起,家养老猫为厌魅,颇有神灵,递相诬告,京都及郡县被诛戮者,数千余家。蜀王秀皆坐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寝。”[2]受“猫鬼”影响,普通百姓家以养老猫为手段,进行各种祈祷或者诅咒活动,企图实现他们的目的,结果“颇有神灵”。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和《外台秘要四十卷》提要均说明了“猫鬼”之术出现的时间范围。“第二十六卷猫鬼病候,见于《北史》及《太平广记》者,亦惟周、齐时有之。”[3]1334“又二十八卷载猫鬼野道方,与《巢氏病原》同。亦南北朝时鬼病,唐以后决不复闻,然存之亦足资考订也。”[3]1336“猫鬼”之术主要出现在北周、北齐以及隋朝,唐朝以后不复存在。
隋朝时期,对“猫鬼”之术记载最详细的是《隋书》卷七九《独孤陁传》和《北史》卷六一《独孤陁传》。《隋书》卷七九《独孤陁传》:“(独孤陁)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转入其家。”《北史》卷六一《独孤陁传》:“陁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两书对于独孤陁家“猫鬼”来源的记载颇不一致:《隋书》中来自于独孤陁妻子的娘家,《北史》中来自于独孤陁的外祖母家即独孤陁母亲的娘家。撇开这两本书记载中的不同部分,可以发现其中相同的部分:那就是蓄养“猫鬼”的都是女性,“猫鬼”之术靠女性来传承。《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中对南方一带人们蓄蛊的传统进行了记载:
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豫章,而庐陵人厖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子孙相传不绝,亦有随女子嫁焉。蛊也有通过女性来相传的,而且子孙世代不断。更有甚者,所蓄之蛊不杀外人,自己就有被杀死的可能,所以蓄蛊者有时会选择杀死自己身边的亲人以使自己避免灾祸。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独孤陁的外祖母杀死其舅是有可能的。现代人类学家对巫蛊之术的研究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传说放蛊人有蛊必放,否则危及自身,蛊发时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4]4“猫鬼”之术不仅害人,而且有时也会害己。
“猫鬼”之术如何实施,必然有自己的程序。《隋书》卷七九《独孤陁传》中记载:
陁婢徐阿尼言,本从陁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陁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陁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阿尼便咒之归。数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从并州还,陁于园中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阿尼复咒之,遂入宫中。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者,云猫鬼已至。
从上例可以看出,“猫鬼”的祀养必须在子日的夜间进行,因为子与鼠相对;而当“猫鬼”收回之时独孤陁的奴婢徐阿尼脸色发青,好像被什么东西牵曳着,这又说明了“猫鬼”从蓄养到放出、收回都有一套完整的程序,有固定的咒语和仪式。
独孤陁让奴婢徐阿尼实施“猫鬼”之术,是希望把杨素家的钱财转移到自己家中,同时也让隋文帝的独孤皇后多赏赐他财物。因此,“猫鬼”之术具有役魂盗财的功能,这也是独孤陁的主要目的。它虽然客观上有可能危害到他人的生命,但并没有直接害人的意思。当徐阿尼给杨素家和独孤皇后实施“猫鬼”之术后,杨素的妻子和独孤皇后出现患病的症状,经过诊断一致认为是“猫鬼”之疾。隋文帝看到身边人所患“猫鬼”之疾后,由不相信转为相信,不仅严惩独孤陁一家人,而且下令“畜猫鬼、蛊毒、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5]43。
隋朝宫廷中这一巫术的出现与当时民间社会所流行的“猫鬼”之术密切相关。隋朝时期,“猫鬼”之术在民间到处流行,“先是有人讼其母为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6]。独孤陁的阴谋暴露以后,隋文帝虽下诏禁止,但是依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到了隋炀帝大业年间依旧流行。
二、偶人:杨广陷害杨秀的伎俩
所谓偶人,就是指“用纸人、草人、木偶、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疑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作法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发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的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4]70。人类学称之为偶像伤害术。弗雷泽的《金枝》中,称这种偶人术为顺势或者模拟巫术,即人们采取破坏或者毁掉敌人偶像的方法来伤害或者消灭敌人,是“同类相生”原则的应用。[7]21在中国历史上,使用这种巫术的例子最多。汉代的“巫蛊之祸”是其典型代表。《汉书》卷六三《戾太子刘据传》中记载:“(江)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8]江充所挖掘出来的桐木人就是用来充当巫蛊的。当杨广陷害杨秀之时,也是利用偶人作为手段。
隋文帝共有五个儿子,长子为杨勇,次子为杨广,三儿子为杨俊,老四为杨秀,小儿子为杨谅。《隋书》卷四五《杨秀传》中有对蜀王杨秀的记载:“秀有胆气,容貌环伟,美须髯,多武艺,甚为朝臣所惮。”可谓仪表堂堂,气质非凡。因此隋文帝对他的独孤皇后说,“秀必以恶终”。当杨勇被废,杨广被立为太子后,杨秀意欲不平,于是杨广先下手为强,“恐秀终为后变,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杨广与杨素便用偶人来陷害杨秀,“太子阴作偶人,书上及汉王姓字,缚手钉心,令人埋之华山下,令杨素发之”。杨广用此巫术可谓一举两得,既能治杨秀于死罪,又能在感情上使隋文帝断绝他和杨秀之间的父子情谊,从根本上击败杨秀。对于巫蛊之术,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严惩不贷的,何况谋害的对象是皇帝本人。“因有巫蛊可以杀人的观念,所以社会极端厌恶仇视这种邪术左道,而自来的法律对于这种行为都认为犯罪而处罪极重。”[9]这样,当隋文帝认定杨秀制造巫蛊谋害自己以及杨谅时,杨秀便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杨秀被“幽逼,愤懑不知所为”[5]1242时,隋文帝下诏数落了他的罪行。其中之一是:
鸠集左道,符书厌镇。汉王于汝,亲则弟也,乃画其形像,书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杻械。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我之于汝,亲则父也,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为开化杨坚夫妻,回心喜欢。又画我形像,缚手撮头,仍云请西岳神兵杨坚鬼魂。如此形状,我今不知杨谅、杨坚是汝何亲也?[5]1243-1244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清晰地判断,隋文帝认为杨秀谋害他们父子的手段是偶人而不是“猫鬼”之术。偶人之术与“猫鬼”之术的应用原理不同,偶人的制作和应用是利用巫术中的顺势或模拟原理,即利用物体之间的相似性来达到目的。“‘顺势’或‘模拟’巫术通常是利用偶像为达到将可憎的人赶出世界这一充满仇恨的目的而实施。”[7]23“猫鬼”之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以供奉某种精灵治人谋财者,属于以‘灵’为害”[4]60。因此,二者是有很大差异的。
当杨广击败曾经身为太子的杨勇后,利用偶人陷害杨秀,目的是防止其与自己争夺皇位。在陷害的过程中,杨广处于主动地位,其原因在于隋文帝对他的宠信,有了这种宠信,杨广可以任意陷害别人。这种信任一方面来自于杨广为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所立下的功劳以及杨素的支持,另一方面来自于杨广的“作秀”行为,适当地隐藏了自己的缺点,适时地表现了自己的“优点”。杨广在与杨勇争夺太子之位的过程中,恰如其分地表现自己,结果被认为是太子之位的合适人选。“其后晋王来朝,车马侍从,皆为俭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声名籍甚,冠于诸王。”[5]1231正是凭借着这种宠信,杨广不仅夺得太子之位,而且击败杨秀,成为皇位唯一的继承人。
三、毒药或蛊毒:杨俊之死因?
上文提到,对于杨俊之死,学者卢向前认为与“猫鬼”有一定联系,高国藩和邓启耀则认为与蛊药有关,中的是蜘蛛蛷蝼蛊。“猫鬼”与蛊药是有区别的:“猫鬼”是以动物精灵的形式存在,蛊药是蓄养毒物,配制成药粉,以此毒害别人。
《太平御览》卷七三五《厌蛊》中对于崔氏谋害秦王杨俊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俊好内,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于瓜中进毒。俊由是遇疾笃。含银,银色异,为遇蛊,未能白。遣使奉表陈谢,帝责以失德。薨,帝哭之数声而已,曰:“晋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拟赐秦王,王亡,可置灵坐之前,心已许之,不可亏信。”帝及后往视,见大蜘蛛大蛷蝼,从柩头出之,不见穷之,知妃所为也。
《太平御览》中的这段文字抄自《隋书》,但今本《隋书》中的记载与这段文字差异很大。《隋书》卷四五《杨俊传》中记载:“俊颇好内,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于瓜中进毒。俊由是遇疾,征还京师”,“俊病笃,未能起,遣使奉表陈谢”,“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诏废绝,赐死于其家”。不过,《北史》卷七七《秦王俊传》中的记载与《太平御览》中的记载基本相似:“俊疾笃,含银,银色变,以为遇蛊”,“二十年六月,薨于秦邸。帝哭之数声而已,曰:‘晋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拟赐秦王。今亡,可置灵坐之前。心已许之,不可亏信。’帝及后往视,见大蜘蛛、大蛷螋从枕头出,求之不见。穷之,知妃所为也”。而《资治通鉴》卷一七八“开皇十七年九月”条中对杨俊中毒的记载和《隋书》卷四五《杨俊传》大致相同。可见《太平御览》、《北史》中的记载与《隋书》、《资治通鉴》中的记载相异。
之所以说崔氏是利用蛊药来谋害杨俊的,有两条证据。一条是“含银,银变色”。在古代用银来检测毒药,不过,只有当毒物中含有硫化物物质时,才能使银的表面产生硫化银物质,从而使银失去光泽变黑。这条材料说明杨俊已经中毒,毒药中含有硫化物物质。另一条是杨俊的棺材里面不断出现大蜘蛛大蛷蝼。根据这条材料可以推测出秦王杨俊中的是蜘蛛蛷蝼蛊,因此,现代研究巫蛊之术的人一致认为杨俊中的是蜘蛛蛷蝼蛊。那么杨俊到底是中毒还是中蛊?这主要看当时人们对蛊的理解。
中国古代巫蛊之术的基本含义和特性就是“人工培养并欲施之于人,将自然界中的毒虫经人为培养或攻击性选择,蓄养起来,欲施之于人,便是蛊”,“蛊术所取之物皆为毒花,具有毒害人、惑乱人的特性”,“巫蛊之术是一种秘密邪术”。[4]47从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蛊’作为病名强调其特异性的致病原因,而作为症候名则侧重于概括某些症状表现,二者的认识角度不同,意义是相分离的”[10]。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卷二五、二六中,叙述了各种不同的蛊毒。第一种是人工蓄养的毒虫,如蛊毒候、蛊吐血候、蛊下血候、氐羌毒、猫鬼以及野道候;第二种是各种地方性的流行性疾病,如射工、沙虱以及水毒候;第三种是中药毒以及饮食中毒,包括解诸毒、解诸药毒候、服药失度候、诸饮食中毒候以及饮酒中毒候等。这几种蛊毒的病因各异,但其症状基本相似,所以巢元方把它们归为一类,列为“蛊毒病”。可见在隋朝时期,人们把中毒也称为中蛊。既然如此,秦王杨俊极有可能是药物中毒。孔颖达在疏《左传·昭公元年》“蛊”时指出:“蛊,非尽由淫也,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今律谓之蛊毒。”[11]因此,以当时人的观念说杨俊中蛊,只是在他不知的情况下被他嫉妒成性的“爱妃”下了毒。
秦王杨俊死于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六月。至于死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因崔氏下毒药损害其健康,另一方面因生活奢靡致使隋文帝责怪。“我戮力开塞,创兹大业,作训垂范,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为吾子,而欲败之,不知何以责汝。”[5]1240以致抑郁而终。
四、结 语
由上可见,隋文帝统治晚期,宫廷之中的“巫蛊之术”主要有“猫鬼”之术、偶人和毒药等。其中,独孤陁实施“猫鬼”之术的主要目的是盗财,他并没有害人的心思;杨广利用偶人来陷害杨秀,目的是防止杨秀和他争夺皇位;关于杨俊所中蛊毒,一般认为所中之蛊为蜘蛛蛷蝼蛊,不过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也可能是中毒,因为当时人有把中毒当作中蛊的观念。
巫术有黑白之分,白巫术以祈福禳灾为目的,黑巫术以伤害别人为目的。无论黑白巫术,在古代社会都相当流行。隋朝宫廷中流行的这几例“巫蛊之术”属于黑巫术。隋文帝对这些使用黑巫术的人严惩不贷,而他们又是隋文帝最重要的亲属,因此唐人赵蕤《长短经》卷三评述隋文帝晚年“巫蛊事兴”。研究隋朝的巫蛊之术,对于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历史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参见卢向前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的《武则天“畏猫说”与隋室“猫鬼之狱”》一文。
②参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的高国藩《中国巫术史》一书第260页,以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一书第142页。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458.
[2]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1004.
[3]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03[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5]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73.
[7]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2742.
[9]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289.
[10]王建新.论古代文献中的“蛊”[J].中医文献杂志, 2004(4):15.
[1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2025.
[责任编辑 文 俊]
K241
:A
:1009-1513(2010)03-0078-04
2010-02-04
李荣华(1978-),男,陕西蒲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