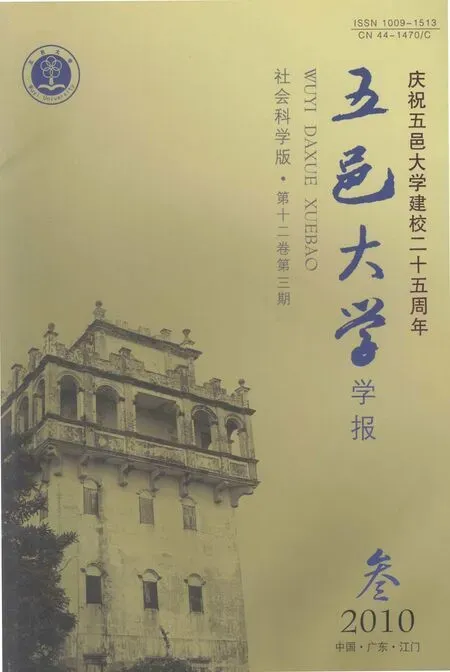“断裂”与“超越”
——“十七年”诗人时间意识的两个维度
2010-03-21巫洪亮
巫洪亮
(龙岩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0)
“断裂”与“超越”
——“十七年”诗人时间意识的两个维度
巫洪亮
(龙岩学院 人文与教育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0)
在“十七年”诗歌中,“时间”成为诗人情感抒发的重要题旨以及结构诗歌的重要方式,“断裂”与“超越”是诗人时间意识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断裂”既与诗人内在的精神诉求有关,又与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密不可分;“时间超越”既培养了人们高度自觉和敏锐的时间意识,又使人被“异化”的时间所围困。
“十七年”诗歌;时间意识;“断裂”;“超越”
千百年来,不同的民族国家、时代语境和宗教信仰,迥异的文化理念、历史记忆和现实境遇,型构了生活在时间之流而又天性敏感的诗人相当丰富且异常复杂的时间体验,这些体验源源不断地化为文人墨客笔下动人的诗篇。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人民的世纪”[1],同时也刷新了人们对时间的认知与记忆,“十七年”诗人正是在这一“新开始”的时间里,获得了有别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文人所拥有的时间体验。迄今为止,学界少有人从“时间”的角度,深入探察“十七年”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诗人的时间观念及由此形成的时间体验。其实,“时间”视野中的“十七年”诗歌存在一些颇为有趣且有待厘清的问题,譬如“十七年”诗人的时间(观念)体验究竟呈现何种独特性,哪些因素催生了诗人的此种时间(观念)体验,这些时间(观念)体验对诗歌产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影响等等。本文拟从“断裂的时间”和“超越的时间”两个维度,考察和反思“十七年”诗歌中诗人时间意识的时代特性及其意义。
一、断裂的时间
在社会历史文化的重大转型期,“时间”不仅是人们界划新旧时代的独特标识,同时也是指认文化价值的重要指标。因此,“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历史上”,“留下了一串大大小小的断裂的现象与时间”[2]17。这种时间“断裂”意识在“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下孕育而生。在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循环时间观”一直广泛流行,直到“19世纪进化论的创立及其被广泛接受,使线性观念彻底取代了循环观的支配地位”[3],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诗人)的思想观念里也包含着相当浓厚的“循环时间观”,乐与悲、分与合、春与秋、成与败、荣与枯、因与果之间都相互接续、相互转化,历史、人生与自然进行着不无悲剧色彩的大循环。“五四”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启蒙思想的不断引入,知识分子的时间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种不断“进化”的单向“线性时间观”逐渐主宰着人们的头脑。这种观念强调时间和历史一样具有一维性和不可逆性,历史在向前涌动的时间洪流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每个新的历史阶段都是对前一历史阶段的“断裂”与“超越”。历史的“断裂”思维不断撩拨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时间“断裂”意识。
时间的“断裂”也就是切断过去与现在、昨天与今天、往年与今年等时间之间的联系,强调后者对前者的“告别”与“僭越”。在“十七年”诗歌中,诗人的“时间断裂”意识可从诗歌的想象方式和结构模式中显现出来。譬如阮章竞《祖国的早晨》如此写道:“在这辽阔纵横的土地上,/昨天,这里是丛草、湿水、泥泞,/今天,这里是钻探机、起重机、建设工棚,/过去,这里只出现老爷们的嘴巴、牙齿和爪子,/现在,这里出现的是棉纱、钢坯、水泥,/昨天,这里是牧人不饮牛羊的河流,/今天,崛起巨大的机器在吸引出石油。”这里,“昨天—今天”成为诗歌显在的结构模式和展开方式,而且诗中的时间是一种“断裂式”的时间,诗人着意呈现的是“昨天”和“今天”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诗人把“时间过程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4],时间逻辑内在地规约着价值逻辑。在诗人看来“今”与“昔”的“时间断裂”是土地“价值”生成的逻辑前提。另一些诗人则有意隐去有关时间的语词,而把时间断裂体验潜藏在文本深处,比如严阵的《老张的手》书写了贫农老张的“双手”,在解放前“放过财主的牛和马,/拉过财主的车和船,/拖秃了多少财主的锄头,/磨钝了多少财主的镰刀”,解放后“就用这双手,/把大山削平,/让河水改流”,“叩响大地的门环,/拉开了丰产的门栓”。这首诗歌以“手”为基本意象,展现在“解放”这一“关节点”的“时间断裂”给底层民众的命运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把“时间断裂”作为人实现自身价值内在依据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十七年”诗人想象的方式。对于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诗人)和底层民众而言,1949年是一个具有时间“拐点”意义的特殊年份,黑暗与光明、压迫与翻身、奴隶与主人、苦难与幸福、死亡与新生似乎都因这一神秘时刻的到来发生“断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伟大的日子来临!/经历了一百年的斗争,/中国人民走进胜利的拱门,/五星红旗飘扬在北京上空,/下面激荡着欢呼的人民
……/礼炮震动着整个地球,/全世界都在庆贺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我们和黑暗告别,/太阳在东方徐徐上升……”(艾青《我想念我的祖国》)。因之,把历史时间流程中的“1949年”设定为时间“断裂点”,并以此为基点将历史时间划为前后两个互不关联的区域,进而展示不同时间区域相异的历史景观,成为“十七年”诗人展开想象的独特方式,以及诗歌的常见结构模式。
“十七年”诗人的“时间断裂”意识既表现为一种诗歌结构模式,又体现为诗人告别过去、昨天的急切心理和兴奋情绪。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一诗洋溢着一种“欢乐”气氛,诗中既有时间开始的紧张与兴奋(“跨过这肃穆的一刹那,/时间,时间!/你一跃地站起来!”),又有实现“新生”的激动(“为了你的新生,/我奉上这欢喜的泪/为了你的母爱/我奉上感激的泪”),同时还有“初生”的荣耀(“在你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全地球都向你敬礼/全地球都向你祝贺”)。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举国上下的民众沉浸在“新生”的狂欢之中,许多人深信“新的时间”从此开始,在他们看来,“新的时间”已经切断了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现代、民主和自由的全新的历史空间。由于人们认为自己和过去历史时空永远决裂,并且奔赴更加美好地未来,因而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时间断裂”的幸福感和激动情绪。艾青的《春姑娘》即为显例,诗人把春天拟想为一个美丽、充满朝气的小姑娘:“她在田垅上走过,/母牛仰头看着,/小牛犊蹦跳着,/大羊羔咩咩地叫着……”;“她来到村子里,/家家户户都高兴,/一个个果园子,/都打开门来欢迎”;“各种各样的鸟,/唱出各种各样的歌,/每一只鸟都说:‘我们的心里真快乐!’”。春天是一年四季的开端,是一个代表万物复苏的时间意象,诗中的春姑娘象征新生的共和国,她的诞生意味着中国漫长的黑暗历史已经结束,新的历史画卷从此展开。满载着温暖、希望、活力的“春天”使大地万物为之“欢呼”、“蹦跳”与“歌唱”,这是“春天”告别“冬天”,时间“断裂”的巨大声响所带来生命振奋。
“断裂”之所以会成为诗人时间意识的重要表征,既与诗人内在的精神诉求有关,又和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密不可分。在“‘生存’成为压倒一切的需要”的1948年,“精神自由对于大多数人已成为一种奢望”,自由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历史循环论的悲观主义与怀疑主义的思维”[5],不断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质疑和批判。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虽然历史循环论能揭示历史的某些内在规律,但这种具有宿命意味的时间观念,却给处于生存困境之中的他们加上一条“永远轮回”的精神枷锁,于是,在艰难的生存现实中为了寻求精神出路,他们开始逐渐相信并最终坚信历史进化论和“时间断裂”观念,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信未来并寄希望于未来,实现精神的自我拯救和精神家园的重建。新中国的诞生作为具有非凡意义的历史事件,为“十七年”诗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的端点,这个带有“原点”性质的时间端点,使“过去”、“现在”和“未来”获得了对立的时间向度,所有的束缚、灾难、不幸和苦痛都向“过去”疾驰而去,所有的自由、安宁、幸福和欢乐都朝“现在”和“未来”飞奔而来。当“十七年”的诗人通过现实体验与历史记忆触摸这一时间“原点”时,他们所信奉的“时间断裂”观念便被有效激活,随着“断裂”的缝隙不断被放大、价值不断被提升,诗歌的深层结构和诗人的时间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在20世纪,中国“断裂和变革可以说是历史的中心主题”[2]102。“断裂”不仅是求变和逐新的知识分子时常表现出来的激进姿态,同时也是国家权力主体重建新的社会历史文化所采取的特殊意识形态策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了建构其历史的合法性,也不断强化知识分子的“时间断裂”意识。因为在文化上相对保守的知识分子看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新与旧之间的联系并不随历史时间的“转折”而中断,而是互相缠绕、互相含纳、互相影响的,这种成熟而又理性的文化理念常使知识分子处在矛盾、犹豫与迷茫之中,在新历史的门外徘徊又找不到归宿。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过于激进的新时代文化提出质疑和批评,这显然危及“新的人民文艺”的合法性建构。为此,国家权力主体通过各种传媒有意培养知识分子的“时间断裂”意识,让知识分子相信黑暗、反动、腐朽、落后的“历史”车轮已经在“断裂”的时间中戛然而止,而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新未来正扑面而至。这样一来,归属于不同时间区域的历史在意识形态系统的规约中逐渐本质化,人们就可以在本质化的历史中展开斗争、宣泄仇恨、拥抱未来,从而有效避免在关系网络中观照历史可能产生的风险。
诚然,这种“断裂”的线性时间观的给“十七年”的诗歌带来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线性的时间观把历史截为三段——过去、现在和未来,未来以及朝向未来的现实一同被注入了光明、希望的先在属性,而过去成为藏污纳垢、罪恶深重之所在,“这种以‘未来’为人类的过去、现实的存在提供终审判决标准的历史意识,隐藏在井井有条的历史表面现象下的无序状态,它并没有为人类的实践提供正确的规范,相反却把人类引向了时尚和浮华虚假表象背后的废墟和灾难”[6]。当“十七年”诗人被意识形态涂抹的历史时间所捕获时,他们一方面不可能揭示不同历史时段中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多维性与缠杂性,另一方面,也极容易把这种历史时间观情感化,即对“现在”与“未来”毫无保留的认同与陶醉和对“过去”妖魔化后的激情控诉:“我的明天将比过去好上无数倍——/它没有残杀与仇视,/它充满了更多的欢笑与友爱,/我的明天是甜美的日子,/欢乐的世界,/诗的时代!//我的明天将比过去好上无数倍——/它没有失业和贫困,/乡村和城市无法区分,/我的明天是美好的日子,/繁花的世界,/歌的时代!”(万里浪《时间之歌》)。这种线性进化的历史时间观极大地限制了诗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使“十七年”诗歌想象被囚禁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之中,出现了被当时一些批评家和后来研究者所诟病的“公式化”(程式化)弊端。
二、超越的时间
“时间断裂”意味着一个新的时间区域的敞开和新的历史画卷的展开,这既极大地振奋了曾经饱受战乱、渴望过上和平生活的诗人,同时又催生了他们力求超越“自然时间”流程以求早日实现生存困境的突围。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开始制定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些规划中的发展目标带有很鲜明的时间期限,这使得希望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设富强、民主国家而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的主体(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与时间赛跑、超越时间的平均流速、赶在时间前头”的时间观念。[7]在当时,超越自然(历史)时间并最终自由地驾驭时间,不仅是广大民众实现“翻身做主人”的别样方式,同时也是国家权力主体对共和国“新民”本质的深层期待。“十七年”诗人肩负着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时代重托,因而在诗歌中渗透并凸显“时间超越”的观念成为他们的时代选择。
首先,在“十七年”诗歌中,诗人的“时间超越”观念体现在描写劳动者以强者姿态对抗自然时间的归限上。对于“翻身”之后“进入一个新世界”[8]的广大民众来说,他们唯有以强者的姿态、崭新的精神面貌站在时间面前,才能真正彰显时代“新人”的英雄本色。雁翼的《夜行》描写了生产建设者与自然时间抗争的场景:在荒山上“一串串电灯挂在山腰,/暴雨浓雾也不能遮住它的光芒”,“在不眠的夜里”,桥梁工地上“电焊工把钢梁装订”,“为了加速建设亲爱的祖国,/我们把白天和黑夜统一起来使用”。一些新民歌亦反映了工农“与时间赛跑”的情景:“抓晴天,抢阴天,/小风小雪当好天,/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无雨拼命干。/赶早摸黑当半天,/汽灯底下当白天,/争取一天当两天……”;“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我们出工老半天,/你睡懒觉迟迟起;/我们抹黑才回来,/你早收工进地里……”这些诗歌反映了人们不断超越“昼”与“夜”的时间界限,试图在最短的单位时间内实现最大生产价值的雄心壮志。很显然,这些诗歌中所传达的是一种有别于农耕时代的现代时间观念。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人们生产生活一般顺应自然节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时间”作为一种神秘且不可抗拒的力量规约着诗人对自然与生命的想象,这一想象所建构的“从容”、“闲适”、“自在”、“怡然自得”的诗化世界,又进一步强化了诗人对周而复始的自然时间的向往、顺从与依赖。“顺从”被认为是人与时间“和解”和实现生命存在价值的最佳方式,这种与时间“和解”的方式使诗人不是以张扬人的生命意志和热力为旨归,而是以自我与时序契合为价值追求,因而也就不会出现人与时间对抗或激烈角逐的时间紧张。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提出要“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9]350。于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走在时间前面”,超越自然时间归限使“自然时间”向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时间”转化,被认为是快速实现富国强民理想的的一条捷径,这使得人们不断产生超越自然时间——白天和黑夜——对生产与生活制约的冲动,并且试图在超越的过程中赢得掌控时间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势中,“十七年”诗人力求通过诗歌激发广大民众投身现代化建设的激情,让他们把个体拥有的“自然时间”,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价值时间”。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尚未摆脱物质贫困的国家,超越时间的梦想有时又不得不受制于时序更替的强大规约力量。因此,不安与焦灼成为人们试图超越自然时间的一种常见心态。就“十七年”的“田园诗”而言,现代性的时间焦虑,使陶渊明诗歌中所描写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田园生活成为永远的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严阵笔下充满时间“焦愁”的农村:“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我们等了你多久多久,/多少次呵,我们从漫卷风雪的窗口,/以焦灼的目光,询问河边的杨柳。//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盼你从没有盼得这般焦愁,/最好的种子已经选出来啦,/我们要把它撒遍地球。”(严阵《春啊,春啊,播种的时候》)。这里,诗人对春天(季节)的“焦灼”等待显然已超越了陶渊明对时间的理解与感悟,这是因为陶渊明从田园获取的是一种精神资源,展示的是“归隐田园”的人生姿态,生命顺应时间律动才具有本真意义;而在1950年代诗人笔下的农村是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基地,因此时间就是物质财富,人们唯有充分驾驭时间,才能展现人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当然在从农村获取物质回报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可规避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希望通过驾驭甚至超越自然时间来获得更多的物质回报,另一方面,在一个农业生产相对落后的国家,农事活动又不得不受四季时序更替和节气的影响,这就引发了诗人的时间焦虑意识,使“十七年”的“田园诗”出现了与古代田园诗相异的别样景观。
其次,构造与渲染有限时间创造无数“奇迹”的“时间神话”,是“十七年”诗人在诗歌中表现“时间超越”观念的另一重要方式。具体表现为,诗人通过今昔比对书写创造“奇迹”的“当下时间”,并赋予其高度和神圣的价值,进而通过这一具有神圣性的时间来讴歌新生的民族国家和人民。1950-1960年代是一个渴望创造且相信能够创造“时间神话”的新时代,诚如冯至的《三门峡》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用五六年有限的时间,/结束了千百年无限的痛苦;/我们用十几年有限的时间,/创造了千百年无限的幸福。”这里,“有限”与“无限”突出了改变三门峡使人们由苦难历史到创造幸福现实之间的时间短暂得超乎过去的想象,即彰显创造“奇迹”的“当下时间”的神圣。同时,在毛泽东看来,时间问题是关乎新中国国家尊严、地位和形象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族人民,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10]“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9]500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唤醒了“十七年”诗人在时间面前的“主体意识”,强化了他们心中“赶超”的“时间意识”,引发了他们对“时间神话”编织的未来的激情想象与无限向往,最终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加入到构造“时间神话”的写作潮流之中。野丁的《世纪的飞跃——迎一九五八年》书写了创造奇迹的“时间神话”:“奔向社会主义的祖国啊,/一个年头你像跨过一个世纪,/我为你自豪但无须夸口,/事实比我的发言有力十倍”;“在火焰冲天的钢炉旁,/钢铁工人用通红的铁水,/创造通红的记录:‘五百二十四万吨!’,/只跨一步,旧中国要爬几十年,//昨天豺狼出没在富拉尔基草原,/如今千万辆汽车在日夜奔驰;/二十天盖起一座四层楼,/十二个月给祖国交来一个‘鞍钢’”。这里“一年”与“一个世纪”、“跨一步”与“爬几十年”之间出现巨大的时间反差,让人们看到的是走向现代化的新中国超越落后的旧中国在时间层面上所拥有的优势,这种“优势”已经或正在改变着现实,创造着“奇迹”。1958年被认为“是不平凡的一年,马克思的预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在这一年里得到了实现”[11]。在这个出现无数“时间神话”的“不平凡”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这一传遍街头巷尾的口号正是人们对“时间神话”的想象与期待,它不仅展现了“翻身”民众的巨大创造力和“宏伟的气魄”,同时还传递了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所爆发的“震惊全世界”的能量与潜力,正如有诗所言:“人有共产主义英雄劲,/马有多快好省四只蹄,/一股劲,/跑出二万五千里;/加鞭再加鞭,/把英国美国都抛在后边。”(何仲平《歌唱总路线》)在这种“时间神话”的激发下,“当下时间”的价值被有效放大,超越历史发展时间的时代梦想藉此不断展开,“现在”与“未来”成为实现人类乌托邦理想的时间政治。
不可否认的是,超越自然(历史)时间规限的时间体验确实改变了诗人感知现实世界的方式,使他们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和敏锐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在激发人的激情和斗志的同时,也使人被异化的时间所围困。“十七年”诗歌因过分关注并诗化“时间超越”的可能,忽视了超越的限度及其存在的危机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它不但没有触及时间之于个体的更加内在和微妙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而且也未能对时间的多维意义展开辩证思考和丰富想象。不过,激进的思想潮流不可能给诗歌预留敞亮的反思空间,“十七年”诗歌亦不以介入“现实”为旨归,担负批判现实的传统使命,因为其本身的特性就是对诗歌这种“传统使命”的蓄意“反动”与“超越”。
[1]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1.
[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吴国盛.时间的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95.
[4]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写作[M]//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9.
[5]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16.
[6]纪逗.本雅明的历史时间观念[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4):47-49.
[7]邵明.时间的意义——十七年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时间维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2):40-44.
[8]韩丁.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M]//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0:66.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89.
[11]天鹰.1958年中国新民歌运动[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1.
[责任编辑 朱 涛]
I227
:A
:1009-1513(2010)03-0039-05
2010-04-29
巫洪亮(1978-),男,福建永定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