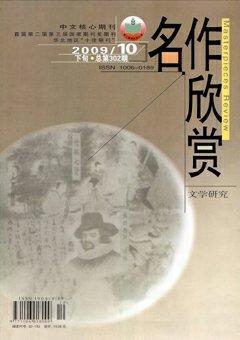叛逆与自溺
2009-10-29谭伟良
关键词:南朝乐府 民歌 女性形象 叛逆 自溺
摘 要:南朝乐府民歌女性形象是爱的化身。她们大胆热烈抒发自身的爱情体验,具有一定的叛逆性;同时又沉溺于爱的樊笼里不能自拔,表现为爱情角色的缺席、视角的褊狭和心理的依附。其性格的双重性反映了特定时代精神风貌。
民歌里风姿绰约的女性形象是中国古典诗歌一道靓丽的风景。如果说《诗经·国风》里的女子犹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汉乐府民歌里的女子像饱经风霜的枫林,闪烁着坚韧的光芒;那么,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子则是带刺的玫瑰,温柔的美丽中隐含着倔强的反抗。她们是爱的化身,大胆热烈抒发爱的情感体验,同时又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而溺于爱的樊笼里不能自拔,其性格的双重性反映了南朝女子特定的时代精神风貌。
一、爱的化身
《乐府诗集》收集的480多首南朝乐府民歌,90%以上为女性口吻歌唱的情诗,是“儿女情多的产物”①,风格自然清新。情诗中那些深情款款的女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叛逆的姿态,率真大胆地吟咏真爱,展示她们丰富细腻的心灵世界,体现了南朝时期女性意识的张扬。
1.女性形象的类型。南朝乐府民歌里的女子,有情窦初开的少女:“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子夜四时歌·春歌·其一》),“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春歌·其十》),两首诗隐约透露了少女爱情上的初醒:明媚的春光叩开了少女的心扉,春花的鲜艳触发了她春情的萌动,多情的春风撩拨着少女的心扉,流露了她内心的惊喜、羞涩和对爱情的期待。更多的是恋爱中深情缠绵的女子。她们或欢娱恨短:“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把怨恨之情一股脑儿发泄在“长鸣鸡”和“乌臼鸟”身上,其嗔怒之态如在目前;或备受相思煎熬:“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子夜歌》)连用三个反问句有力传达出女子独守空房,倚门怀人的思愁。此外,还有凄楚哀怨的弃妇:“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以“丝”谐“思”、以布匹的“匹”双关匹配的“匹”,委婉地表达女子与恋人分手后的悲怨。女性形象类型的丰富性体现了南朝女子情爱完整的内心历程。
2.女性自我意识的彰显。女性的自我意识,是指女性作为有感觉能思维的人的认识主体,对自身存在的价值、道德、审美等一系列活动的认识、感受和评价。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女性形象,集中体现她们自由自主的爱情观。
首先,她们向往自由恋爱。她们渴望一见钟情的邂逅,以此来对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夜歌》前二首写一对少男少女邂逅产生爱慕之情,其中“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两句写女方认为他们的相遇是老天爷的故意安排,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以此表白对男方的爱慕。“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长干曲》)写女子看见邻船的一位男子便邀他同行,且告诉对方自己家住哪,意思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男子身份大多是外地的商贩或四处漂泊的水手,南朝乐府民歌里往往只有女子对他们的爱恋、情长似水,丝毫没有对选择这种一见钟情的漂泊爱情的后悔之意。从她们选择爱的对象、方式和态度看,是对传统思想的一种挑战。
其次,她们表达情感率真热烈,毫无掩饰地抒写爱情中的悲欢忧喜。写与情人的分别令人肝肠寸断:“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便是一曲曲执手相看、泪洒江水的送别哀歌。表达相思之苦和爱情之坚淋漓尽致:《西洲曲》更是把悠悠相思情写得缠绵悱恻。女主人公从春夏到秋冬,从出门采莲到倚楼远望,从现实到“海水悠悠”入梦,极尽时空循环往复的变幻写出她执著的等待,相思虽苦却永远不会放弃。对于爱情,她们如此坚定:“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为情而死;她们坦然面对被弃的命运:“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子夜歌》)以太阳白天的升落比喻男子的朝三暮四并对他进行了谴责,“常虑有贰意,欢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清流乖。”(《子夜歌·其十八》)对负心人颇为不屑和鄙夷,虽然没有《诗经》里的女子那么果敢决绝,但也不全是低三下四哀求对方的回心转意,而是保持了一份清醒与理智。
再次,她们大胆书写性爱的欢乐。人感性的生理欲望,是人的生理本能。情爱之中如果缺少了性爱,就不是完整而健康的爱情。可是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下,情欲视为龌龊卑贱的、难以启齿的东西。汉乐府民歌女子往往更关注伦理道德之美,对情欲的问题,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回避不写;而南朝乐府民歌开始把触角伸到性爱领域。她们对性爱的大胆表露突破了儒教的束缚:“香巾抚玉席,共郎登楼寝”(《子夜四时歌·夏歌》),“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抱郎”(《碧玉歌》),直露描摹幽会的情景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大胆颠覆,在南朝乐府中随处可觅。
南朝乐府民歌前所未有地、集中地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多角度多侧面展示了她们情爱历程和心灵世界。与汉乐府相比,南朝乐府民歌中强化了女性对情爱的强烈的渴求与感受。其情感体验的真实性、态度的真诚性、表达的热烈性正是南朝时代女性对传统道德的叛逆和自我意识的张扬,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诗经·国风》“思无邪”天然美的回归。
“自汉末的社会动荡开始,传统的礼教规范受到了剧烈冲击,造成了精神史上自由、解放的时代。单是女性的自我解放也蔚然成风:她们……对于爱情率性而行。”②此外,商业的发达,享乐风气盛行对人性的解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朝乐府采诗以娱乐声色为目的,便成为人性张扬和女性意识表达的舞台。
二、“他者”的自溺
自人类文明进入男权社会以来,“定义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她是附属的人……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③于是,娇艳柔弱,物化、仆化的女人,成为他们的理想女性,女人按这种标准完成了自己形象的塑造,南朝女子亦不例外浸蕴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城市商品化的审美诉求,文人纵情感官享乐的“物欲化”倾向、流行一时的宫体诗柔弱审美风气的影响,使南朝女子更难以完全摆脱“第二性”的“他者”命运。因此,我们在真诚赞美与讴歌女性意识张扬的同时,亦不能忽视这些女性形象隐性“自溺”的一面,即她们以“他者”“客体”的角色,沉浸在自己按男性理想所构建的情感空间里,始终不能自拔。
1.独白:爱情角色的缺席 爱情是男女之间相互爱恋的感情,是至高至纯至美的美感和情感体验。其外在表征为两性彼此喜欢、相互吸引的愉悦。可南朝民歌,似乎只见轰轰烈烈出场的女性,作为爱情的另一方——男子,处于缺席状态。南朝民歌不再有《诗经·国风》“投之以琼瑶,报之以木瓜”的相悦,见不到男子“道阻且长”却“溯游从之”的执著、“求之不得”而“寤寐思服”的相思和欣然接受女子邀请并“赠之芍药”的大方,只剩下女子的独白、呼唤与期盼,成为一厢情愿的卖弄风情。请听:“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但问相随否,何计道里长”(《襄阳乐·其二》)的女子向男子表达爱情,何等热烈;“折杨柳,百鸟园林啼,道欢不离口”(《读曲歌》)中的女子一声声叫唤自己喜欢的人的名字,何等痴情!然而不过是一出孤零的独角戏罢了。
2.色欲:爱情视角的褊狭 色欲是南朝民歌爱情表达的重要内容。不论“淑女总角时,唤作小姑子。容艳初春花,人见谁不爱”(《欢好曲·其一》)的人见人爱;“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襄阳乐其一》),男子见到如花似玉的少女目眩心动;“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国色”(《碧玉歌》),因没有美色而惭愧,“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下,何处不可怜”(《子夜歌·其三》),写女子慵懒、柔媚的姿态;“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裳。含笑葳幌里,举体兰麝香”、“碧玉捣衣砧,七宝金莲杵。高举徐徐下,轻捣只为汝”(《青阳度》)则是色性赤裸裸的描绘。于是,色欲的欢娱带着轻佻的香艳暧昧,在人性情欲的张扬同时慢慢消解着爱情纯美的内在精神本质。
虽然,“身体本质上是一个表达的空间”④,但色欲的宣泄与放纵必然忽视爱情内涵的丰富性,导致了爱情视角的偏移狭窄。男权社会里,女性生活被裁剪得只剩下婚恋生活的一角,而美色与爱欲成为爱的基础前提和内容,也成为女子的情爱价值仅存。除此,她们不知道自己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男权社会把女性异化为“看”的物品与“用”的工具,而女子在不知不觉沉溺于此,忘了摆脱,也无从摆脱。
3.卑柔:爱情心理的依附 和《诗经》相比便可发现,《诗经》里的女性由于生活在性对男子没有多少依附心理的时代,她们自信乐观而独立:“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郑风·褰裳》),即使被弃,也认为“不我与,其后也悔”(《召南·江有汜》)。而南朝民歌爱情中的女子却是卑柔的:“女萝自微薄,寄托长松表。何惜负霜死,贵得相缭绕”(《襄阳乐·其三》),以富有象征意义的女萝(柔弱)攀绕依附长松比喻女子向男子托付终身。她们即使是沉浸在幸福中也夹杂着一种对未来的忐忑:“烂漫女萝草,结曲绕长松。三春虽同色,岁寒非处侬。”(《襄阳乐·其五》),担心寒冬来临时,松树依旧青翠,而女萝(自己)就要枯萎、凋零。有的女子甚至一开始预料到不幸结局:“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子夜歌·其十三》),最快乐忘情之时也抹不去心头的阴影。总之,两性关系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造成女性主体意识失落与无法复归,南朝乐府女子用卑柔之“藤”编织了情爱幻境而把自己缠绕在其中,无法逃逸。
真正的爱情角色双方,是“相看两不厌”的“相看”,不仅仅是“看”或“被看”;是心心相印的“相爱”,不仅仅是“爱”或“被爱”。南朝乐府爱情诗中的女子无法摆脱作为“他者”的客体身份角色,她们深情美丽而孤独的背影,只能是《诗经·国风》里怡然相悦的两性风情一道微弱的回声。
作者简介:谭伟良,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研究。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13.
② 赵东栓.中国文学史话[M].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37.
③ [法]西蒙那·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4-5.
④ [法]莫里斯·梅洛·庞帝.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46.
(责任编辑:吕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