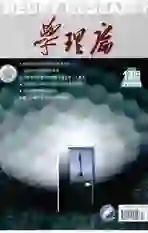国家为什么要补偿犯罪被害人
2009-01-14胡国建
胡国建
摘要: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在西方国家一直是争论不休,主要存在社会契约/保护失败理论、风险共担/社会保险理论、社会福利/道义责任理论、政治动机或政治工具理论等四种学说。归纳并梳理这些观点对我国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被害人;国家补偿;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DF52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2—0073—03
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从犯罪人或其他途径获得赔偿时,由国家依法给予其一定物质帮助的一种司法保护制度。它是与犯罪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完全不同而由国家承担的一种补偿性责任。自1964年新西兰第一个在法律上确立对犯罪被害人给予国家补偿伊始,现代西方国家普遍都建立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但时至今日,关于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具体理论基础的论争一直并未结束。每一种理论基础都将会对补偿制度的内容及其目标模式产生巨大影响。归纳并梳理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本质和我国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被害人补偿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理论或学说:
一、社会契约/保护失败理论
该理论认为国家有责任保护其公民免于犯罪的侵害。认为依据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国家独占防卫力量,有权禁止公民在遭遇犯罪侵害时寻求私力救济;相应地,国家则负有预防犯罪使人民免于犯罪侵害的义务。对于国家未尽预防犯罪之责任而保护失败时,国家即违背了其义务。犯罪对被害人的损害,国家理应负补偿责任,被害人则享有要求国家依法给予补偿的权利。早期英国的社会改革家Margery Fry,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积极倡导者即认为国家有责任补偿被害人。[1]
社会契约/保护失败理论自其产生就受到质疑。批评者认为,第一,“社会契约理论颠倒了责任与是非,因为是罪犯,而不是国家的错误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2]“将犯罪的责任归于国家实为杜撰和虚构,完全忽视了犯罪者的个人意愿”。[3]“而且,国家或政府可以消灭所有的暴力犯罪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企图让国家在其能力之外消灭所有的犯罪将会导致国家警察权力的压迫和肆虐,进而侵害到所有公民的自由。”[4]此外,“将每一个具体的犯罪都归因于某个特定的政府的过错,这种假设本身也是脆弱无力的。”因为“是否成为被害人并不必然依赖于政府的义务或过错,至少对大部分犯罪来说是这样”。[5]第二,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仅犯罪被害人受到特殊的补偿待遇甚至仅仅部分犯罪受害人可以获得补偿”。“以此基础来分析,政府应该负有对犯罪被害人和未参加保险的摩托车事故的被害人平等给予补偿的义务,因为是政府控制着驾驶执照和要求‘强制性保险。”[6]因此,国家对于其无法完全控制的犯罪所造成的被害人的损失给予补偿,而对其更能控制的摩托车事故所致被害人损失,却又不予补偿,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鉴于社会契约/保护失败理论所面临的诸多责难,美国学者Elias1983年曾经提出,补偿应该建立在权利理论基础之上。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责任包括严格责任理论和政府过失理论。严格责任理论建议政府违反保护公民免于犯罪侵害的一般性义务因而违反了社会契约时直接就应对其承担违约责任——补偿被害人,不论国家有无过失;而政府过失理论则认为国家仅对政府执法部门因预防犯罪之过失所致犯罪才承担补偿之责任。[7]政府过失理论实际上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责任的缓和。但仍然认为补偿的依据在于国家自身的责任——非道德意义上的责任。
被害人补偿基础的国家责任的进一步后退或淡化的是国家间接责任论,又被称为妨碍赔偿论的出现。该观点认为国家在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即对犯罪人科处罚金或者自由刑,影响了加害人的经济能力和赔偿能力。因此,国家应该对其影响加害人赔偿能力的行为负责,弥补加害人赔偿能力的不足,在加害人无力赔偿时国家应对被害人补偿。[8]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国家虽然有剥夺被告人因为犯罪所获取经济利益的权利,但却无权因此影响被害人的利益。”[9]妨碍赔偿论该种观点的赞同者不多。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犯罪人未被抓获,国家并未对其施加罚金或自由刑,因而没有影响加害人的经济赔偿能力时,国家依然要对被害人给予补偿。无论是政府过失理论,还是妨碍赔偿论,都强调国家补偿均是出于国家自己责任的存在。因此,所谓的国家补偿,实为国家赔偿。
二、风险共担/社会保险理论
该学说认为有社会就有犯罪,自古皆然,无可避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犯罪行为的潜在被害人。被害人之所以被害实际上是由于他被“适当机会选择出来的不幸者”,对被害人自己的不幸,理应由社会全体成员来共同承担。国家对被害人补偿或援助实乃代表社会共同承担被害人的不幸。因此人民平时向国家缴纳的税金实际上是在购买保险,以应对犯罪侵害后面临困境的意外事故,国家与公民之间实际上以默示方式签定了保险契约。一旦遭受犯罪侵害,在被害人符合保险契约约定的条件下,被害人就有从国家那里获取一定物质补偿的权利,国家则负有依保险契约给付一定金额的义务。此种保险类似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险,属于一种附加的社会保险。该说建立在犯罪被害的宿命论和被害风险的社会化分配的基础之上。与国家责任说不同,它并不强调国家对某种社会契约和保护义务的违反,而仅仅强调被害人风险分散的保险法则。只要被害人符合保险契约中的约定条件,国家就以保险人的身份给予金钱补偿。责任乃违反第一性义务而产生的第二性义务,保险契约给付义务乃第一性义务。被害人国家补偿理论的先驱,英国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最早就是该理论的代表者。边沁认为,“这种公费补偿责任建立在一条公理之上:一笔钱款分摊在众人中,与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身上相比,对每个捐献者而言,实在微不足道。”“犯罪所造成的灾难与自然灾难别无两样。如果由于房屋火灾被保险,房屋主人可以安心的话,如另外又能对抢劫损害保险,他会更为高枕无忧。”[10]
该理论强调所有的公民共同分担犯罪被害的成本和风险,在实践中也受到诸多置疑。批评者认为既为保险,为何偏偏要国家而不是社会性的保险机构来充当保险人呢?不过支持者认为,从损失分配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唯一具有的高效率地分配这些损失的能力以及国家保证公共福利的一般性责任表明,国家有责任建立这样的补偿制度”。[11]批评者还提出,既然公民纳税即为缴纳保险费,那么未成年人或流浪者等“未纳税者”是否就被认为是未缴纳保险费因而无权得到国家补偿呢?既然国家补偿是保险,那么国家补偿基金的来源应是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但实际情况是不少国家的补偿制度都不愿从国家的一般财政收入中支付被害人补偿金,而主要用罪犯的罚金、罪犯服刑期间的所得和从每个罪犯身上征收的特定税收来作为被害人补偿基金。因此,“这种理论并不适用于像弗罗里达州这样不动用一般性税收来补偿被害人的国家”。[12]该理论并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补偿立法的实践。
三、社会福利/道义责任理论
目前,许多国家采纳了这种不定型或盲目的道义责任理论作为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弗罗里达州即是其中一例。该州的《犯罪补偿法》规定:“本法认识到许多直接由于犯罪行为或防止犯罪或抓捕正在实施犯罪或企图实施犯罪因而无辜受到个人伤害或死亡的被害人的痛苦。这些被害人将会遭受伤残、经济困境,或依靠经济援助。本法决定有必要对这些犯罪被害人提供政府经济援助。当然,本法目的仅在于为这些犯罪被害人提供道义责任上的援助。” [13]社会福利/道义责任理论强调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乃是一种对处于不利社会地位者在不存在国家法律义务与责任的前提下的公共援助。该理论认为,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重大财产和身心伤害后在诉讼程序中往往又成为检察官和被告方争斗下的祭品,受到“二次伤害”,在无法从犯罪人处获得应有赔偿时其处境凄惨,极为可怜,对处于这种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害人,国家和政府应伸出援助之手,给予起码的人道扶助。补偿乃自由、社会福利理想之产物,而非被害人之权利。因此帮助因犯罪而陷入贫困之无辜被害人,是国家一般福利的延伸。对被害人进行补偿非国家在承担其责任,而是在行善,被害人没有先验的要求国家赔偿的权利。因此国家有权在其自身财力和经济基础允许的范围内对补偿条件和数额等进行限制。该说又被称为生活保护理论。
该理论也受到了强烈的批评。第一个批评是“这种理论缺乏法律基础;国家创造这样一个道德义务的权力不应与立法的原因相混淆”。[14]“社会福利理论的问题在于,国家有权力提供一般性福利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国家也会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为犯罪被害人提供福利。”[15]因此,该理论无法回答为什么国家仅补偿犯罪的被害人,而忽略其他像自然灾害的被害人等同样值得补偿的被害人呢?补偿既为社会福利,却为何对不同的被害人区别对待、厚此薄彼呢?也许这样重要的问题无法仅仅用“犯罪被害人优先考虑”(“first things first”)来回答,因为立法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政策制定的过程。因此不少人认为国家补偿犯罪被害人而不补偿自然灾害的被害人与以上提到的社会契约/保护失败理论有关,即“既然社会本身创造了犯罪产生的条件,就应该由社会来补偿犯罪被害人。”“然而这种答案并未给社会福利理论提供充分的依据,相反更加反应出社会福利理论本来就缺乏法律基础”。[16]社会福利理论面临的第二个批评是,“社会福利理论扩大了福利国家的权力,助长了对‘政府家长主义的依赖”。[17]这种批评认为,“宁可让犯罪被害人独自忍受经济损失,也不能通过被害人国家补偿来冒助长社会主义风气的风险。”“认为不要政府援助会‘增强人的道德脆弱感的观点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18]
四、政治动机或政治工具理论
该说主张,“国家之所以提供补偿,是因为补偿本身非常流行;国家补偿不仅赢得了被害人对司法制度的支持,而且赢得了那些未被犯罪侵害,不需要国家补偿但因知道该项制度的存在因而感到很安全的公民的支持”。[19]传统司法制度只是一味地保护被告人的利益,现行司法制度依然漠视被害人的利益,由此造成被害人和被告人利益的失衡,无法赢得被害人的信任,致使其不愿与司法机关进行合作,犯罪率上升,犯罪的报案率和追速率却让人失望。这种恶性循环致使社会预防犯罪、打击犯罪功能的减弱。“国家补偿作为政治工具可以赢得公众和被害人对刑事司法制度的支持和在预防、追诉犯罪中的更广泛的合作”。“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被害人补偿实践中都包含了这个原理”。[20]以此为理论基础的补偿法必然要求被害人在被侵害后向司法机关报案和积极协助配合司法为补偿的前提条件。该理论强调增加被害人与司法机关合作的积极性、消除对被害人的排斥与歧视以及延长各届政府的任期等原因作为国家补偿被害人的基础。“然而,仔细分析,这些观点仅仅是被害人补偿立法所带来的额外好处,而非补偿的内在理论基础。”[21]因此,政治动机理论实际上是每个补偿立法制度都内含的企图,甚至可以说是被害人补偿制度确立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但国家补偿被害人的理论根据却并不在于此。因此学界所主张的基于现实政策考虑而提出的被害人补偿根据之“形势政策论”、“现实观察论”等均难以独立作为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根据。[22]
值得注意的是,以现实政策需求为导向的政治动机理论中有一种被称为“奖励说”的观点。该“奖励说”认为,国家刑法的贯彻执行离不开被害人的协助,对被害人的协助,国家应该给予相应的奖励。因为“国家期待着犯罪被害人会告诉并协助国家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人,而对其他各种无偿付能力的一般侵权行为的被害人则无此期待。”“被害人补偿可以象征性地认可被害人对社会总体福利的贡献”。[23]然而在现行绝大多数补偿立法实践中,奖励说是存在问题的。许多被害人补偿立法仅仅补偿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并且经常要求被害人是“无辜的”,以排除对于犯罪发生有责任的被害人。而这些限制反而打击了被害人协助司法的积极性。不仅如此,既为奖励,却又为何又不想让更多的被害人知道呢?既为对被害人对社会总体福利所做贡献的认可,那么必然应该承认社会总体都有帮助建立补偿基金的义务和责任,而不应该是仅仅或主要依靠对罪犯所征纳的税收来建立补偿基金。不愿放弃应由罪犯自己直接或间接补偿被害人的前提,已经弱化了将被害人补偿作为社会集体反应即奖励被害人对社会总体福利所做贡献的理由。[24]
参考文献:
[1]Lynne N.Henderson,《The Wrongs of VictimsRights》,37 Stan.L.Rev.April,1985。
[2]Lesley J. Friedsam《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 ,WINTER,1984。
[3]Childres:《CompensationforCriminallyInflictedPersonalInjury》,39 N.Y .U. L.REV.1964。
[4] Lesley J. Friedsam《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 ,WINTER,1984。
[5]Brooks, < [6]Lynne N.Henderson,《TheWrongsofVictimsRights》,37 Stan.L.Rev.April,1985。 [7]SUSAN KISS SARNOFF:《PAYINGFORCRIME:ThePolicesandPossibilitiesofCrimeVictim Reimbursement 》,PraegerPublishers,1996,P12。 [8] Brooks, < [9]杨正万著.《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从诉讼角度的观察[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35. [10](英)吉米、边沁著,李贵方等译.立法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368. [11]Koning,《CompensationForVictimsofCrime----TheTexasApproach》,34 Sw.L.J.1981。 [12] Lesley J. Friedsam 《 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 》,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 ,WINTER,1984。
[13] Lesley J. Friedsam 《 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 》,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 ,WINTER,1984。
[14] Lesley J. Friedsam 《 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 》,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 ,WINTER,1984。
[15]Koning, 《CompensationForVictimsofCrime----TheTexasApproach》,34 Sw.L.J.1981。
[16]Lesley J. Friedsam 《 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 》,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INTER,1984。
[17]Lesley J. Friedsam 《 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 》,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 ,WINTER,1984。。
[18]Lesley J. Friedsam 《 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 》,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 ,WINTER,1984。
[19]SUSAN KISS SARNOFF:《 PAYINGFORCRIME:ThePolicesandPossibilitiesofCrimeVictimReimbursement 》,PraegerPublishers,1996,P13。
[20]Peggy M.Tobolowsky:《Crime Victim Rights and Remedies》,CAROLINAACADEMICPRESS,2001,P159。
[21]Lesley J. Friedsam 《 LEGISLATIVEASSISTANCETOVICTIMSOFCRIME: THEFLORIDACRIMESCOMPENSATIONACT 》,FLORIDASTATEUNIVERSITYLAWREVIEW ,WINTER,1984。。
[22]杨正万著.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从诉讼角度的观察[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35-336.
[23]Lynne N.Henderson,《TheWrongsofVictimsRights》,37 Stan.L.Rev.April,1985。
[24]Lynne N.Henderson,《TheWrongsofVictimsRights》,37 Stan.L.Rev.April,1985。
(责任编辑/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