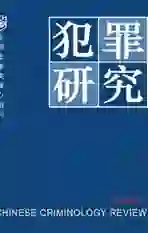诉讼欺诈的财产犯罪侧面
2016-12-01陈文昊
陈文昊
内容摘要: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概念本身是规范意义上的民法概念,不同于刑法中的“犯罪对象”,不能理解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作用者。因此,存在被骗者与被害者相分离的情况,“保姆案”与金融诈骗便是典型的三角诈骗。“自愿交付”系诈骗罪成立的表明构成要素,如果不是“自愿交付”的,不能得出不成立犯罪的结论,而是成立更为严重的敲诈勒索罪或抢劫罪。在诉讼欺诈的理解上,应当考察到其侵害财产的层面,不能为虚假诉讼罪完全评价。诉讼欺诈完全可以视为通过司法机器行使财产犯罪的情形,同时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按照想象竞合原理进行处罚。
关键词:诉讼欺诈;被害人;虚假诉讼罪
杨兴培教授在《法治研究》2015年第六期发表《诉讼欺诈按诈骗罪论处是非探讨——兼论<刑法修正案(九)>之诉讼欺诈罪》(以下简称杨文),对虚假诉讼罪的构成及性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见解独到。笔者对其中部分观点存在于异议,欲就以下问题求教于杨兴培教授。
一、杨文的逻辑线梳理
杨文在“诉讼欺诈不构成诈骗罪”这一核心论点上,主要提出了以下的论据:
(一)“三角诈骗”的概念不应当存在,诉讼诈骗不能理解为成立三角诈骗。主要理由包括:
1.三角诈骗中的被骗人不是被骗之财物的所有权人或占有人,而对于被骗人而言,脱离所有权与占有之外的处分权能在刑法中是不存在的。(第49页)
2.刑事被害人应当是指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因此,被骗者就是诈骗的直接侵害对象。(第49页)
3.在“保姆案”中,无论保姆是否具有雇主的授权或委托处分之权限,都是二元的诈骗关系,不存在三角诈骗的情形。(第49-50页)
4.在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的场合,银行要么作为承担责任的直接被害人;要么其履职行为不构成处分,诈骗发生在行为人与受损客户之间。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没有突破诈骗罪的二元关系结构。(第50页)
(二)诉讼诈骗也不能理解为普通的二元诈骗结构。主要理由包括:
1.虚假诉讼罪骗取的是法院的有利判决而非财物。(第51页)
2.虚假诉讼中法院依据证据规则、法律事实作出的民事判决没有选择性,不能认定为“自愿处分”。(第51页)
3.被害人基于判决结果承担败诉后果,不能认为是“自愿交付”。(第51页)
在笔者来看,抛开实质内容不谈,杨文在以上的论述过程中存在形式上的逻辑漏洞:
首先,论据(一)中1、2的结论与3、4相矛盾。根据论据(一)1,如果认为被骗人对于他人的财物不具有处分权能,意味着通过民事的追偿,被骗人将成为最终的受损者,这一结论与论据(一)2的结论相吻合,即在所谓的“三角诈骗”当中,被骗者就是诈骗的直接侵害对象。然而,在论据(一)的3和4中,无论是“保姆案”还是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的场合,被害人根据情况的不同既有可能是被骗人,又有可能是原权利人。例如,在“保姆案”中,杨文指出,“如果保姆获得了雇主的授权或委托具有处分权限,成立保姆与行为人之间的诈骗;如果保姆不具有处分权限,行为人成立盗窃,雇主是被害人”。(第49-50页)而在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的场合,杨文指出:“信用卡诈骗在只需签名即可的方式之下,银行是金融诈骗罪的直接被害人,这种冒用是普通的二者之间的诈骗关系;而在需要密码和签名双重确认的方式之下,银行只是履约或履职行为,被骗人是持卡人、付款人本人,因此仍是两者之间的诈骗关系”。(第50页)换言之,杨文一方面试图坚持将被骗人作为刑法上的被害人对待,但另一方面在所举的两个案例中却得出了不相自洽的结论。
其次,论据(二)中的1、2与3相矛盾。根据杨文的论证步骤,论据(一)已经排除了三角诈骗的存在空间,论据(二)进一步论证二元诈骗不包括诉讼欺诈的情形。但是,在“二元欺诈的另一方是谁”这一问题上,杨文给出的答案却是莫衷一是的。一方面,论据(二)1和(二)2将法院作为二元欺诈的对方,认为法院由于没有“处分财物”、没有“自愿处分”,不能成立诈骗罪。但是到了论据(二)3当中,杨文的思维突然发生了实质性的跳跃,认为在诉讼中受到损失的原权利人没有“自愿交付”,因而不成立诈骗罪,这便是将欺诈的对象锁定为在诉讼中受到损失的原权利人。问题在于,诉讼欺诈的对象到底是法院还是在诉讼中受到损失的原权利人?从杨文中看不出明确的回答。论据(一)中1、2与3、4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也是同样的问题。
杨文对于“三角诈骗”的概念进行了批判,试图用传统的二元模式解释诈骗罪中的参与结构。但问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大量的被骗人与被害人相分离的情形,无法用传统的二元结构加以说明。因此,杨文在论证中无法从一而终地坚持和贯穿“被骗者就是被害人”的立场,在个案中不断变更作为欺诈对方的角色设定,造成了逻辑上的矛盾。在笔者看来,“三角诈骗”概念具有本身的合理性,试图通过颠覆该理论的论证进路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下文的论证将从实质的角度对杨文中的核心论点进行厘清。
二、刑法中的被害人是受到损失之人
以往否定“诉讼欺诈成立诈骗”的观点,往往都是承认“三角诈骗”的概念,但认为诉讼诈骗与三角诈骗存在本质上的区别。通过这条进路将诉讼欺诈的情形排除在诈骗罪之外。 而杨文另辟蹊径,直指“三角诈骗罪是一个伪命题”。(第48页)其核心论点在于,在刑法中,脱离于所有权人与占有人之外的处分权能并不存在。不同于民事制度中的被害人,刑事被害人应当是指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因此,“受托人、代理人、管理人等受欺诈而产生损害后果由受托人、代理人、管理人对损害后果分配,应当认定为被害人”。(第49页)既然被骗人就是被害人,那么也就不存在对象发生错位的情形,“三角诈骗”的概念就应当被否定。然而,对于这一结论,笔者并不能赞同。
首先,区分“刑法上的被害人”与“民法上的被害人”不仅不必要,而且不可能。在刑事法中,实行行为所作用的人、物、组织被称为“犯罪对象”。由于人、物、组织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因此可以说,“犯罪对象”的概念是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而与之不同,民法中的“被害人”概念是指遭受到财产损失的人,它必须要通过民法体系的评价加以确定,可以说是规范论意义上的。在刑法体系当中,本身并不存在“被害人”这一概念,为了解决财产犯罪中的损失归属与罪名认定等问题,才从民法当中借用了“被害人”的概念。由此可见,既然本身就不存在“刑法上的被害人”这一说法,就更没有必要区分“刑法上的被害人”与“民法上的被害人”。杨文显然是将“被害人”的概念与“犯罪对象”相混淆了。
其次,如果将被害人界定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会存在诸多问题。从上下文的逻辑来看,杨文将“受托人、代理人、管理人”等受到欺骗者视为被害人,是将“直接”理解为身体动作、言语上的“直接作用”了。然而,这样的理解显然存在问题。例如,在行为人教唆他人盗窃的场合,行为人的言语作用于被教唆者,根据杨文的观点,实施盗窃行为的被教唆者才是本案中的被害人;再如,行为人对超市柜台的营业员进行威胁,逼迫其交出超市财物的,根据杨文的观点,营业员是被害人。但是,以上的结论显然不妥。更重要的一点是,在例如盗窃电力的场合,行为人的行为仅仅是作用于物,不存在所谓被犯罪行为直接作用意义上的“被害人”,因此被害人的确定最终还是要回到规范论意义上的所有权人之上。由此可见,将刑法上的被害人界定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实有不妥之处,究其原因,还是将“被害人”的概念与“犯罪对象”的概念一视同仁了。
再次,杨文还指出,在民事关系中,确实存在既不是占有人或所有权人而又享有处分权的权利人,但在刑法中却有所不同。(第49页)但是,这样的结论却是值得推敲的。其实,既然谈到了“处分权”,就不是刑法体系本身衍生出的概念。刑法之所以引入“受托人”、“代理人”、“管理人”、“处分权”这样的概念,无非是为了解决损失归属的问题,进一步对被害人进行锁定,以确定罪名构成。杨文在这里采用了一个奇怪的逻辑,那就认为刑法和民法中的“处分权”不是一个概念,主张将二者独立看待。但问题在于,刑法是解决犯罪问题的部门法,而犯罪体系本身不可能从自身建构出一个“处分权”的概念。一方面引自民法,一方面又脱离民法的框架进行界定,这在逻辑上无法周延。
最后,杨文试图区分“直接被害人”与“间接被害人”的概念。指出:“按照相应的民事制度,代理人、监护人如按照约定或相关规定已恪尽职守而被骗的,他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并且依照民事法律的规定,其受到的损失可以向委托人、代理人追偿”;“委托人、被代理人等被管理人不是诈骗罪的直接被害人,而是基于代理制度、委托制度、管理制度承担损害后果而事后塑造的被害人之身份”。(第49页)在笔者来看,杨文将被骗者视为直接被害人,原权利人视为间接被害人,显然是本末倒置了。实际上,刑法在被害人的确定上考察法益受到侵害者,因而直接受到犯罪侵害的当然是原权利人、占有人。在此之后,如果受骗的代理人、监护人具有责任的,原权利人可以基于“代理制度、委托制度、管理制度”向其追偿,当然,这已经是刑法范围之外的问题了。
由此可见,对于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本来就应当与民法中的“被害人”做相同的理解,也就是财产权利或占有状态遭受戕害的人。实际上,做这样的理解,也与刑法保护法益的机能相弥合。在财产犯罪的法益确定上,本权说与占有说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无论是本权还是占有,都可以作为刑法中的法益加以对待,而本权或占有因犯罪行为受到损害的人就是被害人。
三、“保姆案”与金融诈骗都是典型的三角诈骗
杨文对于“保姆案”与金融诈骗的情形做了颇具见解的分析。在“保姆案”中,杨文提出了以下论点:
第一,“如果保姆获得了雇主之授权或委托具有处分之权限,诈骗关系得以生成,但并非三角诈骗论者声称的行为人与保姆以及雇主之间的三角关系,而是成立了保姆与行为人之间的诈骗关系”。(第49页)
第二,“倘若保姆没有获得授权或委托,即受骗之保姆并不具有处分权,此时诈骗罪便难以成立,行为人的行为便是盗窃”。(第50页)
笔者认同第二个结论,即在保姆没有获得授权或委托的情况下,应当将行为人认定为盗窃罪的间接正犯,这与德日理论中三角诈骗与间接正犯的区分结论是一致的,即“只有当被害人以外的其他人所实施的占有转移行为可以视为‘基于被害人意思的交付时,才可以肯定交付行为” 。问题还是在于,在保姆具有处分权的情况下,杨文否定三角诈骗,将这种情形直接认定为普通的二元诈骗结构。这里需要具体分析的就是,此处将保姆理解为被害人,是否妥当?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不可否认的是,保姆是衣物的占有者,行为人的欺诈行为在侵害雇主所有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保姆的占有。但是,如果将保姆确定为为被害人,那就得出保姆就要为衣物承担损失的结论。问题在于,一方面,占有只是一种事实状态,从一开始,与效用无关的、单纯的占有状态的丧失就不能被评价为“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得到了雇主的授权,雇主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向保姆进行追偿。在这种情况下,由始至终受到损失的只有雇主一人,雇主才是“保姆案”中的被害人。因此,“保姆案”绝非杨文所称的“二元模式”的诈骗结构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于票据诈骗、信用卡诈骗中三角诈骗理论的应有,杨文也提出了批评,并指出了其认为的解释进路:
第一,“一类信用卡是只需要签名即可,特约商户和银行职员比对签名的审查义务。信用卡一旦被人冒用,持卡人能够证明签名错误,或者非持卡人本人消费的,持卡人不具有还款义务,特约商户或者是发卡银行需要自行承担损失,银行以及特约商户是金融诈骗的直接被害人,这种冒用事实上是普通的二者之间的诈骗关系”。(第50页)
第二,“另一类信用卡是密码和签名双重确认的方式,在这一情形下,银行或者特约商户的行为是一种履约或者履职的行为,而机械的执行命令或者是履行义务的行为不应当视为是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行为人冒用、冒领密码卡或者背书、支票等金融凭证的,承受诈骗之侵害的是持卡人、付款人本人,此时是金融诈骗行为仍是两者之间的诈骗关系,而非三角之诈骗”。(第50页)
在笔者看来,论者的论证过程与结论均存在问题。在第一种情况下,论者只是论证了在“持卡人能够证明签名错误,或者非持卡人本人消费的”情形下的处理方式与结论,不可否认,在这种场合,的确可以认定为被骗人与被害人都是银行,从而认定为传统的二元结构诈骗。问题在于,如果持卡人不能够证明签名错误,或者非持卡人本人消费,最终承担责任的将是持卡人本人而非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还是要回到“三角诈骗”的解释进路上来。因此,论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的论证是片面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论者采用了奇怪的解释逻辑:“因为银行构成履约或者履职行为,因而不构成处分行为,因此被骗人不是银行而是持卡人”。但问题在于,仅仅证立“银行不构成处分”这一事实,不代表就可以推导出“持卡人是被骗人”这一结论。显然,杨文在论证逻辑上存在双重标准:一方面,仅因为银行构成履约或者履职行为,就否认了其被骗者的身份;另一方面,仅因为持卡人、付款人本人“承受诈骗之侵害”,就肯定了其被骗者的身份,甚至在后者的论证过程中都没有涉及持卡人是否具有“被骗”以及“处分”的行为。这显然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在第二种情况下,银行具有“处分”这一结论不存在任何问题,不能因为“履约或者履职行为”就加以否定。事实上,“处分行为”只要求被害人的财产转移为行为人或第三人占有即可, 与是否履约或者履职并无关系。例如,在利用假的金融票证在柜台消费的场合,店员的行为都可以视作“履约或者履职行为”,倘若就此否定“处分”的构成,恐怕再无金融诈骗罪成立的空间。因此,无论是杨文所指的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当中,都存在“三角诈骗”的情形,试图证伪这一概念的尝试只会导致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牵强附会、捉襟见肘。
四、“自愿”系财产犯罪的表面构成要件要素
至于杨文指出“虚假诉讼罪骗取的是法院的有利判决而非财物”;“虚假诉讼中法院依据证据规则、法律事实作出的民事判决没有选择性,不能认定为‘自愿处分”(第51页)这两个理由,都是在将法院视为被害人的前提之下提出的辩驳。而在上文已经证明,在诉讼欺诈的结构中,法院是被骗者,原权利人才是被害人。因此,在前提不成立的情况下,这两个论据当然不能成立。
问题在于,对于杨文指出的“被害人基于判决结果承担败诉后果,不能认为是‘自愿交付”(第51页)这一论据,还是值得探讨的。一般而言,“诈骗罪中的‘交付是财物处分人陷入错误认识后的一种行为,是一种自愿行为” 。而在诉讼欺诈中,“被害人对行为人的弄虚作假行为是心知肚明的,但在客观上无力阻止法院的不力裁判,因而不是出于自愿”。(第51页)笔者对这一结论部分赞同,也就是在有些存在强制执行的情况下,由于被害人交付非出于“自愿”,诈骗罪无法成立。但是,是否论证了不成立诈骗罪,就能得出行为人不构成其他财产犯罪的结论呢?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杨文是站在一个割裂的角度审视财产犯罪体系内部的关系,认为盗窃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抢劫罪各自符合单独的构成要件,彼此仅有区别,并无关联。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纵览刑法中财产犯罪的演进史,诈骗罪与盗窃罪在最早是不加区分的。从汉字的起源来看,“盗”原本写作“盜”字,上半部分是贪欲的意思,“皿”是食具的意思,因此“盗”表示因贪欲而取得他人所有的食物。 春秋战国时期,李悝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并指出“以为之政,莫急于盗贼”。《荀子·修身》解释道:“窃货曰盗”,即《盗法》规制的是广义上的侵犯财产的犯罪, 它本身包含了诈骗、敲诈勒索、抢劫等具体的财产犯罪类型。
因此,盗窃、诈骗与敲诈勒索、抢劫之间仅存在人身胁迫程度之间的差异,申言之,对于诈骗罪中的“自愿”而言,属于表面的构成要件要素,它不是出罪与入罪的标准,而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要素。例如,被害人是出于“自愿”交付财物的,可以认定为诈骗罪;但是如果能够阐明被害人并非出于“自愿”交付财物,而是受到了心理上的强制或胁迫的,并非不构成犯罪,而是成立更为严重的敲诈勒索罪或抢劫罪。杨文一面指出,被害人不符合“自愿交付”的要件,行为人不成立诈骗罪,一面又指出:“法院的不利判决以及强制执行力并不等于以恶害相要挟,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的不利判决及其强制执行也没有达到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的程度。不构成抢劫罪”。(第47页)但是,所谓“以恶害相要挟使人产生恐惧”、所谓“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的程度”,都是论者在主观上的揣度,并没有站在体系性和一般人的立场进行客观评价。实际上,从逻辑上来看,既然否认了被害人的“自愿”,要么就认为被害人是出于恐惧交付了财物,要么就认为被害人因“不能反抗、不知反抗”而交付了财物。换言之,否认“自愿交付”只会得出行为人成立敲诈勒索罪或抢劫罪的结论。否则,在被害人“自愿交付”的情况下,行为人成立诈骗罪,在被害人“非自愿交付”的情况下,行为人反而不成立任何犯罪,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因此,杨文一方面否定诈骗罪中被害人的“自愿交付”,一方面否定行为人成立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在体系上并不自洽。
五、诉讼欺诈具有财产犯罪的侧面
杨文指出:“按照三角诈骗理论而将诉讼诈骗定性为诈骗罪不可行,而将诉讼欺诈直接定性为诈骗罪因为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相悖同样不可行。诉讼诈骗不能按照既有的伪证罪、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予以定罪量刑的时候,其特殊的行为构造将其推向了犯罪独立化的境域”。(第51页)
抛开结论不谈,杨文在做出这一结论时在逻辑上存在漏洞。在对“保姆案”的论述中,论者认为:“倘若保姆没有获得授权或委托,即受骗之保姆并不具有处分权,此时诈骗罪便难以成立,行为人的行为便是盗窃”。但是,诉讼欺诈中同样存在成立盗窃罪的可能,而杨文并没有对此论述,直接就得出了“诉讼欺诈无法用既有条文规制”的结论,未免过于唐突。事实上,杨文试图运用以诉讼欺诈行为对比每一个可能符合的构成要件的方式进行犯罪的排除,但是,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是无穷尽的,逐一排除的范式在方法论上显得捉襟见肘。如果不能运用体系化的思维,恐怕难以对罪名进行精确定位。
在笔者看来,诉讼欺诈的行为本身就具有财产犯罪的性质。通俗来说,诉讼欺诈本质上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将手伸到被害人的口袋当中”,因而可能同时侵害司法秩序的法益与他人的财产法益。 问题在于,虚假诉讼罪作为妨害司法一节中的犯罪,因而只能将诉讼欺诈侵害司法秩序的一面评价进来;而对于“将手伸到被害人的口袋当中”这一事实,却没有办法进行评价。
必须看到,虚假诉讼罪只是规制了诉讼欺诈行为的一个侧面,因此其法定刑最高只有七年有期徒刑。问题在于,行为人采用骗的方式取得他人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可以认定为诈骗罪,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而行为人“通过司法机器”采用骗的方式取得他人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如果否认诈骗罪的成立,只能认定为虚假诉讼罪,最高刑仅有七年,这是极度不合理的。也许有学者会提出,“诈骗不能通过诉讼的形式实施,通过诉讼公开向对方主张财产权利是法律主体的合法行为,诉讼行为的本质与特征从根本上排除了当事人通过诉讼实施诈骗行为的可能性” 。也有学者指出:“法院的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中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法院的财产处分权或财产处分地位而去认可法院属于哪个阵营或者是否接近被害人,必将危及法院的中立地位” 。
然而,无论是认为法院“合法”抑或“中立”,都不能作为排除其被利用的可能性。事实上,间接正犯中也肯定了“合法的行为”可以成立被行为人利用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否认司法机器可以成立行为人“伸进被害人口袋的手的延伸”。实际上,行为人诬告陷害他人,将他人判处死刑的,如果行为人具有杀人的故意,可以成立故意杀人的间接正犯,这便是利用司法机器进行杀人的情形。
因此,无论从外表上看如何,诉讼欺诈本质上是行为人利用司法机器进行财产犯罪的过程。这里的财产犯罪类型不限于诈骗,也包括盗窃、抢劫、敲诈勒索。例如,行为人与审判人员串通,判决行为人胜诉,造成诉讼对方财产损失的情况下,根据竞合原理,行为人成立虚假诉讼罪与枉法裁判罪的共犯;审判人员成立枉法裁判罪与虚假诉讼罪的共犯。问题在于,无论是虚假诉讼罪还是枉法裁判罪,所侵犯的法益射程都没有达到遭受损失者的财产。两罪的法定刑也印证了这一点:虚假诉讼罪最高刑七年,枉法裁判罪最高刑十年,在行为人取得数额特别巨大财物的场合,显然存在量刑畸轻、罪刑不均衡的情况。因此,在这情况下,应当将财产犯罪进行递补评价,认为行为人与法官成立盗窃罪的共犯,与构成的其他罪名从一重罪处罚。实际上,即使将这种行为评价为盗窃罪,也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为利用司法机器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完全符合盗窃罪“破坏他人占有、建立新的占有”的构成要件。
再如,由于在诉讼活动当中,可能存在法院通过强制执行取得被害人财物的情形,如果能证明法院的执行达到了强制的程度,完全可以认定为抢劫罪。 再如,在行为人基于对强制执行威慑的恐惧,迫于无奈交付财物的,成立敲诈勒索罪。 即使不能证明强制执行中对被害人人身与精神达到强制的程度,也至少能够评价为罪质较轻的诈骗罪。
由此可见,虚假诉讼罪与财产犯罪之间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评价诉讼欺诈行为的两个角度与侧面。如果一个行为即符合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由成立相应财产犯罪的,按照想象竞合的原理进行处罚。
六、反思:刑法中“工具”的表与实
“诉讼欺诈成立财产犯罪”的否定者最大的一个心理症结在于,认为法院仅仅是中立的裁判者,不能与一般的处分者或被利用的工具一视同仁。问题在于,所谓“中立”、“客观”是事物,也存在可能被利用的可能,也可能成立“人的延伸”。
“媒介即人的延伸”,系马歇尔·麦克卢汉教授提出的著名论断,其指出:“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延伸” 。例如,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麦克卢汉教授认为,“有围墙的城市、住宅、衣服是肌肤的延伸”、“文字是视觉与记忆的延伸”、“货币是劳动与技能的延伸”、“纺锤是手的延伸;轮子是腿的延伸” 。并由此得出结论:“工具使得人的拳头、指甲、牙齿、胳膊得以延伸” 。
这一思维对于犯罪问题的思考是颇有裨益的。应当说,刑事古典学派得以展开的逻辑起点在于承认故意犯罪中人的“自由意志”,它试图证立人的理性与自觉,是启蒙运动后带给人类的的最闪耀的明珠之一。正如费尔巴哈指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的活动,都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因此,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在肯定“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古典学派开始探讨“行为人的理性选择”问题,并在“人天生寻求快乐,避免痛苦”的逻辑前提之下延伸出心理强制说。这一整套理论的轴心在于:之所以惩罚行为人,是因为他在能否选择善的前提之下,选择了向恶。
但是我们不妨考虑这个问题,一个人“决定向恶”的自由意志是如何造成法益侵害事实的呢?例如,行为人想杀人,他挥动砍刀的手便成为了他自由意志的延伸;行为人驾车冲撞危害公共安全,他的车便成了他自由意志的延伸;行为人想引爆炸弹杀人,炸弹便成为了他自由意志的延伸。在这些场合,行为人不能辩解说,造成法益侵害的是他的手、行为人的车、行为人引爆的炸弹,从而应当否认行为人行为的直接性。因为无论是行为人的手、行为人的车、行为人引爆的炸弹,都是“行为人的延伸”,都是行为人加以利用的工具。
正如黄荣坚教授指出的:“所有犯罪都是直接犯罪,也都是间接犯罪。这是由于,人的意志永远无法直接实现侵害,所以人永远是利用工具才能实现侵害” 。那么,行为人通过动作、言语不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我们可以将其评价为盗窃、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形态,此时的“客观、中立”的手足与言语便是“人的延伸”;既然如此,在行为人利用司法机器不法取得他人财物的情况下,为什么就会因为法官的中立地位而否认成立相应的财产犯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