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两性声音共振的研究
2025-02-24胡文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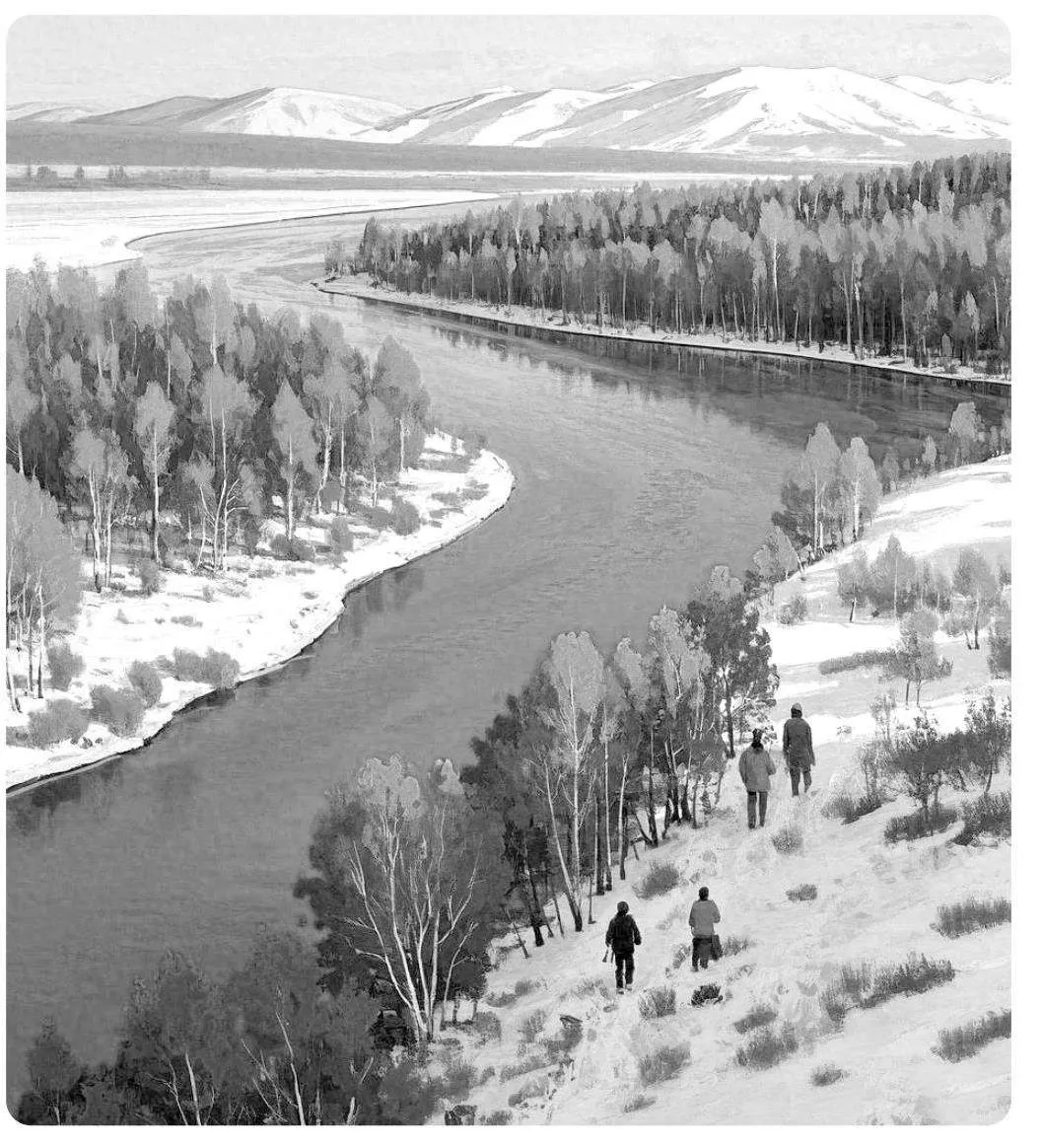
朱丽叶·米切尔认为“小说的精髓就是兼具男性和女性的声音”(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女性声音与男性声音共振的出现是女性书写真正成熟的标志。”(陈曦《〈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性别叙事研究》)迟子建的两性观带有鲜明的“双性和谐”倾向,她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描绘了中国北方鄂温克部落的生存与发展历程,书中一个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诠释着作者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其中女性声音与男性声音的交织,形成了一种美妙的复调,共同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呈现了一幅美好的人类社会画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性别关系和社会角色的崭新视角。
一、女性声音的多面呈现
(一)自我之声—女性的主体意识与温暖柔情的展现
“声音是存在最好的证明,对于那些处于被迫长期保持无声的非主流群体或边缘化个人来说,能够发声弥足珍贵,声音便是身份和权利。”(陈曦《〈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性别叙事研究》)小说的叙述者“我”是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我”的声音是结构上优越的声音,高于其他人物的声音。通过“我”的第一人称视角,读者见证了鄂温克民族近百年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感受到了现代文明入侵带来的冲击。在面临人生抉择时,“我”始终坚定地用自己的声音表达内心世界,为追求真实与自由而努力,这充分体现了女性注重自我主体性的意识。“我”作为叙述者,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更是在传递一种女性的力量,一种敢于追求自我、珍视自我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鄂温克族的历史长河中,虽然可能只是微弱的存在,却如星星之火,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
此外,“我”的叙述中常常包含着女性特有的温暖与柔情,“我”善于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将生活中琐碎的事物描绘得栩栩如生。例如,“我”用“朝我们跑来的白色驯鹿”来比喻半轮淡白的月亮,用“香味舔着我们的脸颊”来赋予香气舌头的感知能力,诗意化的表达不仅展示了女性对美的敏锐感知,也体现了女性内心的柔软与温情。
(二)顺从之声—女性对传统文化与角色价值的认同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对女性角色的定义和期望深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女性被认为应当具备一系列特定的品质,以便履行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如温顺、听话和照顾家庭等。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女性的价值取决于她们是否能遵守这些规范。所谓的“在家从父,出门从夫”成了衡量女性言行举止的准则。这意味着,女性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和服从男性,无论是父亲还是丈夫。而当丈夫不幸离世,女性更是被强烈要求从一而终,终身守节,以彰显她们的忠诚和贞洁。鄂温克族女性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父系文化的影响,她们的发声虽然隐晦,却透露出对这种文化的维护和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认同,在生活中不自觉地遵守着这些传统规范,她们的价值和角色也被严格限定。
林克去世后,尼都萨满和达玛拉互生情愫。可是这种情感却是氏族不允许的,依芙琳指出,按氏族习俗,弟弟去世,哥哥不能娶弟媳;哥哥去世,弟弟可娶兄嫂。依芙琳自从知道尼都萨满和达玛拉的感情后,常常在大家坐在一起商议事情的时候故意地提到林克,试图浇熄他们的爱情之火。而“我”也始终对尼都萨满满怀警惕,甚至对母亲达玛拉也冷嘲热讽:“云和水在一起是对的,哪有火和水在一起的?”部族人对他们情感的敌意,加之父系文化对女性的禁锢,让这段感情注定无果,也让他们因痛苦而癫狂。在鄂温克族的社会结构中,这种顺从之声体现了女性在传统族权文化面前的无奈与妥协。她们在遵守传统规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氏族的稳定和秩序。然而,这种稳定和秩序是以牺牲女性的自由和幸福为代价的。
(三)反叛之声—女性的挑战传统与勇敢抗争的呐喊
在传统的两性模式中,男性通常被视为主导者,负责家庭的外部事务,如采集狩猎等,而女性则被视为依赖者,承担起内部的织布缝纫等家务。鄂温克族遵循这种模式,男女相互扶持,共同应对生活的挑战,从而使婚姻和睦,家庭幸福。而总有颠覆传统形象的反叛者,在艰难生活中发出勇毅的呐喊之声。
歪鼻子的依芙琳则恰恰是这一模式的反叛者,在婚姻生活里,她对坤得那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极为不满,常常指责坤得毫无可取之处。作为惩罚手段,她采取了拒绝与坤得同房的方式,并且在盛怒之下宣称,自己绝对不会与倾慕自己的人同榻而眠。而当部落中的男性被日本人强行带往东大营接受训练,部落里仅剩下女性成员时,依芙琳展现了她的坚强、勇敢和反抗。当女人们为没有新鲜的兽肉吃而抱怨时,她毅然带枪下山出猎,决心自己解决问题。尽管连续去了三个夜晚,仍未有所收获,但她并未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念,顶风行动,做足准备,最终成功猎到一头小鹿,解决了食物难题。此外,当她发现居住地已经没有驯鹿可食的苔藓和蘑菇时,她毫不犹豫地成为拿主意的领头人,她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于是她带领大家沿着贝尔茨河向西南迁移,以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更为令人敬佩的是,当白灾降临,驯鹿失踪时,她依然是第一个站出来寻找驯鹿的人。在小说中,“她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她用反抗日本人、带着女人迁徙、打猎等具体实际行动承担起氏族社会中男性的部分责任,反抗着男性的话语、秩序与霸权”(任毅《鄂温克民族文学〈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女性形象》)。
依芙琳虽在婚姻家庭中被视为“恶女”,但她的反叛与不屈侧面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和勇气,她打破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用实际行动证明,女性不仅能够承担起传统的女性角色,也能够胜任男性角色,为家庭和社会作出重要贡献。她的形象挑战了传统的性别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性别关系和社会角色的崭新视角,发掘了作品中女性力量的当代价值。
二、男性声音的核心表达
(一)欲望之声—男性对生育繁衍的崇拜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巧妙地引入了部落男性与女性群体在发言权方面的对等格局,让男性群体得以坦陈其真实的内心所想与见解。在这部作品中,男性群体的声音主要聚集于生育繁衍这一关键主题之上,这种声音成了女性声音的重要补充,丰富了小说声音的层次,揭示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繁衍生息的渴望,也映射出他们对自然文明和古老传统的敬重与推崇,令整个叙事更富感染力与吸引力。
“父亲看我和列娜像两只蝴蝶离不开花朵一样绕着母亲飞,就嫉妒地说,达玛拉,你一定得送给我个乌特!”达西只要一说话,就与玛利亚的肚子有关,“我的奥木列在哪里?”这些都透露出他们对新生命的深切渴望。新家庭成员的降临,不仅延续了血脉,还带来了尊严的重生,为生活注入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拉吉达在找寻驯鹿前,还惦记着让家中再添新丁;坤得在依芙琳二次怀孕时,全心全意照顾她,期盼丢失的孩子能以某种形式回归;鲁尼面对不愿再孕的妻子,时常当众落泪,他以泪水表达渴望,最终让妻子转变态度,这份对新生命的期盼最终打动了妮浩,而新生命诞生的希望与喜悦拯救了绝望恐惧的妮浩。
在生死交替、轮回不息的漫长进程中,鄂温克民族顽强地存续着。面对民族危机,鄂温克人将对生育的尊崇、对生命本体的敬重,奉为最终依归。作家借助男性集体的声音,揭示出那蕴含神性光辉的生育崇拜,不只是民族文化在性别层面的展现,更是整个民族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石。尽管现代文明的浪潮汹涌袭来,使鄂温克族显得脆弱而渺小,但鄂温克族所展现的民族精神中,却包含着如磐石般的坚韧与永恒不朽的特质,这些特质将永远闪耀,永不磨灭。
(二)失落之声—男性对传统文明沦落的伤感
传统文明秩序无疑是男性本位的,与此相关,当这一秩序受到现代化进程的猛烈冲击时,作为在民族文化内部长期处于“本位”地位的男性所感受的文化焦虑日益加重。被阉割的男性人物形象则是一种文化隐喻,反映了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思考与批判。
文明的本质其实就是压抑,文明的不断发展就是对人的本性的不断压抑过程。这些抑制在文学中体现为对“男性去势”现象的描写。拉吉米在寻找“我们”的时候,途经一片松树林,盘旋的苏军飞机投下了两颗炸弹,剧烈的爆炸声引发马儿狂奔,在这一过程中他的阴囊被撕裂。作为现代文明缩影的热兵器战争导致了拉吉米的悲剧。坤得从精神上被阉割,自从自己来到乌力楞,依芙琳没有接受过他一次求欢,她的拒绝使坤得的欲望长期处于禁锢状态,坤得也确实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逐渐失去男性话语权和行为自主权。正是由于女性自由意志越发强烈,才导致男性精神逐渐消亡。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男性的去势可以看作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的吞噬与对人性的异化,传统文明秩序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然而,在现代化进程的猛烈冲击下,这一传统秩序发生了剧变。面对新的社会环境,男性无法按照传统方式寻求出路,他们在挣扎中寻找适应现代文明的方法,却依然无法适应变革,成为现代文明的附庸。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融入现代社会中。然而,这种融入并非真正的心灵契合,而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他们最终为了维护尊严便选择了缄默与退席。
三、两性声音的共振呈现
迟子建的两性观带有鲜明的“双性和谐”倾向,她认为上帝造人时只有男女两个性别,意味着二者必须相互扶持才能维系世界的正常运转。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紧密联系,不可分割,任何一方处于绝对主导都是不合理的。这也体现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男性声音和女性声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像音乐中的复调一样同时出现、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男性和女性也始终维持着一种和谐平等、彼此尊重的关系。
(一)平等与爱的相互依存
小说叙述者“我”代表了那些渴望并享受平等男女两性关系的群体。“我”以真挚的情感和两任丈夫建立起了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关系。拉吉达爱开玩笑,夏天捉瓢虫塞进“我”的裤腰里,冬天下雪时悄悄攥上一把雪塞到“我”的脖子里,以此要挟“我”说一大堆肉麻话;瓦罗加自己是一名酋长,却为了和“我”在一起,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部落一分为二,带着十几人和“我”的部族合并。当“我”依偎在拉吉达的怀抱时,“我”觉得自己如同在山谷间自由穿行的风,无拘无束,畅快淋漓;而在瓦罗加的怀抱里,“我”则觉得自己宛如一条在春水中尽情畅游的鱼,舒适自在,悠然自得。叙述者以这种方式展示了男女两性在原始生命中自然流淌的美好。“如果说拉吉达是一棵挺拔的大树的话,瓦罗加就是大树上温暖的鸟巢。他们都是我的爱。”这句话寓意着他们在彼此的生命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相互依赖、相互尊重、相互滋养、相互陪伴。
文章通过叙述者“我”的亲身经历,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平等与爱是相互依存的,只有彼此尊重、相互滋养,才能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家庭生活。这种观念在鄂温克民族中传承,成为他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忠诚与包容的彼此融合
在迟子建的笔下,两性关系并非全然被圆满的光环笼罩,其间亦不乏悲情与灰暗的色调交织。然而,和谐且健康的两性关系仿若强劲的主旋律,纵有偶尔弹错的音符,却依然能漾出几分曼妙的余韵。见过了达玛拉与尼都萨满的爱而不得,马粪包与妻子的相互背弃,瓦霞与安道尔的分钗断带等众多悲情的爱情故事,达西和杰芙琳娜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浓墨重彩,表现了同生同死的两性之爱,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忠诚、包容与坚韧的光芒。
杰芙琳娜失去丈夫金得意欲寻死时,达西主动求婚,用自己的真诚与坚定,试图唤醒杰芙琳娜对生活的希望。瘦弱的达西在那个时刻看上去就是一个威武的勇士,她不愿意看到杰芙琳娜的泪水,不忍心看她刚刚新婚就马上成了寡妇,于是宁愿等她守寡三年,宁愿被母亲责骂也要主动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这种无私的爱,让杰芙琳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然而,命运的捉弄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曲折。达西在杰芙琳娜最绝望的时候伸出援手,不离不弃,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忠诚的含义。而杰芙琳娜在达西遭遇困境后,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以殉情的方式表达了她对达西的忠贞不渝。这种生死相随的爱情,超越了世俗的考量,体现了鄂温克族对爱情纯粹性的追求。达西明知杰芙琳娜曾经历过巨大的痛苦,可能会有情绪上的波动和行为上的异常,但他依然选择包容她、理解她,给予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愈合伤口。杰芙琳娜也同样包容了达西为日军效力这一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的无奈之举,没有因为外界的压力和指责而放弃对达西的爱。这种包容体现了鄂温克族在面对生活困境和人性弱点时的豁达与宽容,他们相信爱情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困难和瑕疵。
本文通过对《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男性声音、女性声音及两性声音共振的分析,加深了读者对鄂温克族中两性相敬相守的理解与认同。在作品中,迟子建积极构建男女两性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她用鄂温克族男女朴素的爱恋治愈了现代社会中两性关系失衡所带来的爱情困扰。这种和谐的关系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一种理想描绘,更是她对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的一种期待和呼唤。作品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能够引发人们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思考,促进现代社会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尊重、忠诚和包容的两性关系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