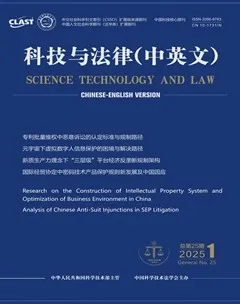科技法的领域法定位与体系构建
2025-01-03万志前王子洁
摘" " 要:科技法作为伴随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新兴学科,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科技法律现象和法律关系,以部门法思维定位科技法,存在逻辑难以自洽、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及阻碍科技法研究与发展等问题。领域法作为回应新兴学科的研究范式,以问题导向性和开放性为基本特点。科技法契合了领域法的特点,将其定位为领域法,可有效回应科技发展中的领域性问题,突破部门法研究的隔离化,促进科技法的整体研究。完善领域法视域下科技法律的体系构建,应当明确其基本要求,确立《科技进步法》的基本法地位,健全科技领域的专门法,衔接好科技法律自身规范与其他领域科技法律规范的关系,保持两者之间的“分”与“合”的张力,由此形成科技法律体系内外协调的层次序列。同时,领域法并非否定传统部门法,包含科技法在内的领域法与传统部门法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关键词:领域法;部门法;科技法
中图分类号:D 912.17" " " " " 文献标志码:A" " " 文章编号:2096-9783(2025)01⁃0014⁃12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当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新兴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加速兴起,必然会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深刻影响。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其导致的风险和“适应不良症”[1]引发人们对科学技术领域法律规制的关注。科技发展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深度关联,科技变革与大国博弈的相互交织,科技创新活动跨界交流的日益频繁,如此等等,使得科技创新面临十分复杂的内外环境,迫切需要一个有效、全面和动态的科技创新法律体系促进、规范、保障科技创新。回顾我国科技法律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法学界首次提出科技法的概念以来,科技法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1985年8月,国家科委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科技立法工作座谈会”,我国科技法治建设就此起步。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88年底,“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寓法学研究、立法实践和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全国性社会团体”[2]——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成立。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下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将科技法学确定为新的独立二级学科1,科技法学学科建设就得到迅速发展;1991年由中国科技法学会主办的《科技法学》(现改为《科技与法律(中英文)》)杂志正式发行;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科技领域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技进步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精简二级学科(专业)目录,将宪法学、行政法学和科技法学合并为一个专业,即宪法与行政法学,科技法学的地位被弱化,带来了学科发展的困扰,如中国法学会至今也没有单独成立科技法学研究会[3]。2007年,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通过的法学学科核心课程未见科技法;201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显示,科技法也被纳入行政法2。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在某种程度反映某一法的地位。从1999年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确立了14门法学本科核心课程始,历经2007年、2018年、2021年的调整,均无科技法的踪影3。科技法学虽然不是独立的二级学科,但科技法学的研究与教育仍然有很大发展,诸多科技法教材与著作出版、很多学校设立了科技法(学)研究所(中心)、数十所高校开设科技法课程,培养科技法硕士、博士高层次人才[4]。2023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其中提出“加快发展社会治理法学、科技法学、数字法学、气候法学、海洋法学等新兴学科”。科技法学及科技法律体系的完善再次引起关注。2024年3月2日,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主持召开了科技法律体系建设座谈会,与会专家就科技发展前沿领域法律问题研究、重点科技立法和推动构建新时期科技法律体系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5]。2024年3月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娄勤俭表示,将研究推进科技创新方面的立法,不断完善科技法律体系[6]。
自首次提出科技法始,其是否具有独立部门法地位,一直是科技法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学界形成了诸多学说。一是隶属其他部门法说,其中又有两种观点:其一,经济法部门说。该观点认为,科技立法旨在推动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科技法作为经济法一个重要的分支,其特性与经济法的精神相契合,同时也符合学术界的主流意识[7]。其二,行政法部门说。认为科技法中存在着大量行政管理规范,并将其定义为行政机关开展科技行政管理活动所依据的法律规范[8]。二是独立部门法说。认为科技法是特殊部门法,与经济法迥然相异[9]。科技法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技术市场的发育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而出现,是从传统部门法(如民商法、行政法等)中分立出来的新兴的独立部门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0]。法律规范目的价值与社会作用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科技法以开拓创新科学技术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为目的,规范科学技术研发活动及科技成果转化行为,是调整社会与自然关系的特殊部门法[11]。且科技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科技活动的独特品性都要求科技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12]。不论是赞成抑或反对科技法独立部门法说,均以传统部门法理论为前提得出结论。这源于我国部门法研究范式的影响,即对于某一法律规范、法律问题或法律学科,习惯于首先将其归于某个部门法,并以此作为后续细化研究的基础[13]。三是领域法律规范系统说。认为科技法同“经济法”概念一样,只是“一个领域法律规范系统”,是“法学理论新概念的引入”[14]。科技领域存在多种性质的社会关系,按照传统部门划分标准,很难找到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全面调整科技领域所有的社会关系,科技法是综合有关法律规范,统一协调科技领域所有社会关系的领域法[15]。此种观点,其实就有某种领域法思想的萌芽。
随着新科技不断涌现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社会活动主体愈加多元、活动空间不断扩大,科技法律关系呈现复杂、综合、交叉等特性。对科技活动的法律调整绝非仅依赖单一部门法就能实现,科技活动的变动不居与法律规范的稳定不倚也面临天然的内在张力[16]。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或“规范价值”和“社会作用”为标准的划分方式难以将科技法划归任何一个或几个既有法律部门。因此,应对多样复杂、交叉融合的科技活动,以传统部门法思维定位科技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故从领域法视角分析科技法的定位并构建科技法律体系实有必要。
二、传统部门法视域下科技法发展的困境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法制变迁总体上是从以刑为主的“诸法合体”结构迈向现代部门法分立格局[17]。自部门法划分引入中国后,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就其概念而言,或认为“凡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就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8];或认为“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或原则对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进行划分所形成的具有某些共同特点法律规范的总称”[19];或认为“是指按照特定的调整方法来调整一定性质和范围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等要素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统一体”[20]。就其划分标准而言,形成了单一标准(调整对象)说[21]、双重标准(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说[22]以及多标准说[23]。但随着社会发展,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愈加复杂,交叉与模糊在所难免,部门法划分方式在应对错综复杂的法律现象与法律关系时捉襟见肘,并可能使有些法律法规支离破碎,极大地限制了法律发展[24]。基于传统部门法思维的影响,科技法定位主要围绕部门法思维展开。部门法思维有助于法律体系化、条理化、精确化与法学范畴的建立,此种思维方式使得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的边界清晰。但科技法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与传统部门法相异,以部门法理论定位科技法是否为独立的部门法显得力有不逮,难以为科技法律问题的综合、整体解决供给充分的理论资源与法律方案。
(一)难以逻辑自洽
自洽性(Self-consistency)源于逻辑学,是指带有主观性的自我协商、自我控制、自我允准和自我认同,是概念、观点、假设、结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25]。逻辑自洽要求部门法划分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即划分应当相称、必须按照同一标准划分、划分所得各子项外延必须相互排斥[26]。部门化的划分尽管按照法律表面的一致性进行了归纳,但缺乏对法律实质内容和内在联系的把握[27]。若将科技法定位为独立部门法,其调整对象为特定的科技社会关系。然而科技社会关系却同时需要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环境法等其他部门法调整。如科技成果的转化,既需要科技成果转化法的调整,其中科技成果转让、许可等又需要民法调整;科技税收关系既是一种因科技活动引起的社会关系,又是一种因行使权力而引起的纵向经济关系,因此科技领域的科技税收关系应当由经济法调整;在科技研发或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可能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此时又会涉及环境法的调整;此外有关技术入股、股权、期权等问题,可能涉及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范;有关科研企业及与科研人员间关系等方面的法律调整则涉及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总之,科技社会关系和其他领域社会关系相互关联,势必造成法律部门之间的牵连与交叉,而法律部门间的交叉重叠与部门法划分的逻辑自洽相悖。
(二)无法适应社会发展
部门法理论有助于形成严谨的法律逻辑结构和搭建以部门法为基础的法律体系4的基本架构。但如果过于渴求塑造精准、稳固的法律体系,则会导致法律与实践相脱离,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因为问题世界并不因为这些体系化努力而丧失其问题性[28]。同时,社会问题并不会完全依照部门法的逻辑和方式呈现,部门法固化、隔离的思维局限难以有效回应日趋复杂、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问题[29]。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以特定社会领域法律现象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新兴法学科逐渐产生,科技法就是其中之一。受传统部门法划分下法学研究的“板块思维”[30]约束,科技法研究也一度被肢解、划分至不同部门法下,或者局限于将科技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理论分析。这种划分方式使得科技法研究和教育受制于特定部门法下,将研究视域和方法限缩于相应的二级学科之下,难以实现新兴法学科所承担的整体性、交叉性、多维性研究的时代使命[31]。部门法理论以所谓部门法属性的分析方法,认为科技法“必须有”或“必然有”抑或“根本无”,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自洽,而且会消减分析和理解法律问题的能力,导致在传统部门法研究视域下的科技法失去把握社会和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32],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科技需求,难以全面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法律挑战。
(三)阻碍科技法研究与发展
部门法研究范式存在着自我封闭、视野局限等不足,难以为日益复杂的领域性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新兴领域的法律调整往往具有交叉性、开放性、协同性,某个科技法律问题研究可能涉及多个不同性质的法律部门,需要整体思维,突破学科边界,形成不同学科之间就同一问题从不同学科路径解释和处理的竞争态势[33]。在部门法视域下,具有领域属性的法实难找到合适的、可充分伸展的一席之地,面临着或多或少的定位焦虑[34]。因此,当前学界对同样具有领域法属性的科技法定位尚未形成统一观点。这种定位的不确定性导致科技法陷于“定位焦虑”,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也难以深入开展。此外,将科技法局限于特定部门法开展研究和教育,会导致过分强调既有部门法体系内法律条文的学理阐释和实践应用,而忽视以科技发展问题为导向的前瞻性研究、跨领域的合作研究、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从而影响科技法研究视野的开放性、解决科技发展所产生问题的有效性,不利于科技法的持续发展。
三、重识科技法定位:以问题为导向的领域法
科技法律横跨民法、行政法、环境法等多个部门法,纵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多个学科,呈现出多领域、跨学科并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回应性特点。科技法研究急需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维。以问题为导向,以开放性为特点的领域法显示出独特的学理优势与实践理性。将科技法定位于以解决科技发展问题为导向的领域法,可以克服传统部门法应对领域性问题的局限,有效回应科技迅速发展的实践需求。
(一)领域法:突破部门法划分的新进路
伴随现代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的迅猛进步以及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法律现象的复杂性和领域性趋势愈加明显。应对此种趋势的法学研究和法律调整随之出现变化,某一类法律现象需要调动各法部门、法学科的力量综合调整,由此产生了领域法(Field of Law)的概念[35]。领域法(学)概念最早在财税法学界由刘剑文教授于2013年提出,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全部与法律有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融多种研究范式于一体的交叉性、开放性、应用性和整合性的新型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5。之后,学界关于领域法的讨论大量出现。领域法是对传统部门法反思的结果,在深刻认识传统部门法视域下学科分类精细化与法律现象复杂化之间的矛盾后,领域法试图为法学研究打开一扇“领域性”的学术视窗,即部门法视域下的学科分散转向领域法视域下的学科融合,围绕特定领域的社会问题,整合法律规范、统合学科知识,促进各学科知识的融合创新及现实问题的综合解决[36]。
领域法具有问题导向性。法学不是理论之知,而是实践之知[37],应当以解决实践问题为根本要求。“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构想,须以现实存在的问题为导向”[38]。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愈加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背景下,法律问题不再是纯粹的部门法问题,任何现实世界的法律问题都具有“跨部门法边界”的属性[39]。与传统部门法以法律规范的性质为切入点不同,领域法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旨在发现并回应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实用主义态度回应新兴领域中出现的法律或法学问题。领域法遵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在分析具体问题的基础上,综合考量相关因素,总结提炼出各类规范及制度,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有效回应[40]。其以联动性、综合性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打破了传统法学研究的“条条框框”,较好契合了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立场和实践秉性[41]。
领域法具有开放性。传统部门法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进行学科划分,各分支学科画地为牢,割裂法律规范群之间的联系,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视野束缚在各相对独立的部门法中,呈现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形成“部门墙”问题[42],而领域法以特定领域的问题类型形成法规则集群,具有开放的品性,以有效解决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联动性的社会问题。因此,领域法秉持开放性研究视角,不受制于学科划分或法律部门的界限。在调整某一新兴社会问题时不仅注重整合传统法律部门要素,在横向上破除“部门墙”的封闭性;还注重综合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在纵向上消除学科壁垒[43]。领域法的开放性使其得以摆脱“僵化的法条”束缚,逐渐形成“活跃的法学”文化[44]。
当然,领域法不是为了替代部门法,只是开发了一个提升法律效用的新视角[45]。传统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仍以法律部门的形式存在。随着科技活动等特定领域法律实践的出现并快速发展,任何一个传统的法律部门无法涵盖该领域的全部内容,未来的法学学科也将更加体现交叉和融合的品性[46],其规范构建及学术研究需要领域法思维。
(二)科技法定位为领域法的必要性
“科技法”这一概念脱离了部门法下法学研究的藩篱,具有“领域法”属性[47]。将科技法定位为领域法可有效解决科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愈加复杂、多元的科技法律难题,克服当前部门法视域下法学研究“封闭性”和“部门墙”问题,化解部门法话语下科技法的定位焦虑。
1. 有效回应科技发展中的领域性问题
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如有利于揭示部门法理论基础、有利于正确适用法律、有利于实定法的有序化等[48]。然而,随着科技发展进入新阶段,科技创新愈加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科技法律制度也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深度融合,部门法理论在面对科技领域内交叉性、综合性法律现象和法律关系时,呈现“先天不足”的缺陷。多样态的科技法律活动对科技法律规范的需求也愈加多元,以领域法的问题导向性和开放性思维构建规则集群,能突破部门法的界限与壁垒,有效回应这一需求。领域法在解决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时,受法律实践目的的推动,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多学科规范和研究方法,形成综合性法学理论,对社会现象进行“对象化指向的思考”,围绕对象化指向的领域开展法律实践活动[49]。将科技法定位于领域法,有助于打破各传统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实现各部门法规范之间相互融通,不同的部门法要素之间相互整合,进而形成整体性、综合性、统摄性的科技领域法律规范,有效回应、解决传统部门法视域下难以解决的交叉性、领域性法律问题。
2. 突破部门法研究的隔离
合理的法学学科划分对法学体系构建确有必要,但过度的学科精分将导致法学研究的“内卷化”和“部门墙”。科技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科技法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单个部门法内展开,否则会导致科技相关问题研究的割裂化、隔离化,无助于科技法律问题的解决。而领域法研究范式以问题为导向,侧重以法律规范、社会现象和价值取向为标准,通过以一定的“事项”划定法律规范的范围,从而打破传统部门法研究条线分割的状态[50]。因此,将科技法定位为领域法,以科技领域的问题为导向,聚集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共同形成科技法的研究群体、研究机构、研究平台,突破传统部门法的隔离化思维,拓宽研究视野,提出更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与传统法学研究者交流与合作,以开放方式开展交叉研究,带动传统法学的发展,共同推动科技领域的法治创新与法治建设,丰富法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拓展科技法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3. 有利于科技法的整体研究
科技法作为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的新兴法律领域,与传统部门法不同,其所调整的科技法律现象与科技法律问题往往呈现一定的交叉性、开放性和复杂性。遵循传统部门法所秉持的“还原论”“解构性”思维与进路,将科技法划归至某一部门法存在困难[51]。根据传统部门法研究范式的划分标准,会将作为特定社会生活领域的科技法律现象人为地割裂至某一独立部门法或从属于某一部门法内,不利于整体性把握科技法律规范,导致知识间的割裂。领域法以其开放性研究视角可消除传统部门法各自为政、条款分割的现象,缓解定位焦虑。将科技法定位为领域法,能使研究者摆脱传统的部门法研究范式,采用更为综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科技法律问题,为解决科技法律问题提供更为丰富的洞见;能吸引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科技法研究队伍,为科技法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科技法的整体性研究。
(三)科技法定位为领域法的可行性
科技法是伴随着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而产生的,科技法律问题的复杂性、综合性与领域法学的内在属性与外在特征相契合。
1. 科技法契合领域法“问题导向”与“开放性”的内在属性
科技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原本就是因为科技发展中的问题而产生。“科技创新法律制度建设,需要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聚焦重大问题”[52]。科技法的产生着眼于解决科技领域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导向”的特质符合领域法“以问题为导向”的特点。科技法对科技领域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整合其他部门法的规范,更要采用跨学科方法,实现科技与法律、经济、社会的融合,这与领域法所强调的开放性、整合性与交叉性的研究范式相契合。惟其如此,科技法才能有效回应科技领域的实践问题,与其他学科协同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法治进步。总之,科技法不同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以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为中心的传统部门法,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往往涉及众多法律部门,无法用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对科技领域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的、统一的调整,需要构建灵活开放的法律体系规范科技活动,契合了领域法问题导向与开放性的特点。
2. 科技法契合领域法“规范集成”的外在特征
“规范集成”是领域法,以问题为导向,开放性解决问题的结果,是领域法的外在特征。“规范集成”的概念来源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领域,学者后将其引入法学领域。“规范集成”通常是指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则的聚集过程及其组合方式,根据组合方法的不同,“规范集成”的依赖路径可以按照调整对象的性质组合,也可以按照所规范事务的不同来排列[53]。与传统部门法不同,领域法以问题为导向,不过度关注法律规范是否具有类似的法律性质,而是围绕现实问题进行概念建构与规范集成[54]。在领域法规范集成方法下,涉及同类或相关社会事务的规范即可组成特定领域法,而不要求这些规范具有相同的法律属性[55]。科技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科技法律规范的多样性与综合性,既包括传统的法律规范,如专利法律规范、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技术合同),又包括与科技发展相关的特殊规范,如科技成果转化法、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数据保护法等,还包括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法律规范。科技法律规范此种综合型特性正好契合领域法规范集成的外在特征,也只有按领域法思路,才能有效整合复杂多样的科技法律规范,形成“领域法律规范系统”[56],灵活地引导、激励、规范科技活动,解决科技法律问题。
四、领域法视角下科技法律体系的构建
目前我国科技法律体系存在如下问题:科技法律体系杂乱无序,处于基本法地位的《科技进步法》没能发挥应有的统摄功能;不同科技领域的法律法规数量庞杂、衔接不够、相互重叠,亟待根据一定的逻辑进行体系整合;某些科技创新过程中的要素和环节缺乏规范或规范层次较低;科技领域专门法与其他法律中科技法律规范尚未形成逻辑体系,等等。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科学技术在我国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为更好发挥法律规范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保障作用,应当以领域法为视角完善科技法律体系,构建科技领域法律规范系统,为推进科技治理现代化,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科技法律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
领域法视角下科技法律体系的构建,应以科技法律问题为导向,突破部门法思维的局限性,立足当下,着眼未来,顺应科技发展趋势,整合各类科技法律规范,实现科技创新与法律制度间的良性互动。为此,科技法律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一是稳定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科技法律作为一种法律规范,要具有稳定性,这是法的内在要求。否则,法律的权威性会受到严重冲击。法律需要稳定,法律体系也需要稳定性。在科技法律体系内,起稳定作用是科技基本法,因此,科技基本法要具有包容性和前瞻性,以维持科技法律基本体系的稳定。同时,科技法律体系要具有一定开放性,以适应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科技发展的趋势。科学技术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总是扮演着最活跃的角色,相应地,也会带来伦理、道德、安全等诸多风险,需要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和建构,以防范和化解风险[57]。但这种修改和构建不影响科技基本法的稳定性,而是根据科技发展的实际需要,推进“小快灵”“小切口”立法,增强科技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及时回应科技发展需求。
二是行业自律与法律规范相结合。规范科技活动需要行业自律。行业自律作为行业内部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的重要形式,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减轻政府负担、降低规制成本[58]。行业自律是一种重要的自主治理形式,是风险治理机制的重要手段[59],如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行业组织——人工智能伙伴关系联盟(Partnership on AI)在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防止人工智能技术滥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行业自律也能有效缓解技术过快发展而引起的立法供给不足问题,可避免盲目和超前立法扼杀技术创新的活力[60]。因此,领域法视角下科技法律体系,除了法律规范外,还应包括行业自律规范,形成“硬法”与“软法”对科技活动的协调治理,这也是领域法开放性的体现。
三是法律与伦理相结合。科技创新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需要一定的自由度,但科技创新的手段、目的、结果必然与人类利益和价值相关涉,受控于人类的价值考量[61]。“法律总是具有道德维度”[62],因此,科技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法规应该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如在人工智能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应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会侵犯人类的隐私、尊严等。科技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法规与科技伦理规范应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伦理虽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但有道德上的导向性和自我约束性[63],引导法律规范向善;法律则是伦理规范的强制性保障,通过规范程序促进科技伦理反思,解决科技伦理困境,引领科技整体向善发展[64]。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更多的福祉。
四是国内与国际规范相结合。科技发展具有全球性和跨境性特点,随着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许多科技问题已经超越国界限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科技挑战。因此,构建科技法律体系,要坚持国内与国际规范相结合原则,实现科技法律规范和标准的协调与统一。既要根据国内的科技发展水平、社会实际需求、法律传统,建立健全符合本国实际的法律制度,也要积极借鉴、对接国际科技法律制度,实现国内科技法律与国际规则接轨。为此,应密切关注国际科技法律的发展动态,积极参与科技法律规则的制定,建立国际科技法律交流机制等。
(二)健全科技法律体系
应以科技基本法为核心,以规范特定领域、特定对象、特定活动的专门法为重要组成,健全有内在逻辑的科技法律体系。
我国当前科技法律体系呈现“平面式”特点,缺乏能够发挥统帅作用的科技基本法[65]。《科技进步法》是科技领域的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法律,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企业科技创新、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科学技术人员、区域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等,尤其是2021年12月第二次修订的《科技进步法》更是“全面升级中国科技治理体系”[66],是全面促进科技进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本法治保障。但《科技进步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之间在效力上无高低之分,各法律之间处于平行关系,有基本法之实而无基本法之名。因此,科技法律自身体系的完善,首当其冲的是确立《科技进步法》的基本法地位。
首先,通过明确《科技进步法》的“依据”地位,发挥其基本法功能。在我国,“基本法”是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律,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某个领域重大和全局性事项作出规范的法律[67]。其应当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形式要件,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二是内容要件,即调整和规范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全局性、长远的、普遍的和起骨干作用的社会关系[68]。就形式要件而言,《科技进步法》本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而具备基本法的形式要件6,但目前《科技进步法》的制定和修订(2007年、2021年两次修订)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已成事实,再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实无必要。2021年8月17日,李学勇在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作关于科技进步法草案的说明时,已明确将《科技进步法》定性为科技领域的基本法7。就内容要件而言,《科技进步法》明确将“推动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宗旨之一,其主要内容包含科技创新的全链条、全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69]。可以说科技创新关系国家强盛、民族进步、科技自立自强,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因此,《科技进步法》满足基本法的形式要件与内容要件。“基本法”作为介于宪法和“非基本法”之间的法律层次,它所规范的内容应当较之“非基本法”更具有全局性和重要性,与宪法一起成为“非基本法”及以下各个层次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70]。故可通过明确《科技进步法》的“依据”地位,实现其基本法地位,发挥其基本法功能,即科技领域的专门性法律应规定“依据《科技进步法》制定本法”8,科技领域其他法律当以贯彻执行《科技进步法》为己任,明确科技基本法与非基本法的位阶关系。其次,完善《科技进步法》内容,体现科技法综合型、概括性的特点,使科技基本法规范尽可能涵盖所有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活动[71],以此保障科技领域基本法的稳定性。可根据各类科技活动和科技法律制度的共性因素,提炼“公因式”,纳入科技基本法规范中,形成基础性框架,发挥其统领和指引作用。最后,作为科技领域的基本法,应规定更多授权性规范,授权相关立法机构制定其他科技法律规范,从而实现科技法律规范的具体化[72]。同时,规定参照适用的援引规范,以此明确与其他特别科技法律规范的关系,打通法律规范之间的壁垒,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法律适用的繁琐程度,避免法律规则的过度抽象[73]。
在明确《科技进步法》基本法地位、完善《科技进步法》相关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科技创新活动的核心要素和环节,制定和完善科技领域的专门法律规范,这是科技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研究开发方面,健全科研院(所)法、科学技术基金法等;在科技成果保护和转化方面,除已有的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外,还需要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等;在科技普及与推广方面,已有科学技术普及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但需要根据国家科技强国建设要求进一步完善9;此外,还涉及条件保障与激励立法(科技投入法、科技奖励法等)、科技安全立法(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立法等。上述针对专门要素和环节的法律规范由不同层级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等构成。如此,可围绕《科技进步法》形成多层次配套法律制度体系,使科技法律制度成为一个体系完整、内容完备的有机整体,增加科技法律规范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其实际效能[74]。
(三)衔接好与其他领域科技法律规范的关系
从2024年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发布的300部“现行有效法律目录”10中可以发现,现行法律规范中与科技创新相关的有100多部,分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法律领域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涉及知识产权、数据保护、技术合同、虚拟财产、信息安全和基因技术等与科技领域相关的法律规范,科技法律规范的“泛在性”可见一斑。因此,领域法视角下科技法律体系的构建还应当做好科技基本法、专门性科技法律与其他领域相关科技法律规范的有效衔接,保持科技法律规范与相关领域知识体系之间的适当张力,实现各领域部门法“分”与“合”的双重变奏[74],形成既各有侧重又相互配合、系统协调的制度体系,共同调整科技社会关系。
“分”意味着承认不同法律调整的领域有所侧重,不是“诸法不分”,但“分”又不是“泾渭分明”。“分”不是封闭排他,而是在承认“界限”的基础上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性,搭建与其他法律规范沟通与合作的桥梁,为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预留对外沟通的窗口。为此,可以借助准用性规范在科技法与传统部门法或其他领域法之间打开一扇窗口,打破不同法之间的壁垒,实现科技法与其他法之间互联互通。“合”意味着以解决科技问题为中心,集合科技相关法律规范,形成统一整体格局,共同引导、激励、规范科技活动。“合”也要求专门性科技法律制度与其他非科技专门法中的科技法律规范形成“和谐”,避免相互抵牾。如此,形成以科技基本法为核心,以其他专门性科技法为主体,以其他领域相关科技法律规范为辅助的差序格局。依照与需要解决的特定科技问题的关联性强弱,由内至外划分相关法律规范的层次序列。科技基本法、与科技活动直接相关的专门法律规范居于内部圈层,关联较弱的则处于相对边缘圈层。当然,科技法律体系并非单纯的静态规则,而是一个动态系统。根据所要解决的具体科技问题,法律规范的关联强弱与层次序列会不同。此外,有关科技的国际法律文件(公约、条约、议定书等)、科技行业自律规范、科技伦理等“软法”,也属于科技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五、结语
领域法的兴起为某些新兴领域复杂社会问题的法律综合调整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但其并非否定或替代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仍保持部门法的传统,新兴领域各种交错的问题通过领域法加以回应,无需对传统部门法作频繁、大幅度的修改,亦不必“另立门户”构建一个新的部门法,以此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更好地适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科技法因科技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生,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法又面临着新问题和新挑战,试图通过单一部门法调整科技社会关系愈加困难,需要利用领域法思维完善科技法律体系。科技法所呈现的复杂性、交叉性、领域性特征,契合领域法的特性。将科技法定位于领域法,能更好地研究和解决科技与法律交叉领域的问题,促进科技与法律的协调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应用,推动科技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领域法视角下科技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遵循科技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明确《科技进步法》基本法地位,以科技法律问题为导向,健全各项科技专门法律规范体系;保持科技法律自身体系与相关领域科技法律规范的适当张力,加强科技法与其他领域法律之间的协同运作,构建内外协调、适应科技创新需要的科技法体系。这既是建设科技法学、培养高素质科技法治人才的需要,也是加强科技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需求,更是提高科技自立自强与科技强国建设法治保障水平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龙卫球. 科技法迭代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立法[J]. 法商研究,2020,37(1):57⁃72.
[2] 段瑞春,王家福. 繁荣科技法学研究,加快科技法制建设——纪念中国科学技术法学会成立十五周年[J]. 科技与法律,2003(4):1⁃2.
[3] 曹昌祯. 科技法学——新兴法律交叉学科[J]. 科技与法律,2007(1):5⁃9.
[4] 何悦. 科技法学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2⁃13.
[5] 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朝晖主持召开科技法律体系建设座谈会[EB/OL]. (2024-03-08)[2024-03-18].https://www. most. gov. cn/kjbgz/202403/t20240308_189940. html.
[6] 娄勤俭:将研究推进科技创新方面的立法[EB/OL]. (2024-03-04)[2024-03-18]. http://www. xinhuanet. com/tech/20240304/dba59f9e1b69446aa13b9b9ace7e440a/c. html.
[7] 张宇润,王学忠. 科技法的定位和价值目标[J].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6(2):202⁃213.
[8] 牛忠志. 科技法通论[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14.
[9] 倪正茂. 科技法学和中国的科技法学研究[J]. 中外法学,1989(4):46⁃49.
[10] 罗玉中. 科技法学[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1.
[11] 曹昌祯. 科技法在法律体系中定位问题的再思考[J].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6(1):1⁃8.
[12] 牛忠志. 论科技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地位——兼论传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的与时俱进理解[J]. 科技与法律,2007(5):9⁃15.
[13] 刘剑文,侯卓,耿颖,等. 财税法总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66.
[14] 陈仲,张勇健. 科技法性质新探——法学理论新概念的引入[J]. 科技法学,1990(2):25.
[15] 蒋坡,陈乃蔚,刘晓海,等. 加强科技法学学科建设纵横论[J]. 科技与法律,2007(1):10⁃44.
[16] 胡朝阳. 科技法前沿[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3:2.
[17] 宋亚辉. 社会基础变迁与部门法分立格局的现代发展[J]. 法学家,2021(1):1⁃191.
[18] 杨紫烜. 论经济法的若干理论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61⁃82.
[19] 舒国滢. 法理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3.
[20] 孙笑侠. 法理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60.
[21] 孙国华,朱景文. 法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98.
[22] 张文显. 法理学[M]. 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103.
[23] 沈宗灵. 法理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97.
[24] 李昌庚. 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与出路——兼对社会法等部门法划分的反思[J]. 北方法学,2014,8(5):81⁃89.
[25] 张国启.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自洽性及其当代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1):101⁃109.
[26] 张钢. 部门法理论源流及其对我国法治实践的影响[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137.
[27] 张志成. 论科技法学的法理学基础及其二元结构[J]. 科技与法律,2005(3):4⁃9.
[28] 舒国滢. 法学的知识谱系(全三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07.
[29] 范志勇. 部门法与领域法融合视域下的新时代法学学科建设[J]. 北方论丛,2023(4):92⁃99.
[30] 刘剑文. 财税法论丛(第17卷)[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48⁃67.
[31] 陈伟伟,刘毅. 论卫生法学:学科定位、逻辑起点与体系建构[J]. 社会科学研究,2022(1):106⁃112.
[32] 易继明. 开创科技法学研究的新局面[J]. 社会科学家,2013(12):88⁃94.
[33] 梁文永.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J]. 政法论丛,2017(1):64⁃76.
[34] 耿颖. 现代社会转型与领域法话语的展开[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6):32⁃39.
[35] 王桦宇. 领域法学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J]. 法学论坛,2018,33(4):107⁃115.
[36] 佘倩影. “领域法学”:法理视野与话语共建[J]. 法学论坛,2018,33(4):87⁃97.
[37] 郑永流. 重识法学:学科矩阵的建构[J]. 清华法学,2014,8(6):97⁃116.
[38] 季卫东. 问题导向的法治中国构思[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20(5):20⁃24.
[39] 梁文永. 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J]. 政法论丛,2017(1):64⁃76.
[40] 熊伟. 法学现代化背景下领域法学之契机[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1-05.
[41] 王桦宇. 论领域法学作为法学研究的新思维——兼论财税法学研究范式转型[J]. 政法论丛,2016(6):62⁃68.
[42] 刘诚. 部门法理论批判[J]. 河北法学,2003(3):10⁃22.
[43] 洪治纲. 论领域法学理论在金融法学中的应用[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7(1):108⁃119.
[44] 王利明. 法治具有目的性[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71.
[45] 熊伟. 问题导向、规范集成与领域法学之精神[J]. 政法论丛,2016(6):54⁃61.
[46] 孙笑侠. 论行业法[J]. 中国法学,2013(1):46⁃59.
[47] 初萌. 科技立法基本原则、监管趋势与未来展望[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41(5):90⁃98.
[48] 叶必丰. 论部门法的划分[J]. 法学评论,1996(3):38⁃72.
[49] 舒国滢. 走近论题学法学[J]. 现代法学,2011,33(4):3⁃18.
[50] 杨大春. 从部门法学到领域法学——《大明律》转型的历史启示[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7(1):120⁃130.
[51] 方印,王明东. 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焦虑、理性回归及归位效应[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0(2):61⁃77.
[52] 何亮. 完善科技创新法律制度为高水平科技自力自强提供法治保障[N]. 科技日报,2022-06-24(005).
[53] 廉睿,鲁涛,孙长壮. 国家安全法学的场域面向、规范集成与学科归属[J]. 情报杂志,2022,41(8):75⁃79.
[54] 廉睿,卫跃宁. 中国民族法学:问题导向、规范集成与回归田野[J]. 青海民族研究,2018,29(2):61⁃66.
[55] 陈乃尉. 略论科技法调整对象[J]. 科技与法律,1991(4):52⁃54.
[56] 吴汉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28⁃136.
[57] 常健,郭薇. 行业自律的定位、动因、模式和局限[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33⁃140.
[58] 邓小兵,刘晓思. 中英网络治理的行业自律比较研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5):116.
[59] 张新宝.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 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J]. 中国法学,2015(3):38⁃59.
[60] 王学川. 科技伦理价值冲突及其化解[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138.
[61] 苏力. 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J]. 中国社会科学,1999(5):57⁃71.
[62] 黎来芳. 商业伦理、诚信义务与不道德控制——鸿仪系“掏空”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J]." 会计研究,2005(11):8⁃14.
[63] 谢尧雯,赵鹏. 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及适度法制化发展[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6):109⁃116.
[64] 周海源. 创新的法治之维:科技法律制度建设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24.
[65] 刘垠. 新版科技进步法来了! 这些重大变化和科研人员息息相关[EB/OL]. (2022-01-02)[2024-01-15]. https://news. sciencenet. cn/htmlnews/2022/1/471936. shtm.
[66] 韩大元,刘松山. 宪法文本中“基本法律”的实证分析[J]. 法学,2003(4):3⁃15.
[67] 李克杰. 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及范围扩张[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18(2):14⁃27.
[68] 袁勃,赵欣悦.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01).
[69] 韩大元.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法能否优于全国人大旧法[J]. 法学,2008(10):3⁃16.
[70] 刘银良,吴柯苇. 创新型国家导向的中国科技立法与政策:理念与体系[J]. 科技导报,2021,39(21):45⁃51.
[71] 朱涛. 论中国科技法的双重体系及其建构[J]. 科技与法律,2016(5):854⁃866.
[72] 王利明. 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J]. 比较法研究,2020(4):1⁃13.
[73] 杨利华,王诗童. 科技创新的法律之治:科技法律体系的构建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2022,40(5):2⁃12.
[74] 宋亚辉. 风险控制的部门法思路及其超越[J]. 中国社会科学,2017(10):136⁃207.
Field Law Orientation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Wan Zhiqian,Wang Ziji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ollege of Humanities amp; Social Sciences /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ule of Law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as a new subje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 legal system." In the face of complex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egal phenomena and relations, the orient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aw by department law, there will be logical difficulties in self-consistency, unable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imped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aw." As a research paradigm responding to emerging disciplines, field law is characterized by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openne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f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eld law, and its field law orientation can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field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reak through the isolation of department law research, and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as a whole." To perfect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as field law, its basic requirements should be clarified, law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basic law status, the special law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ould be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and ot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should be well connected, and tension of \"division\" and \"merging\"between the two should be kept." Thus, the hierarchy sequence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gal system is formed." At the same time, field law does not negate the traditional department law." The field law inclu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and department law constitute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field law; department la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基金项目:华中农业大学教学改革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乡村振兴法治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研究”(2022090)
作者简介:万志前(1974—),男,湖北仙桃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科技法;
王子洁(2000—),女,湖北襄阳人,助理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科技法。
1 该目录确定的法学二级学科有16个,分别是:法学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环境法学、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法、军事法学、科技法学。
2 根据该白皮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行政法部分罗列了科学技术进步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促进科技进步、保护和繁荣文化法律法规。
3 1999年教育部高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所确立的14 门法学本科核心课程,包含: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知识产权法、商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2007 年,又增补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2门核心课程。2018年教育部发布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其中《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将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采取“10+X”分类设置模式。“10”指法学专业学生必须完成的10门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律史、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国际法和法律职业伦理。“X” 指各高校根据办学特色开设的其他专业必修课程,包括: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商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环境资源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证据法和财税法,“X”选择设置的课程门数原则上不低于5门。2021年修订的《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2021版)》将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采取“1+10+X”分类设置模式。“1”指“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课程,“10”与“X”所指不变。
4 1980年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法学词典》中对法律体系的解释是:“由各法律部门组成的一国法律有机联系的整体”,即法律体系由部门法组成。
5 “财税法学是一个以财税为领域,法学为基本元素,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于一体的应用性的‘领域法学学科’”。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关于“强化财税法基础理论研究.繁荣现代财税法”的倡议》,财税法学科与财税法理论前沿专栏,南昌,2013年12月,第1-3页。
6 该法不是“基本法律”实属意外。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规划,《科技进步法》本应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1990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的立法规划中,《科技进步法》作为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列入我国第七届人大重要立法计划。1992年10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草案作了初步审议,后来由于未来得及提交1993年3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而社会各界又迫切希望早日颁布这部法律,遂由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于同年7月2日通过。参见罗玉中主编《科技法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94。
7 李学勇:“作为我国科技领域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科技进步法对保障和促进科学技术健康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大网: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8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均未明确规定“依据《科技进步法》制定”。
9 科技部于2022年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改工作,并于2023年4月14日发布“关于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修改草案)》意见的公告”。
1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行有效法律目录(300件)》,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403/t20240301_43497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