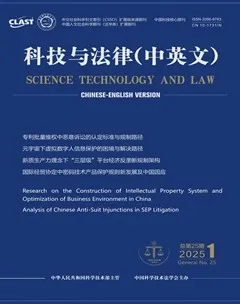“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
2025-01-03管荣齐赵旖鑫
摘" "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逾十载,我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具备了规则创新的能力与契机,该种创新可由缺乏国际协调的实用新型制度先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沿线区域性知识产权组织存在实用新型制度本土化的立法基础、改革经验及协调实践,考虑实用新型制度在保护渐进式创新、维护共建发展中国家利益、提升知识产权国际博弈话语权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国应当推行从软法到硬法的实用新型国际协调行动。包括但非限于借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起协调倡议、倡导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出台《实用新型示范法》、借鉴欧盟的开放协调机制进行规则协商等,并将实用新型制度引入更多双边、多边贸易协定谈判场景。
关键词:“一带一路”;实用新型;渐进式创新;国际协调;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D 923" " " " " 文献标志码: A" " " " " " " " 文章编号:2096-9783(2025)01⁃0091⁃12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该倡议逐渐成为我国深化“多边、周边、小多边、双边”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关系,形成“四边联动、协调推进”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已经与50余个共建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知识产权合作关系,有11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来华提交专利申请1。实证层面,“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参与企业的发明、实用新型等专利产出[1]。但现有研究表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国际协调机制依然缺乏。“循序渐进,由小及大”法律模式的设计[2],知识产权一体化制度的建立[3],统一专利区的创立[4],双边条约机制的创新[5],标准化合作机制的构建[6],跨国常设机构及专业性的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7]均为实现“一带一路”知识产权规则国际协调的有益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以“软法—硬法”的路径推行实用新型(Utility Model)制度的国际协调与规则创新亦被证明具有可行性[8]。实用新型制度自1891年于德国创立以来,便因适用的灵活性而在激励中小企业发展、提高专利制度运行效率等方面具有较优表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10年间,共建国家在我国申请实用新型专利1.4万件,年均增速高达12%2。与此同时,实用新型与商品、服务、资本的全球化流通之间的正向关联正在被探索:2013年《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第13.2条第5项明确将实用新型作为知识产权客体之一;2015年《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实用新型纳入我国参与的自贸协定中3;2015年《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2017年《中国—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也将实用新型纳入其中4。
实用新型制度虽具备深厚的历史基础及比较优势,但相较于其他知识产权事项,其国际协调的脉络并不清晰。这一方面被视为实用新型制度具有灵活性的例证;另一方面则导致实用新型制度在国际规则层面研究的匮乏。“一带一路”倡议呼吁知识产权规则的创新与共建,聚焦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创造与维护。如此,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问题,贡献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方案,不仅是因应《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中“中国要更加深入地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愿景的有益举措,也是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快中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目标的积极动作,更是创新“一带一路”知识产权生态体系的重要环节。
二、描述与统计:“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的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需先行释明两个问题:一是从宏观上探求实用新型制度既有的国际保护框架为何;二是以微观视角考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否具有相应的立法基础。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下简称为WIPO)管理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以下简称为《巴黎公约》)、《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专利合作条约》(以下简称为《PCT条约》),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为WTO)管理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下简称为《TRIPs协定》)被视为对知识产权制度国际协调的典型例证。
实用新型制度自建立之初即缺乏国际层面的统一协调。1911年《巴黎公约》对实用新型在知识产权中的地位确认后,仅在其第1条之(2)概念部分、第4条优先权部分、第5条专利权的限制部分、第11条临时保护部分对实用新型制度作出协调。《TRIPs协定》直接赋予各签署国自由选择空间,未对实用新型制度进行任何协调。《PCT条约》第2条承认实用新型为专利类型之一,申请人可以国际申请为基础请求指定国授予实用新型专利。但《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6.5条、第13.5条规定,鉴于各国实用新型制度的差异性,指定国可适用本国法的有关规定对实用新型申请进行审查5。WIPO于1979年编写的《发展中国家发明专利示范法》虽在第104条d项认可了各国采用的“实用新型”“实用证书”“附加专利”“附加实用新型证书”等概念,却并未对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尚未对实用新型制度施以关注。《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领域合作的共同倡议》《关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我国与WIPO于2017年5月签署并进行修订的《加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协议》以及其他文件中并不包含实用新型制度的相关内容,不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提供实用新型制度的协调思路。
(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用新型制度及其特征
统计发现,有73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了实用新型制度或者类似制度,占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总数的48%,占到建有实用新型制度国家总数的78%6。同时,建有实用新型制度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全世界实用新型申请量排名中表现良好。WIPO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2023》显示,2022年全世界实用新型申请量排名较优的20个国家中,约有65%的国家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7。综合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用新型制度具有如下特征:
1. 建立方式具有复杂性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地理空间辽阔,沿线穿越若干个主要的区域协定。73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建立实用新型制度的方式本就具有复杂性,再叠加诸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于其所签署的区域协定保护实用新型,就使得“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用新型制度的梳理更为复杂。
中非、几内亚比绍等16个国家为非洲知识产权组织(Af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为OAPI)成员国,利比里亚、津巴布韦等9个国家为非洲地区工业产权组织(African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为ARIPO)成员国。按照《班吉协定》的规定,OAPI成员国即便缺乏本土化的实用新型制度,只要其承认OAPI颁发的实用新型注册证书的效力,具备本国新颖性的、适于实用的有形产品也可以得到实用新型制度的保护。相对而言,依照《卢萨卡协定》,ARIPO相关协议只有在转化为成员国国内法后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由ARIPO管理的《非洲区域知识产权组织框架内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计哈拉雷议定书》(以下简称为《哈拉雷议定书》)设立了ARIPO框架下的一体化实用新型制度,但当作为ARIPO成员国的津巴布韦、索马里、苏丹、卢旺达基于ARIPO相关协议的自由度,也可以选择不将其纳入本国法律框架。
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五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订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其第26项附件《保护执行知识产权议定书》第9部分将实用新型纳入专利权的保护客体,该议定书一方面尊重各成员国以国内立法保护实用新型的既有实践,另一方面就部分保护条件设定了最低标准,包括实用新型的保护期限至少为5年,实用新型的优先权应当被保障等。
依《卡塔赫纳协定》成立的“安第斯共同体”(Andean Community)作为拉美地区最早成立的地区一体化组织,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三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占据该共同体四分之三席位,亦对实用新型制度的保护达成了协调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实用新型仅保护有形产品,需满足绝对新颖性、绝对创造性与实用性要求,给予10年的保护期。
2.保护方式存在较大差别
建有实用新型制度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仅有爱沙尼亚、韩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与奥地利7个国家以单独立法的方式对实用新型提供保护;中国等国家采用“三位一体”的立法模式,将实用新型与发明、外观设计统一于一部专利法中;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采用“部分合并立法模式”,将实用新型与发明合并立法,而将外观设计单独立法;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的实用新型制度则融入本国的知识产权法典或者民法典中。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保护客体问题上的分歧,不仅在于产品制造方法应否纳入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还在于该种保护能否延及至所有形态的产品。对于前一问题,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实用新型立法采取开放态度;对于后一问题,中国、韩国等国家仅认可有形状结构之产品获得实用新型保护的正当性,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等国家则将该国实用新型立法的保护范围扩充至所有类别的产品中8。
形式审查制、初步审查制、实质审查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授予实用新型专利前对其进行审查的主要模式,分别见于中国、阿曼与韩国立法等。各国专利行政机构对相关实用新型申请进行审查时,申请人将因各共建国家相异的审查标准而面临不同障碍。如泰国、菲律宾等国家要求该实用新型申请满足绝对新颖性要求;在绝对新颖性要求之外,莫桑比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要求该申请的创造性程度与发明专利等同,中国、布隆迪等国家则强调两种专利在创造性高低之上的区别。冈比亚、莱索托等国家甚至仅关注该申请的相对新颖性,在相对新颖性的标准之上,匈牙利、塞舌尔等国家不强调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的区别,摩尔多瓦则坚持二者的差异性9。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于实用新型所提供的保护期限亦存在5种不同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保护10年且不可延长模式”、以韩国为代表的“保护10年且可延长模式”、以埃及为代表的“保护7年且不可延长模式”、以罗马尼亚为代表的“保护6年且可延长至10年模式”、以捷克为代表的“保护4年且可延长至10年模式”10。
3. 国别上多为发展中国家
从国家发展水平来看,建立实用新型制度或者类似制度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现有研究认为,实用新型制度相较于发明专利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发达国家[9],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别分布规律能够证实这一研究结论。
建有实用新型制度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虽然韩国、捷克、波兰、斯洛伐克、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奥地利8个国家属于发达国家,但其余约71%的国家均属于发展中国家,其中老挝、也门、柬埔寨、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莫桑比克、冈比亚、布隆迪、莱索托、安哥拉10个国家甚至属于联合国认定的47个最不发达国家。
对照世界银行2023年发布的全球经济体分类标准发现,建立实用新型制度或者类似制度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高收入经济体的占比仅为26%,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占比也仅为37%,其他绝大多数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即发展中国家。
三、机遇与可为:“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的前景
实用新型制度在国际公约中的缺位具有复杂的成因,但不能因此得出“实用新型制度不具备国际协调前景”的结论。面向“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为该问题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现今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具有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利好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的必要性。
1. 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具备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
从制度的初始设计目标和运行发展实效来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具备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这是因为:
首先,实用新型制度能够保护渐进式创新。现有研究表明,实用新型制度的诞生旨在弥补知识产权领域中既存的、伴随着新兴技术的产生而扩大的空白地带[10]。不同于有形财产的单一所有权,无形财产的权利谱系错综层叠。创新通常遵循迭代性的基本规律,相应行为既是连续的又是非零和的[11],因而广阔的公共领域与保护渐进式创新被视作创新的两个重要条件[12]。渐进式创新通常用于解决一般实用技术问题,但因其数量巨大而对社会经济技术进步的驱动能力并不弱于数量有限的重大创新[13],实用新型制度则为该种提高社会福利的渐进式创新提供了保护路径[14],从而实现了对权利人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激励。同时,实用新型制度所提供的较短保护期限亦契合渐进式创新的较短生命周期。欧盟委员会于1997年经过调查认为,“机械工程、电子工程与汽车等具有较短产品生命周期的行业适宜使用实用新型制度”11。
其次,实用新型制度能够为发明人提供更多选择。作为一种二级专利制度抑或阶梯式专利保护模式[15],实用新型制度被视为专利制度中具有灵活性的典型代表[16],这种灵活性不仅指向某一国家适用与否的自由,更多体现为权利人尤其是创造者保护渐进式创新的便捷。当渐进式创新无法满足发明专利“创造性”要件但又具备正外部性时,创造者便转向保护门槛更低的实用新型制度。即便渐进式创新具有较高的创造性,当权利人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或者寻求更加便捷的保护时,亦会选择实用新型制度。
另外,实用新型制度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均有实效。实用新型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发挥的制度优势,包括但不限于该制度对于韩国非制造业部门技术发展[17];对于日本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实现战后技术追赶[18]、实现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19]。有学者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对比后发现,实用新型制度的实施甚至有利于实现最高级别的创新[20]。实用新型在巴西和菲律宾等国家也促进了当地的技术进步12。对于中国而言,实用新型制度与技术进步[21]之间的正向关联亦已被证实。WIPO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22年中国、捷克、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参与统计的132个经济体而言显著受到了实用新型制度的激励13,同时,实用新型制度亦助力斯洛伐克、泰国两国在同等收入经济体内获得了发展优势。
2. 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助力中国增加国际话语权
全球化时代实现知识产权的治理目标,需要从一国国内治理走向全球治理[22]。国际舞台上,知识产权议题的利益博弈十分复杂,各国通常对体现特殊战略利益的议题表现出更高的关注度,并试图在相关议题内取得国际话语权。印度基于其国内蓬勃发展的电影市场而对版权问题更关注[23],新西兰基于其多元的历史文化而对遗传资源、民间文艺和传统知识问题更重视[24]都能窥见其所偏好的知识产权国际议题。
然而,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不仅凭借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还应当以丰富的知识体系证成话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25]。《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22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列第11位。与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比,中国的技术水平具有明显优势,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经过了更多实践层面的考验,适宜培育知识产权优势议题。作为首倡国的中国应当基于“一带一路”场域发挥“后发优势”,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形成过程中将面向高质量创造机制的实用新型制度,建构成为契合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反映产业利益、占据经验优势的知识产权国际议题。
3. 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利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为共建国家间的非零和博弈提供了必要空间。习近平主席于2023年10月18日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指出:“‘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首创“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中国企业可与有关国家企业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共同在第三方市场开展经济合作。
建设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等标志性项目的过程中,产业的转移与双边价值链的升级是高度可能发生的现象。对于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的互惠共生为其模仿与再创新提供了条件。如果不对该过程中产生的、体现该承接国家智慧的渐进式创新提供保护,承接产业转移的共建国家将无法逐步建立本国的创新环境。事实上,如果参与方认为共建方有“搭便车”的意图或者阻碍集体决策的动机,国际合作的价值就会降低[8]。当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共建国家企业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选择“走出去”时,若东道国的实用新型法律制度可获得性较低使之丧失了可选择的空间时,其可能会因此减少在该国的贸易活动。
不同于“大基建”项目,“小而美”项目的规模小、风险低、利润高,合作成果更多由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及全球性公共产品,自提出以来便锚定于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的使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道路上,每一个共建国家都应成为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实用新型制度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国,中国有关注其利益的动机与责任。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的可行性
“一带一路”倡议对知识产权规则创新的强烈需求为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提供了基础条件,不同实用新型立法例的动态调整向其供给了参考性方案,区域层面的已有协调尝试则赋予这一行动更多的决策空间。当前,实用新型制度在各国的立法改革中逐渐具备了新的发展动能,在各区域一体化框架下不断探索更优的要素结合方式。
1.“一带一路”倡议呼吁知识产权规则的创新与共建
研究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知识产权国际条约设立的弹性规范正在受到西方国家“体制转换”活动的挤压[26],CPTPP体系的确立可能进一步缩减中国在国际法变革中的创新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在后危机时代对原有的世界经济、法律结构体系进行矫正式努力提供了平台[27],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望成为国际规则创新的主导者。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已提出十年有余,但其采取的是非正式的、弱机制的发展路径。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虽展开了点对点的“单线”合作,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网状”合作格局并未形成[5]。“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创新之路”的过程中,“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实践若需走向丰富、立体、全面的形态,就须呼吁知识产权规则的创新与共建。
相较于其他知识产权规则,实用新型国际规则的创新在当前更具可行性。譬如,作为“一带一路”首倡国的中国发布《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探索制定地理标志、外观设计等专门法律法规”。可以预见,当外观设计法探索成熟逐渐与专利法相分离时,实用新型立法的方式与路径也将进一步被理论与实践所拷问,这有助于中国形成规则创新的依据并进一步在“一带一路”倡议内推广。伴随着“丝路电商”成为“一带一路”多双边经贸合作的新渠道,“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正在这一新兴业态中进一步发挥实用新型制度“短、平、快”的优势。2019年11月,中国印发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第四部分之(十)要求推动电商平台建立有效运用专利权评价报告快速处置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的投诉制度。这为实用新型制度在共建国家内的协调提供了动能。
2.“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具有实用新型制度改革经验
实用新型申请量与社会经济水平之间呈现着“倒U型”的线性关系,“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防止陷入“制度陷阱”而形成的实践经验值得参考。譬如,韩国的实用新型制度在审查程序上经历了“实质审查制”到“形式审查制”再到“实质审查制”的变革,其经验表明实用新型制度的要素并不具备最优的排列范式,而应伴随国内创新环境的变化作出动态调整;波兰目前正处于该种动态调整中,其基于效率的考量推行了UD263号计划草案,该草案探索将实用新型的实质审查程序变更为形式审查程序,并将进一步扩大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28]。
以改革的视野看待中国实用新型制度时,1992年续展程序的取消、2000年检索报告制度的引入、2008年“相对新颖性”向“绝对新颖性”的转换、2013年检索手段的准入、2023年明显创造性审查的推进,均见证了实用新型保护的长度、宽度、高度与速度在量与质、快与慢、高与低、远与近几对矛盾间的探索,这些改革步伐正合力将实用新型保护引入高质量的轨道之内,并进一步发挥实用新型制度优势。政策层面内,地方政府已经或者正在取消基于实用新型的资助政策以减轻制度外部的不当激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下简称为国知局)业已推行的专利质量提升工程要求在保证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审查标准,具体可见于2023年11月2日发布的《关于实用新型专利保护客体判断的指引》。国知局网站公布的2023年前半年知识产权主要统计数据显示,较2022年同期数据相比,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同比下降26.62%。由此可见,实用新型制度已经成为中国专利制度改革的重要切口,并已经取得了部分改革成就。这些改革经验具有可推广价值,能够成为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的重要论据。
3. 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存在可参考的区域性方案
面对各成员国“实用新型”“实用证书”“创新专利”等立法模式的区别,为了实现实用新型专利产品在欧盟市场内的无障碍流动、协调不同的实用新型保护模式及为中小企业创造发展机遇,欧盟委员会于1995年发布《单一市场实用新型保护绿皮书》,并于1997年发布《实用新型发明保护法律安排的指令》。欧盟委员会提出区域实用新型制度协调的三种路径:一是以欧盟指令的方式协调各成员国的实用新型立法;二是促使不同成员国间实用新型制度的相互承认;三是建立单一的、联盟层面的实用新型制度。上述立法建议于1999年6月被欧盟议会审议,欧盟议会一方面修改了相关立法建议,另一方面指明了第三种协调路径的非可行性14。
欧盟的协调行动所达成的实用新型立法方案包括:实用新型制度在保护客体上不作三维形式的要求并可以延伸至产品的制造方法;同时,相关申请的审查采形式审查方式,以及绝对新颖性、较低的创造性与实用性的审查标准;实用新型所指向的具体权项与发明专利并无差别,其最高可通过两次续展程序获得10年的保护期限。虽然这一协调方案因不同成员国间的利益冲突并未得到实践的考验,但欧盟为实用新型制度所建构的法律环境仍传递出保护该制度的重要信号。
非洲范围内,1977年通过的《班吉协定》第5条第2款将实用新型的注册视作一个区域层面的问题后,以附件形式述及了实用新型的各项保护要件:那些具有相对新颖性的、适于实用的有形产品可以向OAPI申请注册。根据《哈拉雷议定书》,ARIPO亦有权处理区域层面实用新型的申请,对于ARIPO实用新型而言,其需满足该《协定书》第3节中对其施以的各项限定,包括本国新颖性要求、实用性要求,ARIPO将对有关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同时,两组织都对实用新型提供为期10年的保护。另外,欧亚经济联盟、安第斯共同体亦就实用新型制度形成区域一体化方案,对此前文已详述,此处不再重述。
四、障碍与路径:“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的证成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考虑实用新型制度并非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中的典型议题,应当首先破除实用新型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困境,进一步明确部署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行动在国际法中的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面临的困境
当前实用新型制度及其国际协调面临诸多困境,主要包括:实用新型制度是否还能发挥预期效用,实用新型保护是否属于超TRIPs义务。
1. 实用新型制度是否还能发挥预期效用
中国于2010年越过中低等收入国家的阈值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持续增长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产生了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实用新型法律质量偏低而引发的效力不稳定问题,审查环境宽松而引发的重复授权乃至资源浪费问题,授权数量畸高而引发的市场寻租问题,策略性使用而引发的重复诉讼问题。由此,实用新型制度是否还能发挥预期效用甚至应否取消或废弃,成为悬于实用新型制度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分别于2008年、2009年、2021年废弃了实用新型制度性质的短期专利制度(Short-Term Patent)、创新专利制度(Innovation Patent),这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必须首先突破实用新型制度是否还能发挥预期效用的困境。
事实上,该困境的产生主要源于非科学的使用方式,即外部因素。政策对于专利行为的鼓励性干预,企业对于专利的策略性使用,资本对于专利的套利性应用,法律对于专利的反向性调整等,均为阻碍实用新型制度功能实现的外部因素[29]。创新主体对于实用新型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也受到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剥离外部因素的过程亦是重新认识实用新型制度的过程。
同时,日本对于此问题给出了肯定性的答案。日本于1993年将实用新型的审查方式由实质审查制改为形式审查制以后,其实用新型申请数量急剧下降。面对“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实用新型制度应与专利制度相整合”的声音,日本知识产权局设立的产业结构审议会知识产权分委会下设的专利制度小组委员会,经过十年调研后得出结论:“对于迫切需要市场化的技术而言,有效利用实用新型制度的强烈需求依然存在,实用新型制度应继续在日本施行。”同时,其还将保护对象的扩大、创造性标准的提升、检索报告的第三方审核,认定为有待继续研究的三个议题15。
2. 实用新型保护是否属于超TRIPs义务
美欧所引领的超TRIPs造法态势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强烈批判,双边和区域性协定中的超TRIPs义务与霸权主义的连结被不断塑造。如前所述,《TRIPs协定》中并未就实用新型的保护作出规定,因而讨论“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前,应当厘清实用新型保护是否属于超TRIPs义务。这一问题应作否定回答,以下可作为论证依据:
(1)《TRIPs协定》不排斥实用新型的保护。《TRIPs协定》第1条指出:“各成员可以,但并无义务,在其法律中实施比本协定要求更广泛的保护,只要此种保护不违反本协定的规定。”由此可知,《TRIPs协定》本身并不反对成员国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方式,只要该种方式不与《TRIPs协定》的保护标准相左。还有学者进一步论述认为,《TRIPs协定》纳入了《巴黎公约》,而《巴黎公约》第1条规定的保护对象包括实用新型,因此在双边协定中纳入实用新型条款并不违反《TRIPs协定》[30]。
(2)《TRIPs协定》需要进一步革新。即使实用新型保护并非《TRIPs协定》的应有之义,也并不意味着《TRIPs协定》系应对知识产权问题的“万全之策”。《TRIPs协定》本身属于发达国家控制和操纵的结果,并未完全反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另外,《TRIPs协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数字技术的变革[31]。
(3)超TRIPs义务已经成为国际实践。如前所述,中国与瑞士、韩国、澳大利亚先后达成的自贸协定中已经出现了部分超TRIPs条款,《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自贸协定》《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中甚至已经涉及实用新型制度问题。既然超TRIPs义务并不等同于国际知识产权合作场景中的霸权行为,当实用新型制度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具有协调的可行性与正当性时,理性的行为即研究其可能的路径。
(二)“一带一路”倡议下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的可行路径
国家通常在经济学研究中被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理性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差异性的法治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未来利益诉求增加了规则治理的难度。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价值追求和关键立场的趋同性有待提升,区域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合作规则尚待建构,对于循序渐进的“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模式的诉求因应产生[32]。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应当分阶段部署由双边到多边的、从示范法到条约的、从软法到硬法的实用新型制度国际协调行动。
1. 第一阶段:部署实用新型的“软法”协调
仅表达“共同价值、兴趣、意愿或不确定的希望”的软法虽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却有“法律实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部署实用新型“软法”协调的目标有二:一是对于建有实用新型制度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而言,制度共识的寻求与制度运行的合力将为本国企业在其他共建国家的经营活动减少阻力,比较法层面的镜鉴亦为本国制度的改革提供新的视野;二是对于尚未建立实用新型制度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该类协调行动为其创造了引入该制度的契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规划该行动:
第一,借助“一带一路”现有机制的力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下简称为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倡议下最高规模的国际活动及共享互利合作成果的重要国际性合作平台。于2023年10月闭幕的第三届高峰论坛即达成了89项多边合作成果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发起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高级别论坛成果16。作为第一阶段的行动,中方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发起相关倡议,就实用新型制度的核心问题展开国际交流并与特定国家达成联合声明。在这一过程中,值得进一步探索的实用新型国际议题既可涵盖如何促使实用新型制度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助力欠发达经济体建立实用新型制度实现技术追赶等宏观问题,亦可涉及实用新型制度如何迎接计算机程序所带来之挑战、实用新型的最优保护期限等微观问题。
第二,发挥示范法的作用。发端于国际商事合同领域及仲裁领域的示范法是软法(soft law)最为常见的表现方式,其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统一国际私法协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3]。相较于条约“强制性的一体化”方式,示范法更能顾及各国实际情况,其注重的是对知识产权制度一体化趋势的引领[34]。示范法的制定主体广泛,国际法范围内该工作主要由国际组织承担。考虑仅有3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并非WIPO成员国,而中国又与该组织达成了诸如《加强“一带一路”知识产权合作协议》等共识性文件,中国可倡议由WIPO出台《实用新型示范法》。
WIPO分别于1966年、1970年、1976年编写的《发展中国家商标、商号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示范法》《发展中国家外观设计示范法》《发展中国家发明专利示范法》可作为参照,这表明该组织不仅有出台示范法的先例与动力,亦表明某一单独的知识产权客体已经成为示范法所规范之对象。《实用新型示范法》的酝酿过程是各异的二级专利制度比较、碰撞乃至融合之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示范法文本后续可以为各国在立法、修法过程中选择性接受。
第三,借鉴其他协调机制的已有实践。作为一个尊重成员多样性与实现欧盟治理统一性间的平衡政策,开放协调机制(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由欧盟于2000年召开的里斯本首脑峰会中引入,后由教育议题逐步扩展至其他多项议题。开放协调机制共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目标的提前设计,即由欧盟制定某一需协调问题的短、中、长期目标及时间安排;二是指标的预先规划,欧盟需依据各成员国的不同情况预先设计定量、定性指标及基准;三是问题的国内转化,各成员国可依自身情况采取措施将上述目标等转化成为国内政策;四是评估的后续开展,同行评价及定期监督是这一机制顺利运行的保障性条件[35],由各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的专家代表组成的政策委员会对各国执行情况针对需协调之问题评出最佳实践。虽然这一机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并不具备完全移植的可行性,却能对某一问题展开的多国协调产生镜鉴。譬如,协调开展前应当充分评估、协调过程中应当尊重各国的差异性及能动性,又如可引入某种监督机制确保某一国际议题能够在本国得到深入研讨。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用新型制度的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可以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目标借鉴开放协调机制就该制度的引入、发展、改革进行公开协商。
值得说明的是,软法亦具有硬化的基础[36],上述三项行动建议虽不具备国际法意义上的直接约束力,但围绕实用新型制度所达成的共识均能够成为后续行动的有益经验。
2. 第二阶段:开展实用新型的“硬法”协调
我国2023年11月24日发布的《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将“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作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之一。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制定是一个复杂系统[37],在与建立了本土化实用新型制度的国家进行自贸协定谈判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提前形成实用新型谈判的稳定范式。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国家规则的一致性输出有利于向海外投资和贸易的企业及个人提供相似的制度环境并实现规则在其他缔约主体间的推广[38],目前中国的自贸协定缺乏明确的知识产权战略安排与关切自身利益的统一文本[39]。若试图将实用新型制度构造成为中国自贸协定谈判中的攻势议题,就应形成范本化的条款作为供给。中国—韩国、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格鲁吉亚的自由贸易协定文本虽将实用新型条款纳入双边谈判的视野,却不能因此得出“中国已就实用新型制度的双边谈判形成了制度性的范本”之结论。这是因为,对于中国—澳大利亚、中国—格鲁吉亚的自由贸易协定而言,实用新型制度仅在“透明度条款”中被提及,即缔约方应当保证实用新型及其他知识产权客体数据库在互联网上可获取。
相较之下,《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就实用新型法律框架的交流问题和实用新型的稳定性问题展开了意见交换,但有关探讨仍有可深入的空间。譬如,格鲁吉亚将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拓宽至所有产品及方法,对实用新型的授权以本国新颖性的标准开展初步审查,这与中国在实用新型的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差异,但双方仍然将实用新型写入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透明度”条款,这是因为双方存在着某种层面的共识,该种共识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应当体现为实用新型的共识性条款。实用新型共识性条款主要包括概念性条款和合作宣示性条款,这是缔约双方协调实用新型其他细节性事项的基础。《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第13.2条将实用新型纳入该《协定》所定义的“知识产权”的范畴;在《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第15.16条第1款中,缔约双方已经认识到促进公众对实用新型制度的了解和利用的重要性,达成了交换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信息与经验的共识。这两个条款,可以成为中国提前起草实用新型谈判文本的参考。
第二,结合缔约方的立法适时调整实用新型的谈判策略。实用新型制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决定了各国可以根据本国需要对该制度进行塑造。譬如,中韩两国对于实用新型的审查存在着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之别,中国业已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较韩国而言存在着稳定性不高的问题,诉讼过程中基于现有技术所作的评价报告之效力因此成为该《自由贸易协定》关注的事项。在谈判过程中,若试图将实用新型制度作为缔约双方共同关注的知识产权事项,应当立足比较法的视角首先梳理出缔约双方实用新型制度的异同,科学应对对方的利益攻击点。
目前,中国正与摩尔多瓦、巴拿马、秘鲁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自贸协定谈判。上述三个国家均建立了本土化的实用新型制度:摩尔多瓦对实用新型(短期专利)的保护延及产品的制造方法,实用新型在该国的授权需经实质审查程序,并仅需满足相对新颖性和相对创造性的条件。相较之下,巴拿马、秘鲁与中国虽在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上秉持一致观点,但两国所采用的形式审查辅以评价报告制使其与中国的实用新型立法仍存在可协调的空间。谈判过程中,上述三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认为中国的实用新型立法无法满足其开拓国际市场和保护国内市场的谈判需求时,将针对二者关键性的差异提出相应诉求,中国应在这一过程中适时调整谈判策略,明确实用新型制度的核心进攻点,确保中国实用新型法律规则的稳定输出。
五、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已被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等决议纳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时指出,中国将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知识产权等领域改革。未来的世界知识产权合作格局仍有可探索的空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用新型制度的国际协调即可行的路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拥有广泛的实用新型制度基础及改革经验、较强的保护渐进式创新的实际需求,中国作为首倡国有能力、有契机将实用新型制度塑造为增强知识产权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论据及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要途径。这一行动应考虑“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的基本态势。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开展上述行动时,相关成果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一种从软法到硬法的协调路径更契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品格,以实用新型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多边条约在未来有待形成。
在这一过程中,应当首先明确实用新型制度的实际效用,一方面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参与此行动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国应着力实现实用新型制度等知识产权制度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统筹推进,积极推动域内实用新型等知识产权立法的域外适用,并加强国内法院应对涉外实用新型等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管辖能力。
参考文献:
[1] 余长林,孟祥旭.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创新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2 (12): 130⁃147.
[2] 马忠法,王悦玥.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知识产权国际协调法律制度 [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2, 24 (2): 122⁃136.
[3] 王泽君. “一带一路”倡议与知识产权区域制度一体化问题研究 [J]. 电子知识产权, 2019(4): 40⁃50.
[4] 季景书,孙力舟. 关于“一带一路”专利区的设想及简要论证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 (21): 116⁃119.
[5] 任虎. “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双边条约法律机制创新研究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 (1): 19⁃31.
[6] 温军,张森,蒋仁爱. “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国际合作的战略思考 [J]. 国际贸易, 2019 (7): 88⁃96.
[7] 孙南翔,王玉婷. 从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法治化机制建设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5 (3): 101⁃111.
[8] 王衡,肖震宇. 比较视域下的中美欧自贸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兼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规则的发展 [J]. 法学, 2019 (2): 107⁃128.
[9] 丁文君,庄子银,肖小勇. 发展中国家的实用新型专利与自主创新 [J]. 技术经济, 2019, 38 (4): 33⁃41.
[10] HIGASHIMA T, USHIKU K. A new means of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computer programs through the Paris convention-a new concept of utility model[J]. Computer/LJ, 1986(7): 1.
[11] 蒋舸. 著作权法与专利法中“惩罚性赔偿”之非惩罚性 [J]. 法学研究, 2015, 37 (6): 80⁃97.
[12] HOVENKAMP H. Innovation and the domain of competition policy[J]. Ala. L. Rev., 2008, 60: 103.
[13] 管荣齐. 对实用新型实质条件改革的思考 [J]. 知识产权, 2015 (9): 62⁃67.
[14] SUTHERSANEN U. Utility models and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2006:7.
[15] 董涛,贺慧. 中国专利质量报告——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实施情况研究 [J]. 科技与法律, 2015 (2): 220⁃305.
[16] ENCAOUA D, GUELLEC D, MARINEZ C. Patent systems for encouraging innovation: lessons from economic analysis[J]. Research policy, 2006, 35(9): 1423⁃1440.
[17] EVENSON R E, WESTPHAL L 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echnology strategy[J].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5, 3: 2209⁃2299.
[18] MASKUS K E, MCDANIEL C. Impacts of the Japanese patent system on productivity growth[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99, 11(4): 557⁃574.
[19] KARDAM K S. Utility model–a tool for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Japan[J].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and Japanese Patent Office, 2007.
[20] KUMAR 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Asian Countries[R]. Commiss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2002.
[21] LI W. Analysis of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patents o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China[J].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2012, 6(10): 3623.
[22] 刘雪凤,许超. 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的结构功能主义解读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 (9): 81⁃84.
[23] PILLANIA R K. The globalization of Indian hindi movie industry[J]. Management, 2008, 3(2): 115⁃123.
[24] RAMSTAD K M, NELSON N J, PAINE G, et al. Species and cultural conservation in New Zealand: maori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of tuatara[J]. Conservation Biology, 2007, 21(2): 455⁃464.
[25] 高云峰. “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保护区域合作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20.
[26] 范超. 知识产权保护全球化体制变革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J]. 国际贸易, 2014 (1): 25⁃29.
[27] 孔庆江.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与创新的理论展开 [J]. 政法论丛, 2023 (4): 26⁃35.
[28] BURY M. Protection of utility models in poland: a brief history and perspective for the future[J]. Law and Business, 2(1): 35⁃47.
[29] 毛昊. 中国专利质量提升之路:时代挑战与制度思考 [J]. 知识产权, 2018 (3): 61⁃71.
[30] 刘彬.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文本的体系化构建 [J]. 环球法律评论, 2016, 38 (4): 179⁃192.
[31] 刘彬. 论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超TRIPs”义务新实践 [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5): 70⁃79.
[32] 刘亚军,高云峰. “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区域合作差异性探析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9 (6): 38⁃44.
[33] 曾涛. 全球化视野中的示范法 [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6 (3): 35⁃46.
[34] 林应钦. 知识产权制度一体化问题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35] 朱贵昌. 开放协调机制——欧盟应对成员国多样性的新治理模式 [J]. 国际论坛, 2010, 12 (3): 8⁃79.
[36] 顾宾. 软法治理与“一带一路”法治化和全球化 [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2, 39 (4): 1⁃165.
[37] 夏玮.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规则制定的路径研究 [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2, 29 (3): 101⁃110.
[38] 王燕. 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话语权与法律输出研究 [J]. 政治与法律, 2017 (1): 108⁃117.
[39] 杨静,朱雪忠.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知识产权范本建设研究——以应对TRIPs-plus扩张为视角[J]. 现代法学, 2013, 35 (2): 149⁃160.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of Utility Model System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uan Rongqi , Zhao Yixin
(Law School,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110,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ten years since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process, China has gradually acquired the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to innovate rules, such as the utility model rules which lacking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reg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legislative basis, reform experience and coordination practice for the utility model system.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utility model system in protecting incremental innovation,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participa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mproving the strength of international gam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hina should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ed action of utility model from soft law to hard law. This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initiating coordination initiatives with the help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voca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 model law on utility models by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drawing on the EU's open 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rule negotiation, etc., and introducing the utility model system into mor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 scenario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utility model; increment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基金项目:天津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项“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全面深化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研究”(2024YJ-015)
作者简介:管荣齐(1967—),男,山东德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
赵旖鑫(1996—),女,河北涿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
1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十周年专利统计报告(2013—2022年)》。
2 同①。
3 《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第15.16条第1款规定“为了促进双方权利人和公众对实用新型制度的了解和利用,以及保持权利人和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缔约双方同意通过交换有关实用新型法律法规的信息和经验,在实用新型法律框架方面加强合作”;该条第2款规定“在缔约方没有规定实质审查的情况下,在实用新型侵权纠纷中,法院可以要求原告出具由有权机构基于现有技术检索所做的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实用新型侵权纠纷的证据”。
4" 2015年《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2017年《中国—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明确要求“应使其已授权或已注册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工业(品外观)设计、植物品种(保护)、地理标识(志)和商标数据库在互联网上可获得”。
5 《专利合作条约实施细则》第6.5条规定:“申请人依据国际申请,请求指定国授予实用新型的,只要国际申请的处理已在该国开始,关于本细则6.1至6.4规定的事项,该指定国可以适用该国本国法关于实用新型的规定,而不适用本细则上述的规定,但应允许申请人自条约第22条规定的期限届满日起至少有2个月的时间,以调整其申请适应该国本国法的要求。”第13.5条规定:“申请人依据国际申请请求指定国授予实用新型的,只要国际申请的处理已在该国开始,关于本细则13.1至13.4规定的事项,该指定国可以适用该国本国法关于实用新型的规定,而不适用本细则上述的规定,但应允许申请人自条约第22条规定的期限届满日起至少有2个月的时间,以调整其申请适应该国本国法的要求。”
6 经统计,全世界共有94个国家建立了本土化的实用新型制度。
7 根据该报告,在全世界实用新型申请量排名较优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乌克兰、意大利、菲律宾、捷克、波兰、越南和乌兹别克斯坦。
8 马来西亚《专利法》(2006)Section 17;埃塞俄比亚《发明、实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公告》(1995)第38.1条;中国《专利法》(2020)第二条第三款;韩国《实用新型法》(2023)第4条第1款;斯洛文尼亚《工业产权法》(2020)第16条第1款;匈牙利《1991年保护实用新型的第38号法案》(1991)第1条第1款。
9 阿曼《工业产权法》(2008)第1条;我国《专利法》(2020)第40条; 韩国《实用新型法》(2023)第12条;泰国《专利法》(1999)第65条bis;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2015)第109.1条;莫桑比克《工业产权法》(2015)第97条;斯洛伐克《实用新型法》(1992)第1条;我国《专利法》(2020)第22条第3款;布隆迪《工业产权法》(2009)第106条;冈比亚《工业产权法》(1989)第4条第2项之b;莱索托《工业产权法令》(1997)第5条第3项之b;匈牙利《1991年保护实用新型的第38号法案》(1991)第3条第1款;塞舌尔《工业产权法》(2014)第5条第4款;摩尔多瓦《2008年3月7日第50-L号关于发明保护的法案》(2023)第12条第(2)项。
10 中国《专利法》(2020),第四十二条第二款;韩国《实用新型法》(2015),第34条;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2015),第109.3条;罗马尼亚《实用新型法》(2013),第7条;捷克《实用新型法》(2017),第15条。
11" European Commission,The Protection of Utility Models in the Single Market,COM(95) 370 final.
12"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6.
13 《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捷克、白俄罗斯、安哥拉、亚美尼亚、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蒙古、菲律宾、斯洛伐克、泰国、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较参与统计的132个经济体而言显著受到了实用新型制度的激励。
14 同11。
15 《Enhancement of Attraction of Utility Model System》, at https://www.jpo.go.jp/e/resources/shingikai/sangyou_kouzou/archive/document/utilitymodel/report.pdf.
16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多边合作成果文件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