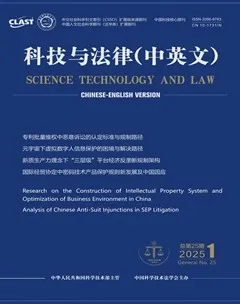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规则的适用与反思
2025-01-03陈绍伟
摘" 要: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是反垄断合理分析过程中一项基础且复杂的认识活动。为增强规范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并实现对经营者的有效监管,反垄断法基于市场份额,推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在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规则的适用需要把握一定的限度,科学分析市场份额和市场进入障碍,以平衡市场竞争与创新保护。具体到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而言,“必要性”推定方法尚不可替代市场份额的推定。因而,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市场支配地位推定仍须回归市场份额规则,同时考虑标准必要专利的特殊性和相关市场竞争环境,辅之以市场进入障碍、买方抵消力量等因素。
关键词:市场支配地位;知识产权;推定规则;标准必要专利
中图分类号:D 923" " " "文献标志码:A" " " " 文章编号:2096-9783(2025)01⁃0113⁃12
在市场经营活动中,经营者的最终目标通常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实现这一目标,经营者通常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提高价格。但受市场竞争秩序的约束,经营者一旦涨价,消费者会转而购买竞争性的商品。因而,经营者如果想成功实施理性的提价的策略,就必须有能力阻止消费者的转移。这种能力被称为市场支配地位(dominant position)。在早期的联合商标案中,欧盟法院对市场支配地位概念作了具体解释,即“涉及企业享有的一种经济实力地位,这种地位能够使其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其竞争者、客户,最终独立于其消费者,从而阻碍在相关市场上保持有效竞争。1”概言之,市场支配地位本质上是一种让消费者别无选择的市场力量[1]。
在反垄断法实践中,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推定主要是基于经济学测算的方式完成,有着许多技术性难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应地,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专利的标准化更是给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带来了新挑战。然而,在面对各种新问题时,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被表面和技术性的细节吸引,而不是诉诸反垄断法的基本原理,偏离了通往本质的轨道。所以,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反垄断法中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与推定的基本逻辑,再去反思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限度,以及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市场支配地位推定的新挑战。
一、反垄断法中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与推定
(一)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经济学家往往会通过引入测试市场力量程度的勒纳指数等剩余需求弹性(residual demand elasticity)工具,直接认定是否构成市场支配地位[2]。并且,这种直接衡量方法中还不需要事先界定相关市场[3]。但测算剩余需求是一项高度复杂的技术性工作,通常需要借助于回归分析方法以及大量的价格和成本变化数据。欧盟和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实际上都没有选择直接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方法,因为法律认定和事实认定存在认识论上的迥异,即各自对应着实践理性的不同面向。事实认定的实践理性指向依据具体的研究或探索以获得结论,需要运用可统计证实的受控实验或自然实验方法。而法律认定的实践理性旨在让“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实证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4]。现实生活中,经济学可以采用严格、精密且确定的科学研究模式,但法官审判过程不能以科学研究为模式。一方面,诉讼当事人缺乏市场实验等科学研究的金钱和时间成本,市场信息在当事人之间通常是不对等的,甚至有一些信息双方均难以得到或不可能得到。另一方面,法官与经济学家不同,囿于知识的分工和信息的不完全,法官一般在经济分析的技艺方面力有不逮,法官也没有时间等到证据足够确定之后再做出结论,他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判决,并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决定提供理由。是故,实际可操作性也很重要。若要法律可确定,就需法律可预测;若要法律可预测,就需法律可操作;若要法律可操作,就需进行法律上的改造。
法律上的改造通常需要先将经济学原理等基础事实转化成法律规则,再经由各类法学论证模型解释构成要件(或要素),以涵摄案件事实。就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而言,其基础事实是:无论是经济学强调的提价能力,抑或是法院指出的独立地位,其最终的效果都是抵消因消费者转移而带来的预期销售损失(predicted loss),也就是假定垄断者因价格上涨而预期损失的产品销售数量。理性的经营者并不随意设定涨价幅度,而是要考虑由消费者转移所产生的预期销售损失成本,继而统筹盈亏平衡,保证提高价格后预期销售损失不会超过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使经营者有利可图[5]。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转移成本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因为在没有产品壁垒或有意识阻碍等情形下,消费者(用户)可以在数字产品(如各类搜索引擎)之间轻松转移,对于相关市场上的经营者来说,“竞争仅仅是点击一下”[6]。换言之,经营者若想拥有市场支配地位,至关重要的市场策略是锁定(locked in)消费者,不让消费者流失的成本超过提价获得的利润。是以,市场支配地位的本质是让消费者别无选择。
而消费者之所以别无选择,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营者占有极大比重的市场产能,而其他经营者无力充分增加产能,无法大量满足消费者的转向需求,且消费者自身又不具备抗衡的能力。由是观之,让消费者别无选择的基本条件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经营者自己必须在相关市场总生产能力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只有在总产能中占很大的比重,经营者提高价格后,其他经营者所增加的产出只能满足少量消费者的转向需求,其他经营者的产能也就不足以阻止经营者的涨价行为,否则会造成消费者的大量流失。反垄断法一般采用市场份额数据来反映这种关系。其次,除了自身的产能比重外,经营者产能占比的比率还受到相关市场总产能比重的影响。而相关市场增加总产能的来源主要包括实际竞争者扩大产能和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实际竞争者是否能够扩大产出,一方面需要观察实际竞争者的闲置产能能否及时、充分扩大产出,通常而言,每个经营者都会闲置一部分产能以应付不时之需;另一方面,还需要注意扩大产能所需要的财力、技术水平等,倘若扩大产能需要一定的技术壁垒,实际竞争者扩大产能的计划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那么在短时间内实际竞争者很难对经营者的涨价策略造成竞争压力。至于潜在竞争者,尽管他们目前尚未在相关市场从事经营活动,但如果他们能够在价格上涨时迅速进入相关市场,同样也能够增加相关市场的总产出,消费者也就不会别无选择。申言之,一个潜在竞争者的市场进入只有在满足以下三要件时才可能被视作削弱市场支配地位的对抗力量:一是及时性,即潜在的竞争者能够及时进入市场;二是可能性,即潜在竞争者可获得适当的销售机会;三是充分性,即潜在竞争者需具备足够的生产技术和财力,方能充分实现其销售产品的机会[7]。最后,除了与实际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力量对比之外,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还取决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对比,即买方的抵消力量。如果买方力量集中,买方则不会接受卖方的涨价行为,可能会减少自己的购买量,转向卖方的竞争对手;强大的买方甚至可以为卖方的竞争对手提供财力或技术,或者亲自进入上游市场,为自己的需求作支撑。当然,有些情况下买卖双方相互依赖,互有需求。例如,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叉许可,则买方只需要直接提高自己的商品要价就足以对抗卖方,不需要转向或进入市场等方式。上述三因素是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组合要件,分开来看,每一个并不一定能够起到决定作用[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规定是基于上述基本条件衍生出的六项法律认定。《反垄断法》第二十三条的第一款、第二款以及第四款涉及经营者的单方力量,第一款旨在考察市场份额,而第二款和第四款旨在考察市场份额以外的支配地位来源。例如,控制最好的原料来源,会造成竞争对手交易成本提高,从而拉大其与竞争者之间市场力量的差距,而这又是市场份额所不能反映出来的,增加这一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考察的前瞻性。第三款和第五款则涉及实际或潜在竞争者扩大产出和进入市场的能力。实际竞争者增加产能主要取决于其财力状况和技术水平,即能否筹集足够的资金来增加土地、设备、人工等成本,以及能否大规模生产的技术能力。潜在竞争者增加产能则是看进入市场的难易程度。遗憾的是,《反垄断法》没有明文规定买方的抵消力量,但我国的司法实践对这一漏洞作出了弥补。例如,在华为诉IDC案中,法院考察了华为等标准必要专利实施者对IDC专利权人是否构成有效制约2。
(二)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
法律改造后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之规范可供法律人分析和适用,可操作性困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纾解。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纠纷的解决机制,也要考虑司法认定的成本和效率问题。换言之,法院在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时也要考虑司法成本的最小化。在此背景下,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规则应需而生[9]。法律推定是经法律规定并由司法人员作出的具有推断性质的事实认定,以减少不必要的证明和避免难以完成的证明,其直接后果是证明责任的免除或重新配置[10]。从法律的可操作性角度来看,把个别适用的事实推断上升为普遍适用的法律推定,可以精简那些非必要的证明活动,有效降低司法成本,同时防止个别难以证实的事实问题对案件整体进展造成阻碍或延误,进而提升司法效率。
然而,不是任何与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因素都能成为推定的前提要件。推定是否合理取决于前提要件与推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当联系的盖然性越高,推定越合理。当然,这种高度盖然性还没有达到必然性的程度。简言之,并不是有前提要件就一定有推定事实;如果有前提要件就可能有推定事实,那么前提要件与推定事实之间便具有一定的盖然性;如果有前提要件就很有可能有推定事实,盖然性达到较高的程度,那么推定就是合理的。
各国反垄断法,不论是成文法,抑或是普通法,均将市场份额作为市场支配地位的表征(proxy),其主要原因是市场份额与市场支配地位之间存在正相关性[11]。但这也是一种有限度的表征。亦即,如果需求弹性、供给弹性两变量保持不变,那么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与其市场份额成正比[11]。现实是,不同相关市场之间的市场弹性迥然不同。反垄断执法机构不得不多方面地收集信息,不仅需要掌握经营者的市场份额数据,还需要了解经营者所面对的需求和供给情况。随着司法经验的不断积累,法院在需要证明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案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推定公式,即先判定是否存在相关市场,再调查市场份额。欧盟法院更是在大陆制罐案中因欧盟委员会未能界定相关商品市场,直接撤销了其处罚决定。由此可见,相关市场界定成为市场份额测算的前置程序,界定相关市场的目的是识别竞争者,使市场份额尽可能精确地反映市场支配地位;界定的范围包括相关商品市场、相关地域市场和相关时间市场;界定的方法包括假定垄断者测试(small but significant not-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SSNIP)等,以预估需求替代、供给替代和潜在竞争的约束。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鞋业案中指出:“一个产品市场的范围取决于消费者使用时可合理进行替代的产品以及产品本身与替代品之间的需求弹性。3”美国第三巡回法院继而在比萨饼案中提出了需求交叉弹性的测试要求,并指出,“除了产品的价格、用途以及质量,一种产品与另一种产品之间的需求交叉弹性也可以说明合理的可替代性。4”是以,相关市场界定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划定竞争范围的替代性分析过程。
市场份额之所以能成为市场支配地位的表征,除了经济学原理作支撑之外,其更现实的理由是,很多时候实施违法排他性行为的经营者占据了市场很大的份额。例如,掠夺性行为的相应成本与掠夺者的市场份额相对应。另外,经营者的各种市场封锁行为之所以能成功,也往往依仗其巨大的市场份额。
尽管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是以一定的客观规律或经验法则为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其推定结论具有可假性,即不一定都符合客观真实情况。在霍夫曼忠诚折扣案中,欧盟法院虽然认为“除非有特殊情况,很大份额本身就表明存在支配地位”,但它也承认“市场份额的重要性因市场而异”,“巨大市场份额作为存在支配地位的证据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因素”5。市场份额是识别市场支配地位的不完全指示器,市场份额的证明力很可能基于对不同因素的考量而被削弱。例如,在差异化产品市场,市场份额通常不适合作为证明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的证据,美国的玻璃纸案业已证实这类市场的界定总是会出现错误。倘若经营者已经开始收取垄断价格,经营者自身价格的弹性就很高,因为其再进一步提价,消费者可能会停止购买或转向替代产品,此时进行SSNIP测试,就会得出高度可替代性的结论,市场份额也随之被低估,即著名的“玻璃纸谬误”(cellopane fallacy)[12]。另外,即使经营者有很高的市场份额,也不一定能证明经营者不存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例如,若相关市场上市场进入的自由可以得以保障,高市场份额的经营者也不会被法院认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在布鲁什维克案件中指出:“被告在一个与保龄球相关的地方市场占百分之百的份额,尽管高市场份额可以证明存在垄断势力,但在市场进入障碍很低的市场,却不具有这样的证明力。6”该法律推断的理论依据是,在市场进入自由的情况下,市场调节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与畸高的市场份额,如独占或寡占,都将很快转型为竞争市场。
基于可假性,推定在纯粹逻辑层面上是可以被反驳的。事实上,无论是欧美的司法实践,还是我国反垄断立法,都将市场份额的推定视为一种可反驳的推定,即根据一定事实作出的构成表见证明的推断,可以通过提出相反证据来推翻。这些相反证据包括差异化产品市场、动态市场、招投标市场、市场份额的历史发展、市场准入限制、买方抵消力量等[13]。总而言之,市场支配地位推定的方法分为三步:首先界定相关市场;其次确定市场份额;最后结合相关市场竞争环境综合考量。
二、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
(一)知识产权的拥有与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
知识产权与市场支配地位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下,人们对于这两者间关系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14]。在反垄断法执行较为严格的时期,一些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处理知识产权领域垄断案件,尤其是涉及搭售行为时,往往会倾向于采取一种预设立场,即认为拥有知识产权等同于具有了市场支配地位7。
历史上,美国对于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关系从分离向统一的认知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15]。第一和第二阶段,美国法院意识到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之间存在固有的冲突。在这两个时期,法院都把专利法和版权法视为授予垄断,但他们对这些垄断的适用范围的看法有很大不同。第一阶段基本上将任何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商业行为视为本身合法,而不考虑其随后的反竞争效果;第二阶段虽然对其本身合法性有着同样的看法,但前提是这些商业行为属于法院定义的知识产权交易范围。在第二阶段,分离观点达到顶峰,形成后来被称为“九大禁忌”的规则(the“Nine No-No’s”)8。第三阶段对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当时的美国副助理司法部长阿伯特·利普斯基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布埋葬九大禁忌:“作为理性经济政策的陈述,‘九大禁忌’包含的错误多于准确。”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不再被视为相互冲突的法律部门,而是统一法律制度内的互补政策。这两项政策都有着相同的经济目标,“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消费者想要的东西,从而实现财富最大化”和“鼓励创新、产业和竞争”。这一互补观点在由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共同颁布的《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中得到明确的体现。该指南认为知识产权与任何其他形式的财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仅仅拥有知识产权并不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知识产权许可允许经营者将互补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因而通常是有利于竞争的。在伊利诺伊州工具工厂诉独立墨水公司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由于知识产权不一定赋予市场力量,法院不应假定知识产权赋予市场力量,从而废除了其先前的一些判决9。该决定与《知识产权许可的反垄断指南》相一致,在该指南中,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确立的三大核心原则之一便是不会假定知识产权赋予市场支配地位。
现有欧盟法的框架下,欧盟竞争政策的倡导者和知识产权的支持者达成共识,承认竞争法和知识产权立法是现代产业政策的互补组成部分[16]。它们被设计用来实现相同的目标,即优化资源的使用和提高福利。长期以来,欧盟法院试图在尊重产权的基础上协调欧盟竞争政策的经济标准,并认为拥有知识产权并不等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欧盟竞争法规制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权利的实质特点及经济效应上,而非建立在对该权利是否属于知识产权或其他财产权的区别上[17]。我国在《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指南》的分析原则中亦明文规定,不因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而推定其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我国首例非标准必要专利拒绝许可垄断案中,最高法撤销了一审判决,认定日本某株式会社不构成拒绝交易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最高法在裁判文书中指出:“鉴于相同商品可能存在不同生产技术且不同生产技术之间可能具有替代性,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可以构成认定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但不能仅根据经营者拥有知识产权推定其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10”
从世界主要国家的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司法实践来看,一般不直接推定持有知识产权的经营者必然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也没有排除一个事实,即知识产权的持有与运用,在特定情境下,确实存在构成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性。
(二)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推定的限度
无论是在美国、欧盟、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均遵循反垄断法的一般分析规则,即在相关市场界定之后,从市场份额入手推定知识产权权利人是否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即使知识产权的客体已构成一个独立且近乎垄断的相关市场,亦即该市场中不存在可替代的商品,司法机关在裁决时往往仍会展现出一定的宽容态度,审慎地平衡创新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因为知识产权客体构成独立的相关市场,表明权利人的创新具有重大的价值,应允许他们在市场上获得充分的回报。
市场力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市场支配地位是设定临界值的市场力量。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和推定并非纯粹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这取决于反垄断执法成本以及我们想从市场中剔除多少的市场力量[11]。更进一步而言,何种程度的市场力量又是可接受的,关键在于反垄断法究竟是以短期考察,还是长期考察为基准[13]。如果反垄断法更偏向于市场力量对短期市场竞争影响的考察,那么配置效率是首选的经济目标,即将社会的现有资源投入经济最有意义的用途上。换成经济学的表述,当供需均衡时,倘若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则所有能够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收益都能得到实现,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在追求以配置效率为主的竞争政策目标下,创新的回报不应当高于竞争水平,社会给予创新者的回报仅限于其投入的平均固定成本[18]。而在长期主义者看来,这般规定不利于创新激励,最终不利于经济增长。正如伊斯布鲁克大法官所言:“如果降低产品5%价格的代价是,牺牲1%的创新增长率,这将是一场灾难。[19]”侧重长期考察的反垄断法更加包容以创新为核心竞争手段的市场。
因而,在设计知识产权领域市场支配地位的规范性标准时,市场份额的推定是有限度的,法院会接受更高的临界值,并在市场份额要件之外要求补充其他要件,以维持推定论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微软垄断案中,美国地区法院法官杰克逊经过审查,判定微软公司在全球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市场中占据市场支配地位,这一结论的直接依据是微软在该领域持有的高达95%的市场份额。除了市场份额,杰克逊法官在裁决过程中还考虑了另外两个因素:其一,微软的市场份额受到进入操作系统时的高壁垒保护;其二,作为高壁垒的后果,微软用户没有商业上可行的替代品来取代视窗操作系统11。同样,欧盟法院在布罗纳案也指出,仅知识产权权利人在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是不够的,该市场支配地位还必须对进入市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2。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使一个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在相关市场上占到了近乎100%的市场份额,即拥有事实上垄断地位,仍然有必要考察是否存在阻碍潜在竞争者的市场进入障碍,换言之,是否还可能有新的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20]。
三、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
(一)对必要性推定方法的质疑
标准必要专利的特殊性在于标准层面[21],即如若是强制性标准,只能依照标准生产产品,此时标准必要专利构成独立的相关商品或技术市场[22];但对于非强制性标准而言,标准的适用具有可选择性,换言之,市场上存在可替代的商品或技术。在多起标准必要专利垄断案件的裁判文书中,关于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分析可能过于简化。有时,仅凭“必不可少、不可替代是其本质内涵”,就界定每一个标准必要专利都是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又因为“每一个标准必要专利都是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进而推定每一个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独占100%的市场份额,具有市场支配地位[23]。这种必要性推定方法既没有界定相关市场,也没有测量市场份额。尽管该方法避免了复杂的经济学分析,但标准必要专利的必要性与市场支配地位之间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其证明力是否与市场份额相当,都有待商榷。
“必要”并非标准制定组织(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SSO)认定标准专利的原有条件,而是经过了一段从无到有的过程13。美国最早的SSO专利政策不包括与专利必要性相关的明确要求。ANSI的政策起初适用于“涵盖”(covering)标准化产品生产的专利,尽管“涵盖”的含义ANSI也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在1983年出台的政策中又删除了“涵盖”一词。直到IEEE在其政策中引入了“必要”专利声明的概念后,ANSI才开始效仿。欧洲的SSO比美国更早使用了“必要”概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电信机构达成了一项技术合作协议,将“必要”专利定义为:“从标准直接衍生出来的、被认为是实现标准绝对必要的专利。”1993年,ETSI定义比四国达成的技术合作协议中有关“必要”的表述更为微妙,它规定:“适用于知识产权的‘必要’是指基于技术而非商业理由,考虑正常的技术惯例和标准化时通常可获得的技术水平,不可能制造、销售、租赁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修理、使用或操作符合标准的设备或方法而不侵犯该知识产权。”该定义被ETSI沿用至今。易言之,倘若实施者不侵犯专利,在技术上就没有可能制造、使用或销售标准化产品。可见,ETSI政策中“必要”概念的范畴要小于IEEE政策的。在必要性的认定过程中,ETSI比IEEE更关心专利在技术上的可替代性,而IEEE还要求标准必要专利在商业上同样不可替代。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应当考虑商业必要性(commercial essentiality),即是否将成本、效率等因素考虑在内。
一项调查表明,所检查的10个SSO策略中只有2个使用了“商业”而不是“技术”必要性,且只有ETSI明确排除了确定必要性的商业因素,还有7个没有明确说明“必要性”是指技术上的还是商业上的必要性[24]。现实中,SSO是选择技术必要性抑或商业必要性,各有其目的。选择技术必要性可以限制专利披露和许可要求所涵盖的专利数量,可以减少非必要专利可能借商业必要性之机进入标准必要专利范围的机会主义成本,也可以让消费者避免承受实施者转嫁的经济成本。同时也会增强该SSO的强制性要求,降低对实际或潜在参与者加入SSO的积极性。其次,商业必要性的选择也并非不无道理。乔治·康特拉斯教授受到联合管道案的启发14,假设了一个合理的例子,某市政电气标准规定了布线管道的公差范围(压力、温度、耐腐蚀性、抗穿刺性等)。这种管道通常由铝制成,铝作为管道布线材料,在技术上不可能没有替代品,黄金和聚氯乙烯都可以在技术上替代铝,但后两者的成本过高,就商业替代而言,是不切实际的[25]。该例说明商业必要性对一些标准的认定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由是观之,SSO政策的文义或目的解释都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必要性”含义。或许格式合同的中间解释方法是一个更为合理的进路。SSO与专利权人之间签订的许可申明表是一份格式合同,乃是由SSO一方制定,主要内容包括标准必要专利的信息披露和FRAND许可[26]。诉讼当事人对于格式合同中的“必要性”产生分歧时,法院应当采取中间立场听取各方诉求以客观合理解释标准必要专利的“必要性”。因而,“必要”是定义为技术性的,还是商业性的,事前不能确定,需要进行个案的具体分析。
再则,并非所有申报的标准必要专利都是必要的,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度声明(over-declaration)。由于资源和人员的限制,SSO很少审查或验证标准必要专利的必要性。事实上,为了吸引更多的专利权人,某些SSO通过制定标准说明文件,明文规定内部工作组不应评估标准必要专利的必要性,不应干预标准必要专利的可适用性,并规定内部工作组只有从表面上审查待披露专利权人陈述的义务。因此,根据SSO政策的自愿原则,专利权人是否有义务向SSO披露哪些专利确实是必要的,或将其标准必要专利以何种方式许可给其他人,均由专利权人单方面确定,仅受诉讼的约束。这可能为标准必要专利的过度声明打开了口子,欧盟委员会2017年的一份通报也证实了普遍存在的过度声明问题。证据表明,在已申报的关键技术专利中,只有一半可能是真正必要的[27]。甚至在无线星球诉华为的案件中,英国高院业已意识到,“在确定适当的专利许可费率时,标准必要专利可能存在过度声明的问题15”。过度声明问题也是TCL诉爱立信案件的争议焦点之一16,两份判决的法官都呼吁提高专利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令人担忧的是,过度声明的问题可能在未来会更加泛滥。因为,当下的一些显著非必要的专利还能够通过同行内部共有知识在SSO形式审查中予以排除,但随着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技术的发展,万物互联,SSO和实施者更加难以对跨行业的标准必要专利之必要性作出形式上的评估和排查[28]。
(二)回归市场份额的推定规则
定义的多样性和过度声明无不说明必要性推定方法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在细节上又经不起推敲。而市场份额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要件,一则有经济学原理作为其基础,二则有排他性行为反垄断规制的执法经验证明了市场份额与市场支配地位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相较之下,标准必要专利的必要性推定方法难以成为与市场份额一般的市场支配地位推定要件。因此,在处理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纠纷时,对于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我们应当回归到更为根本的出发点,即依据市场份额作为核心判断依据,再结合知识产权领域的特点,辅之以市场进入障碍等要素进行综合考量。
为确定经营者在某一时间段的市场份额,必须确定该时间段的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在界定相关市场之前,有必要先扫清另一个认知偏差。我们不能被现实中知识产权权利人规模或组织形式所误导,部分经营者虽然拥有很多重要的标准必要专利,而其企业规模却很小,尤其是像非实施者(non-practicing entities, NPE)这类的组织形式,他们甚至没有或几乎没有实体业务。企业规模小或组织形式特殊并不意味着市场份额很低,市场份额的高低取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相关市场界定本质上是可替代性问题,如果产品或服务可以被认为是可替代的,那么它们就属于同一个相关市场[8]。
通常而言,界定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的相关市场遵循反垄断相关市场界定的一般办法,即界定相关商品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上的需求交叉弹性和供给弹性。其中,界定相关地域市场时需考虑专利的地域限制,相关地域市场可能包括国内市场、国外市场以及全球市场;在界定标准必要专利相关商品市场时,鉴于标准必要专利的核心是技术,法院还需要考虑相关技术市场。相关技术市场在本质属性上就是相关商品市场,它只是相较传统的产品市场而言在内容上更为复杂些,但是并未因此而完全超出产品市场的范畴[29]。在界定标准必要专利的技术市场时,还需要区分许可范围。若仅对标准必要专利本身进行许可,那么其许可范围应界定为该专利技术及其可替代技术;若许可包含标准必要专利技术及其产品,那么许可范围应将该专利技术和产品以及对应的替代技术和产品纳入市场。另外,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相关市场的界定切忌以结果为导向。研究发现,多起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法院均判定“一个标准必要专利构成一个相关技术市场[30]”。这是多方要素考量的个案推定结果,但绝不是一般性的认定结论。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反垄断执法宽严程度的晴雨表,有一定的政策性[31]。如果市场界定得十分狭窄的话,产品的每一个供应者都有可能是垄断者。波斯纳也曾对相关市场界定的灵活性表示担忧,“市场界定足够弹性,高度集中变得无处不在,数量惊人的良性兼并能够被弄得好像带有危险的垄断性[32]”。在标准必要专利的相关技术市场界定过程中,有时需要事先解决“必要性”多义的问题,因为若只考虑技术因素,标准必要专利的相关市场可以界定为其许可的相关市场,但加入商业因素,具有同样或类似商业效果的替代技术或产品与标准必要专利及其产品可能共同构成相关市场[33]。
在某些案件中,法院在计算市场份额时,借由“一个标准必要专利构成一个相关技术市场”的推定,直接认定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具有100%市场份额,这种市场份额的计算方式也值得商榷。或许在标准必要专利单独构成相关市场时,该推导的结论可能与实际市场状况一致,但论证不一定可靠。易言之,推导过程中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关联性不甚明显,需要加强论证。标准必要专利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也有无形性的特点,在成本结构和更新速度上,都有别于有形商品。标准必要专利更注重技术创新上的投入,专利权人必须保持持续的创新才能保证自己的市场竞争优势,因而标准必要专利及其产品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同质性产品,而是差异化产品。同质性产品之间如果没有显著的价格差异时,可以对相关市场上的市场份额进行数量上的考察。而差异化产品更适合以销售额为基础的计算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相比价值低的产品,价值更高的产品的应有权重可以得到实现,以销量为基础的计算不能反映市场参与者的真实市场支配地位。可现实是,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许可费率往往被当事人视为商业机密,法院很难获取准确的许可费信息,这也导致许可费率争议不断。此时,可以借鉴欧盟和美国两大法域的执法经验,即倒推法和可比法17。在无法获取相关数据信息时,可以根据个案的特殊情况,选择最优证明力的因素作为计算市场份额的依据。
(三)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市场支配地位推定的其他要素
最后,必须承认的是,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领域,市场份额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的重要性正在减弱,同时出现一些新现象,构成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市场支配地位推定的关键因素。传统产业经营者的竞争主要发生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一旦经营者价格上涨,消费者会转而购买其竞争对手的替代性产品,其竞争者则可以借此扩大产能,填补经营者的剩余空间。多数情况下,竞争者的生产能力与其市场份额呈正比,是以在考量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时,市场份额可以作为主要的推定指标。新兴产业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研究与开发阶段,反而在进入生产销售环节,经营者增量成本很小,即经济学家所言的“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34]。例如,开发一款软件的投入成本很大,但复制的成本却很低。因此,竞争环节的转移以及成本结构的变化削弱了市场份额与扩大产能能力之间的关系,市场份额推定规则的功能有所退化。“创造性破坏”更是加剧了这一过程,如果竞争对手开发出性能更好的产品,则现有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很快便被颠覆,即使他有很高的市场份额[35]。
标准必要专利是技术与经济的链接,技术会改变,但经济规则和原理不会。我们必须追究根本,探寻市场支配地位的源头,回归市场支配地位的本质。亦即,要想获得或维持市场支配地位,必须能够阻止消费者转向。在新兴产业中,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认定要素中的市场进入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边际成本相对不高,竞争者只要能够有效进入市场,则其扩大产出的能力一般不会受到严重制约。而市场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进出,取决于市场壁垒有多高。传统的市场壁垒有资本壁垒、技术壁垒等,新兴产业下的市场壁垒有网络外部性和锁定效应。市场上,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可以通过路径依赖锁定实施者。当今,技术标准是繁荣社会经济活动、促进贸易合作的技术纽带。SSO的主要目标是更加高效地管理标准的制定、实施和推广,他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保持技术的互操作性。所以SSO力图让专利权人作出FRAND承诺,以竞争性价格实施许可,避免不必要的专利和不公平高价[36]。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为了加入SSO,增加许可机会,一般有动力与SSO达成FRAND承诺,不会过度使用专利权。当其专利宣布为标准必要专利,在实施者形成路径依赖后,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可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规避事前的FRAND承诺,或者以禁令威胁的方式实施专利劫持(patent hold-up)行为[37]。这将会对许可谈判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对含有标准必要专利产品的生产已经进行事前投资的经营者来说,专利劫持使得专利权利可以获得远超其经济贡献的许可费用,这种许可费用被夏皮罗形象地称为许可税,实际上是阻碍而非推动了创新[38]。
除了市场进入障碍之外,买方的抵消力量也是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尤其是在交叉许可(Cross-licensing)中。谈判是一种商业行为,也是一种市场解决纠纷的机制。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和实施者可以在谈判中达成FRAND的许可协议,也可以在谈判中解决标准必要专利的许可费率纠纷。也即,根据Lemley-Shapiro仲裁机制,设立一个独立的仲裁处,让当事人回到谈判桌前,自愿以报价的方式确定趋近于真实的许可费率[39]。在华为诉中兴案中,欧盟法院确立的免于承担反垄断责任的安全港规则,鼓励专利权人和实施者主动、积极地谈判18,该规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谈判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的重要性。中国、美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公布的标准必要专利指南中都规定了善意谈判规则19,以促进私人谈判许可使用标准必要专利,专利持有人自愿向标SSO承诺以FRAND条款向寻求实施标准的第三方提供许可。如果说合同法在意谈判双方的善意,那么反垄断法更关心谈判双方的议价能力。合同法遵循的自愿原则,强调意思自治和双方合意,尽管合同法也有显失公平等规定,但在双方实质议价能力平衡上的作用有限[40]。反垄断法不仅规制卖方垄断,也监管买方垄断(monopsony)。买方垄断者通过减少对产品购买需求,可以迫使供应商以低于竞争价格向其出售产品,该行为通常会减少买方垄断市场的产出量,与卖方垄断一样会损害消费者福利。因而,在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买方的抵消性力量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摩托罗拉案中,构成抵消性买方力量的关键在于买方是否有能力(或威胁)转向竞争供应商20。而这种能力取决于买方是否存在可靠的替代选择、是否有证据证明买方有动机制约卖方势力,以及买方是否构成足够的规模[13]。在标准必要专利的交叉许可谈判中,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与实施者之间是博弈的关系,彼此之间都需要获得双方的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双方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更容易达成许可。并且,与专利劫持相对,实施者也可能实行反向劫持(patent hold-out),即实施者利用其谈判筹码拒绝专利权人的FRAND许可或索取低于FRAND水平的许可费率,抑或为实现前述目的而推迟谈判[41]。因而,在认定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市场支配地位时,须考虑实施者的抵消性力量,评估其与专利权人之间交易的对称性[42]。
四、结语
竞争约束既可能来自竞争对手的现有供应和未来扩张,也可能来自潜在竞争者的进入[43]。当某一经营者试图在相关市场中摆脱枷锁,拥有我行我素、不受竞争约束的行为自由,能以超出竞争价格定价而获取垄断利润时,该经营者就拥有了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因为某些经营者因其规模、技术优势或市场策略等因素自然占据了市场的支配地位。只有当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且不具有任何正当理由时,反垄断法才将其纳入规制范畴。
为了保证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我们不断改进评估工具,并创造出了市场份额的推定规则。但适用推定规则具有双刃剑的效应:一方面,它可以为认定难以证明的市场支配地位提供捷径;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使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事实认定落入陷阱或步入歧途。为了防止后一种情况的出现,法官在适用推定规则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该规则的条件,在具体案件情况不完全符合推定条件时不能扩大适用,以压缩产生负面效应的可能性空间。在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中,“必要性”推定论证不足,缺乏理据,并不能替代市场份额的推定规则。另外,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市场份额推定规则的证明力有所弱化,需要辅之以市场进入障碍和买方抵消性力量等更多因素的考量。概而言之,合理推定应建立在充分的说理和足够强的证明力基础之上,切忌过于轻率地推定经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
参考文献:
[1] 许光耀.支配地位滥用行为的反垄断法调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8:16.
[2] BAKER J B. Market definition: an analytical overview[J]. Antitrust L J, 2017, 74: 97⁃142.
[3] KAPLOW L. Market definition: impossible and counterproductive[J]. Antitrust LJ, 2013, 79: 361.
[4] 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力, 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91.
[5] KATZ M L, SHAPIRO C. Critical loss: let's tell the whole story[J]. Antitrust, 2002, 17: 49.
[6] 戴维·S. 埃文斯.数字世界的纵向约束[J].竞争政策研究,2020(6):31⁃45.
[7] 王晓晔.反垄断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3⁃85.
[8] 理查德·威尔士,大卫·贝利.欧盟竞争法[M].刘迪,等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34⁃231.
[9] KIRKWOOD J B. Market power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J]. BUL Rev., 2018, 98: 1169.
[10] 何家弘.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J].中外法学,2008,20(6):866⁃880.
[11] 赫伯特·霍文坎普.美国反垄断:原理与案例[M].陈文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61⁃66.
[12] TURNER D F. Antitrust policy and the cellophane case[J]. Harvard Law Review, 1956, 70(2): 281⁃318.
[13] 乌尔里希·施瓦尔贝,丹尼尔·齐默尔.卡特尔法与经济学[M].顾一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75⁃249.
[14] 王先林.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0:272.
[15] TOM W K, NEWBERG J A. Antitrus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separate spheres to unified field[J]. Antitrust LJ, 1997, 66: 167.
[16] JONES A, SUFRIN B. EU competition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813.
[17] 乔纳森·特纳.欧盟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M].李硕,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5.
[18] LEMLEY M A.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ree riding[J]. Tex L. Rev., 2004, 83: 1031.
[19] GILBERT R J. Innovation matters: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high-technology economy[M]. Cambridge: MIT Press, 2022: 13.
[20] 史蒂文·D.安德曼.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M].梁思思,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43.
[21] 郭壬癸.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滥用司法规制困境与完善[J].中国科技论坛,2019(1):143⁃151.
[22] 时建中,陈鸣.技术标准化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兼论新经济下知识产权法与反垄断法的互动[J].科技与法律,2008(5):45⁃50.
[23] 袁波.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兼议“推定说”和“认定说”之争[J].法学,2017(3):154⁃164.
[24] A study of IPR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a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Standards Setting Organizations worldwide[R/OL]. (2012-09-17)[2024-03-09].http://home.tm.tue.nl/rbekkers/nas/Bekkers_Updegrove_NAS2012_main_report.
[25] CONTRERAS J L.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echnical standardization law: competition, antitrust, and paten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209⁃230.
[26] 宁立志.专利的竞争法规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355.
[27] Van Audenrode M, Royer J, Stitzing R, et al. Over-declaration o 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nd Determinants of Essentiality[R/OL]. (2017-08-27)[2024-03-09].https://www.cresse.info/wp-content/uploads/2020/02/2017_pa13_d2_Over-Declaration.
[28] STORM C 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versus the world: how the internet of things will change patent licensing forever[J]. Tex. Intell. Prop. LJ, 2021, 30: 259.
[29] 丁茂中.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技术市场问题[J].电子知识产权,2018(5):13⁃20.
[30] 王晓晔.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诉讼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5(6):217⁃238.
[31] 王先林.论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相关市场界定[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8(1):123⁃129.
[32] 理查德·A.波斯纳.反托拉斯法[M].孙秋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72.
[33] 仲春.标准必要专利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研究[J].知识产权,2017(7):32⁃37.
[34] KATZ M L, SHAPIRO C.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3): 424⁃440.
[35] 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et 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2): 701⁃728.
[36] HOVENKAMP H. FRAND and antitrust[J]. Cornell L. Rev., 2019, 105: 1683.
[37] LEMLEY M A, SHAPIRO C.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J]. Tex. L. Rev., 2006, 85: 1991.
[38] SHAPIRO C, WAEHRER K.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vs. qualcomm: mangling microeconomics[J]. Qualcomm: Mangling Microeconomics, 2022, 10: 294⁃314.
[39] LEMLEY M A, SHAPIRO C. A simple approach to setting reasonable royalt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J]. Berkeley Tech. LJ, 2013, 28: 1135.
[40] LEMLEY M A. The benefit of the bargain[J]. Wis. L. Rev., 2023(1): 20.
[41] EPSTEIN R A, NOROOZI K B. Why incentives for \"patent holdout\" threaten to dismantle FRAND, and why it matters[J]. Berkeley Tech. LJ, 2017, 32(4): 1381⁃1432.
[42] 李剑.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标准必要专利与抗衡力量[J].法学评论,2018,36(2):54⁃65.
[43] 时建中.反垄断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4:4.
Applic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Rule of Presumption of Market Dominance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ak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as an Example
Cheng Shaowei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determination of market dominance is a basic and complex cognitive a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rational analysis of anti-monopol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operability and enforceability of the norm and achieve effective supervision of business operators, the Anti-Monopoly Law presumes the existence of a dominant market position based on market share.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sumption of market dominance needs to grasp certain limits, and scientifically analyze market share and market entry barriers to balance innovation protection and market competition. Specifically, as far as the presumption of market dominance of SEP owners is concerned, the \"necessity\" presumption is not yet a substitute for the presumption of market share. Therefore, the presumption of market dominance of SEP owners still needs to return to the market share ru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articularity of SEPs and the relevant market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supplemented by factors such as market entry barriers and buyers' countervailing power.
Keywords: market domin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esumption rule;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课题“数字经济背景下《反垄断法》理论与实践路径研究”(21SFB2024)
作者简介:陈绍伟(1995—),男,安徽铜陵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竞争法,知识产权法。
1 United Brands v Commission Case 27/76.
2 (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06号。
3 Brown Shoe Co., Inc. v. United States, 370 U.S. 294 (1962).
4 Queen City Pizza, Inc. v. Domino's Pizza, Inc.,124 F.3d 430 (1997).
5 Hoffmann-La Roche v. Commission,Case 85/76.
6 Brunswick Corp. v. Pueblo Bowl-O-Mat, Inc., 429 U.S. 477 (1977).
7 Jefferson Parish Hospital District No. 2 v. Hyde, 466 U.S. 2 (1984).
8 “九大禁忌”包括:将非专利材料与专利捆绑在一起;将授予被许可人的专利强制返还给许可人;对专利产品转售的限制;限制被许可人与他人往来的自由;许可人不得许可他人使用的协议;强制“一揽子”许可;与销售专利物品无关的转让费;限制销售采用专利方法生产的非专利产品和转售价格维持。
9 Ill. Tool Works Inc. v. Indep. Ink, Inc. (ITW), 547 U.S. 28 (2006).
10 (2021)最高法知民终1413号。
11 U.S. v. Microsoft Corp., 253 F.3d 34 (D.C. Cir. 2001).
12 Oscar Bronner GmbH amp; Co. KG v. Mediaprint Zeitungs- und Zeitschriftenverlag GmbH amp; Co. KG and others Case C-7/97.
13 标准制定组织,顾名思义,是一个专门负责制定、修订和推广标准的组织。根据组织的地域性,可以分为国际化标准组织和区域性或行业性标准组织。较为典型的有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简称ANSI)、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简称IEEE)、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简称ETSI)。
14 Allied Tube v. Indian Head, Inc., 486 U.S. 492 (1988).
15 Unwired Planet v Huawei, High Court of Justice for England and Wales, judgment dated 5 April 2017, Case No. [2017] EWHC 711(Pat).
16 TC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oldings Ltd et al. v.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 et al.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 Case 8:14-cv-00341-JVS-DFM, 8 November 2017.
17 倒推法是指,依据使用所涉技术制造的产品在下游商品市场的销售额占比倒推出该技术所有人在上游技术许可市场的市场份额;可比法是指,可通过确定所涉技术的可替代技术数量估算市场份额, 此时执法机构将假定每个技术所有人占有相同的市场份额。
18 Huawei Technologies v ZTE,Case C-170/13.
19 欧盟在2017年发布的《制定关于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欧盟方法》中提到“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双方应本着善意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许可条件”,同样强调谈判双方的善意;美国USPTO、DOJ、NIST在2021年12月联合发布的《2021年联合政策声明(草案)》首次对SEP权人与实施者双方都提出了善意谈判的行为框架指引。2023年6月30日,我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对标准必要专利善意谈判加以讨论。
20 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No. 12-1548 (Fed. Cir.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