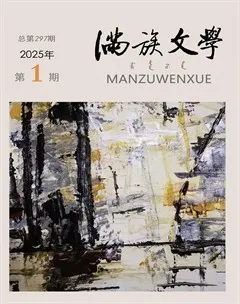风箱
2025-01-01紫藤晴儿
树枝的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那些忽明忽暗的节奏让生活慢下来。火的烘烤让一颗心始终保暖。多么好,你生起的人间烟火也像一些勾连的引线穿过我心底的盲点,让我看到了一些发亮的事物,它们不再模糊。幻灭的事物都在复出。这些年四处奔走,远离了土地,远离了故乡,也远离了一架陈旧的风箱。隔着几十年的时空已没有再走近过一架风箱,我早已忘记了它曾经的存在。承认遗忘使我再次向一架风箱靠近。我弯曲着身体也学着祖母的样子,拉动着风箱,扇动着火苗,让日子也像一团火,有了滋味,有了五谷杂粮的味道。锅里汩汩冒出的水汽,让我泪流满面。
不知道从两岁还是三岁起,我便在锅台旁烧火,不为别的,只为去拉动风箱。风箱在农村家家都有,只是大小各不相同。要根据自家的灶台大小去找木匠定做。我不记得我家是哪位巧手的木匠做的,我拉的永远是那一架原木风箱。它不会坏,也不会变老,只会越用越灵。风箱和灶台有一个管道用来通风,风力越大,火苗就越高。随着身体慢慢长大,我的力气也越来越大了。小时候拉风箱需要两只胳膊一起用力,母亲不让我拉,我却非要拉。一是可以随时讨要到一些好吃的,比如烧火时需要随时劈柴,父亲发现里面有能吃的虫子就会单独放在一个小的铁锹上在火上烤给我吃。那样的白色的蛤虫是可以吃的。穷日子里闻到它就是闻到肉的香味,我总是美得不亦乐乎。在秋天,有时也会烧点红薯和玉米还有花生什么的。总之可以烧的,母亲也总会给我烧一点吃。当然我也吃过烧的麦穗,无论是烧什么我都是要求亲自拉着风箱,听着风箱呼哒呼哒地响,像一头卖力的老黄牛在一个劲地喘息着。我不记得那时的天是如何黑下来的,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觉得也很快乐。有吃有喝的很是满足,最主要的是一架风箱,随时可以充当一个玩具。最为调皮的事是,即便不烧火做饭我也想拉它,烟灰从炉口直接冒出来,一定会被母亲骂上一顿。还是再说说那烧熟的粮食吧,无论是红薯还是玉米还是麦穗,它们都有独到的味道,这些年我再也没有吃过,也没有再摸过一次风箱。味觉和记忆好像是捆绑在一起的。现在我的口角在流着口水,似乎会滴落在我敲打的键盘上。只是我确实是一个嘴馋的孩子。日子过好了,想吃什么都可以吃到,可此刻,我好想把一架风箱安放在楼房中,虽然这想法是那么不合时宜。
拉风箱是一个力气活,但我从来不觉得累,我一个人可以全包下这个活。后来家里有了妹妹,她要和我抢着拉,我的手和她的手一起拉。有时候我也会和她一起吃炉火里烧的好吃的。有时候母亲还会烧一块包裹在玉米叶子上的咸鱼,鱼在火堆里冒油并且还会滋滋地响,我和妹妹都在舔着舌头,等着鱼快点烧熟。只是吃鱼一定要连玉米片片一起吃,那时我是很不情愿再吃玉米片片了,若不是因为有鱼,我很不想咽下去的,还不如吃红薯好吃。只是没有别的更好的吃的了。幸好还有风箱,它的呼哒呼哒声让我觉得童年还是有一个玩伴的,它推动着生活不断向前。我慢慢也能吃上馒头和包子了。饭碗里也有了肉,有了更多的菜,菜的品种也在不断地变化增多。
风箱家家都有,它好像一个住家过日子的象征或标识,每一家都需要这么一个物件,我一直喜欢听它的声响。记得上小学时,母亲总是早起做饭,我在梦里也会听到风箱的呼哒呼哒声,它让我觉得幸福和踏实,在睡梦里听到风箱的声音睡得更香了。那个时候时间过得好像很慢,我每天早晨都能听到母亲拉着风箱在烧火做饭。风箱在角落中似乎无人去关注它太多,但是它的手柄被母亲的掌纹越摩越光滑,光滑得发亮,我的小手也不知道拉过它多少次。
风箱在灶台最不起眼的地方,很少有人关注,它不像谁家有一个像样的家具还能被人观赏,风箱大都是一个模样,仿佛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只是木质不一样,它拉动的风力也不一样。父亲说过梧桐木是不适合做风箱的,因为梧桐木太轻。刺槐还可以,只是要把木头晾干了才能做,而且这种风箱会很沉。最好是楸木,不轻也不重,做出的风箱也不会风干有裂纹,用几十年都不会坏的。只是楸木很少有,因为长得慢,也不容易成材。大多数人家用的都是刺槐木,它是比较粗糙一些,需要用砂纸把那些纹理打平了才可以,做好了也不用刷漆就可以直接用了。只是一定要找一个手艺好的人打做一架风箱,这样用的年头才会久。打造风箱也是一手绝活,只是很少有人学这门手艺,估计现在很少有人会了。因为风箱好多年不再用了。
确切地说有了电风机,它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乡村有一些老人不舍得用电,也不舍得买一台电风机,就一直还用风箱。我家买了一台电风机后,把风箱放在另一个灶台上用,只是那个灶台很少起火,它用的机会就少了很多。电风机也会有一个风的声响,是发动机的呜呜声,像飞轮在不停地飞旋着大风或小风,它可以调节风速大小,显然是比风箱方便多了。我也很少有机会再拉动风箱,母亲也不用那么卖力地做饭了,生活一下子方便多了。有了电,一切也都在改变之中。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我家的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再也不用风箱了,有了煤气灶台。风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有了时代的沧桑,你看到它满身的尘埃,时间的褶皱都在它的皮肤上表露出来。父亲把它放在一个角落,还没有想它有什么用,是把它劈成柴火,还是用来当个架子,或是把它当成废品卖了呢?好像还没有考虑好,它就一直放在那里,身上堆满了东西,好像它仅有的一点用途,就是可以放一些杂物。因为它不是很碍眼,所以父亲也一直没有扔掉它。
风箱拉动着风将时间推移,回忆总会觉得模糊了许多,但又在某一个时刻清晰起来。那些串乡的师傅去村里爆爆米花,通常都会带一台风箱。在大街上找一个没风的地方,安排好火炉,一个铁制的椭圆形的匣子上面还有秒表。我们几个小孩一直围着那个人打转转,怎么也不肯走开。看着他拉动风箱,他的风箱大,大风也呜呜地响。他的力气大,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火炉下填柴。谁家要爆爆米花,要自己带着柴火,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是柴草,有的是玉米棒子,还有的是果树枝条,最好的要数玉米棒子,那样的火焰不高也不低,正好适合爆爆米花,这样不会煳锅,爆米花会又脆又大。爆爆米花还要加上几颗糖精,这样爆出的爆米花甜甜的。我们几个小孩子就是要围着那个人的,看着爆米花机的秒表在跑动,当它的转速越来越快,就快要爆炸时,我们个个撒腿就跑开。那个人会把大炮似的匣子放进一个麻袋里,然后砰的一声打开了,爆米花在袋子里飞。谁家的谁就去接过口袋,大人们总会分给我们小孩一人一把,我们把爆米花装在口袋里,等着回头慢慢品尝。听着风箱的呼呼声,再听着爆米花的开锅爆炸声,别提是多么欢快了。我喜欢吃糖精多一点的爆米花,满嘴的甜味和香味儿。我们把没有完全爆开的叫哑巴,连哑巴都是很好吃的,越嚼越香。去村里爆爆米花的师傅很多,谁能爆出好的爆米花,要先看他的行头,是不是带来一架又结实又大的风箱,是不是风箱拉起来呼呼地响,要是小的风箱,就不会有多少人理会他,他就会冷冷地站在那儿。年纪大的老人会告诉他,让他打一架大风箱再来。
闲暇的时光是在农忙之后,在哪一个村子都会见到拉着风箱爆爆米花的师傅,很是热闹。拉风箱的师傅还有走街串巷打铁的。打铁的师傅通常是两个人,有一个专门拉风箱填煤块的,有一个人负责打铁。拉风箱的和打铁的都会穿一个大的皮围裙,他们的装扮和爆爆米花的不同,看起来威严多了。这次小孩一定不肯靠前的,打起铁来,铁花会乱窜的。不小心火花会溅到衣服上,甚至皮肤上的。
我看到打铁的师傅在用力拉着风箱,大风也是呼呼地响,看起来是最大风力,煤火很旺,另一个人在叮叮当当地用一个大的铁锤子砸铁,要什么农具他就会打出什么样的铁农具来。铁在煤火的烘烤下变软,火星四射,看起来也很是壮观。但他是不同于爆爆米花的,不是特别热闹。只是一群大人围在边上,来来回回打农具,我们小孩在远处听个动静就好了,也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风箱的风力还是让我们觉得很有力度,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大的呼呼声,像一个神奇的武士,使出全身的力量把大风吹出来。在那个时代,风箱是不可缺席的,当然我们的围观也不可缺席,它聚拢了一个乡村的快乐。打铁的风箱是巨大的,比家用的大了一倍的体积,像一个大的箱子,木头的质地坚硬,也许是楸木的吧。等到他们要把打铁的工具搬到拖拉机上时,一定是需要两个师傅抬上去的,普通的风箱一个人就可以抱起来。它这个看起来很重,是我见过最大最沉的风箱了。
好多年过去了,我好想再拉一拉风箱烧火做饭,像一匹马拉回旧时的日子。风箱的天空一定升起了烟火,那是许多人的乡愁。
母亲说,村里极少有人再用风箱了,老人拉得费力,年轻人又不肯用。现在的很多小孩不曾见过一架风箱,更别说拉风箱了。当然我也许久没有再拉过它。我是多么想听听它的呼哒呼哒声,那熟悉的声音,便是亲切的故乡。
【责任编辑】涉 祺
紫藤晴儿,本名张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四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诗刊》《扬子江诗刊》《草堂》《诗选刊》等。出版诗集《返回镜中》《大风劲吹》。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