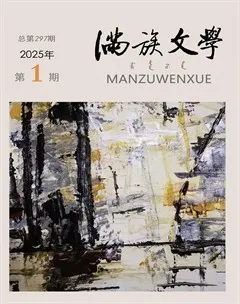作为消费品的文学
2025-01-01周立民
一、出圈,流量,消费品
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里有一篇《诗人金希普》,这位诗人的名片上写的是:“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诗人:金希普。”他不在乎别人的脸色和笑声,经常游走于官场商场中,说话一般是这种口气:“今年一年,我在全国一百所大学做了巡回演讲,出版了五本诗集,并举办了三场诗歌朗诵会。我要掀起一个诗歌复兴高潮,让中国的诗歌走向世界。”还有更为完整的自我介绍:“我叫金希普,1971年出生。从小就热爱诗歌,五岁时即能背诵三百首唐诗宋词。小学时即开始写诗,我小学三年级时写的一首诗被编进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材,新加坡一位内阁部长亲口对我说,正是读了我这首诗,才发奋立志,走上了从政的道路。初中时我发起成立的女神诗社,成为全中国最有名的学生诗社。截至目前,我已出版诗集五十八部,荣获国际国内重要文学奖项一百零八个,我现在是国内外三十八所著名学府的客座教授,去年我去美国访问时,曾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林肯中心同台演讲,受到了一万一千多名听众的热烈欢迎……”这种腔调似曾相识,不过,这么“伟大”的人物,小说里竟然给了他一个“骗子、混子、油子”的评价。
金希普只是一个个案,不具备多大代表性,不足以证明当今从事写作的群体都是这样。然而,读过这个短篇小说之后,面对这个出版了五十八本诗集,得了一百零八项大奖的“诗人”,我感到其中有一个角色十分尴尬,那就是曾被很多人视为神圣之物的文学在金希普们的眉飞色舞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贴在脸上的金箔,交换利益的筹码,招摇撞骗的幌子?在公众层面,文学式微已不是行业秘密,在金希普们这里,它仍然可以风生水起。通过金希普,人们怎么看文学呢?或许,这个问题言过其实、自作多情了,现在早已没有多少人会认真、隆重地对待文学了,文学不过是人们的消费品、娱乐品而已,谈起它来,就像“俄国有个普希金,中国有个金希普”一样,大家不过一笑而过。
当然,对于另外一批作家和作品,人们还是投以钦佩的目光,比如莫言、余华、迟子建以及李娟等人,毫无疑问,他们个个“货真价实”。然而,他们正在“重生”或“重新”被发现。按说,这里最年轻的一位李娟都不是最新涌现出来的作家,他们的流行作品也是以前“旧作”,怎么还需要发现呢?他们上一次的名声是依靠纸面图书获得的,现在则是网络流量,这是一次语境完全不同的转换。现在,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据说是以能否“出圈”为标准,作家也不例外。出圈依靠的是流量,在流量世界里,莫言和余华是《红高粱家族》和《活着》的作者未必重要,大家知道的是他们是文坛可爱的段子手,迟子建也是某个主播间推出的“新作家”,李娟在直播间之外,还有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加持。于是,文学再一次尴尬了,作家与读者中间原来是文学作品,在今天则不一定,它可以是网络短视频。只要自己的作品能像印钞机飞快转动一样飞快印刷,作家本人也不在乎,也乐意去直播间露露面。三十年前,作家聚会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说:一位诗人,他的诗集要是卖得超过五百本,那是诗人的耻辱。今天,我再也不会听到这么豪迈的表白。在今天,卖上五百万册才是人生的自豪呢。也就是说,作家、诗人面对金钱、销量再也不用那么羞羞答答了。毕竟,谁跟白花花的票子都没有仇啊。
文学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消费品——它原本也有这个属性,现在是投怀送抱,全面委身。有人说这只是一类文学作品,不是全部。这一类作品消费属性本来就很强,或经市场选择颇有流量,自然转化为消费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出圈的传统作家之外,网络文学应属十分典型的大众消费所构置的产品。然而,从文化层面看消费主义,它就不是一个仅限于经济和市场领域内的问题,它的渗透和“占有”无所不在,几乎不留“死角”,它会把各种因素都纳入消费行为。除了前述的第一类作为消费品的文学,还有第二类,意识形态消费品,以权威部门的某种奖项、倡导、主题、纪念日为导向。它们照样不会拒绝市场和大众,且“喜闻乐见”为检验标准。从需求、采购、订货、培育、回馈这样的流程看,也是典型的消费行为。它们也并不绝缘于市场,时时与市场媾和。某个文学大奖颁发时,查一下图书销售数量,不难明白这一点。第三类是“专业人士”的消费品。“专业人士”可以是从事文学研究、教学的教授、研究员、评论家、编辑等,俗称“圈里人”,依靠传统文学体制下的权力等级,结合商场的需要,他们形成特定的文学阶层,为作家和作品贴标签、评等级、做营销。他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圈外人几乎不怎么看了的文学期刊(包括评论和研究刊物)的维护者、维持者。以上粗分的三类,并不存在截然的鸿沟,它们完全可以相互关联,相互利用,相互“繁荣”。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大家都喜滋滋地躺在消费主义的温床上,乐得本以为无用的文学作为消费品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二、被收购的灵魂
在网络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参与到人们生活之时,有人就曾设想,如果普鲁斯特(“马塞尔”)和卡夫卡也在网上与我们交流,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
如今,社交网络让大家觉得作家一直都在网上,他随时有空,可以近距离接触,就好像他和您住在同一层楼,如果您高兴的话,可以向他问个好:“你好!马塞尔。”文学“交流”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近乎是单向性的。作家在遥远的地方与我们交流,在铺着软木地板的房间深处;在布拉格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里(这里指的是卡夫卡。——译者注);有时甚至更遥远,他们用我们陌生的语言、不认识的字母,甚至不是字母的文字,在一两千年以前的时空和我们交流。而如今,作者近在咫尺,这是一种发展趋势,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近乎两千多年来,作家一直习惯保持距离、保持沉默,突然他们开口和我们说话了。设想,拥有“灵晕”的莎士比亚或普鲁斯特在“脸书”上和您打招呼,那简直就是奇迹,他们一边和马塞尔说“嗨”,突然又和这边的樊尚、威利说“嗨”,同时又和另一边的温妮“嗨”上了。(樊尚·考夫曼:《“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第210页,李适嬿译,南京大学出社2019年9月第1版)
“灵晕”是那些优秀的艺术品灵光乍现的一刻,按照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说法:“在艺术品的可复制时代,枯萎的是艺术品的灵魂。”这大约就是前面那位学者担心的“灵晕”失效。他曾提醒我们:“‘灵晕’和‘脸书’此二者是不可兼容的,近距离地和那个拥有“灵晕”的人在一起,会让他要么失去‘灵晕’,要么失去自己。”(樊尚·考夫曼:《“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第210页)我认为这些并不是尝到商品消费甜头的中国作家所关心的问题,大家更关心印数、流量、奖金。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思想解放,传统文人总认为可爱的银元有“铜臭气”何尝不是掩耳盗铃呢?现代文学,自诞生那天起,就与经济和消费有着直接关系。现代的印刷术、传播技术的革命,才有书刊、报纸出版与发达,新的消费群体促使职业作家的诞生,稿酬制度保证了创作群体的稳定……尽管现代文学高傲地面对这些,而事实上又无时不与他们融合,在文学、文化从精英化的特权走向普罗大众化共享的趋势里,经济因素是实现文化平等的重要杠杆。1901年,乔伊斯引用布鲁诺的话说:“一个人,如果他对大众口味不加回避,便不会热爱真和善。”然而,这种“高傲”在现代社会里未能维持太久,“美国的情况其实一直就是如此,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早就见证了现代作家制度形式,它一方面带有浓郁的商业气息(1854年,专栏作家范妮·弗恩出版了第一部具有争议的名人小说《路德·霍尔》),另一方面带有自我封闭的、充满着躁动的文学实验的性质,对大众文化既有痴迷,又有排斥。”这个时候还有所“排斥”,而当伍尔夫在评《尤利西斯》时,说这是一部“漠视公众意见,追求震撼效果”的小说,显然能够看出“公众意见”在文学领域中的话语权了。随着市场经济的翻云覆雨,很快,文学就全面“沦陷”:“这时的文学与商品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妙的。具体而言,文学不得不迎合商品文化,从而使自己沦为通俗杂志的内容……文学是一种矛盾体,它是价值观念的载体,但又享有一定的‘自由’;它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但又与文化消费紧密相连。”(阿姆斯特朗:《现代主义:一部文化史》第88页,孙生茂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译)
“迎合商品文化”的局面,倘若不是从民国走来的中国作家,那还是在1990年以后才有亲身体会。那个时候的思维还刚刚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是带着惊喜接纳消费文化,并充分感受到它带来的解放感。比如对于人性的解放,正视欲望和消费的价值,肯定世俗生活的价值,看到了活跃的商品经济给生活和思想带来的活力,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它对文学、文化、世道人心的改变有着特殊的价值和功绩,商品消费对于社会和文化的腐蚀性也不容否认。对此,我不是从道德伦理的层面来评价,而是从影响文学精神的层面来看待,尤其是当人们毫无警惕地乐呵呵地拥抱它们的时候,我们得有一个警醒感和忧患感。在当下,文学已无法与商品消费平等对话,文学几乎就是受它驱使的奴隶,听凭它的调度,而且开始投怀送抱。频频“出圈”的强调,已经看出作家们的躁动不安,流量为大的思维成为不容反驳的真理。
消费携裹资本,资本成为调到社会最前沿的因素。有学者谈过“有利于营销”是怎么改变作家的:
社交网络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正在建立自身权威,尤其在文化产品的制造领域中,正在为拥有很多粉丝的网民添加“灵晕”,它们试图在市场上制定法规,对市场施加标准(或取消标准)。从最平庸的角度来看,社交网络非常有利于市场营销,所以作者最好是出现在社交网络,在那里和网民合作。您是一位热爱网络的作家,那么很简单,网络也会爱上您,因为您为网络服务。因此,出现在网络,效忠于网络,这一切都关乎您的切身利益,在这样一个美好新世界里,所有的一切就如同智能手机屏幕一样在闪闪发光,尤其是您。(樊尚·考夫曼:《“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第211页)
再极端一点,文学变成消费品时,市场营销便决定作家的思维。市场,消费,产出,投入,在当代都不是自发的现象,而是由社会运转的系统促成,它们带有强大的控制力。这种控制,侵入作家的创作,侵入文学精神,那绝对不是“我替你多卖几本书”“扩大销量”这么简单。当一件事物成为消费品时,它不但外在和内在符合消费要求,而且消费会制约和影响它的生产。在订货的思维下,作家和文学创作的主体性渐渐丧失。鲍德里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流行以前的一切艺术都是建立在某种‘深刻’世界观基础上的,而流行,则希望自己与符号的这种内在秩序同质:与它们的工业性和系列性生产同质,因而与周围一切人造事物的特点同质、与广延上的完备性同质、同时与这一新的事物秩序的文化修养抽象作用同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04、105页,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4版)“内在光辉”不复存在,泯然众人矣,成为大众消费品,于是作家便是一个个“没有个性的人”,作品便是一部部没有个性的作品。你难道没有发现,今天,你越来越记不住一些作家标志性的作品吗?他们创作中的同质化倾向太严重了。而回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莫言的小说,你能和韩少功、贾平凹、李锐……混同吗?哪怕他们都表现乡村中国。
有人说作家做出的是灵魂饭,是“饭”,也要有“灵魂”,现在“灵魂”被购买了……
三、与“此时此地”无关
消费主义制造出来的产品,会腐蚀文学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消费”满足的是公众的社会想象,而不是专属于作家的艺术想象。前者强调的潮流、时尚和平均审美,需要满足市场的消费性,而后者是前卫者,注定也是孤独者,它属于个人,极具探索性。它的特点便是不可复制的唯一性,这与前者针锋相对。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最为缺乏具有原创力的艺术大师,因为消费市场不需要。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状况,便是如此,它要为大众趣味所消费,要为影视剧导演所消费,便不可“一意孤行”,平庸的故事和语言反而成为流通“货币”。灵光一现的先锋文学探索,今天不但残骸难寻,连先锋的精神都成为传说和被质疑与嘲笑的对象。可是,文学作品充当的都是平庸生活的赝品、复制品,它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呢?特别是同样也有叙述功能的短视频铺天盖地而来,文学、文学语言、文学表现方式,如果不能从这里超拔出来,还是陈旧的套路不断衍生,它不就是人们文化生活里面的痈赘吗?写过《我们》的苏联作家扎米亚京曾说:“真正的文学,唯有创作于疯子、隐士、异教徒、梦想家、反叛者和怀疑者之手,而非勤勉可靠的官员之手,方能存在。”这里并非歧视官员,只是说文学这个行当不适合他们而已,这是一个需要反叛和冒犯精神的行业,平庸是最大的敌人,而生产作为消费品的当代某些作家倒是的确像一位“勤勉可靠”的官员。
市场消费还具有相当的麻醉性,它与权力压制不同,权力粗暴、残酷,而消费则是温暖、甜蜜,给人以相当的舒适感、虚幻的成就感、满足感,这一点,它是符合人性的。可是,人毕竟是一个精神性的动物,以此为终极追求,那么还是把自己降低为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动物,缺乏精神支撑——也不排除我们误以为这些就是精神性的满足?总而言之,商品消费,在精神上不能给我们以终极皈依,倒可以产生一种归顺感。归顺,安安稳稳,自自在在,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们即便不是洋洋自得、志得意满,至少也没有忧伤,不存困惑,更不知担忧,完美实现鲁迅所说的“坐稳了奴隶”。体现在创作上,就是不断制造可以作为精神致幻剂的文字消费品来。它们最大的特征就是,作品无比“现实”又不见现实,回避了现实和精神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重大问题。未来的历史如果来检阅本时代的文学作品,会惊讶地发现,作家都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因为他们表现的大部分内容与“此时此地”无关。
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在这里主张作家去写“报告文学”,也不主张唯有“现实主义”才称得上上述称赞的写作。写过《证言》的意大利女作家阿特伍德,以“寓言”方式表现的仍然是人类当下面对的现实和精神困境。这是作家与历史和现实对话,没有归顺于现世消费世界的一种证明和能力。最近,我在阅读她的2004—2021年随笔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难发现,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重要命题在这位作家笔下都有关注和判断,她没有从现实中逃避、缺席、退场,没有装作什么看不见,没有看见了也沉默不语,没有市侩式的随风摇摆。她并非给这个社会寻找解决方案,她在为人心找寻生存的彼岸。然而,她又是多么具体啊,不是高高在上空喊口号。这一句关于小说的看法就是充分证明:“我想,如果你热衷于诸如‘人类的完善’和‘绝对的正义与平等’等抽象概念,就不会怎么喜欢小说,因为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个体之人及其处境。……”(阿特伍德:《〈形影不离〉序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384页,赖小婵、张剑锋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6月版)她还说一句话:“有恐惧,就有希望:两者并非毫无关联。”(阿特伍德:〈证言〉创作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第399页)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谈论过“现代文学的终结”,他解释,这个“终结”特指小说或小说家有着重要地位的时代结束,在近代,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于一个民族——作为‘共情’的共同体,也即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而言,小说成了基础。小说让知识分子与大众,也即让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能借助这一‘共情’而变得一样,从而形成全民族共同体”。“文学虽然是一种虚构,却比那些被当成真实的东西更加透露了真实。……却要比(制度化的)革命政治更具有革命性……”(柄谷行人:《现代文学的终结》,《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第24-25页、第25页,吉琛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当文学承担的这些功能和责任都被丢失时,它的地位也降低了,柄谷行人认为“文学的地位提升,与文学背负起道德责任,两者是互为表里的。一旦从这项责任中解放而获得自由,文学便成了单纯的娱乐”。(同前,第26页)“单纯的娱乐”,作为消费品的文学,在国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自我瓦解。它的最大作用,就像诗人金希普那样,宴会时给官员、权贵们朗诵一首歌颂家乡大馒头的诗歌?他的才能就是,不仅会做自由诗,而且还会写格律诗呢。
这样的苛责,并不代表我认为作家完全没有超越这种商品消费陷阱的可能,每个时代总会有与之可以抗衡的巨大力量,我们往往称这些人为“大师”。这也并不表示我认为当代文学中没有好作家,没有好作品,我搜集了很多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其中不乏很精彩的创作,可惜这些作品没有流量,他们还不是流量作家,没有资格成为“消费品”,进而也就在各种关注和“推流”之外,更无法对抗强大的文学权力体制。可是,对于真正的写作,这些重要吗?当然,对于作为消费品的文学产品,这些太重要了。我真心希望那些有前途的作家珍惜这些还生产不出“消费品”的日子,有定力拒绝“消费”的诱惑,为一个时代留下风吹不走、雨冲不掉的文字。
2024年10月18日凌晨两点于上海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