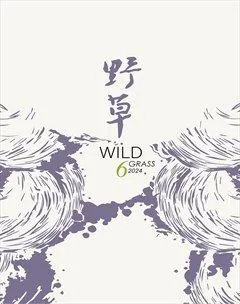穿搭风
2024-11-26黄立宇

讲究衣着,还是近些年的事。
在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女人都是天生的裁缝。特别是当家里添置了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的时候,母亲似乎一刻也不想离开它。我总觉得母亲在缝纫里得到的快乐,远比我们得到的温暖要多。那时候,冬天要寒冷得多,她开始在一个已经裁好的布料上,均匀地铺上一小片一小片的棉花。我对此没有期待,永远是臃肿的模样,差不多就是五花大绑,我的两只胳膊像稻草人一样支棱着,动弹不了。我的潜意识里,觉得只有死人才会穿这种僵死的棉袄棉裤。我不肯穿呀,犹如屈辱中的贞女,坚决不从,拼死抵抗。
母亲在棉花上有强烈的囤积癖,大姐结婚的时候,婚床上全都是高耸的新花被子。这样的排场一直让我搞不懂,这简直就是对棉花作物的图腾崇拜。棉花其实不是“花”,而是花凋谢后的果实:棉桃。我的学生时代,三天两头给生产队送肥,也去一望无际的朱家尖农场采过棉花。后来读了闲书才知道,这个神奇的植物,曾经撬动了一段并不短暂的世界史。想当年,我们对棉花完全无感,正痴迷于一种叫“的确良”的化纤面料,它有棉质所不具备的光泽和顺滑。还有锦纶运动裤,大致分为红蓝两种,饰有白色的边款,穿的时候,一定会在裤管下面泄一点“春光”出来。当有人告诉我们,美国佬都喜欢棉衣,喜欢自来旧,就是新裤子也要想办法在上面弄些破洞出来,我们真是笑死了,我们不是笑美国,而是嘲笑那个胡说八道的人,他晓得个屁啊!
成人之前,我只穿过一件衬衫——还是因为学校要举行什么仪式,我像屠宰场的猪一样打滚嚎叫了一个下午,才动了母亲的恻隐之心,连忙去做了一件白衬衫——当时还是夏天,单做一件短袖白衬衫,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长袖可以卷起来。后来,这件衬衫给妹妹穿,妹妹死活不穿,男式衬衫上的表袋(这个可恶的男权象征)令她备感屈辱。再后来,开始流行假领子,假领子不是假领子,领头是真的,其他也不假,是没有,是空屁。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是对衬衫的高度概括和精确提炼,在如此窘迫的日子里,维持所谓的体面。因为是假领子,谁也不肯随便把外套脱下来,哪怕彼此的心知肚明,依然无法消解假领子背后的寒酸,像男人穿了胸罩一样的窘辱,简直无法直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流行喇叭裤,遭到主流社会的排斥,甚至剪刀侍候,但最后都敌不过年轻群体的自我认同。我看现在的年轻人,反正都是打工的命,廉价西服加牛仔裤,已经没了当年标新立异的心思。本人歪瓜裂枣,这辈子没有穿过西服。西服的魅力不用我说,关键是合身,质地要考究,劣质西服就算了。还有领带,领带这个东西不好说,风险巨大,搞不好就变成了保险推销员。本来,我是蛮喜欢夹克衫的,不过它现在的行政色彩很浓郁。有一个重量级的单品,哈灵顿夹克,它简直就是万千公务员最稳重的选择。据说它连口袋也没有,就这个有点反人性。我想起来了,我平生第一天上班,领导就批评我,说我把手揣在裤兜里,不正经。我一直没明白过来,把手揣在裤兜里怎么就不正经了呢?
五十年代,曾经流行过中山装和列宁装,一度成为新政府机关干部的典型服式。我不太喜欢中山装拘谨瘦瘪的模样,女士穿列宁装还不错,那些因为保守而层层包裹的身体,似乎远比裸露来得更加的神秘和性感。这就说到了服装的民族性,我总归有点恍惚,一件衣服而已,非要宏大叙事,细论起来,袄褂裙袍都是满族的,旗袍也然,汉族兼收并蓄而已。去年我去了一趟西安,满大街都是汉服唐装,热闹归热闹,我是敬而远之的。
以前不太明白,电影人物进门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外衣脱下来呢。现在知道了,这是北方的生活场景。在南方,室内与户外的温度无异,进了家门以后,基本上还是户外的装备,这真是北方不懂南方的冷。现在,南方的房子也慢慢有了暖气。搁以前,到了晚上,我穿上棉裤,裹上军大衣,为了抽上几支烟,不开空调,把自己穿得像狗熊一样,如处冰窟,伸着脖子,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不时地在黑夜中嘿嘿地笑上两声。
军大衣在当时,可谓是头面人物政治舞台上的一个极妙的道具,他们披着军大衣,踱着方步,两只手还得撑着腰,任凭两只空袖子荡来荡去,让你担心军大衣有随时掉下来的可能,这不是你操心的,你偏偏操心了,这就是权力的奥妙所在。他们的肩膀向后一挺,军大衣掉将下来,掉下来没有关系,自然会有人及时接走,这一点很迷人。军大衣披在我的身上,稍有不慎,就会要掉下来,这让我很气馁,它似乎预告了我的注定失败的人生。
军用产品在地方一直有着良好的口碑,便宜,耐用,保暖,而且还不失腔调。我有个诗人朋友一直以穿军用反毛皮鞋作为他的标配,以标榜他心底的不羁。还有他的海魂衫,海魂衫一度很文学。他永远是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他跟我交流过,他认为戴帽子的风险也很大,我深以为然。我有几顶棒球帽,棒球帽固然散发着积极、乐观的气息,但它是挑脸的。再比如在年轻人中间颇为流行的包头帽,仅适合于身材高挑、英气逼人的,脸部有点欧化的族群,至于大饼脸、婴儿肥、灯泡茄之类,我看就算了。
鸭舌帽是另一个方向,那是上了一点年纪的、中等个头的老克勒子们的最爱。戴鸭舌帽的人,必备一条上等的英伦风短式围巾,能够优雅地塞在夹克衫里。围巾是文艺中年男的最爱。它既有五四青年运动的文化底蕴,又有通常为咖啡色为主调的品质围巾所体现出来的明朗、宽厚、怀旧的气息。八十年代中期,电视连续剧《上海滩》风行一时,满街都是白围巾,貌似谁都是许文强。那时候,女孩子手里都在织那种围巾。在街上碰见围着类似白围巾的男孩子,都是一副“爱情好像回来过”的样子。
以前,我在网上买过一款皮质手套,非常贴肉,舟山人叫“候口好”,在手指的夹缝间不留任何余地。我很喜欢那副手套,却一次也没有用过它,因为那一年的冬天,我买了小车。我记得,早年上海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戴白手套的,当时他们还算是高端行业,车窗上都配有窗帘,仿佛里面坐的都是身负神秘使命的人物。现在,手套的时尚指向已经丧失,它把人类的手差不多已经托付给了暖手宝、热水袋、电汤婆子之类的玩意儿,这些看起来只适合老年人的东西,纷纷出现在那些貌似有点家庭气息的女孩子的手上,“家庭气息”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出身草根、身材矮小、相貌平平、收入有限等等,她们似乎有一种以自暴自弃的方式与时尚决绝的勇气,大胆到把什么暖和的东西都往自己身上裹的程度。
我曾经多么想有一件风衣啊。风衣在男人世界中早被经典电影定格了半个多世纪,你懂的。在这个秋天开始的时候,太太在商场看上了一件风格稳健的短款风衣,试穿后确实也合适。就是贵,贵得叫我肉疼,不过,她最终还是说服了我。她最近在看木心的书,其中有一句深得她心。木心说,衣着讲究,是对自己的温柔。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