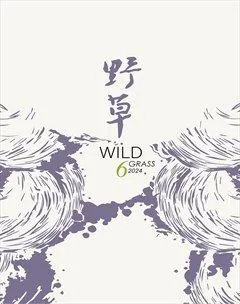如何在对接现代性中重新发明传统
2024-11-26刘波
如何在一种古典阅读里找到自己现代性的切口和语调,对于木叶来说,既是自觉,也是挑战。尽管他从熟读古典诗词后开始写作现代诗,但他也深受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因伴随着某种时代症候,这些已成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积累和文学价值观形成的前提。在全面阅读木叶这组与古典传统相关的诗歌近作之前,我读完了他的随笔集《那些无法赞美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版),书中文章虽大都写于1995至2008年之间,但一种雅致和尖锐交替的风韵仍然弥漫着全书。无论是对于古人古诗的解读,还是对于诗歌的领悟,都显出了木叶身上其来有自的幼学功底。他在现代诗上一直笔耕不辍,很多时候却又“秘不示人”,其写作时间跨度很长的作品里隐藏着他深度的诗学探索和美学追求。通过词语唤醒内心深处的诗情,也许是木叶一直以来的愿望,他时常翻检出旧作,审视一番,然后放下,这样的回味显然也佐证了他对于过往思考的看重和珍视。不同于文学批评,诗歌是木叶的志趣,是他安放自由心灵的精神家园,他可以在诗歌中隐秘地创造,随时触及生活的感悟、阅读的心得、观看的体验、凝视的快感、怀疑的真诚与对存在的反复强化和改写,这些都是其诗歌要处理的命题。为此,木叶与割舍不断的诗歌的关联,已趋于相对自由的境界。当然,他的书写仍然是有限的,仅仅针对词语本身,他时常深感困惑,否则,也可能会像很多“无障碍”写作的诗人那样,顺畅而无警惕之心。木叶越写越具有难度意识,同时也越写越慢,慢到他能够接受所有的失败,并理解和践行里尔克所言的“无所谓胜利,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因此,我在木叶的诗歌里读到了时间的意义,他总是将跨度够长的作品拿出来,重新修改或者不动一字,就这样原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接受时间的审判。好在他从一开始就确立的方向是正确的,不在所谓的诗坛之中,但又坚定地将诗歌当作了生活的一部分,虽然隐秘,却又至关重要。这些年来,他没有偏离轨道,只是以低空飞行的方式一路走到了时间之外,在古典时空里敏锐地捕捉那些人与事所带来的飞翔的诗意。古典不是木叶处理“词与物”之关系的形式中介,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就像他在变换工作的间隙不自觉地回望过去的生活一样,这种拉开时间距离之后的审视,也可能转化为一场体验诗歌美学流变的自我启蒙与修行。木叶在诗集《乘一根刺穿越大海》的“后记”中写道:“在艰难、危险抑或幸运的时刻,诗人与世界往往更有动能也更有可能相互看见,甚至相互发明。”在个人与时代的较量中,诗人与诗歌也在相互博弈,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诗人与诗歌同样又在相互温暖,相互成就。木叶这些年的创作,多是在对话,与自我对话,与他人对话,除了他熟悉的至亲与好友,还有那些隐于尘烟的人生过客,他们是残酷的现实,同样也是悠远历史的一部分。在对传统的透视中,木叶选择了和古人进行隔空对话,李白、杜甫、屈原、鱼玄机、马致远、曹植等,都成了其诗歌的素材,而绝句这一古诗体裁,也成了木叶进行现代性再造的形式,所有带有“元诗”色彩的方法论范式,都可能出于他对诗歌本体的追溯与强调。
在新作《李白》中,木叶以一个读者的身份与李白对话,此时,他似乎成了李白的兄弟,既回到李白生活的时代,试图走近他,解读他,形塑他,也身处当下的现实,让李白成为一个富有当代性的形象。正是在各种切近、颠覆与翻转中,木叶以自己的视角写出了李白的多种可能性,他如何影响了杜甫,又怎样左右了历史,这是一个大时代的大诗人所要完成的使命,尽管这样的使命也可能就是宿命。囿于性格与脾气等各种因素,李白一直是以“仙”的角色成了历史上值得玩味的人物,木叶以更为理性的方式深入诗人的内心,将他拉下了神坛,将其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李白有才华,但恃才傲物,所以他终究也是怀才不遇,浪迹四方,以酒为乐,可并未郁郁而终。“你的局限是从不绝望,也无杀死自己的决心。/花儿、美酒与野蛮都生长在你身上,/你狂放,与空对饮,与影同眠,/你笑孔丘,歌苦寒,梦中与童子一起扫落英,/所有的诋毁和赞美都有着伤口一样的缝隙。”狂放的李白在诗人笔下也是一个矛盾体,有些他能自我消化与解决,更多的他只能借助于诗歌来纾解,这种自我认知一方面是李白在现实逻辑中给予的一个定位,另一方面,则是木叶在历史和现实交织的维度上赋予李白的一种“两难”的姿态。也就是说,李白是自我完成的塑造,而木叶从李白其人其诗中看到了自己。“我和你没有代沟,就像你和庄子和敬亭山/没有代沟。”诗人之间有着惺惺相惜的理解,不管有多少爱与恨,都需要在自己身上克服时代的困难。而对于他们一生所钟爱的诗歌事业,木叶欣赏李白的才情,也懂得他的局限。他将李白的个体性转换成了一种普遍的境遇,“通过你,人们懂得诗歌对诗歌的解放,/也体验到诗歌对诗歌的限制。”只有诗歌最终成就了李白,让他在诗仙的位置上定格了自己,并构成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诗学谱系。然而,李白作为凡人和圣人的形象,则充满着尖锐、无解和理想主义气质,他悬置在某种引人遐想的可能性之上,始终无法像杜甫那样落地。“你终究不过是一个符号,超级具体而又抽象。/在历史的分水岭,你未能重新发明自己,/却同时发明了自己的敌人和继承者,/他们模仿你,背叛你,重写你,重写世界。/就像一度失去杜甫,并注定会反复失去他,/这个世界拥有你,又不得不一次次重新拥有你。”(《李白》)在木叶笔下,李白是被重新发现乃至“发明”的,李白在他自己的时代留下了作品,但他的诗歌与个体形象是在后世读者的不断解读与传承中被反复发明的,这也同构于古典传统在现代的发明,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由此看来,李白在木叶的诗歌中是一个动态的形象,木叶同样重新发明了他心目中的李白,并赋予这位浪漫主义诗人以更多元的成长诗学的可能。
木叶对话李白,不仅对话的是李白这个人,更重要的,还有对他的诗歌进行再创造。比如很多古代诗人都写过敬亭山,但唯有李白写的《独坐敬亭山》更具影响力,“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而木叶也写敬亭山:“天空运行/在你身上;孤云运行/在众鸟身上。一个一去不复返的魂灵/一束来自石头内部的光/一瓮清水,一片溢出了时间的绿/一株你没有歌唱过的花轻轻将你举过头顶”(《敬亭山》)。这看似对李白之诗的现代演绎,实际上,此诗是将李白书写敬亭山的终点作为创造的一个新起点,从自身内部来观看敬亭山,并延宕出了新的风景,正契合于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言的“风景之发现”的观念——风景是由孤独的“内面的人”发现的,是一种具有自我主体性的“认识装置”。木叶更像是写了一出现代寓言,在富有戏剧性的叙述中,一方面关联于自己直接的观看经验,另一方面则溢出现实,开启了想象之门,呈现出辩证多样的景观世界。木叶并非在刻意消解李白所建构的宏大世界观,而是重新回到个体内部,寻求对一种现代之美的召唤。因此,在时空的维度上,他复归了对传统更先锋和动态的理解,这体现出诗人独到的审美立场和历史视野。
对于历史,木叶也许不一定完全遵循还原真实现场的原则,但他试图在共时性的体系里来揭示历史的真相。如同他写唐朝传奇女诗人鱼玄机,由自己在图书馆偶然读到鱼玄机入手,让思绪延伸到更久远的想象世界,以勾勒出一个既反叛时代又迎合时代的才女形象。然而,这一悲剧最后并没有停留于红颜薄命的固化观念,诗人恰恰以灵魂对话的方式反抗了森严的伦理秩序。“三颗素昧平生的灵魂在真实/之中坠落。在坠落之中相遇/所有偶然。所有偶然锻造着战栗和开端”(《玄机》)。阅读的偶然,相遇的偶然,其实都对应于命运的必然,这是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法。木叶只是借鱼玄机的身世道出了他对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理解,但是,他最后还是将偶然性置于必然性之中,这也指认了诗人灵魂相遇的存在主义意识。而他化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歌《沧浪歌》所写的《沧浪之水》,则又是另一番风致。原诗出于屈原的《渔父》,有着很强的批判色彩,“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借渔父之口道出的自己的遭遇和选择,都是基于他对时势的清醒认知。而木叶对这一民歌进行了改写,他打破了原诗辩证法的二元对立格局,从“河水清”的假设中展开了诸多丰富的想象,这种执于一端的写法,带有某种隐喻意味,但又为独特思维方式的生成提供了契机。木叶也像屈原一样,借古人之口道出了当下个体面对琐碎生活时的真实状况,有着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同样在《天净沙》一诗中,木叶化用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对演员和导演姜文进行了调侃式的演绎。虽然全诗极具戏谑意味,但从不严肃的表达里透出了更严肃的批判性力量,有着反差性的张力之美。这种对历史稍显夸张的描述,也许并非诗人本意,但其所具有的能动性与诗人追求古典自由主义精神的努力息息相关,古典传统和历史被诗人重新“发明”了。而在重新“发明”的同时,木叶对于古典传统的回返,如同他自己所言,也可能是另一种“先锋”。他在更具“当代性”的写作实践中,有着更多趋于解构现实和审视当下的实验性探索,比如《疯秀英》《变形金刚》《铁链》和历时十余年的《S组诗》等,皆是诗人综合创造力的体现与佐证。
当然,最重要的发明还是属于木叶所写的系列“当代绝句”诗。绝句虽为近体诗的一种形式,四句一绝,对于整饬的古诗来说,简洁明了,朗朗上口,经典佳作颇多。可能也是因为这一文体的亲民性,木叶同样化用了“绝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写出了一批带有“截句”色彩的四行体诗歌。用木叶自己的解释,就是“因其形制自然而然冠以此名”(木叶《通向格律之门》,《那些无法赞美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15页),这不仅体现为一种写作姿态,更显示了写作现代诗的独特的方法论。他曾以绝句的形式写过一首《自画像》:“房贷,车贷,最后一代;/国事,战事,今日无事。/我是此时此刻此地的赝品。/诗歌!诗人所能背叛的只有你。”这虽然写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化用了一副经典的对联,但也充分折射出了诗人的生活现状与内心世界,既深感现实的无奈,也有着对现实境遇不可言说的无力感。不管木叶是针对现实发声,还是就历史进行表态,他最后总是将笔触对准当下的现实。“有的人建造悬崖,/期待刻上金句华章;/有的人坠落悬崖,/看着就像正在飞翔。”(《悬崖》)历史上那些刻于悬崖上的“金句华章”触动了诗人思考这一行为的目的,这可能并非青史留名,而是有感而发。然而,悬崖也在另一个层面上构成了与现实的对位,它涉及生死、禁锢与自由的生活想象,也更具现实性和当下性。初读此诗,我自然地想到了曾卓的那首《悬崖边的树》,悬崖边的树所呈现的形貌,既像是要拥抱自由,又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样的心绪也同构于木叶对于悬崖的描绘和认知。他在历史中发掘存在的踪迹,同时又在现实书写里运用这一历史遗迹所延展出的当代性,对历史进行了本质性的穿透。这种当代性的体现也具有历史的纵深感,诗人在形式上打破了新诗与古诗之间的界线,同时又在四句的形式上限制了表达的自由,这一矛盾折射出的正是新旧之间的断裂甚至背道而驰。诗人还曾写过一首绝句诗《你的正式工作是皇帝》,题目不乏神秘感,但我们读进去之后,发现他还是在描绘自画像:“你的正式工作是皇帝。你写诗,/作画,打败仗,在屈辱的牢中遇见自己。/被动地成为历史,被动地成为一门学问。/一千年过去,遗忘依旧是我们的镇静剂。”作为画家的皇帝,其身份被固定了,他无法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只能被动地忍受与承担,但他因为皇帝这一身份,最终没有活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来。这首诗是在写历史,然而,我们从字里行间看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历史虽然经历了变化,但人性与人心是相通的。因此,我们总是在颠覆历史的时候又不断重复历史,这一悖论构成了木叶审视历史的问题意识。
在“绝句”中重新发明传统,既是木叶书写历史的主体意志,也是他在以传统对接当代性的方法论。在具体的文本写作中,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以古典与现代交融的形式,抵达了异质混成的诗性境界,这种诗性随着温柔敦厚之古典性的弥漫而在词语周边大面积延展,并且具有了持续的生产性。带着这样一种诗学抱负,木叶将历史与传统也纳入到了现实,并赋予其当代性,这是跨时空的创造。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诗歌不仅承担了传承的功能,而且也将其范围进行了深度拓展。木叶说,“诗歌是自在的,隐秘而偶然,好的诗歌是一种‘无’,逸出作者乃至时代”(木叶诗集《乘一根刺穿越大海》后记),这一观点不仅是针对木叶自己的写作,也适用于古代经典诗人如何穿越历史而进入当下的诗歌现场。他所对话的李白、杜甫、屈原、曹植等,也都属于超越了自己时代的诗人。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木叶在写作上放得更开了,他在“绝句”诗中打破了过去稳固的结构,对其进行当代性的变革。“一朵闪电花开放在童年的雨中,也开放在南京/东路的夜空。魂牵梦绕仍未能写出其神采。正/是它教导我接受失败。总有些独一无二与神秘/难以被赋形,就像人总要有个永无法实现的梦”(《闪电花》)。通过童年的回忆,诗人以“闪电花”的意象指涉了“失败”之人生的法则,那是理想所主导的人生,如果缺少了这一主导,我们无法看到更高远的人生。木叶时刻警惕自己陷入俗务,尤其是对传统的接受,还是要有独特的探索性与未来性。在《春风斩》这首诗里,木叶转化了古典诗词的资源,在疏离中融入,引诗似曾相识,而总体整合之后,字里行间却又蕴含着陌生化的美学和现代性的可能。
当我们回到木叶在诗歌写作上的起点时会发现,他沉浸其中的,仍然是“词与物”和“诗与思”的关系,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维度上来审视自己的写作,也意味着他对于诗歌本体性的极致追求。“在我看来,诗歌是一种殊异的万有引力,是万物之间的相互辨认与应和,神秘而又具体,诗人就是那个用文字‘重新发明’万有引力的人,使得万有引力获得文本的形状,完成‘词与物’向‘诗歌与万物’的转化。”(木叶《万物赋诗》,《上海文化(新批评)》2018年第6期)这是诗歌写作为木叶带来的思想启蒙,也是他的古典性写作富有“元诗”意识的体现。诗人在自己的慢节奏中扩充诗的疆域和空间,也形成了其少而精的原创性,而这种话语方式,也正逐渐成为一条新的写作路径。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