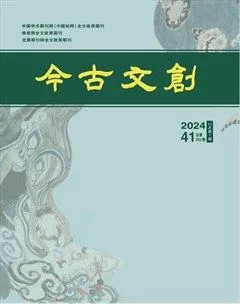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 肉夹馍 ” 构词探析
2024-11-21刁晨雨

【摘要】历来人们对于“肉夹馍”这一食品名称的命名都莫衷一是,针对“肉夹馍”这一语言现象,文章首先就“肉夹馍”名称的由来,列出多种关于“肉夹馍”这一名称结构形成的观点,加以分析比较。而这些观点都是基于传统语法的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从中式食物命名的角度入手进而分析“肉夹馍”,同时指出这种命名方式符合国人的心理认知,也就是说“肉夹馍”的命名符合语法与逻辑。
【关键词】肉夹馍;由来;“N1+V+N2”式中式食物名;心理认知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12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34
肉夹馍是关中地区的一个有名美食,它把两种食物完美地组合到一起。肉夹馍中的肉是指腊汁肉,所谓腊汁肉,是选用上好的硬肋肉,再辅以盐、姜、葱、丁香、桂皮等20多种调料汤熬制而成,相传在战国时期就有了这种做法并且当时把腊汁肉称为“寒肉”。馍是指白吉馍,这里所说的白吉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馍,它是烙熟的,或者可以把白吉馍理解为一种没有芝麻的烧饼。制好的白吉馍形似“铁圈虎背菊花心”,皮薄松脆,内心软绵。腊汁肉和肉夹馍搭配在一起,相得益彰,吃起来唇齿留香。
关于“肉夹馍”这一名称的分析,一直以来大部分都是基于传统语法来对其进行研究,主要的争议是“肉夹馍”这一名称是否合乎逻辑与语法,是否应该将其改为“馍夹肉”。对于“肉夹馍”这一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认识,同时对于这种语言现象我们应该持何种态度,都是语言文字工作者需要面对的现实话题。本文围绕这一话题,对“肉夹馍”这一语言现象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肉夹馍”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关于肉夹馍的名称的构词理据这一语言问题一直以来都引人注意并且是个有意思的话题,这个名字的由来始终存有争议,其争议的来源主要是“肉夹馍”这一名称与其所描述的客观事实是否相符,它是否是一种不和语言规范的一种语言现象。一提到“肉夹馍”人们常常会疑惑,从食品做法来说,肉夹馍是将腊汁肉切碎夹入掰开的白吉馍中,由此按照一般的逻辑“肉夹馍”或许叫作“馍夹肉”更为合适。那么为什么人们要把“馍夹肉”称作“肉夹馍”?“肉夹馍”这一名称又从何而来?总结目前已有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省略说
省略说认为“肉夹馍”是古代汉语“肉夹于馍”的一种缩写,这种看法把“肉夹馍”视为是古代汉语里的语法的残留物,是一种地点状语后置现象,省略了介词“于”。目前这种说法普遍为大众所接受。在古代汉语中,要找到一些介词省略的现象并非难事。如:“后数日驿至,果地震(于)陇西。”句中便省略了介词“于”。现代汉语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之上发展和演变而来的,因而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古代汉语的残留也是一种常见的普遍现象。
贾志刚曾提出关于肉夹馍这一名称什么时候得来的可能无法得知,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肉夹馍的制作方法应该最早出现于唐代”。关于以馍夹肉这种食法,最早在唐人刘餗《隋唐嘉话》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饼试手。帝屡目焉,士佯为不悟,更徐拭而便啖之。”李裕德所撰的《次柳氏旧闻》中记载有:“肃宗既割,余污漫在刃,以饼洁之。”这些史料中所记载的无论是“以饼拭手”抑或是“以饼洁刃”,这两种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饼上抹上切下来的熟的碎肉再进行食用。这种行为的目的或许已无法考证,可能是用于祭祀抑或是其他活动,但不管这种行为基于的目的是什么,其与现代的肉夹馍的制作方法有很大的相似性。也就是说肉夹馍的做法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但具体的名称不得而知,那么说“肉夹馍”是古代汉语的语法残留物是容易理解的。
此外,还有一种省略的观点是认为“肉夹馍”可能是“肉夹在馍里”的缩略语。按照韵律句法规律,在把短语简缩成词语的时候,较为合理的做法是“留下重读词,去掉轻读词”。去掉短语“肉夹在馍里”中的轻声词“在”和“里”,自然就简化压缩成了“肉夹馍”,符合普通话语法规律。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有句法规律为依据,但是缺乏历史资料的支撑,在现代汉语和方言中也缺乏类似的语料进行印证,这种省略的说法有待考究。
(二)宾语前置说
这种说法把“肉夹馍”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宾语前置,就是说“肉夹馍”原来的形式应该是“夹肉馍”,意思为“肉被夹着的馍”,是由“夹肉”和“馍”组成的偏正结构。把“夹肉”中的宾语“肉”前置从而变成“肉夹”,“夹肉馍”便成了“肉夹馍”。宾语前置其实也是古代汉语的语法残留,正如上述观点中所提到的,在现代汉语中有古代汉语的残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所以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存在。
省略说和宾语前置说观点其实都是认为“肉夹馍”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
(三)短语结构说
短语结构说认为“肉夹馍”不应当看成是一个主谓宾结构,其中的“夹馍”属于偏正结构,“夹”修饰“馍”,意为“夹东西的馍”。“肉”用来作为“夹馍”的修饰成分,意为“夹着肉的夹馍”。所以说“肉夹馍”是一个分为两层的偏正结构。这里把“夹”当作形容词来看待并不是所谓的“望文生义”,其实是有依据的,刘继超先生认为“夹馍”结构与“夹具” “夹棍”“夹板”是一样的。查阅《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夹”的词条,其中“夹具”是夹工件的装置,而不是别的东西夹着它;“夹棍”是为夹受刑者的足部所用的三根相连的木棍;“夹板”一词,特指用于固定物体的板子,并非指板子本身被夹持于其中。据此可以说,“夹X”就是夹住东西的“X”(且X均为左右、上下两个部分)。那么“夹馍”就可以理解为“夹住东西的馍”。接下来探讨汉语语素“肉”的用法。在由“肉”构成的词语中,“肉食”可以指“食肉”;“肉食性”指的是具有食肉的习性;而“肉用鸽”则是指那些被饲养用于食用其肉的鸽子。这样看来,“肉夹馍”就可以理解为夹着肉的馍。
如杨锡彭先生所言:所谓夹馍,或将一块馍掰开形成一个夹层,或将两块馍上下叠放,中间加上肉、蔬菜什么的,就形成了“夹馍”,“夹”是就其作用而言的。至于在“馍”中夹什么材料,是可以自由选择进行搭配的,所以有肉夹馍,此后也有了菜夹馍、油泼辣子夹馍、土豆丝夹馍等“X+馍”的形式。
这种语法解释可以帮助理解“肉夹馍”的结构,从而把它看作一个搭配合理的词。
(四)文化说
这与陕西地区方言有关,因为“馍夹肉”若用当地语音去读,听起来像“没加肉”,叫卖的时候不利于吸引消费者,遂改为“肉夹馍”,“肉”字在前,也会给人一种肉量充足的感觉。这种说法其实很难去考证,因为搜集到的依据是十分有限的,具有民间的特点。但是这种基于文化的说法往往也是极具参考意义的。语言符号本身具有任意性,只要为社会使用者所共同认可,就可以成为某种事物的名称。在历史中由于一次读法的改变,然后为人们接受并发生了后来的“习非成是”,这种缘由现在难以考证,但是难以考证并不意味着就是否定,相反,这种关于文化的说法往往可能是最本质的。
从以上几种说法无论是宾语前置说抑或是短语结构说,不难看出目前关于“肉夹馍”这一名称的研究大都基于传统语法。那如果抛开传统语法的束缚,不去纠结语法上的问题,本文认为“肉夹馍”隶属一种食物名称短语,分析其命名应从中式食物名称中去溯源。中式食品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命名也是各有特点。虽然肉夹馍不能算作是可以摆上餐桌的一道菜,但肉夹馍也算是通过一定的烹饪手法做成的一道风味小吃,那或许可以从中式食物的命名这个角度来去分析“肉夹馍”这一名称的形成。
二、从中式食物名称命名的角度分析“肉夹馍”
(一)一般中式食物命名结构
食物的种类有很多,文章讨论的是“肉夹馍”,那么本文所关注的对象便是人们通过一些烹饪手法所做出来的美食佳肴。此类中式食物名称多由短语构成,一般食物名称需要体现原料、做法、调料等内容。这里主要针对一般写实的中式食物名称,不涉及其他寓意丰富而富有新意的食物之名。一般常见的食物名称结构短语主要为并列式(如可乐鸡翅、芹菜牛肉),另一种则是突出做法的偏正式(如番茄炒蛋、醋熘大白菜)。
大多数食物名称短语属于不对称结构,人们一般通过语序手段来突出主要材料。常见的写实的中式食物的命名中包含原材料、烹饪方法、烹饪工具等这些比较基本的方面。常见的中式美食的名称有“N1+N2”结构形式,此类结构形式可以看成并列式,其中“N1”可以为材料、工具或者风味等,而“N2”多为原材料,也可以说多为主料,如:椒盐土豆片、铁板豆腐、土豆排骨、鱼香肉丝、糖醋里脊、泡椒凤爪、地锅鸡等。在此结构类型中不难看出,对于一个食物名称中信息顺序的安排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大部分是不对称结构,即一种食物的主要原材料居于名称的末尾位置。这里所谓主要原材料的判断基于人们的心理认知,比如会根据材料的价值、营养、用量、价格等方面来进行比较。另一些常见的中式食物名便是跟“N1+V+N2”结构形式,“N1”和“N2”为材料,“V”为制作方法,比如:粉蒸排骨、番茄炒鸡蛋、土豆焖排骨、梅菜扣肉等。这些中式菜肴的结构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显而易见即使结构不同而人们的认知方式以及思维却是一样的,一般也是会把价值较高、用量较多的主料放在名称的最后。
从结构层面上来看,作为风味小吃的“肉夹馍”符合“N1+V+N2”式中式食物名称结构形式,所以本文重点讨论该结构形式。
(二)“N1+V+N2”式食物名称结构
在“N1+V+N2”式食物短语结构中,N1和N2主要由食材类的名词充当,N1部分有时候也会由小型的烹饪方式或者由制作工具来充当,V部分主要是表示制作方式的动词,比如:炒、焖、炖、炸、蒸、拌、煮、煎、煸、烤、泡、酿、卷、腌、泡、烧、熏等。这种形式在中式菜品中应用比较常见,比如:芋头炒肉、山药炖鸡汤、芝麻拌芹菜、青椒炒肉、油淋茄子、栗子焖羊肉、生菜滑牛肉、油炸花生米、板栗烧鸡、五香烤鸭、银鱼煎蛋、纸包鱼、潮式腌虾、咸蛋黄焗虾、古法煨甲鱼、锅包肉、豆腐夹鳢鱼、锅贴饼等。
“肉夹馍”作为一种西安特色美食,结构上满足“N1+V+N2”式食物名称结构,对于“肉夹馍”来说,虽然其中食材中的“肉”是属于高蛋白、价格高的食材,但是它是夹在馍里,是用肉来填充馍,像“馍”等类似这种面食在人们心中一直是主食的代表,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主料。可以看出“肉夹馍”不仅在结构上符合“N1+V+N2”类的食物名称,而且在食材编排上也符合这类食物名称的排列顺序。像“肉夹馍”这种满足“N1+V+N2”式食物名称的街头吃食并不是个例,其他比如:羊肉泡馍、豆花泡馍、鸡蛋灌饼、杂粮煎饼等,像这种虽然称不上一道菜,却也都是中国的美食,其命名在结构安排上也符合此类命名规则。“肉夹馍”的材料排列顺序是符合人们认知的,后面还会对此再做进一步补充。“肉”是其中的辅料,“馍”是主料,“夹”是该吃食的制作方式。“N1+V+N2”式食物名烹饪主料常后置,符合中式食物命名的一般规则。
对于“肉夹馍”一词,其中“夹”的词性是一个争议的焦点,也可以说对于“肉夹馍”理解的关键便是“夹”字究竟应当如何解释。从传统语法角度入手,一般把“夹”当作动词来看,“肉”为受事,那么“肉夹馍”一词便不合乎逻辑和语法。文章前面一部分提到的关于肉夹馍由来的结构短语说认为“夹馍”是偏正结构,“夹”理解为形容词,整个结构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修饰关系,“夹”虽是动词性语素,却是机构中的修饰性成分,这里“夹”的词性要发生变化。对“肉夹馍”进行层级划分,可以划分为两个层级体系,这两个层级体系都是定中结构。在第一层层级划分中,“肉”是定语,“夹馍”是中心语。继续划分“夹”是定语,“馍”为中心语。总的来看“肉”和“夹”是修饰成分,“馍”是中心语。那么动词成分“夹”在这一短语结构中应当具有了形容词的用法,用来修饰馍这一名词成分。
基于此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去划分N1+V+N2”式食物名,N2是中心语,N1和V都是修饰成分。也就是说,动词性成分的V在这个结构短语中被赋予了形容词的用法,意为“V的N2”。总的来看,“N1+V+N2”的组合方式,不应当理解为主谓结构,而是一种偏正结构。用划线法进行层次分析可以划分为:
N1 V N2
1 2 1-2定中关系
3 4 3-4定中关系
“N1+V+N2”类食物名称将主要原材料放在最后位置,是符合中国传统食品命名的一种方式。那么“肉夹馍”这一名称的命名是符合这一命名规律的,并且“肉夹馍”在传播过程中一直具有生命力,一直服务社会且被大家普遍接受,与其名符合人们心理认知这一点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受了中式食物命名时的思维模式的影响。
(三)“N1+V+N2”式食物名称结构意义
对于“N1+V+N2”式食物名称短语结构可以笼统地理解为:辅料N1配上V的方式从而做成N2类的食物。例如咸蛋黄焗虾,便是用咸蛋黄通过“焗”这种烹饪方式做出来的虾。这类短语结构中包含了材料与动作之间的关系,即“动作-受事”的语义关系。在这个语义关系中,动词居于受事的前面,语义指向后面的受事。当动词前面的成分为方式、材料、结果、程度时,这个时候动词也可以前指。那么在“肉夹馍”一词中,“肉”是材料,“夹”是动作,是材料与动作的关系。“肉”是作为“馍”的填充材料,这里的“夹”语义指向材料“肉”和受事“馍”。
“N1+V+N2”类食物名称结构由于其中的“V”会使整个短语的意义更为具体,从而使整个短语意义精细化。例如在一些小吃中:鸡蛋灌饼、鸡蛋煎饼、鸡蛋摊饼,不同的动词搭配相同的词项,这些不同的动词使得整个构式的意义更加具体明确,也就是更加精细化。动词不同做法不同,食材相同做出来的食物无论是外观、味道都是不同的。在这类结构式中“N1”和“N2”也发生关系,它们之间有一种互动关系,也正是这种互动让整个短语的意义更加完整和详细。以下是一些菜肴实例的展示,比如:山药炖排骨、土豆炖牛肉、香菇炖鸡、番茄炖牛腩、川贝炖梨,在“N1+炖+N2”结构中,“N1”与“N2”之间进行互动,整个短语意义更加具体。
(四)“N1+V+N2”式食物名称的认知的形成
关于“肉夹馍”之名的形成与流传,与人们的认知心理以及方式是有密切关系的。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就是在说话者或听话者的大脑里所激活的概念,详细点来说,意义乃是人所赋予,存在于人类对世界的阐释之中,因此,其具有主观性,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
丹麦的心理学家Rubin设计了著名的花瓶/人脸图形,这一图形后来被完型心理学家所借鉴,并应用于知觉组织的研究领域。研究结果表明,主体的知觉理解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图形和背景。学者们发现人们对于这两部分信息的感知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美国语言学家Talmy率先把图形—背景理论运用于认知语言学研究中。根据图形—背景理论可以了解到,在一个事物被认知的过程中,它会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图形和背景。图形是指那些在认知过程中需要突出和强调的部分,而背景则是相对不那么显著的部分。这种划分实际上反映了认知过程中的优势和次优势。图形部分因其显著性和突出性,往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背景则为图形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情境支持,但通常不会引起同等程度的关注。图形存在于背景之中同时突显于背景,在认知中占优势,它是一个变量且最容易成为注意的焦点;它通常来说体积比较小、不易意料,同时依赖性较强。而背景相对来说在认知中不占优势,突显程度相较于图形低,可作为认知的参照点;它一般体积比较大,会更容易预料并且独立性强。在语言范畴去运用这个思维模式,其实就是将人们心中的“焦点”事物转换成概念中的“突显”问题。
文章中分析的“N1+V+N2”类食物名,成分N1所占比重以及其独立性相对于N2而言较弱,属于认知中的图形部分,是认知中的突显部分,也就是构式中的突显成分。与之相对,成分N2独立性较强,属于认知中的背景,在认知中没有N1占优势,位于次突显的位置。如“肉夹馍”,对于这一美食,人们第一眼所关注的是馍里面美味的肉,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也是腊汁肉,肉无疑是该美食中的突显成分。而馍则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相当于背景。若将这一认知意象投射到语言中,就形成了一个语义框架,语义框架投射到具体的语言中,就形成这个短语框架(突显+方式+次突显),最后把选取的项“肉”“馍”填充到该框架中,“肉夹馍”这一名称就形成了。
“N1+V+N2”类食物名称中的N1既是突显成分同时也是这个结构中的语义焦点。N1置于最前面,新的信息首先传达以引起听话者的注意。比如“香菇拌面”,“香菇”是语义焦点,放在结构的前面,表示这道菜的特点在于香菇,用于区别“椒麻鸡拌面”“小龙虾拌面”等其他不同特色的拌面。“肉夹馍”亦是如此,“肉”在最前面,产生新鲜感,形成以“肉”为多的心理体验,同时跟同组成员形成对比焦点,强调不是花干夹馍、菜夹馍、鸡蛋夹馍,而是含肉的馍。
人们在给事物命名时,一般会参考事物的所属类别同时选取事物引人关注的某个特征作为命名的理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某个特征的作用便相当于图形,用它作为命名依据以便摹拟事物而使名称能够充当表明对象特征的代表,并且以此表现出事物的特性。从另一方面来说,抓住事物的特征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人们说到或听到某种事物的名称时,总可以联想起一个或者几个别的要素,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联系,以便从对象的整体性来设想对象。“肉夹馍”之名流传至今,作为一种食物名称一直服务于社会并被大众接受。
然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并没有收录“肉夹馍”,其中“馍”是以方言形式保留的古语词,“肉夹馍”无疑是一个具有方言味道的名称,它蕴含着一种文化,在普通话中没有相适当的名称与之相对应,不吸收它便难以恰如其分地表达这种特有的食品。其实这样的方言名称应该纳入普通话中来,以适应交际的需要。
三、结语
“肉夹馍”受到了“N1+V+N2”式食物名称命名的影响,这种短语结构也符合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和认知心理,所以“肉夹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存在。总的来说,“肉夹馍”的形成主要还是由于“主观性”及“主观化”的原因,也就是说跟大众认知心理和方式有关。当然对于“肉夹馍”的生成机制学界也应该持怀疑态度,若是对其结构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探究,或许对于汉语的研究会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语言现象中不应仅因其不符合语法规则便断定其不合理。语言现象的丰富多彩也是大众生活丰富多样的见证。同时学者们也应该注意到类似“肉夹馍”这种会引起争议的语言现象,这种现象是存在于大众口语中的,并且许多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如果都要用传统语法给出一个解释,那不免让语言显得呆板无趣。有时候换一种角度,如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或许对于那些不合传统的语例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刘继超.“肉夹馍”: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J].人文杂志,1997,(2):119-121.
[2]王彦,徐赟.小议“肉夹馍”[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9,35(06):71-74.
[3]邓佳欣.“肉夹馍”之名流行的构式动因[J].现代语言学,2019,(2):125-130.
[4]田惠刚.肉夹馍小议[J].语文建设,1995,(12):32.
[5]付佩.关于“肉夹馍”的几点思考[J].语文学刊, 2014,(12):47-48.
[6]贾志刚.为西安肉夹馍正本清源:以饼夹肉食用法始于唐朝新论[J].唐都学刊,2013,(29):81-83.
[7]雁红.也谈“肉夹馍”[J].西海语言教学通讯,2004, (8):36-38.
[8]林美宇.“N1+N2”和“N1+V+N2”式菜名短语词序考察[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8-91.
[9]周光庆.汉语命名造词的哲学意蕴——兼论任意性与可论证性的争议[J].语言文字应用,2004,(01):26-33.
[10]杨锡彭.“肉夹馍”、“冰糖葫芦”的层次结构[N].语言文字周报,2012-1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