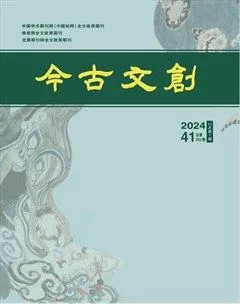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 三美论 ” 视角下 《雨霖铃 · 寒蝉凄切》英译本对比研究
2024-11-21李清云
【摘要】中国古曲文学璨若星河,富有独特韵味和内涵的宋词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魅力跨越国界,引起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以下简称《雨霖铃》)以其情感和特色,被誉为千古绝唱,英译版本众多。本文旨在使用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对《雨霖铃》的三个英译本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传递原诗情感色彩方面的成就,以此考察译本的异同。
【关键词】三美论;《雨霖铃》;诗歌翻译;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10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29
一、引言
文化交流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不同文明间的桥梁。作为中国文化瑰宝的古典诗歌在中西方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诗歌英译不仅利于传播我国的文化,更有利于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在诗歌翻译中,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该翻译理论强调,在进行诗歌翻译时要传达出原作的意境,展现出原作的音韵美和形式上的美,这便要求译诗要有美学的效果。宋代词人柳永创作的这首《雨霖铃》语言优美、感情真挚,被誉为千古绝唱。本文旨在探讨《雨霖铃》的英译本是否实现了译诗与原诗在意、音、形三方面的对等,尽可能发掘翻译理论指导诗歌翻译的意义,对比分析出不同译者在实现“三美”原则方面的独特之处。
二、诗歌翻译“三美论”
若提诗歌翻译,首先想到的便是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如果诗歌翻译遵循音美、意美和形美,那么译语读者在品诗时便能感知原语读者相似的情感。意美指的是译诗要以其内容、丰富的情感来激发读者的共鸣和兴趣,让读者更好地体验到诗歌所要传达出的意境;音美指的是译诗要以其节奏、平仄与韵律,让读者品读时得以尽心享受诗的音韵之美;形美指的是译诗以其工整、对仗的结构为读者呈现出诗歌的视觉美。
诗之所为诗歌,原因在于它固有的音律和格律,正因为音律优美,格律严密,才可以将某些创作称之为诗歌。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诗歌的形式,其形式严谨,才能呈现出完美的诗歌。严格的形式,也是诗歌翻译中最难的部分,译者在进行诗歌翻译时,很难保持译文和诗歌形式的一致。众多译者会选择保持译作和原作形式的一致,导致诗歌的翻译较为古板,所以,进行诗歌翻译时,能否完全做到音美、意美和形美三者的统一是衡量诗歌翻译质量的关键,如果一首诗在翻译时,能很好地体现出原诗的意境和情感色彩,这可谓是一首好的译作。如果能同时做到这三美的融合,可谓译诗的最高标准。
三、《雨霖铃》及其英译本对比分析
(一)柳永
柳永,北宋词人,他一生专心写词,在词坛极具影响力,是宋词的集大成者。叶梦得曾在《避暑录话》中如此评价柳永:他的词可谓是流传广泛,凡有人烟处,便咏柳永词。这在侧面反映出柳永词作的流行与影响的广泛。《雨霖铃》是柳永的代表作,语言优美、感情真挚、千古流传,该词创作于公元1024年,柳永在其第四次科举考试中不得志,便怀着失落和愤懑之情离开京城,这首词便作于柳永与情人虫娘分别之际,深切地表达了他的离别情绪和对爱情的依依不舍。
(二)从音美角度比较《雨霖铃》三个英译本
要想使诗歌读起来更有韵味,翻译中的音律和节奏必不可少,二者的协调可以使诗歌的翻译更加有韵味,读起来朗朗上口。诗词歌赋讲究的是节奏美和韵律美的统一,由此构成了诗歌的音美,没有节奏和韵律,无以成诗。《雨霖铃》便因其独特的韵律,展示出了古典诗歌的美,该词前后阕各五仄韵,均押入声韵。众所周知,很多英文诗歌也有头韵和尾韵,但是其诗歌的形式较为自由,所以我们在翻译中文诗歌的时候,很难保持原有的韵律。在译诗的过程中,要多方考虑用词,以此来寻找英文中能够表达原诗音律的形式,这样的译文不仅能够忠实于原文,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
本文在进行分析时,选用的分别是许渊冲先生、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以及徐忠杰先生的译本,在下文中,许渊冲译本统称为许译或许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译本统称为杨译或杨译本、徐忠杰译本统称为徐译或徐译本。
在分析《雨霖铃》的三个英译本时,可以注意到许渊冲先生的译本特别强调音韵之美。在其译本中,通过每句结尾处的押韵,如“Cicadas chill,Drearily shrill.Hour-shower,old-cold,part-heart”,读者可以感受到其朗朗上口的韵律和节奏感。许渊冲先生的翻译不仅注重韵律的表达,而且深刻体现了翻译在传达原文意蕴和情感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的译作能够将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感传递出来,读者在品读时便能很好地欣赏到诗歌的音美。相比之下,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则更像是一篇优秀的散文,其译作并不特别强调诗歌的音韵,译本中几乎没有尾韵,读起来更像是流畅的散文而非诗篇,,例如译作的前两句的结尾单词为“stops-dusk,gate-on”,我们从中读不出节奏感以及韵律。至于徐忠杰先生的译本,虽然在某些地方有押韵,但整体上押韵不够明显,译作的节奏感不强,没有很好地传达原文的音韵之美,例如其译作的最后两句的结尾处,其用词分别为“may be和with me”,读到这两句话时,我们可以感觉出“may be和with me”起到了押韵的作用。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译者在翻译诗歌时的不同侧重点和风格,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阅读体验和感受。
(三)从形美角度比较《雨霖铃》三个英译本
我们的诗词歌赋语言优美,高度凝练,能够很好地抒发作者的思想。虽说诗歌要体现出节奏美和音律美,但是它的形式往往也不可忽视,形式上完美的诗歌流传得更广更久。若说写一首诗,或译一首诗,缺乏篇章的美,字句对照不规整,便称不上完美。形式完美的关键是语言的凝练,柳永的《雨霖铃》原作共有102个字,这一百来字很好地抒发了词人柳永与情人分别时的不舍之情,以及仕途上的失意不得志的情感,虽说词本身字数不多,但可谓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再看《雨霖铃》的三篇译作,许渊冲的译本共有166个词,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共有189个词,徐忠杰的译本共有187个词,从这三个英译本中可以看出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字数更少,语言相较于其他二者较为凝练简洁。
其次,从词句的对仗角度来看,许渊冲的译本大量采用了主动语态,并省略了一些不必要的主语,使得翻译作品更加精炼,形式更加规整。相比之下,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翻译则较多地使用了倒装句式,且较少运用中文诗歌的描写手法,这可以被看作是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徐忠杰的译本篇幅较长,并未体现出诗歌的形式和句子的对仗。例如,“念去去”一句蕴含着激动的情感,读起来给人以停顿之感。
如上文所述,“念去去”的中间要有停顿,许渊冲的译本直接将其翻译为了两句话“I’ll go my way.Far,far away”,这两句话和原作读起来的形式相似,似乎传递出了翻译中遵循的形式美。通过理解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发现他们并未将“念去去”单独翻译,而是和“千里烟波”翻译为一句话“Ahead lies a journey a thousand li of misty waves”,虽说该译本并未遵循原文的形式,但是,翻译是一项发挥主观能动的事情,译者在创作的时候会根据自身的理解来翻译,将其合并为一句话,其原作的含义也并未丢失。徐忠杰的译本虽读不出停顿之感,但他也将此句进行了单独翻译“Thinking of the distance to be covered”,表达了原作的含义。综合上述分析,诗歌的翻译应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形式,然后再进行翻译,但是翻译极具灵活性,所以应该辩证看待和学习每一种翻译风格。
(四)从意美角度比较《雨霖铃》三个英译本
诗词讲究的是表达的意境,如果能很好地传递出意境,便可传递出诗歌的灵魂。不论是写诗,还是译诗,若读者无法感受诗歌的意境,那就不算成功。总的来说,如果诗歌翻译体现不出诗歌的意境,那么诗歌的音美和形美体现得再好,从整体上讲,也不能很好地呈现出原作的情感。
下文选取了《雨霖铃·寒蝉凄切》中的一些典型例句,并对这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究译本中是否较好地传递了原作中的意境。
例1:
《雨霖铃》
这三个英译本,可以看出徐译本“Yu LinLing”和杨译本“Yu LinLing”虽说将词牌名直接翻译为汉语拼音,更加忠实于原文,虽保留了原作的含义,但可能不利于国外读者的理解,将其直译,无法让译语读者明白词牌名所要表达的内涵,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整首词的理解。相比之下,许译本词牌名翻译为“Bells Ringing in the rain”,使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雨中的钟声似乎更好地传递出了悲伤之感,雨夜多为表达思念,这对于译文读者来说,更加的生动形象,更易于外国读者的理解,也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境。
例2:
对长亭晚
“对长亭晚”的原意若理解为人在长亭面对面站立,难以分别更好,如此一来,许译本“West and face to face in an evening hour.Before the pavilion”更为生动,形象,人在长亭面对面,体现出难舍难分的情感,杨译本“And we face the roadside pavilion at dusk”稍有些误译,原作应为人面对着长亭,而不是面对面。而徐译本“Near the rest-house”,则和前两个都有所不同,他并未体现出人这一角色。三个版本的理解各有不同,若根据市面上的中文释义,徐译本对其含义把握的较为准确,能更好地体现出原词的意境。
例3:
兰舟催发
“兰舟”体现的是即将离别的愁绪,杨译本“But the magnolia-wood boat beckons me on”将“兰舟”译为“the magnolia-wood boat”,采取了直译,忠实于原文的方法,但是这里并不适合将“兰舟”直译出来,此处并不是去强调船有多好,而营造的是一种离别时伤心的氛围,主要还是要抒发离愁之感。许译本“But the boat is waiting for me to depart”,直接就是将其翻译为“船在等着我”,虽言语不多,但也能表达出即将别离的情感,表达出“我”不得不离去的情感色彩。徐译本“When all aboard I heard the boatman blare”,虽未将其翻译为船在等人,但也有船即将启程出发的含义,整体说来,徐译本和许译本对原文含义的理解更为准确。
例4:
执手相看泪眼
“相看泪眼”表达的是两人即将要分别,彼此在分别前夕四目相对,忍不住泪眼相迎,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Hands clasped together we see our tears,so overcome”中的“we see our tears”、徐忠杰先生的译本“Face to face,hand in hand,with tearful eyes—”中的“with tearful eyes” 都不如许渊冲先生的译本“Hand in hand we gaze at each other’s tearful eyes”中的“gaze at”更加形象,它强调的是彼此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凝视着对方不愿离去。许渊冲的译本更能表现两个有情之人分别时久久不愿离去,彼此深情注视着对方的情景,意境描写更好,也能使译文读者更好地体会其中的情绪表达。总之,三个文本的翻译各具特色,且总体看来都保留了原作的意象和情感。
例5:
竟无语凝噎
此句主要也是在描写两人分别时的忧伤。许渊冲的译本“burst into sobs with words congealed on our lips”,描述了即将分别的两人心中的话语到嘴边无论如何也无法说出来的悲伤,杨宪益的译本“unable to utter a single word”,主要是在描述俩人因为泪流满面而无法说出话的场景,徐忠杰的译本“Speechless,we were choked by our very sights”,描述的是由于两人即将分别,他们二人依依不舍以至于悲伤之情将两人的喉咙都给堵上了,无法说话,如此看来,徐忠杰的译本感情表达得较为丰富,因悲伤过度说不出话来,表达的意境要比前两个译本更为充沛些。
例6:
千里烟波
大家在读原作时,可以感受到“千里烟波”这一朦胧的画面感,好似乘船远行,路途遥远,看不到边。许译本“On miles and miles of misty waves where sail ships”,直接将“千里烟波”翻译为了“On miles and miles of misty waves”,直观描述出水面上的雾气弥漫千里之感,但是品读起来似乎少了原作那种似静而动的意境。由上文可知,杨译本“Ahead lies a journey a thousand li of misty waves”,将“念去去”和“千里烟波”合并翻译,暗示此去一程路途遥远,乘船千里。并且他们将“千里”翻译为“a thousand li”保留了原作的特色。许译本和杨译本都将“烟波”翻译为了“misty waves”,体现出原作的朦胧之感。徐译本“O’er the billows,a murky vapour lies”,将“千里烟波”翻译成了两个小短句“O’er the billows”和 “a murky vapour lies”,并且“O’er”是一个古体英语,用词典雅,但译本的重点似乎是“雾气”,“水波”起到衬托作用,在传达原文意境方面有所欠缺。
例7:
今宵酒醒何处
此句是词人自己设想,设想船靠岸之后,自己因酒醒身在哪里的景象,这三个英译本所表达之意皆能很好地表达原作的含义,解释原作所要传递出的意境。许译本“Where shall I be found at day break. From wine awake”,该译本的句子结构较为简单,也能够传到出原作的含义,但是“From wine awake”读起来略显生硬。杨译本“what is this place where I have sobered from my drunken stupor”中的“drunken stupor”传达了词人醉酒的状态,增强了意境的表达,能够感受到词人的迷茫和困惑,较好地传递出了原作的思想情感。徐译本“Where’d I be when I sober up,too soon”中的“too soon”使用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了词人对时间流逝的无奈。三个译本都能够传达词人的思想,但杨译本更贴近原词思想。
例8: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这句词,笔者理解为“我这一去,不知多年,和你分别后一切都显得不再重要,无须流连”。许译本“I’ll be gone for a year.In vain would good times and fine scenes appear”,用词简单易懂,“in vain”一词直截了当解释了“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之意,可理解为,这一别,对“我”来说再好的风景也失去了色彩,不过是一场徒劳,体现出了离别时的那种伤感之情,周围的一切似乎都随着伤情显得暗淡。杨译本“Our parting will last for years,fine hours and scenes of beauty have no appeal”,也能体现出原作的意境,因悲伤的离别,时光和美景都已失去了吸引力,译文可以让读者在品读诗歌时感受到作者的愁绪。徐译本“Once gone,for years lonely,I shall remain.Happy or festive as the day may be”,用“lonely”一词,直抒别离后的孤独之情,这一离去,无法和爱人相伴,将会是孤独伴词人左右,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这一情感表达丰富,感受出词人对离别的哀愁。这三个译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抒发了词人的哀伤,传达了原作的意境,都以不同的方式捕捉原词的“意美”。
四、结语
在对以上三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中,可以了解他们各自独特的翻译风格,不论是词汇选择,篇章形式还是对原作意境的传递,都有自己的巧妙之处,也能够较好地传递出原文所具有的诗歌情感色彩。
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在整体的结构和押韵方面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翻译风格,不论是音韵,形式还是意境的传递,其译本都展现出了很高的艺术特点。杨宪益夫妇的译本读起来更像是一首散文诗,倾向于归化的翻译策略,他们对原作的表达用词值得大家学习和参考。徐忠杰有其独特的翻译风格,尽管其诗歌的翻译可能与原作存在着些许差异,但这正是译者在翻译时融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总之,如果进行诗歌翻译时使用将音美、意美和形美三者完美结合,并作为诗歌翻译标准的“三美论”,可将诗歌的神韵更好地传达出来,完美地呈现出诗歌的整体美。同时,诗词歌赋的翻译需对其语言、词汇、文化背景等多方面进行考量,上述各位译者所展现的翻译风格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正是他们翻译风格的各异才体现了作品翻译中的多样性,这也有助于翻译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郭航乐.诗歌翻译中音、形、意三美的再现——基于《雨霖铃》两种英译本的评析[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3):398-399.
[2]李谧.许渊冲的诗译“三美”说[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
[3]许渊冲.宋词三百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4]杨宪益,戴乃迭.古诗苑汉英译丛·宋词[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5]祝一舒.试析许渊冲翻译思想的“中国之根”[J].外语教学,2020,41(03).
[6]曾祥宏.“三美对等”视角下的古诗翻译——以许渊冲的古诗英译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2,32(11).
[7]杨林浩.许渊冲诗歌翻译“三美”原则下的中国古典诗词英译对比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13.
[8]黄惠萍.“三美”理论视角下李清照词英译的对比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9]王凯.三美论原则下李清照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翻译对比研究[J].海外英语,2020,(17).
[10]黄天骥.说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J].书城, 2023,(02).
[11]刘丽娜,姜晓燕.《雨霖铃》两个英译版本之对比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S1).
[12]欧荣.同为赠别诗,情境各不同——约翰·多恩的《别离辞:莫伤悲》和柳永的《雨霖铃》的对比[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01).
[13]叶婧晶.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看《雨霖铃》两个英译本文化意象翻译[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27(09).
[14]张静幽,张欢,王梦薇.文化传播视角下的宋词英译研究——以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的译本为例[J].海外英语,2020,(05).
[15]甘慧慧.从译者主体性看文学翻译中的移情——朱纯深译《雨霖铃》分析[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3,29(02).
[16]詹小毅.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及其在宋词英译中的应用[D].四川师范大学,2015.
[17]王晓倩,刘亚楼.前景化视角下《雨霖铃》英译本对比研究[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