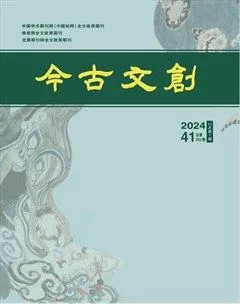神池道情戏的在地性探究
2024-11-21丁嘉玲

【摘要】近些年来,文化自信、文化保护一直是关注热点,在民俗学界也掀起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热潮,神池的道情戏作为神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并且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神池的道情戏,填补了以往在晋西北道情戏这条戏曲脉络中神池道情戏的空白,但综观这些已有的、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多是立足于神池道情戏作为民间艺术角度的探讨。本文以神池道情戏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调查和文献查询两种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在地性理论”对神池道情戏作为文化事象的文化价值进行深度分析和探讨,从神池孕育道情戏、道情戏反映神池地域文化以及文化价值意义三个方面整合分析得出神池道情戏与地方文化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神池道情戏;在地性理论;地方文化;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97-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26
道情,就全国范围内分布极广,有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山西、陕西、甘肃7个省以及内蒙古、宁夏2个自治区,在这7个省份和2个自治区中又结合各自的地域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道情剧种,但是其中道情戏分布最广的地方还属黄河流域的北部区域,而在山西的道情戏就分为晋北道情戏、洪洞道情戏、临县道情戏和永济道情戏。神池道情戏属于晋北道情的分支。本文将以“在地性”理论作为分析神池道情戏的一个支撑点,探索神池县所孕育的道情戏与神池地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传承的价值意义。
“在地性”是应对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而提出的一个对立概念,后来又发展融合形成了“全球在地化”的概念,即指任何环境下的全球因素和地方因素复杂的交互作用。[1]初次在中国提到这个概念的是台湾学者杨弘任,之后“在地性”的说法多在建筑领域和公共艺术方面出现,在民俗学科方面应用极少;目前已知的对于“在地性理论”的民俗探讨方面多为其分支“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渗透。事实上,“在地性理论”及其相关内容是从社会学及人类学中借鉴过来的,自从民俗学科发展以来,囿于研究方法的困境,一直在寻找突破口,而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方法的借鉴恰好为研究民俗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神池孕育了道情戏
“在地性”强调“边界感”,即一个地区的人群有一个地区的认同感,例如一个生长和生活在神池的人会说“我是一个神池人”,而不是说“我是一个静乐人”,反之也一样;生活于特定区域的人会对这片土地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他的认知、习惯、行为都受此影响;即使超出这个边界到另一片土地去生存,也带有原生土地浓厚的意识。因此,生活在神池这片土地上的人用他们的勤劳与汗水创造出了独有的神池文化。
历史上,“神池”这个奇特的名字,肇始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因县城西北“有水一泓,出无源,去无迹,旱不涸,雨不盈,鱼藻胥不生,湛然清澈,若有神焉”而得名。[2]它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处于一个极其偏僻的地理位置,但同时也因山西这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历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它是胡汉的交融之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融,由此孕育出了多元的文化基因。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却诞生了丰富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同时也为道情戏的发展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直至今天依旧生生不息。
(一)神池道情戏与地理文化
神池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东依长城俯朔州,南屏管涔望宁武,西连平川毗五寨,北踞洪涛接偏关。地势东高西低,群山绵亘,沟壑纵横,为黄土高原山地丘陵典型地貌。洪涛山宛若游龙,贯穿东北;管涔山犹如屏障,雄峙西南;朱家山连绵起伏,横亘中部。县川、朱家川夹于其间,故县境有“三山夹两川”之称。道情传入神池,大约始于金代,由于当时道教传播人丘处机在途经山西时,受气候的影响,长时间逗留在此地,故此地的道情传播范围极大且留下众多传承。神池道情戏相传最早活动于三山村,其班社成立时间最早,道情艺人也最多。许多知名的老艺人皆出于此,例如:宫钰、柴田成等人。自此道情戏就在神池扎下了根,清道光、咸丰年间,全县已有道情班社20多个;民国时达到顶峰,民国21年(1932年),县内班社已多达114个[2]。也正是民间众多自组班社的出现,使得当地形成相互竞争的局面,使得神池道情戏演出专业化程度和表演技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3]。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组建了神池道情剧团,培养专业人员,人才辈出,获得了不少剧目奖章。
据现有记载,神池出现过的道情班社有:三山班、大磨沟班、东土棚板、大严备班、杨家坡班、虎鼻道情班、攒班道情、杨侉子班、项桂山班、昌盛班等。
上述出现过的班社都是神池县出现的延续时间长且较有影响力的班社,其中昌盛班的班主王占帮是1954年神池县道情剧团的基底,神池道情剧团在此基础上聘请专业人士成立,才有后续神池道情戏的辉煌发展。
神池地处晋西北大风口,高寒风大,气候恶劣。历来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民谚,史上甚至有超过百天的记载。县境海拔平均1509米,为华北海拔最高之县,更有“六月冻雀蛋,七月陨霜杀嫁”的记载。[4] 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农民的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限制,再加上干旱、霜冻、冰雹、暴雪等气候灾害,使得农业生产时间受限,为了缓解闲暇时光以及人民内心的悲苦,各村镇便搭台唱戏,年复一年,自娱自乐,从而形成了神池人爱听戏曲的喜好。
神池古有“边关要冲”“宁偏肩臂”“列塞严疆”的名称,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拉锯征战之地,胡汉交融,铸就了自身独特的民俗和生活秉性。光绪《神池县志》载“士无奔竞之习,民鲜强悍之风”,是对神池人性情的概况。神池道情戏受到了它的巨大影响,受文化交融的影响,神池人粗犷、豪爽,表现在戏剧中就是敢于反抗,绝不屈服,如生活戏《哑女告状》,掌上珠帮助未婚夫读书夺取功名,却不料被继母陷害欲烧死她,不成又设计毒哑她,想告状却有口难辩,反被继母之女赛珠诬陷,最后在管家掌忠和丫鬟的帮助下成功洗脱罪名,戏中唱道:
“掌中双珠姐妹花,她面如观音心如虎!姐妹花成了冤家。”
掌上珠和赛珠本是亲人,却为了荣华富贵而结成仇家,但是掌上珠即使口不能言,也要为自己洗清冤屈,不向卑劣无耻的继母和赛珠妥协,从而表达生活中人民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
(二)神池道情戏与戏曲文化
综观整个山西,戏曲文化在其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地下的文物,还是地上的戏台、碑文、壁刻均有戏曲的身影。山西剧种丰富,四大梆子——中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以及道情戏、赛戏、耍孩儿、二人台等等,不同的地区流行着各自独具特色的地方小戏。神池县的剧种有晋剧、北路梆子、二人台、耍孩儿、大秧歌几个剧种,道情戏就是在境内小戏流行的情况下,结合其特点并与境内民间歌谣相结合逐步演变,日臻完善。神池道情戏能发展到今天与庙会社火有着密切的关系,据《神池县志》记载:境内古会繁多,仅县城庙会就四季不断。农历二月二绅土献戏3天,四月十八娘娘庙献戏,五月初一城隍庙、龙王庙各献女戏3天,五月初五关帝庙唱大戏,六月初八龙泉寺古会,六月二十四青泉寺古会等等,而今龙泉镇窑子上村六月六庙会依旧经久不衰,每逢此日必定民众云集,颇为热闹。神池目前现存的古戏台已不多,包括磁窑沟戏台、银洞窳龙王庙戏台、银洞窳老爷庙戏台、石湖戏台、小井沟戏台五处戏台。神池道情戏已然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海德格尔曾说:“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了一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的和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5]对神池道情戏,亦是如此,神池的地理、宗教、戏曲文化孕育了神池道情戏,多层次的文化因素铸就了如今神池道情戏独特的民间文化。
二、神池道情戏反映神池地域文化
提及“在地性”,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是“地方知识”,它包括认知化的常识和身体化的技术,其中认知化的常识是指潜藏在人心中的行事准则等经验原则[6]。就这一解释来说,神池道情戏的剧本内容中除了已有的固定情节,也加入了神池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生活经验和智慧,并且在语言方面也体现了不同于本地区的语音、俗语、谚语等特征。
道情戏作为神池剧种,必然要从神池的土壤里汲取营养发展自己,因此道情戏与神池文化有着浓厚的血脉联系。
(一)剧本特色
神池是道情戏目前现存最多剧目和曲牌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神池道情剧目的收集开始于1954年神池道情剧团的成立,到1956年山西省文化局派遣武艺民来此正式收集、整理道情剧目,迄今为止,神池道情戏可以说才正式进入广大人民的视野,让相关文化者注意到神池道情戏的重要性。目前大约有170多本传统道情剧目,后又增加了移植的戏曲和新编剧目,下表是依据剧目种类进行的划分。
此外,论戏曲的剧本创作,它的创作灵感归根结底一定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即使是其中的神仙道化戏也是来源于民众口耳相传,代代传承的生活与虚幻的结合。上面表格所罗列的三类剧目中,传统剧目和移植剧目中的生活戏曲以及新编剧目都处处充满了神池人民日常生活的色彩。
神池道情戏目前记载的生活戏多达90多部,但常出现在神池戏剧舞台上的也只有其中的数十种,它是根据民众的喜好和接受程度成为百姓耳熟能详的戏曲。
《牧羊圈》(也称《牧羊卷》),故事的内容是唐朝西凉节度使黄龙叛变,朱春登替叔父参军,与婶母宋氏的外甥宋成同行。在路上,宋成试图将朱春登的妻子赵锦棠据为己有,所以宋成回到家中,谎称朱春登已经战死,强迫赵锦棠与宋成结婚,赵锦棠不肯,宋成便把赵锦棠和朱春登的母亲赶到深山放牧,欲将朱春登的妻子和母亲冻死。不久,朱春登立下大功,封侯回来,向宋氏询问母亲和夫人的消息,宋氏谎称已经死亡。朱春登伤心欲绝,到墓前拜了七日,正好赵锦棠和朱春登的母亲来讨食,朱春登认出了赵锦棠手中的“朱痕”印记,夫妇二人终于重逢。该剧传达了民间传统的家庭美德,反映了人们希望家庭和睦、和谐共处的愿望。
《九件衣》说的是唐贞观年间,钱雨林要随朋友赴京参加科举,向舅父借钱,却又不好开口,恰好遇上了舅父的女儿姜巧云,她将九套嫁衣送给了钱雨林,钱雨林想要将其换成一笔钱,却不幸遇上了乔举人之女乔翠花的九套嫁衣失窃;在钱雨林典当时,被张虎拿了回来,在公堂上对质,乔举人在质问钱雨林的九件衣服时,一口咬定是他偷了自己女儿的九件嫁衣。杨知县严刑逼供,钱雨林无辜受辱,屈死刑房。姜巧云闻此消息,不顾脸面闯上公堂,与乔翠花当面对质,真相大白,总算还了钱雨林一个清白,此时望着包裹姜巧云百感交集悲伤难禁,在公堂上殉情自尽。杨知县这时才醒悟过来,虽然重罚了凶手,宣布了自己的疏忽,却也没脸去见姜九卿和钱家两位孤苦伶仃的夫妻,于是把一对儿女送到钱家以赎罪,才得以宽恕。
除上述移植剧目中的生活戏,还有现代以来新创编的剧目,有《夸月饼》《情系道情》《神池颂》等等,这些都是神池道情剧团自成立以后由其亲身经历而创作的。其中由刘文堂、张鹏所编创的《情系道情》曾获忻州市地方戏新人新作大赛二等奖。《夸月饼》在2006年编曲、编剧完成,它是以神池非常流行的特色小吃“月饼”为创作灵感的戏曲,月饼可以说是神池人拿得出手的一张靓丽名片,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神池的热爱。《情系道情》从名字中就可以窥探其意,人民的情感在道情戏中被反映,它是民众情感宣泄的工具,是民众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二)语言特点
神池道情戏的语言特色表现在使用了大量当地的民俗谚语。如“圪洞”“圪梁”“忽歇”“忽扇”“日嘴哇脸”“讨吃棍”等,在《九件衣》第一场里有一段唱词:
“我小子乔三,每日起来东庄玩钱,输下人家些赌博烂账,无钱交还。不免去到三叔家中借些银两,好打这些赌博烂账定是这般主意。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三叔门上。(狗咬)三叔毕竟是有钱人家。穷人家那狗子咬得是“糠棒子!糠棒子!”三叔这狗也咬得是“面瓮!面瓮!”观见门子半掩半开,待我各自进去。三叔三婶子!啊三叔三婶都然不在家下,上房门子半闭半开,待我各自进去。呀!上有皮箱一个,下有焦砖一块,待我手拿焦砖将皮箱砸坏,哑喳!原是满箱衣服,包袱一个,待我拿上,这才是:家贼难防狗不咬,圪夹上包袱当铺里跑。
我是明人不做暗事,三叔家中有了贼了!
……
什么无有,伙计们,打!你们年轻哩,毛嫩哩,坐不得马尾板凳哩,脚发在你圪洞里,爬起来发愣哩,二十四五交运哩,三十二三背兴哩,吃上青草便粪哩,绿圪茵茵行姓哩,有老哥在此你们算甚哩!将这顽童打死,你担,我担?王人小人鳖担?你不担,还是我担呀!”
这其中出现的“糠棒子”“圪夹”“毛嫩”“圪洞”“绿圪茵茵”是民间百姓说话时常用的俗语,不仅在语言上具有地方特色,而且能够让听众和唱戏的人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关于道情戏语言的特色,还涉及歇后语的使用,如“黑豆泡粉子——黑汤拉水的赖种子”“清水池里扬顽石哩——一眼见底啦”“戴上凉帽烧窑哩——红到顶啦”“老鼠钻进面缸了——动不动就翻起你那白眼了”“鸟头钉盒子哩——尽嘴”“四两的鸭子半斤嘴——圪崩圪崩嘴巴硬”[7]。这些俗语、谚语的使用,使得戏曲具有通俗性、乡土性和地域性。正如郭克俭所说:“各地戏曲对本土居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地观众对本地区的方言、歇后语有天然的亲切之感。”[8]一个地方的戏曲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它的身上有着当地民众的影子。
“地方知识”概念的出现,完美地诠释了为什么同一种文化或物品会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同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态地理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认知体系,由此发展出一套异于他乡的逻辑知识体系,从而造就了各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全国都有道情戏,而神池的道情戏却呈现了与众不同的特点,就在于神池人民所创造的神池文化的特殊性。
三、神池道情戏的文化价值意义
(一)神池道情戏于神池的文化价值
神池道情戏是流传于神池县的一种民间戏曲形式,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渊源,它扎根于民间,与广大神池人民的生活娱乐息息相关,是根植于人民心中一种重要的娱乐形式。神池本身就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是胡汉交融的地方,民风淳朴,兼具着粗犷、豪爽、热情却又含蓄内敛的性格特点;而这样的性格特点又通过神池道情戏体现得淋漓尽致。神池道情戏中的神仙道化戏揭示了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对于宗教的信仰和热忱,它是人民苦难生活的精神支柱。追寻神池道情戏的起源就是在回顾神池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回顾人民的日常生活;戏曲中的桥段、语音都是在记录神池人民祖祖辈辈的发展。神池道情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弘扬和传承神池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神池道情戏于道情的文化价值
道情戏作为戏曲的一个类别,形成于清代以后,是曲艺道情或皮影道情受当地戏曲影响后,以代言体方言搬上舞台的剧种统称。[9]神池道情戏作为整个黄河流域的道情剧种之一,也是临近地区道情戏的一个发端,从三山村的道情传承人走街串巷,游走于各个县表演,从而使神池道情戏扩散到其他领域,为道情戏的繁衍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神池道情戏的戏剧种类是保存最多的,唱腔种类繁复,包括单曲式、联曲式、集曲式三种,唱腔的调式除了有单一调式,还有综合调式和调式交替的方式,这为研究全国道情戏提供了新的材料和例证。
总之,神池道情戏的存在不仅是人民的精神娱乐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此地的民风民俗与地域文化;同时,它也对研究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四、结语
神池道情戏作为地方戏曲的一个代表,除了具备整个黄河流域道情戏的共同之处外,它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它从道情歌曲、说唱道情发展到戏曲道情再结合地方民歌和各式戏曲的长处,才发展成为今天的神池道情。从“在地性理论”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虽然目前关于在地性理论尚未有较为完整的论述,但也不失为一个新出发点,同时也通过“在地性理论”分析明确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间艺术诞生于特定的文化空间以及在这方空间内民间艺术所呈现出来的独特之处,并且在此基础上作者也在思考戏曲艺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民间小戏的交流实践[10],从而更好地推动戏曲艺术的保护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杨淑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1.
[2]神池县志编撰委员会编.神池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王萍.略论明清时期西北民间小戏的传承、传播与“在地化”[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37(03):2-9.
[4]何茜.晋北道情戏及其文化生态环境研究[D].中国艺术研究院,2007.
[5]武艺民.中国道情艺术概论[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6]杨弘任.何谓在地性从地方知识与在地范畴出发[J]. 思与言,2011,(04).
[7]张建芳.神池道情调查与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 2015.
[8]张璐.地方戏曲传承中的本土语言研究[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8,(02).
[9]杨志敏.道情戏与黄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10]周全明.从文本到实践:民间小戏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演进路径[J].民俗研究,2022,(01):119-130+159.
作者简介:
丁嘉玲,女,山西忻州人,南宁师范大学2022级民俗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方习俗与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