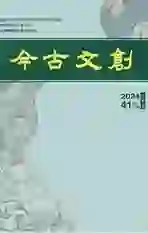中韩古典园林植物景观意匠比较研究
2024-11-21任勤红
【摘要】在中韩古典园林中,植物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本文以中韩两国著名的私家名园拙政园和潇洒园为中心,根据《拙政园三十一咏》和《潇洒园四十八咏》等原始材料,研究两国古典园林植物景观的营造,从植物的选择、配置方式以及植物景观审美意境与文化内涵式等方面探讨中韩两国古典园林植物景观营造的异同。
【关键词】植物景观;拙政园;潇洒园;中韩古典园林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41-008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41.023
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广泛影响了日本、朝鲜半岛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内核类似又各有特点的汉儒文化圈。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韩国古典园林的造园理念、建筑布局、堆山置石、植物造景等都受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极大影响。根据韩国学者裴常善的研究,韩国文献中出现的植物共98种,其中三国时代14种,高丽时代39种,其余为朝鲜时代出现的树种,这些植物中51%为中国原产的植物。韩国的造景植物也常常被赋予“节气”“君子”“子孙昌盛”等象征意义。据韩国花卉古籍《养花小录》记载,韩国著名的花木大部分是高丽时代忠肃王到访中国时元朝皇帝所赠,书中花木的介绍大多引用中国文人的诗文或字句。韩国古典园林在植物的选择和应用上与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和中国古典园林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但由于其民族所生存的物质空间的不同,两国植物景观也呈现出一定差异。
学术界从种植手法[1][2]、植物的文化和意义[3]、古籍文献中的植物构成[4][5]以及植物与其他园林要素所组成的园林空间之间的关系[6]等方面对中国和韩国古典园林植物造景进行了研究,但在两国间,古典园林植物造景文化的异同上还缺乏系统和深入地比较,对两国古典园林植物文化之间的渊源及演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下文将通过对比两国不同园林对此进行进一步说明。
一、拙政园与潇洒园的建造背景
始建于明代的拙政园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是江南园林的代表。拙政园一带曾是三国时代郁林太守陆绩、东晋高士戴颙、初唐诗人陆龟蒙故宅。明正德五年(1511),御史王献臣因连遭贬谪,归乡隐居苏州,筑园以识,取西晋潘岳闲居赋中“拙者之为政”命名为“拙政园”。
16世纪,朝鲜党争混乱,进步势力士林派与保守势力熏旧派对立,许多士人受到迫害,纷纷退隐山林。潇洒园园主梁山甫(1503—1557),15岁跟从父亲进京(首尔),师从当时士林派领袖赵光祖(1482—1520)。在目睹恩师遭遇己卯士祸之后,梁山甫毅然回乡,于1525年左右开始建造潇洒亭,约历时十年建成潇洒园。梁山甫年少时便陶醉于支石溪谷的胜景,早有卜筑之志,他欣赏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又钦慕周敦颐的道学造诣,因此在目睹恩师的遭遇后,为保持节操毅然摈弃功名利禄而归隐山林。
拙政园与潇洒园建成时代相同,同属士人园林,不仅有游观乐趣的实际作用,还寄托着文人所追求的精神上的意义。
二、《拙政园三十一咏》与《潇洒园四十八咏》
文征明除了为拙政园作园记外,还多次为拙政园绘图,留存至今的是嘉靖十二年所绘的三十一景及对景所作的诗句,即《拙政园三十一咏》。绘画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并不能完全反映拙政园当时的园林面貌,但是其《园记》与诗中的描述和诗文却能一一相对。与潇洒园有关的文献古籍有造园初期金麟厚创作的《潇洒园四十八咏》、1755年刻制的《潇洒园图》、1731年编撰的梁山甫文集《潇洒园事实》以及高敬命(1533-1592)1547年4月造访潇洒园时所写的游记《游瑞石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潇洒园四十八咏》与《潇洒园图》。
本文根据《拙政园三十一咏》和《潇洒园四十八咏》研究拙政园和潇洒园建造初期的植物景观,揭示中华传统文化在韩国园林中的影响,加深两国对彼此园林文化异同的理解 ; 在实地调查拙政园与潇洒园现状植物的基础上,从中韩两国自然地理、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结构等层面,探索两园植物景观变迁的内在原因,为进一步研究和创作体现本土文化特征和精神气质园林艺术景观提供精神力量。
三、《拙政园三十一咏》与《潇洒园四十八咏》中的
造景植物
《拙政园三十一咏》与《潇洒园四十八咏》中以植物为主题的诗咏如下:拙政园有繁香坞、芙蓉隈、柳隩、水华池、待霜亭、怡颜处、听松风处、来禽囿、玫瑰柴、珍李坂、得真亭、蔷薇径、桃花沜、湘筠坞、槐幄、槐雨亭、芭蕉槛、竹涧、瑶圃、嘉实亭20咏,占比64.5%,植物是园林中的主角;四十八咏中以植物为主题的诗咏有千竿风响、松石天成、遍石苍藓、倚睡槐石、断桥双松、散崖松菊、石趺孤梅、夹路修篁、迸石竹根、激湍菖蒲、斜檐四季、桃坞春晓、桐台夏阴、隔涧芙蕖、散池莼芽、衬涧紫薇、滴雨芭蕉、映壑丹枫、带雪红栀等19咏,占比39.6%,潇洒园还将水体(危岩展流、刳木通流、槽潭放浴)、石头(负山鳌岩、榻岩静坐、玉湫横琴、床岩对棋)、构筑物(舂云水碓、阳坛冬午)、动物(绝崖巢禽、丛筠暮鸟、壑渚眠鸭)等作为描写对象。两诗咏中共同出现了松、竹、槐、梅、桃、柳等植物,其中竹出现的次数最多,《拙政园三十一咏》中共7次(13.5%),《潇洒园四十八咏》中共15次(32.6%);其次是梅,三十一咏中共4次(8.7%),四十八咏中共4次(8.7%)。
《拙政园三十一咏》中林檎(来禽囿)、李(珍李阪)、桃(桃花沜)、梅(瑶圃、嘉实亭)等经济作物构成了园林的突出面貌。
四十八咏与潇洒园木版图中出现的木本植物有十三种,其中原产自中国的有梅、杏、梧桐、柳、桃、紫薇、栀、四季(月季),韩国乡土植物有侧柏、竹,赤松、韩国槐、丹枫;草本植物五种,原产中国的有菊、芙蕖、芭蕉,韩国乡土植物有菖蒲、莼。
四、拙政园与潇洒园的植物配置
(一)植物配置的方式
1.孤植欣赏
植物的选择和配置是园林中最基本的环节。植物的干、枝、叶、花、果实等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拙政园三十一咏》中将植物单株的形态作为欣赏对象的有怡颜处和“槐幄”,槐幄所欣赏的就是“古槐一株,蟠屈如翠蛟,阴覆数弓”。《潇洒园四十八咏》中不存在孤植。
2.丛植欣赏
丛植是一株以上至十余株的树木,组合成一个整体结构。《拙政园三十一咏》的“繁香坞”景点中“杂植牡丹、芍药、丹桂、海棠、紫璚诸花”都是欣赏春季繁花似锦的景象;第二十一咏“得真亭”植四桧结亭,是以桧树为结枝形成一个类似亭的围合空间,这一做法能形成特别的空间感,有着自然的幽趣。《潇洒园四十八咏》中也不存在丛植的配置方式。
3.群植欣赏
群植的数量较多,主要表现植物的群体美。《拙政园三十一咏》中众多果树以群植的形式种植,如“瑶圃”是“中植江梅百本,花时灿烂若瑶华”;“待霜亭”旁种植柑橘数株,待到霜降之后可欣赏到“嘉树玉离离,黄金子满枝”。除了对植物本身的欣赏,植物还被设置来形成空间的划分和营造。在水边种植以修竹,形成一个“背负修竹,下瞰平池”的围合空间。“湘筠坞”通过修竹连亘围绕平冈,营造清幽回合之境。除了单一树种的群植,其他树木也有群植,如对“槐雨亭”所述是“榆槐竹柏,所植非一”。《潇洒园四十八咏》中“石迳攀危”为沿着一条登山的小路种植了松、竹、梅岁寒三友。“千竿风响”是在潇洒园的内外种植了大片竹林,在风力的作用下营造出连绵不绝的竹林声景观(无情风与竹,日夕奏笙篁)。
综上,植物在拙政园中用过“游观”的效果得到营造,而在潇洒园中主要以“静观”的作用来营造。
(二)植物与其他要素的配置
《拙政园三十一咏》与《潇洒园四十八咏》中大部分的植物是与其他要素如建筑、水体、山石等一起配置。
1.植物与山石
《拙政园三十一咏》中“倚玉轩”旁的竹丛与昆山石搭配,昆山石与其后的万竿修竹交相呼应,在春风的摇曳中形成“琳琅满目”的美妙景致。尔耳轩旁边叠石为山,上列灌莽,下引寒泉,这里的“拳石”,与植物(植菖蒲、水冬青)、水景组合成为一组盆景类的小景在当时苏州人喜爱的欣赏方式。作者“未能免俗,聊复尔耳”,以达到“载欣载遨,以永逍遥”的无为境界。《潇洒园四十八咏》中“假山草树”的假山是流水的冲刷造成的积土,并未对假山的形态进行塑造,通过在土山上种植植物来与山林丘壑的景致相协调,体现了人工与自然的结合。“松石天成”“迸石竹根”“遍石苍藓”“倚睡槐石”以及“石趺孤梅”等诗咏都描写了植物与石头的配置。
2.水体植物配置
拙政园水面应用最多的是荷花,成片种植时,达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水岸边植物有柳树,木芙蓉,还有桃花,“时见流残片,常疑有隐家”,通过水中的桃花花瓣,使人联想到《桃花源记》中的隐居者。潇洒园在静态的方池中种植了荷花和莼菜,在动态的溪流中种植了菖蒲。“隔涧芙蕖”取自周敦颐的《爱莲说》,在光风阁中欣赏溪流对岸池塘中荷花的清净仙姿,营造“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欣赏模式。“杏阴曲流”则为在溪流旁种植了杏树,在杏阴下揣测孔子的“川上意”(当年川上意,今日杏边求)。
3.植物与建筑物
建筑物旁的植物配置在体量和色彩等方面都要相协调统一,《拙政园三十一咏》中建筑有若墅堂、梦隐楼、倚玉轩、小沧浪亭、深净亭、待霜亭等,以亭为主,建筑色彩淡雅,且园林面积不大,选择竹、荷花、桧、槐树、梅树等能体现诗情画意和文化内涵的植物,进行精巧布置或画龙点睛式的点缀。岭南园林用炮仗花等藤本植物爬满建筑屋顶,开花时繁花似锦,丰富了建筑的色彩。《潇洒园四十八咏》中建筑有小亭(潇洒亭),文房(光风阁),“斜檐四季”是在潇洒亭旁边种植了月季、梅与竹构成一个三季有花、四季有景的植物景观。
4.植物与构筑物
《拙政园三十一咏》中“芭蕉槛”是芭蕉和栏杆的组合,《潇洒园四十八咏》中“透竹危桥”表现的是竹林中的危桥,以竹景取胜,有清邃、出尘的境界。
(三)植物景观审美意境与文化内涵
1.精神载体
《潇洒园四十八咏》中“松石天成”描绘了溪旁老松根深扎岩石的景观,其挺拔而苍劲的身姿不畏惧环境的恶劣,表达了始终如一的坚贞精神。“断桥双松”取材于我国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散文《蓝田县丞厅壁记》,效仿崔斯立对植两棵松树,水声汩汩沿庭阶而鸣,“㶁㶁循除水,桥边树二松。蓝田犹有事,争及此从容”,表明作者远离官场的豁达胸襟。竹是题咏诗中出现最多的植物,“桐台夏阴”将梧桐与舜帝的南风联系在一起,借此比喻期待明君的出现,以实现治世理想和完美政治。
2.退隐归意
《拙政园三十一咏》中“听松风处”通过松林静坐的意象表现造园者跟随陶弘景的隐逸之志。《潇洒园四十八咏》中“桃坞春晓”是依据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艺术境界而构建的园景。桃花盛开之际,晓雾低迷时,“如涉武陵溪”。“柳汀迎客”取自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意指具有情致高雅的隐士的居住环境。“倚睡槐石”中“睡来惊起立,恐被蚁王知”取自中国唐代典故《南柯太守传》,体现了作者对于追求富贵荣华不过是作茧自缚的人生感悟。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潇洒园中并没有槐树,东北角有一株榉树,在韩国槐亦指榉树,是用榉树表达槐的寓意。
3.比照人格
人们常常借园林花木的自然属性比喻人的社会属性,倾注花木以深沉的感情。《拙政园三十一咏》的“嘉实亭”中,用江梅花表现造园者的清白。《潇洒园四十八咏》中“迸石竹根”的“贞心老更苦”,“激湍菖蒲”的“一色贯炎凉”,“遍石苍藓”的“一般丘壑性,绝义向繁华”都是通过植物来表达自己的人格理想。菖蒲无视激湍的精神正是作者直面困难的精神写照,表达了作者对待人生的盛与衰都能泰然处之的心态。莲花天生丽质,被喻为花中君子,正是园主寄情花草,清高脱俗,追求人生的另一种超凡境界。《潇洒园四十八咏》中“隔涧芙蕖”取自周敦颐《爱莲说》之“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净植非凡卉,闲姿可远观。香风横度壑,入室胜芝兰”,赞美莲花的清香、洁净、亭立、脱俗。
4.四季之序
潇洒园中利用植物营造四季景观,造园者通过四季景观和花草枯荣体察自然之变化。“斜檐四季”描绘了潇洒亭的植物景观,“定自花中圣,清和备四时”,月季如圣者一般镇定自若,具有清和备四时的品性,正是作者追求的人生境界,月季与梅、竹构成和谐之景。“衬涧紫薇”描写溪水两旁对植的紫薇,紫薇花期逾白日,作者借紫薇表达与世无争的山中日月长的豁达心境。“平园铺雪”一起完成了季节上的转换。雪中栀子的红果交青叶,正是作者面对任何权势和压迫决不低头的高尚品德的具体体现。
五、结语
从古至今,园林的发展其实都离不开植物配植。近年来,我国园林设计和应用越来越多偏向于硬质景观设计和布置,虽然富丽堂皇,却无法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中韩古典园林同属于东方园林,拙政园的植物景观营造体现了一定的经济性和象征性,也追求游观效果。潇洒园的植物景观营造注重静观效果,造园者对植物景观意义的追求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当今,中国园林种植设计的民族特色正在逐渐消失,如何挖掘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特性,传承和发展我国传统园林种植设计审美观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问题。重视设计的立意,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挖掘传统诗歌的意义,是园林建设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1]刘丛禹.中国古典园林植物造景手法初探——以南京瞻园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9,(8):111-112.
[2]宋正花.韩国传统庭院的植物配置类型研究[J].J.Korean Soc.People Plants Environ,2012,15(4):287-299.
[3]裴常善.造景植物的象征性的相关基础研究[J].韩国传统造景学会志,1989,8(1):281-313.
[4]朴熙圣.《养花小录》与《长物志》中花木反映的文人园林趣味比较[J].韩国造景学会志,2016,44(3):79-93.
[5]邬秀杰.论王世懋《学圃杂疏》中的植物造景艺术[J].建筑与文化,2019,(6):157-158.
[6]胡露瑶,郑文俊.《园冶》植景设计理法探析[J].中国园林,2018,(12):122-125.
作者简介:
任勤红,女,汉族,贵州毕节人,博士研究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韩古典园林文化研究、艺术设计教学工作。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韩古典园林植物景观意匠比较研究——以拙政园和潇洒园为中心”(项目编号:2020SJA0676);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中韩古典园林造园思想对空间营造模式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20SKYJ05)共同资助。